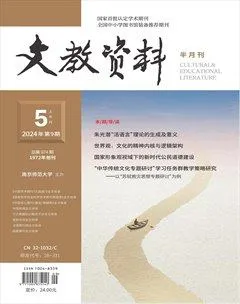朱光潜“活语言”理论的生成及意义
2024-10-23陶宇佳
摘 要:朱光潜作为中西文论的融会贯通者,其文学理论既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滋养,也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他提出的“活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在中国古代“活法”传统影响下,诗歌创作追求自然、体物缘情;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语言”则与“表现”紧密联系,作家的情感通过语言得以抒发。朱光潜的“活语言”理论在二者基础上,着重探讨“语言”与“文字”、“语言”及“表现”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入挖掘由语言之“活”带来的诗歌之“活”。
关键词:朱光潜;“活语言”;语言与文字;表现
语言是文学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作家的情感经由语言抒发,读者也由语言这一媒介领略作品内涵。但在朱光潜眼里,文学创作的“语言”与“文字”之间有着极大差异。他提出“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要尽美尽善,才能引起美感”[1],并且相较于散落在书本中的“死文字”,说出来的“活语言”拥有无限活力,是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也是评判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故而他提倡在诗歌创作中要注重遣词造句,以语言之活创造诗歌之活。
一、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活语言”
早在朱光潜之前,就有部分文学理论家关注并探讨了“活语言”这一概念。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主要集中于诗歌创造方法的引导;西方理论语境中则是从语言理论出发。虽然二者涉及方面有所不同,但这些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促使朱光潜提出了“活语言”的观点并进行了实践。
(一)古代语境中的“活语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活”这一理论的提出可追溯至宋代。佛教经典《五灯会元》中曾谈到“死句”“活句”,缘密禅师认为意在言内为死句,意在言外方是活句,人们应追求活句。[2]朱光潜也多次提及诗歌创作应达到“言不尽意”的境界,在他看来,以言达意只能得其近似,故其谈及文学创作要俭省,文学之美更在于“欲辩已忘言”的含蓄,只是这种“含蓄”亦需要注意“弹性”,若即若离、余味无穷。
宋人吕本中最早将“活法”一词应用于诗歌创作,他认为“学诗当识活法”[3],作诗既要在乎法内又要出乎法外,守规矩又游移于规矩之外。这一理论对宋早期诗歌写作易陷入固定模式的状态进行反驳,亦挑战宋诗中“夺胎换骨”“点石成金”等固化创作思维。而后陆游谈及作诗,也提出师从曾几“文章切忌参死句”[4]。同时期诗人杨万里更是将“活”应用得淋漓尽致。葛天民在《寄杨诚斋》一诗中用“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鲅鲅”[5]来评价杨万里的诗,并提及“死蛇弄活”这一禅语,在吕本中的“活法”理论上有所发展。杨万里在《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中提及“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6],回答为何作诗。继而他用“别具一只眼”,对常见的大自然景物加以再造;用“摄影之快镜”对于世间一切事物“系风捕影”“踪矢蹑风”,追逐其“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不让活泼泼的大自然被前人固有之印象所限制,而是“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7]。不是诗人闭门造车寻找诗句,而是诗歌隐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主动为诗人献上诗材,虚静澄澈中万物复归于一体,诗人师法自然、感物缘情,诗意也随之自然而然流淌。
朱光潜曾批判宋诗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现象,认为宋诗缺乏唐诗的清新活泼和自然流露。但他大加称赞宋诗,尤其是哲理诗中的源头活水趣味,认为宋诗中亦有“言不尽意”的余味悠长与体物缘情的活泼自然。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对生命澄悟和留恋的趣味生生不息、绵绵不断,如同不腐的流水,更是诗歌中最为宝贵的“活法”。
(二)西学理论中的语言观念
朱光潜早期的表现理论受意大利文艺批评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影响颇深,他同克罗齐一样认同语言在文学“表现”中的重要作用,也极为强调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
朱光潜与克罗齐皆批判流行表现说中内容与形式分离的看法,谈及创造与表现应为直觉,情趣与意象交融中作品随之完成。并且,二人反对流行表现说中“心中先有情感再通过纸笔记录反映到文学作品”的创造行为,克罗齐认为“表现(即创造)全在心里成就”[8],记录或传达则是物理事实,与艺术无关。在他看来,传达并非绝对重要,重要的是直觉,所有感情都在直觉一瞬间内表现,美也在那一瞬间传达。朱光潜同样谈及“诗人心中直觉到一个情趣饱和的意象,情趣便已表现于意象”[9],他认为情趣是被表现者,而意象是表现者。诗歌为表现情感而存在,诗的语言更是情趣饱和的语言。而语言与思想,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一致的,这与克罗齐观点相契合。二人都认为语言与艺术同为表现,语言与表现一同产生,表现依赖于语言的传达。
至于语言的认识与研究,西方自古有之,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多次梳理“语言”在美学体系中的发展。克罗齐汲取前人经验,将前人形象思维学说发展为“直觉即表现说”,重构美学体系。克罗齐侧重语言在传达过程中的作用,不过他心中的语言仿佛是“一次性”的。他认为讲述语言是创造新词的过程,即使人们讲述原有的词语与句子,也会改变或增加旧字的意义。[10]并且,随着客观情境与主观思想情感的变化,语言不断刷新人们认知,重新赋予语词意义与生命。因此,克罗齐提出,在“美”的展现过程中,表现与传达是分开的,传达并不重要,仅是物理事实的记录,语言则在传达和转述中逐渐丧失其原本意义。如此,语言的活跃带来表现意义的流动,过度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也导致表现的不稳定性,克罗齐淡化“语言”在表现过程中的作用,将语言划归于仅限传达的工具。
然而,相较克罗齐将语言与传达一起置于物理层面,朱光潜却对克罗齐的观点有所反叛。他谈及克罗齐继承了维柯美学最薄弱的环节——将感性认识活动和理性认识活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把艺术和直觉等同起来,美学就只是一个“独立的等式”——“艺术内容等于个人的霎时的情感,艺术形式等于表现这情感的意象”[11]。故朱光潜将语言与表现归于心理层面,他认为在传达中,“语言”和“文字”为两个阶段,语言属于心理层面,文字则在物理记载层面,表现与传达之间紧密相连,沟通二者的桥梁即是语言。
二、朱光潜“活语言”理论的提出
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更是诗得以表现、不可或缺的手段,为了更好地说明诗歌、表现与语言的关系,朱光潜提出“活语言”与“死文字”的观点。
(一)活语言的引入
朱光潜认为:“语言的实质就是情感思想的实质,语言的形式也就是情感思想的形式,情感思想和语言本是平行一致的,并无先后内外的关系。”[12]并且,实质和形式也没有先后之别,不独立于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同实质与形式紧密结合一致,思想情感与语言也紧紧缠绕在一起。当诗人情感一泻千里,语言随之而来;情感与语言消散之后,语言则由符号记录,语言和思想仿佛成为两个独立个体。
对此,朱光潜引入“文字”这一概念,在其看来,诗的语言是活语言,不是刻在纸张上的死文字。人类早期为了记录语言而创造文字,文字作为一个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双重含义,二者的关系则由人确认与书写。例如“文”,先有“wén”这一读音,读音同时传达相应的意思。对于仅出现在字典或书本上的汉字“文”,其背后内涵有多重解释;在沟通交流中,语言“文”根据上下文语境,更快抵达“文”的意义层面。在沟通交流中,语言的符号所指意义得以稳定,从而约定俗成为人沟通交流的一种形式,服务于人际交往。
因此,朱光潜认为,语言是由情感和思想赋予意义和生命的文字组织,离开情感和思想,语言也就丧失了意义和生命,成为散落在字典里的“死文字”。[13]“死文字”是僵化与无生命的,而让“死文字”重焕生机、变成“活文字”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情感和思想赋予其中,将文字置于具体语境,这时文字就变成了语言。“语言”代表“活”,“文字”代表“死”,文字借语言获得生命,语言也会因僵化变成死气沉沉的文字,活文字则嵌套在活语言之中。诗的语言也非一般文字可比拟,是毋庸置疑的“活文字”,极富情思和意蕴,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体。
由此,朱光潜抛弃了古人形式与内容之争,而是将诗的情感思想和语言关系重新定义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文字背后的语言和情感并非完全重叠,人们用极简的文字表达丰富意蕴;而情感中也有细微曲折无法被语言所表达。诗的审美功能更在于此,以部分语言唤起全部情感,以含蓄的意象和情趣表现诗人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以有限表达无限。
(二)对“作诗如说话”的反驳
但是,诗所需要的“活语言”并非不经过任何加工改造的“说的语言”,朱光潜提出语言之活应在一定界限之内。五四时期,胡适提出“作诗如说话”的主张,他认为唐诗到宋诗的玄妙之处在于作诗近于作文、近于说话,从而提倡用白话文写诗,反对雕琢粉饰。朱光潜对此观点进行了一定的反驳,在他看来,日常粗浅芜乱的情思不可入诗,必须经过精妙剪裁才可成就诗篇。不可否认,诗是诗人的情感表达,是诗人“说”出来的,但其在语言上的努力不容忽视,有如古典诗歌中的格律、典故、意象等,这些都是直接“说”出来的语言所不具备的如切如磋,是“写的语言”。
当代学者葛兆光曾谈及早期白话诗源头在宋诗,宋代“以文为诗”的创作观念影响了后期白话诗歌的创作,而在宋诗和白话诗的共通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促使诗趋向散文或口语的语言形式背后所萌发的相同诗歌观念,这是一种“须言之有物”的诗歌理想追求。所谓“言之有物”,就是在白话诗创作中更强调个人“我”的存在。然而,早期白话诗歌创作缺少语言的锤炼[14],使得早期白话诗粗糙浅俗,直到后期诗人纠正,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再一次被提起,诗人们试图在白话与日常语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要白话的明白晓畅,又要诗的铿锵音律、精美格式、含蓄意境。这与朱光潜对诗歌语言的认识一致,追求语言的活跃灵动与一刹那的感觉,但个中需要加工后的语言,以此提高描述准确性。
三、语言之“活”到诗歌之“活”
朱光潜在谈论语言之“活”时,极为重视“活语言”在诗歌中的运用。“活语言”抑或“活文字”,诗歌语言大抵都离不开“活”这一范畴,而如何让语言“活起来”更是诗歌创作中的一件大事。朱光潜提出“活语言”的实践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声、顿、韵的尝试,二为特殊语词的运用。格律、典故、诗眼都是将诗歌语言盘活的有效方式,能使语言千变万化,让语言在其中“活”了起来。
(一) 声、顿、韵的尝试
声、顿、韵都是语言在诗歌结构上的尝试,其三者的交叉使用、混合搭配更是让语言“活”起来的重要手段。大自然中本有节奏,大海的潮涨潮落、山峰的连绵交错、春夏秋冬的四季更迭都是节奏的外在显现。不仅如此,节奏也隐于人体之中,呼吸时胸腔的扩张和收缩、脉搏的跳动皆为日常难以觉察的节奏。而作为抒发人主观感受的诗歌也在展现节奏,艺术美模仿着自然美。声音的节奏是音高、音强、音长带来的,朱光潜用物理学的知识对三者进行解释,谈及“声音是在时间上纵直地绵延着”[15]。在西方诗歌中以“音步”标记,而中国诗歌中则是声、顿、韵的实际运用。
朱光潜谈及单“平上去入”四声对诗歌节奏的影响极小,平仄的组合排列虽然有限,但相同排列组合诗歌的节奏感受并非完全相同。如“日暮人归尽,沙禽上钓舟”[16]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17]两句都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格律组合,但在诵读过程中其节奏感并非一致。早期诗歌中虽未有平仄的认识,诵读中仍有节奏,这得益于诗歌中的“顿”。仍是上述的例子,断句为“日暮/人/归尽,沙禽/上/钓舟”“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二者停顿因意思不同而略有不同,故读者诵读感受也稍有不同。
此外,诗歌中的“韵”也同样重要,诗中之“韵”主要为句内押韵、句尾押韵两种,双声、叠韵、对偶等皆为“韵”在诗歌创造中的外在显现。“韵”的使用效果也与“声”“顿”一样,于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中标记语言之外的意义和情感。声、顿、韵三者的混合使用,使得诗歌既有浮声切响的金石之声,亦传达作诗之人的万般心绪。
(二)特殊语词的运用
除声、顿、韵带来的节奏变化外,字眼、典故、意象都是诗歌创作时常见的特殊语词,也是诗歌语言较日常说话更具有诗意的体现。在以诗歌展现别样的世界时,特殊语词的使用必不可少,它们使诗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受。
上文提及语言自产生之初便有一定意义,在社交环境的发展中语言拥有约定俗成的内涵,这是时人对目力所及之处的最初定义。后人使用语言时自然而然地陷入前人编织的密网中。万物由语言命名,究竟什么才是事物的本来样貌,无人知之,大多是修饰加工后的产物;概念取代事物,人也随之丧失对世界的感知力,留下的只不过“是其所是”的逻辑。由语言写就的诗则是感官接触世界的最佳产物,是人与世界发生直接关联的媒介,蕴含着诗人对外界的观照与外在事物的反映。但大千世界物象万千,诗人不可能将其全部模拟,只能抓住一点加以裁取成篇。故而,诗歌语言的再次加工难以避免,如“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的一字之差[18],仅“推”“敲”二字变换,诗歌便更为轻盈与柔和。以典故和意象丰盈诗歌之美著称的李商隐,在《锦瑟》中连用五个意象、四个典故,罗列叠加中促成整首诗情感的层层递进,相互渗透中给予读者全方位、多层次的丰富体验。
周密的意象、反复择取的诗眼、精心挑选的典故,都是诗人反复思考下的创作成果。进而,诗境也随之扩大,仅仅一刹那、一片段,却在诗人笔下获得永恒的生命力,让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景反复咀嚼个中滋味。即使人生境遇不同,但江月年年照人、江畔年年送人,在千般诗境中人总能找到与自己最契合的地方。这亦是诗的奇妙所在,“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19]。诵诗的人是自由、无边无际、不确定而又确定的,而诗的语言“‘逃避了决断的严肃性’而以‘游戏’的轻松赋予自我一个‘想象的国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比语言所构造的世界更‘真实’的世界”[20]。
因此,相对于前文中所述克罗齐对于传达的语言处于一种极其不信任的态度,朱光潜对语言却抱有极大的信心,在诗歌创作中,成也语言、败也语言,语言承载着诗人的所思所想。与情趣意象同时生成的语言也承担着诗歌的表现功能,是表现得以有效完成的工具,而这种生成的传达和表现更是文学创作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四、结语
朱光潜的“活语言”理论既有古代诗歌文学的滋养,亦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促进了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其实,无论是诗歌语言上的不断开拓,还是对于诗歌表现功能认识的不断加深,诗歌始终以语言为桥梁,传递着诗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想象。诗的生命亦在于此,开拓与创造,追寻前人无法抵达的彼岸,只要诗人存在,这一探索就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6.
[2](宋)普济.五灯会元[M].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935.
[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3:485.
[4]剑南诗稿校注[M]//钱仲联,马亚中.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267.
[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5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062.
[6](宋)杨万里.诚斋集[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555-556.
[7]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55.
[8]朱光潜.谈文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52.
[9]朱光潜.诗论讲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2.
[10][意]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5.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全二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534.
[12][13][15][19]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25,298,201,59.
[14][20]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M].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03,72.
[16](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07.
[17](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朱金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68.
[18]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96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