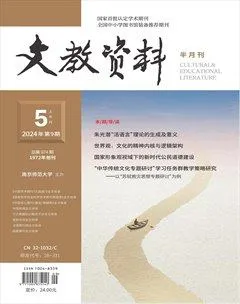汉语难易结构综述研究
2024-10-23戴丽丽
摘 要:本文首先从句法和语义特征两个维度出发,对汉语难易结构中的“好V”结构和“容易V”结构进行了分析。随后,基于心理组块效应和动词状态化假设,本文重新讨论了 “好V”类难易结构和“容易V”类难易结构的生成机制,旨在阐明这两类结构在形成过程中的差异。通过这一研究,有望更全面地理解汉语难易结构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关键词:汉语难易结构;“好V”;“容易V”;心理组块;动词状态化
受事名词短语NP常与“好/不好/难/容易+V”共现,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汉语难易结构。该结构因其独特的句法和语义特征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尽管如此,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过“好V”结构的句法生成。如吴炳章认为,“好V”是经过三个层阶的句法形成的。[1]其中,关于“好V”的句法性质,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此外,“容易V”类难易结构的研究更是鲜有涉及,学界对其句法性质及生成机制的认识尚不明确。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好V”类难易结构和“容易V”类难易结构在生成机制上的差异,以揭示两者的异同点。
一、表层结构特征
汉语难易结构主要由三大要素构成:名词短语(NP)、难易谓词(Adj)和及物性动词(Vt)。其表层线性排列可以码化为:NP+Adj+Vt。此外,汉语难易句通常表现为主被动语态,即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潜在动词通常为单纯现在时,无须经历被动化,这与主动语态句式相似。
例1 这个问题好解决。
例2 这个问题好被解决。
例3 这问题容易/很难解决。
例4 这问题容易被解决。
例5 这问题很难被解决。
例1中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复杂形式“好解决”中潜在动词“解决”的受事宾语,但是该动词仍保留着单纯现在时形式。若在“解决”前添加被动标记,反而会导致句子不通顺,甚至违反语法规则,如例2所示。然而,在例3、例4和例5中,当难易谓词为“容易”或“难”时,“解决”K8B8fgPAPwVCgDpJfeZJ0A==的被动化,似乎并不影响原句的顺畅性,这说明“好V”类难易句和“容易V”类难易句在句法表现上可能存在某些细微差异。
第二,句首主语NP通常与潜在动词Vt缺失的宾语成分之间存在共指关系,因此,NP常被解读为Vt的受事宾语。这一点与被动语态的句式特征颇为相似。例6和例7中的“这个问题”和“这本书”可视作“解决”和“找”的受事宾语,而其真正的施事主语却被隐匿,在句中通过PROarb标识。
例6 这个问题i 好/容易 [PROarb 解决 ei].
例7 这本书i不好/很难 [PROarb 找 ei].
在大多数情况下,汉语难易句的受事主语多为非生命性名词。当主语为生命性名词时,该句式既可以理解为宾语空位,也可以理解为主语空位。在特定语境下,例8可以理解为“他容易被别人忘记”或“他容易忘事儿”。
例8 他容易忘记。
事实上,汉语难易句中的主语不仅可由受事论元充当,还可由工具、材料、处所、方式等非常规的旁格论元充当,如例9—例12所示。这可能是受到汉语语言类型的影响。作为主题突出语,汉语对哪些成分可以作为主题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基于此,汉语难易句可进一步分为以核心受事论元为主语的典型汉语难易句和以旁格角色为主语的非典型汉语难易句。
例9 这把钥匙不好开。(工具)
例10 这种布料好裁。(材料)
例11 这条路容易走。(处所)
例12 女低音难唱。(方式)
二、语义特征
(一)因果关系
普遍认为,难易谓词是主观词,其语义指向事件V-NP。传统语法将难易谓词归为“非人称形容词”[2],这一分类凸显了其描述动作或事件特性的功能。此外,转换生成语法认为,无论是在难易结构还是在非难易结构中,难易谓词的题元结构都保持不变。然而,胡丽珍和雷冬平提出,汉语难易结构的基本语义是,句首主语NP 具备某种特性,使得施事者在某些事件中感到满意或困难。[3]本文更同意这一说法,其依据在于汉语难易结构和非难易结构之间确实存在细微的语义差异。
例13 这座山很难爬。
例14 爬上这座山很难。
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构式表达必然导致语义上的区别。虽然例13和14都在讨论“爬山”的难易程度,但是由于其构式不同,强调的焦点不同,使得两者传达的语义信息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例13中,难易结构聚焦句首主语“这座山”,并强调其特性(如山势陡峭、高耸等)使爬山变得困难。这里的“很难爬”不仅仅是对“爬”这一动作难易程度的描述,更是对“这座山”本身属性的反映。而例14则侧重“爬上这座山”整个事件,并强调其困难性。这里的困难性是基于整个事件的总体评估,而非 “山”本身或施事者的特性。
(二)非事件性和泛指性
汉语难易句的非事件性主要体现在其潜在动词的无标记形式。在汉语中,对具体事件的描述通常需要结合动词以及动词后的体标记如“着、了、过”等,以反映该事件是在某一特定时刻或特定情境下发生的,而潜在动词的无标记形式则表明,此类句子不再局限于描述某一具体事件。例如,“这本书好读”是一个典型的非事件性句子。这个句子并不描述具体的事件,比如“某人正在读这本书”或者“某人已经读完了这本书”,而是在强调“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即可读性。这里的“好读”是一个主观评价或描述,描述的是“这本书”的一种普遍性特征,而非某个具体情境下的行为或状态。由于这种评价不涉及具体的施事者(即正在读书的人),因此具有泛指性,即这一评价适用于所有潜在的读者,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人。
综上所述,难易结构与非难易结构在因果关系的解读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侧重凸显受事主语NP的固有属性对主观感受的影响,而后者则强调对整个事件或情境的主观感知。此外,非事件性和泛指性也是汉语难易句语义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突出主语NP所指代事物或实体的普遍性特征。
三、“好V”类结构与“容易V ”类结构的句法差异
(一)汉语难易谓词的分析
关于汉语难易谓词的语法性质,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吕叔湘认为,“‘难’的作用类似助动词”[4]。朱德熙认为,“‘难、容易、好意思’等几个形容词也有助动词的用法”[5]。曹宏依据朱德熙所归纳的助动词语法特征,试图论证“好”为助动词。其中一项基本特征是,助动词后可以带谓词性宾语,而不能带体词性宾语。[6]然而,经过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难易谓词“好/难/容易”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特征。其所接的动词并非典型的谓词性宾语,原因是这些动词无法像其他助动词后的动词那样自由地带宾语。
假设难易谓词后的动词可以带宾语,如例15b、例16b 和例17b所示,那么为了保证句子的合法性,动词的施事主语必须明确出现。然而,在例15c、例16c和例17c中,“好/难/容易”的意思发生了转变,它们不再表示原有的“容易/困难”之义。具体来说,例15c中“好”已转变为“喜好”的含义,而例16c与例17c中的“难/容易”则用来表达“可能性大小”。
例15 a.英语好学。b.好学英语。c.张三好学英语。
例16 a.群众容易召集。b.容易召集群众。c.集市这里容易召集群众。
例17 a.哈姆雷特很难演。b.很难演哈姆雷特。c.小明很难演哈姆雷特。
赵元任主张“难/容易/好”应归为副词,原因是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导致形容词与副词之间界限模糊,难以明确区分。朱德熙则定义副词为仅能充当状语的虚词。[7]一般来说,虚词在句子中的省略对整体语义影响应该不大。然而,当“好/难/容易”被省略时,原有句子的语义却发生显著变化,如例18b所示。
例18 a.这个问题好/很难/容易解决。b.这个问题解决。
综上所述,汉语难易句中的“好/难/容易”既非副词,也非助动词,而是用于表示难易程度的形容词。
(二)“好V”难易句的性质和生成机制
1. “好V”的语法性质
熊仲儒从生成语法视角出发,认为“好V”是句法派生的形容词。形容词“好”作为核心,制约着动词V,V通过核心移位跟“好”融合。融合后的“好V”结构保持了“好”的范畴特征,因此,“好V”为形容词。此外,他还采用了结构主义的隔开法和扩展法来支持“好V”为词的论断。[8]虽然“好V”的确具备形容词性特征,但它是否独立成词仍有待商榷。
首先,从语义层面来看,词的意义应当具有完整性和特定性。例如“铁x/6Tbije8qelsNonbGKcCCg7kxoVFVinlejvQ/bm4No=路”“蝴蝶”“白菜”等词汇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专有名词,具有特定的意义。然而,“好V”的意义仅仅是简单地将词素义叠加,而并非由词素融合而产生新义。比如“好解决”表示的是某事容易解决。
其次,有学者通过能产性、开放性等特征,来说明“好V”结构的松散性。古川裕指出,“好V”结构相对开放,其动词部分灵活多变,可自由替换。[9]申惠仁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好V”的内部结构尚未完全凝固,因此允许使用者构建出不同的表达形式。[10]具体来说,“好”不仅能够与很多单音节动词自由搭配,如“好办”“好懂”等,还可以与双音节以上的动词性成分搭配,如 “好解决”“好伺候”等。
再次,钟蔚苹根据朱德熙提出的语法特征——凡是受程度副词“很”修饰且不带宾语的谓词为形容词,将“好吃”“好看”“好听”等判定为不可分割的形容词。[11]同样,“好V”类难易结构也受“很”的修饰,且不带宾语,如“很好办”“很好懂”“很好解决”“很好回答”等,体现了其形容词性的特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修饰的是“好”还是“好V”,这取决于“好V”的词汇化程度。当V为单音节词时,如“好办”,我们难以断定“很”修饰的是“好”还是“好办”,因为“很/好办”或“很好/办”在韵律上都显得自然;当V为双音节词时,如 “很好解决”,其韵律节奏更倾向于“很好/解决”,此时“很”主要修饰的是“好”,而非 “好解决”。通常而言,认知主体越容易体验的动词,其聚焦度就越高。[12]因此,“好”和 “看”“听”“闻”等感官动词相结合时,更容易发生词汇化。由于“好V”类难易结构中的动词成分可自由替换且其聚焦度各异,构成的“好 V”的融合度也会有所不同:有的可能已经完成了词汇化,成为形容词;有的则尚处于词汇化过程中,接近形容词。即便是结构较为松散的“好V”,在语义上也相当于一个形容词,具有形容词的某些功能和特性。
综上所述,“好V”是一个具有形容词特征的动态结构,其语义主要源于“好”的贡献,在融合度较低的“好V”结构中,V的作用主要是对“好”所凸显的特征进行补充说明。因此,“好V”结构可近似处理为以“好”为语义重心的复合形容词,以便与“容易V”结构区分开来。
2. “好V”的生成机制
在“好V”类难易句中,动词“V”首先经历了重新分析的过程。董秀芳指出,由于心理组块效应,两个原本独立的句法单元在长期共现和使用中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复合词,这是重新分析的结果。[13]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好”与动词的频繁共现,语言使用者倾向于将它们重新分析为一个整体语块,从而完成了从两个独立成分到复合词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成分之间的原始距离逐渐减小甚至消失,最终从旧的语法结构中衍生出一个双音节或多音节复合形容词“好V”。 在这一语法化过程中,NP从动词V的直接宾语变成了复合形容词“好V”的补语。复合形容词“好V”在形式上与过去分词十分相似,它既不能为其补语指派宾格,也不能为动词“V”的逻辑主语指派施事题元角色。 然而,“好V”仍保留着“V”为其内部论元NP指派题元角色的能力。当“V”的逻辑宾语NP获得受事题元角色后,受格要求的驱动,它不得不移位至句首主语位置,以满足“扩充投射原则”[14]和“格特征核查机制”[15]。
(三)“容易V”的性质与生成机制
在“容易+V”类难易结构中,其潜在动词经历了与中动结构中的动词相类似的“状态化”过程。“状态化”这一术语,最早由韩景泉提出,指动词从原先的行为动作义转变为状态义。[16]在例19中,当形容词“容易”与动词“掌握”结合时,由于受到了难易结构“主观凸显NP属性”语义的压制,动词“掌握”经历了状态化的过程。
例19 这种结构容易掌握。
此时,“掌握”不再单纯地描述施事者的行为动作,而是转而描述受事者NP的性质状态。这种语义上的转变导致了其论元结构的相应调整,动词原本的逻辑施事主语在状态化过程中受到了贬抑。同时,动词本身还失去了为逻辑宾语“这种结构”指派宾格的能力。为满足“格”的要求,逻辑宾语“这种结构”通过句法移位的方式,从原本的宾语位置移到了句首主语位置。这种句法移动不仅改变了句子成分的语法位置,还重构了句子的信息焦点和语义重心。通过动词状态化和受事论元移位,汉语中的“NP+容易+V”难易结构得以生成。
四、结语
无论是汉语难易句中的“NP+好V”或“NP+容易+V”,其生成大都经历了与被动结构生成相似的句法操作。难易词的出现相当于将主动形式的谓语动词转变成过去分词,过去分词从语义上不再表示主动意义的施事行为动作,而是转而描述受事者的性质或状态。在句法表现上,原有动词的逻辑主语受到贬抑,而其逻辑宾语虽然获得了受事题元角色,但因无法在原始生成位置上获取必要的“格”,而不得不移至句首主语位置。
参考文献
[1]吴炳章.从形态—句法接口看“好V”的派生问题[J].外语学刊,2023(1):11-18.
[2]贾磊.英语语法辞典[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5:144.
[3]胡丽珍,雷冬平.“NP+好+V/A”的多义同构性及其承继理据的历时考察[J].语言科学,2013(5):505-519.
[4]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06.
[5][7]朱德熙.语法讲义[M].商务印书馆,1982:66,192.
[6]曹宏.中动句的语用特点及教学建议[J].汉语学习,2005(5):61-68.
[8]熊仲儒.“NP+好V”的句法分析[J].当代语言学,2011(1):63-72,94.
[9]古川裕.现代汉语的“中动语态句式”——语态变换的句法实现和词法实现[J].汉语学报,2005(2):22-32,95.
[10]申惠仁.现代汉语四种“好V”结构[J].语文学刊,2009(9):65-67.
[11]钟蔚苹.“好看”的词汇化及其语素“好”的语法化[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1(3):1-8.
[12]雷冬平,胡丽珍.“NP+好V”构式的认知机制与动态演变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3(4):470-484.
[13]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46.
[14]Noam Chomsky.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M].Cambridge MIT Press,1997:10.
[15]Noam Chomsky.The Minimalist Program[M].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2014:101.
[16]韩景泉.英语中间结构的生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3):179-188,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