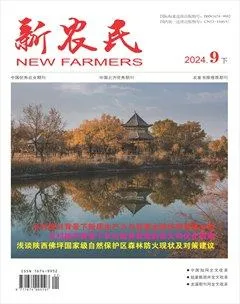论农户的民事主体地位
2024-10-21程楠
摘要:我国法律对于“农户”这一主体存在概念规定模糊、民事主体缺位的现象。但是,从历史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农户作为我国传统农村行权主体,其符合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是继承和延续中国特色的时代产物,还有利于保障农户成员的利益,具有成为民事主体的正当性。基于此认识,应当构建农户民事主体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事主体部分将“农村承包经营户”替换为“农户”,通过司法解释界定“农户”的概念,并完善其他涉农主体单行法的内容,进而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关键词:农户;民事主体;制度构建
农户主体在我国涉农领域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存在,但面对这一现实,“农户”却在我国法律处于一种模糊和缺位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早将农村承包经营户规定在“自然人”一章,确立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民事主体地位,但并未明确农户的主体地位。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涉及“农户”这一术语,但也未对农户是否具有民事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分类,我国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其中,自然人中又包括农村承包经营户[1]。但是,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农户之间并非完全等同关系,农户是否具有民事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视同农村承包经营户而认为其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农户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区分。广义的农户与自然生活中的概念相同,是指农村自然户。为方便本文研究农户的民事主体地位,应当将农户概念进行限缩,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于家庭关系所组成的为保障农民生存权的共同体。
农户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兼具个人性与社会性,它是自然人结合的共同体,但又并非自然人或法人,它不能完全适配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主体的分类,但若是就此否定农户的民事主体地位也会过于武断。学术界对于农户是否具有民事主体地位这一问题具有极大的争议,主要包括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中又分为非法人组织体说、自然人说、法人说、类似合伙的独立组织体说、新型主体说和行使主体说。他们主张应赋予农户相应的民事主体地位,理由主要从农地使用权的功能定位、家庭的民事主体地位确立、农户作为特殊主体的本土化确认需求等角度进行论述。而否定说主张农户不具有民事法律地位。理由主要从社会主体与法律主体的区分、农户作为自然人结合的产物、农地权利主体的应然设定等角度论述[2]。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构建的进程中,“农户”是否享有民事主体地位是一个绕不开去的话题。不仅如此,在实践中,涉农纠纷诉讼主体不明也是基层法院的一大心病,明确农户主体地位存在其裁判意义。在当前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之下,解决农户主体缺位问题已然成为现实要求。基于此,对农户民事主体地位进行研究,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确立农户民事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分析
法律主体在整个法律行为的大系统中起着中轴的作用,其他法律行为和事件都必须以法律主体的轴心为起始。因此,明确农户的民事主体地位有其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近些年来自西方的个体主义逐渐深入人心,学术界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将以家户主义为基础的农户行权转为农户内部成员行权,将农户这一概念直接抛弃,转而注重于农户内部个体成员,此种主张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农户应当确立其民事主体地位,具体表现在其符合民事主体构成要件,是继承延续中国特色的成果,且更有利于保障农户成员利益。
1.1 符合民事主体构成要件
民事主体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归属之主体”[3]。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包括名义独立、意志独立、财产独立和责任独立[4]。农户这一主体完全具备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第一,农户名义独立。我国涉农领域行使权利时大部分都是以农户为名义进行的,在登记时也是登记农户的名义。农户具有区别于其他主体的能力,也有作为主体对外行使权利的习惯,故符合名义独立这一条件。第二,农户意志独立。虽然有学者指出农户最终的意愿最终是由农户成员作出的,不应遮蔽实际农户个体成员意思表示的事实。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在实践中一般由户主作出意思表示,但这并不影响对外意思表示是整个农户协商一致后的结果,而非个人意志的表达。第三,农户财产独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条第2款提到了农户财产,法律承认农户财产独立,并且在债务承担时是以农户的财产进行承担的。农户具有完全独立的财产,农户的收益、支出都是以其主体整体财产进行的,不同于农户内部成员个人收入,其属于家庭共同财产。第四,农户责任独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条第2款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其农户财产承担责任,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
因此,农户完全符合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应当被确定为一个特殊的民事主体。并且我国完善的户籍制度让农户成为民事主体成为可能,作为一个高度契合民事主体本质内涵的存在,单纯以其与现有民事主体分类不能高度匹配为由否认其民事主体地位是失之偏颇的。国家立法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应当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以弥补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不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事业的进步。
1.2 继承延续中国特色
以农户为主体行使权利这一习惯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农户应运而生,从此我国农村形成了“以户为主田,各归其户”的情景。即使在我国近代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停滞,但是,从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操作来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将农户视为民事主体地位行动的。农户这一主体是基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在中华大地上茁壮生长的且被实践检验过符合我国发展的主体,是专属于我国的中国特色。
当前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二元化结构逐渐解体,传统小农经济时代已然过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户也面临着内部成员频繁流动的局面。个体主义的兴起更加促进城镇一体化,农户内部成员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涌入城镇中心寻求机会或外出务工,农户整体不断被侵蚀、解构。在当前的这种背景下,农户是否还适合作为民事主体?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当前人们未实现思想的彻底革命,中国人对家户主义有强烈的认同感,农户依然是维系农村社会文化底蕴的连接点。只要现实中人们仍然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对外交往,法律就无法不回应这种实践。即使城乡二元结构在不断缩小,但长久以来割裂的城乡结构,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仍然是巨大的鸿沟,以农户为主体仍然是当前农村背景下最好的选择。基尔克的社会化私法理论指出,民族性不是传统规则继续适用的理由,但根据民族性形成的社会模式为传统规则提供了继续存在的土壤。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赋予农户民事主体地位并非凭空想象毫无逻辑的想法,其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底色,是继承并延续历史实践的中国特色,契合于我国当前的农地权利体系和民事主体体系。
1.3 保障农户成员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系统可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5]。生产方式属于经济基础,它对法的内容、形式和效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新福利经济学,以农户作为权利主体是保障土地分配权能切实落到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最好形式,最低限度保障每一个农户成员的生存权,防止被非农成员剥夺生存权。这就意味着当前社会下,将农户明确在民事主体的法律体系中是更为合理的存在。在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法律也能发挥出他更大的活力,促进农村经济文化事业更加茁壮成长[6]。
此外,对于特殊的农户成员,例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独立实施法律行为。当前社会下,农村内部留守老人和儿童的占比不断提高,他们的利益亟待我们去重视与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由于缺乏完全行为能力,他们无法签订、履行合同,如果以农户内部成员个体行权就是完全忽视这类群体社会保障的客观事实,也违反了我们国家想要倾斜保护权利的原则。通过将农户确立为民事主体,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三元框架,以农户为主体对外行使权利,解决了因行为能力遭受利益缺失的问题,保护了这类特殊群体应享有的社会保障。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确立农户民事主体地位也应当是正当的、必要的,其是维护、保障农户成员利益的有效的工具。农户民事主体确认有利于法律体系内部和农村经济活动外部的配套协调,有利于从国家全局出发,提高立法质量、保障每位农户成员利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农户民事主体的完善
从民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民事主体经历了从一元主体到二元主体,再从二元主体到多元主体的演变过程[7]。民事主体就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根据时代的需要调整民事主体的类型。一个良好的法律就是要不断克服固有的滞后性,回应时代的呼唤,即“事随时迁,而法必变”。而我国目前法律上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把农户定在应有的法律地位。
由上述可知,农户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正当性,但农户究竟是将其放入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还是新设一类特殊主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法人、非法人组织都是组织体,拥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而农户实际缺乏并未完全具备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条件,农户是传统中国继承下来的特殊产物,其不等同于法人、非法人组织这一类新兴主体,强硬将其归类会造成与传统法律理论相冲突的现象。因此,将其分类到法人、非法人组织显然存在不足之处。但若是将农户新设一类特殊主体,容易开出民事主体分类过多的口子,若是之后又想归类一类主体,无限增加民事主体,无疑会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因此,应当在保持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审慎地将农户放入自然人一类中。农户是农户内部自然人的结合体,在实际农村生活中,其实很难区分农户行权还是农户内部人员行权,所以,将其看成一种特殊的自然人的结合体较为合适。现行法中将农村承包经营户归入自然人一类也是此做法。既然已有将农村承包经营户归入自然人的先例,作为与其相似度极高的农户归入自然人也更能为大众所接受。
首先,我国法律应当构建农户主体制度,将农户明确为民事主体,归入自然人一类,删除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农户为主体行权是中国本土化的典型,从政策的制定上来看,我国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中均多次采用“农户”这一术语。我们应当保持法律与政策的相一致性,保持各个法律条文的一致性,多个类似概念有损法律的权威,会造成法律适用者的误会和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条文中出现了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及农户三个术语,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条第2款中农村承包经营户债务承担是由农户财产进行承担的,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农户之间是等同关系的误会。事实上,农户不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必要条件,不必然拥有农业生产功能。从逻辑上来看,农户是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上位概念,且具有交叉关系,农户的概念远大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范围。因此,应当区分农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这两个术语,并以农户这一上位概念替换农村承包经营户更为合理。并且应当对“农户”这一主体进行概念界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大幅度修改。
其次,应当修改单行法中涉农民事主体不一致的条文,并在之后出台的法律和政策中均统一使用“农户”为涉农权利主体。由于之前我国法律并未清楚界定“农户”,在涉农法律条文中总是存在多个术语模糊不清的情况。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中指出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农户,但该法第5条又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发包,这就造成了人们会存在究竟是农户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主体,抑或是该两者是否属于等同关系的疑问。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认农户的民事主体地位之后,相对应的单行法条文也应当修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未来出台的法律和政策中也应当统一使用“农户”这一正式主体概念。
3 结语
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对“农户”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也并未明确农户作为民事主体存在,这极大地影响了当前农村经济生产生活。农户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楚厘清农户与其他术语之间的区别以及确认农户民事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不断适应时事要求、与时俱进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明确农户民事主体地位,取代农村承包经营户,并修改和完善其他涉农民事单行法条文,在法律制度层面作出安排和保障,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共同构建适应中国农业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法治所需要的农户民事主体制度。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2] 李伟.当代“两户”民事主体地位的历史解释与未来因应[J].政法论丛,2022(5):150-160.
[3] 梁慧星.民商法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4] 陈华,刘勇.合伙可以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和民事诉讼主体[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9(5):44-49.
[5] [苏联]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6] 李爱荣.“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行使主体探析[J].当代法学,2019,33(6):104-112.
[7] 江平,木拉提.《民法典》编纂中民事主体的三个问题[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