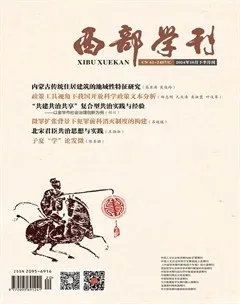《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宗密“知即是心”思想探析
2024-10-21朱宣锦
摘要:“心性”一直是佛教哲学中讨论的核心议题,对心性的认识被认为是解决众生身心问题、达到解脱的门径。《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宗密在对佛教各宗派判教的同时探讨心性问题,并提出了“知即是心”的命题,在区分心、知、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知”界定“心”阐释万法源流问题。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不仅初探圆融华严、菏泽思想的可能性,还以“知即是心”的心性禅思为日后禅教合一融汇发展奠定了理论前提,并且宗密的心性论对宋明心本论思想建构亦有启示。
关键词: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知即是心;禅宗哲学
中图分类号:B94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20-0153-04
On Zongmi’s Thought of “To know is to be the mind”
in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Chan Sources
Zhu Xuanjin
(Law School,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ind nature” has been the core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cept is recognized as the way of sentient beings to address existential conundrums and achieve liberation. In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Chan Sources, Zongmi, while examining various Buddhist sects, delves into the mind nature and proposes that “to know is to be the mind”. Utilizing this proposition, he delineates between mind, knowledge, and wisdom, and further elucidates the issue of the origin and flow of all phenomena by defining “mind” with “knowledge”. This contemplation on mind nature not onl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synthesis of the Huayan and Heze thoughts, but also lays the theoretical groundwork for the subsequent integr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Chan Buddhism. Moreover, Zongmi’s discourse on mind nature offers illuminating insights in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 theory of mind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Keywords: Zongmi;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8bbc16353b08eea187f9b84faf87e86bf Chan Sources; to know is to be the mind; Chan Buddhist philosophy
圭峰宗密(780—841年)被尊为华严宗第五祖,他曾学习菏泽宗禅法,正因如此华严宗和菏泽宗对其佛教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宗密的哲学思想承接澄观的灵知真性说,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以下简称《都序》)中圆融华严宗和菏泽宗禅思,进一步提出“知即是心”的命题。胡建明在《宗密思想综合研究》中细致梳理了宗密的心性论思想,《都序》《原人论》中集中体现了宗密主张佛教内部的思想融通,教禅一致的思想。并且宗密还将儒、释、道三者思想统摄于一心之内,强调修行由凡转圣的妙门在于“知”,这为后世的心性论、教禅合一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一、宗密思想中的“心”和“知”
宗密的哲学思想融通华严宗和菏泽宗,心性论是他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不论是对判教,还是禅教合一的主张,都源自心性论的探讨。在宗密的心性思想中,蕴含着两个重要概念:“心”和“知”。宗密将心的概念分成四种:肉团心、缘虑心、集起心、真实心。关于第四心真实心,宗密在《都序》中解释道:“然第八识无别自体,但是真心,以不觉故,与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义。和合义者,能含染净,目为藏识;不和合者,体常不变,目为真如,都是如来藏。”故《楞伽》云:“寂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即如来藏。”[1]30
前三种心都是现象并非本真,最后第四种真实心才是本相,前三心在真实心上升起。在宗密的理论中真实心且自性纯净不受污染,哪怕是受到无明尘染,本性仍是无垢澄澈的,这与《大乘起信录》中的“自性清净”观点相一致。可见在宗密哲学思想中,心的概念被划分为现象与本质两类,真实心才是心的本质部分,并且是不染、无妄,不会被熏染的空寂之心。宗密禅思中“知”的概念并非其独创,在《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中可见宗密“知”的观点主要承袭菏泽宗的“灵知”思想。宗密认为菏泽宗禅法的关键就在于“寂”与“知”,即“谓万法既空,心体本寂,寂即法身,即寂而知。知即真智,亦名菩提涅槃”[2]535。在此,寂是本体法身,知是真智、涅槃,无论本体是染净,觉或不觉,本心都天然具备知,这表现出宗密对知的强调,认为其较“寂”更为重要,堪称众妙之门。
唯有领悟这空寂之“知”,方能摆脱迷惘圆满涅槃。然而“知”并非实体,它是“无念无形”难以言说的,只能悟证。陈兵认为“以心性为空寂灵明之‘知’,乃是中国佛学‘真常心论’‘心性本觉’说的一种具体诠释,可谓中国佛学心性论有别于印度佛学的一大亮点”[3]。由此来看,宗密哲学中的“知”是心的恒常属性和本体。
二、“知即是心”命题的提出
《禅源诸诠集都序》是宗密晚年编纂的百卷作品《禅源诸诠集》所作的序,但由于《禅源诸诠集》已经遗失,只能从《都序》一窥宗密教禅观的纲要。《都序》中宗密力图主张禅教合流,阐述其必然性和可能性。在此结构中,包括“知即是心”的认知论与方法论,同时该命题的提出也是宗密认知论之核心。通过论证“知即是心”,宗密于思想上会通华严与菏泽之心性,剖示众生真如本质,明示涅槃之基础。“知即是心”的命题并不是宗密独特的创造,关于心性的看法他受到华严宗和菏泽宗的影响很大,“知即是心”的命题正是宗密进一步融通华严与菏泽二者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澄观认为心是缘起众生与佛的根本,佛与众生的心本质上并无差别。在《华严心要法门注》中澄观点明“试将心比佛,与佛始终同”[4]426可见众生与佛性无异,差别仅是佛心不染已觉,众生心妄念未觉。澄观所言“灵知不昧”是心之本质特征,指人们对现象世界不再产生无明妄念后的灵妙知见,即佛心与众生心俱有的部分——如来藏心。澄观以“无住心体,灵知不昧,性相寂默,包含德用,该摄内外,能广能深,非有非空,不生不灭”[4]426描绘此灵妙真知、即心即佛境界的显现。但此种直造心源的直觉认知是无法言明的,对于究极澄澈莹净的状态,澄观只能通过不断描述它的外延以图接近。方立天指出“这种以认知、真知、觉悟论佛性,发展了法藏以自性清净圆明为特征的佛性论”[5]。而菏泽宗神会更是认为众生心与佛心俱为一体无有差别,即“众生心即是佛心,佛心即是众生心”明确地将两者等同见性成佛。宗密吸收了两种学说的内容后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在灵知不昧和佛心、众生心无差别的心性论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个佛与众生共有灵明空寂的心体实际上与“知”是异名而同体。
《都序》中宗密并不是以叙述的方式解释“知即是心”的命题,而是通过一段设问对话道出“知即是心”。
设有人问:“每闻诸经云,迷之即垢,悟之即净,纵之即凡,修之即圣,能生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此是何物?”答云:“是心。”愚者认名,便谓已识,智者应更问:“何者是心?”答:“知即是心。”[1]60宗密以此问答解释心与知的联系,前半段对“心”的解释沿袭了澄观灵知不昧的思路,将心归为本源凡圣俱在一心,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在心上升起。后半句则进一步阐明,愚人满足于名相,得“心”便止问,而智者则深究心之本质。当深入讨论这个能升起万法,人佛无差的“心”究竟是什么时,宗密给出的答案是“知即是心”。并在下文解释道:“湿之一字,贯于清浊等万用万义之中:知之一字,亦贯于贪嗔慈忍、善恶苦乐万用万义之处。”[1]60宗密以水与湿对照心与知,水为名,湿则贯穿于水清、浊等变化万用万义之中。湿性是水的特性,且是最为根本的属性,无论水如何改变湿始终是其不变核心的内容。心与知的关系亦是如此,心法万变,然不离“知”。当拨开贪嗔痴、慈悲忍让、喜怒哀乐变化无穷的心相,认识到心为名体后,其不变的更为本质性的规定是“知”。
因此“心即是知”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华严澄观与菏泽神会心性论的基础之上对心性的纵深剖析,点名明“知”是那个心相万变背后岿然不动的本原。
三、“知即是心”宗密禅思的核心内容
宗密将“知”归纳为其心性论思想的核心,足见其重要性。在《都序》中对心的论述,更接近于对心性论问题的总结,包含“心寂而知”和“自然常知”两个重要部分。解释心与知关系时,宗密以水与湿作喻,说明了心是名字而知是本体的区别。对于这两者的关系他注解道“答:‘知即是心’(指其体也。此言最的。余字不如。若云非性非相能语言运动等是心者。何异他所问词也。)”[1]60宗密明确地表示,知才是不变、始终随性的本体,而心一方面是人佛共具的不动本性,另一方面则是随势而变的。如何认识并把握“心”,进而认识到这变化背后不变的“知”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宗密给出的解答是“心寂而知”。
在《圆觉经略疏钞》中他回应道“答云:寂而能知也。寂者是实体。坚固常定。不喧动不变异之义。经云一切空寂法是法寂不空”[2]468。可见,寂是认识的关键。寂是体,知为用。并且强调寂的坚实不动,寂法既静然不变,又能缘起和合成知,只有当心中灵明寂照真如,也就是澄观说的“见闻觉知一切事法,心常寂静即如来藏”[6]。宗密接着解释体与用的关系:“若无真心之体,说何物寂何物不动不变邪。知者谓体自知觉。昭昭不昧。弃之不得。取之不得。是当体表显义。非分别比量义。上言不喧不变动等者。只说此知寂而不变等也。寂是知寂。知是寂知。寂是知之自性体。知是寂之自性用。故清凉大师答顺宗皇师心要云。灵知不昧性相寂然。又云以知寂不二之一心。”[2]468在这里宗密详细说明了“心”“知”“寂”三者的关系,强调真心的重要性,同时提到知与寂不可分割“寂是知寂,知是寂知”,寂是知的规定性本体属性,知是寂不需要相对应的因缘便能感知的用。心需常寂,后心寂而知。冉云华指出宗密这段论述“一方面承认‘体’是本体,在理论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却也一再强调体、用不分”[7]。在悟证到“心寂而知”后,天地之道归于这一心,人的心体拨尘离垢,冲虚灿然显示灵明达到“心寂而知,目之圆觉”[8],这圆觉照亮世间万物显示万物达到寂知后的境界。
真心即性教和直显心性宗在宗密的心性体系下融合,实现教禅的一致性。他在探讨显示真心即性教时,表明真心即性教强调直接指向真心即为性,其性质“明明不昧,了了常知”[1]47。真如之性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坚实不动也即真性。宗密认为的真如之性,并不是一般性对事物浅层表象的认识,或是肉团心所具备的常知,以心传心直显本性后的本质性规定与特征。这里所指的“知”,实际上只是真如之性自然作用的结果,超越了对外部认知和内在心知的界限,表现为灵知之心即真性本具的特征。通过这种“知”,宗密强调了对“心”本质的超越,揭示了自然常知的重要性以及其在佛教哲学中的独特地位。“知”为心的体,这便是将“知”定义为世界的本源。知既不是外物强加也不是有形有念,它是了了常知,达摩以心传心传的便是“知”。宗密强调知的重要性世界本源、本觉真心、“知”三者统一,并进一步指出“非如缘境分别之识,非如照体了达之智,真是一真如之性,自然常知”[1]48宗密解释了知的特点并将它和“智”做了区分,强调知对心的超越作用,与心比较而言知更具本真、本原的意义。并且知并不是需要逻辑判断推理所证的智,它更接近一种以灵明观世界后的彻悟本觉,直显心性。蔡方鹿认为“宗密既指出心常寂是真心本体,心常知是本体的作用,又批评脱离心性的空寂、常知而追求思想、语言和动作的做法。从而把俗知排除在‘真如之性,自然常知’的范围之外”[9]。宗密主张应当渴求摆脱世俗心智的束缚,以纯粹的心境来对待思想、语言和行为。才能真正接近真如之性并领悟自然常知的境界。宗密的“知”论所体现的佛教哲学独特之处在于,它强调的不是依靠外在的逻辑推理或经验观察,而是通过内在的洞察和超越表象的方式,来认知事物的本质。真正的智慧不是通过外在的知识获取,而是通过内观和超越来实现。这种追求并非脱离现实,而是在超越世俗认知的基础上,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和领悟。
通过对心性的深入探索,宗密呼吁人们回归内心,体验自然常知的境界,以达到更高层次的觉知和体认。在宗密的哲学体系中,他对“知”的独特阐释,与世俗的繁琐认知观念产生鲜明对比。
四、“知即是心”思想对宋明理学心本论的影响
宗密“知即是心”关于万法起源的讨论,为禅教一致和会儒家打下理论基础,确立了以“知”为体的心性本体论,对宋明理学心本论也有所影响。宗密将“知”一诀确定为其佛教哲学的本体,“知”本体论的铸成标志着其哲学体系的完善,这也是其能圆融三教的理论依据。同时宗密认为只有先认识到本体论的问题,才能解决后续方法论即如何禅修达到解脱成佛的问题,他指出“故一言直示认得体已。方于体上照察义用。故无不通矣”[1]61。在认识到知是心性本体之后,才能去理解这种灵知感受心体上的觉悟智慧之灵光,此时再去体察效用无有不通的。邱高兴认为“宗密通过强调本体之心的知的特点,把本心之用发挥出来了。这就是宗密所说的‘寂而能知’”[1]24。这种本体论上的统一,使宗密可以将华严思想融入菏泽禅思中,并以知为本体建构了一整套心性论,这也是教禅合一思想基础。教是佛语和经论法义,禅是佛意。两者不会相排斥,都是由这心体流出。以知为依据自然不会“意语不一”,这为和合两种思想提供了根据。那么二者何必委屈会和?宗密答“何必会之。答至道归一精义无二。不应两存。至道非边了义不偏。不应单取。故必须会之为一令皆圆妙”[1]23。会和二者不但是思想上令二者更加精义,两者并存或单取一道反倒会使义理不甚圆融。并且宗派和教禅并非固有,把握知一字圆融教禅才不会随情互执,要“以人就法”佛说为根本依据便不会产生差别。宗密巧妙地将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融合,强调心性以灵知为体。在追求生命本质中内在性与超越性统一的过程中,心性本体的重要性被充分体现。陆九渊将程朱的理论与心性结合,提出了“心理本体”论。他论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0]其理由在于“心即理,理即心”。他强调,众人的心只是同一心,万物的理只是同一理。基于这一根本,他将心称为本心,即人类内在的善性。本心超越时空界限,宇宙万物皆在其中,体现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董群认为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与宗密的“至道归一,精义无二,不应两存”完全契合[11]。这种本心为本体的观点,使人能够以心为依托理解世界,体现了心含万法的思想。这种观点与佛教的唯心立场相一致,重视心与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坚信心外无物,心为物的本体。陆九渊的心本体论在理学乃至阳明学派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将宗密的“至道归一,精义无二”的思想与宋明儒学相结合,开创了道德形上学的新途径,探索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心性本体统一。
五、结束语
“知即是心”作为宗密禅思的核心,将“知”与“心”融合,探讨心性的本质与认知。在其心性体系中一切众生皆有灵知,只是无法从遮蔽的心认识到这一点。于此,宗密将三教会和、禅教合一的基础放在了“心”之上,建构起了灵知为核心的心本体论,表达其真心原人的心学观点。冯友兰认为宗密的心学观在隋唐佛学、唐后儒学、宋明理学中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2],并且宗密的心学在方法论将三教思想包容囊括,论证结构上重视分析推论,力图从逻辑上得出结论。其圆融广博、辩证分析的特点受到理学家们的重视,并直接影响到阳明心学与陆九渊心本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M].邱高兴,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9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0.
[3]陈兵.论宗密的“知”字诀[C].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77-84.
[4]澄观.华严心要法门注,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58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0.
[5]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38.
[6]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大正新修大藏经[M].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261.
[7]冉云华.宗密[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160.
[8]宗密.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0:149.
[9]蔡方鹿.佛教哲学“知”论探讨[J].中华文化论坛,2002(1):91-99.
[10]陆九渊.陆九渊集[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149.
[11]董群.论华严禅在佛学和理学之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哲学史,2000(2):35-43.
[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47:799.
作者简介:朱宣锦(1995—),男,汉族,甘肃甘谷人,单位为宁夏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为宗教学、佛教哲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