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并不是免除责任的护身符
2024-10-17陈顺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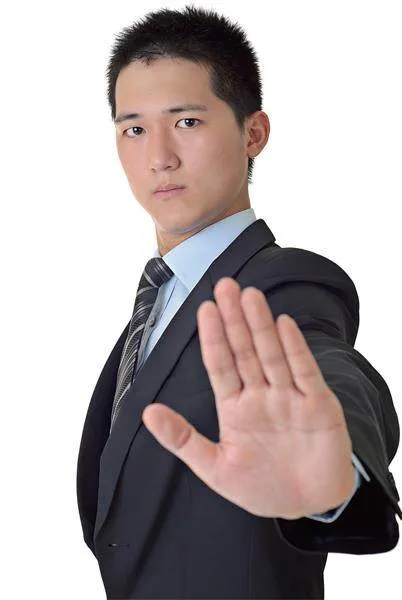
又到了下班时间,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上班的小赵完成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与好友相聚小酌,谈天说地,气氛轻松愉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聊天的范围也越来越宽。历来做事冲动、马马虎虎的小虎吐槽完前几天在路上开车,遇到对方路怒后发生争吵的事,拿小赵开玩笑说道:“赵哥,你看你在司法鉴定中心工作,哪天我也上你那儿给鉴定一下,出个什么精神病证明,再遇到生气的事时,我打他还不用负责任。”
此话一出,小赵嘴里的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帅气的发型也被晃散了,直接摆手否认三连,“不可以,没可能,千万别想这个事。”把一桌四个人给看懵了,平时也没见过小赵这么大反应。小赵整理了一下发型,在八只眼睛期盼地注视下,悠悠地开始说话:
“大家可能平时或多或少听说过一些精神疾病患者出现毁物、伤人甚至杀人的严重事件,也总有一部分人会简单地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如果出现冲动行为,如毁物或伤人了,不用承担责任,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咱们可都是有文化的人,不能人云亦云地道听途说。”
说罢白了小虎一眼,小虎略显尴尬地直挠头,直说愿闻其详。小赵说既然大家都感兴趣,那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来说说咱们法医精神病鉴定的法律依据,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方针,法律、法条要读完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几个曾经的案例来大致理解一下这条法律的含义。
案例一
李某,男,28岁,自幼内向少语,心胸狭小,脾气急,行事冲动鲁莽,爱惹事,有时打人、砸物,伤害小动物,存在性格缺陷。
其在18岁左右,间断出现精神不正常,表现为厌食消瘦,情绪低,自责,悲观厌世,活动减少,兴趣减退。有时又表现情感高涨,话多活动多,兴奋冲动,挑剔易激惹,甚至殴打父母,每种情况持续约1个月以上。曾至精神专科医院诊治,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服药后好转。十多年来坚持服药,病情偶有波动,多数时间病情缓解,与人交流正常,能自理生活、找工作,社会功能尚可。
2022年9月的某天晚间,李某与朋友边吃饭喝酒,边商量给人介绍工作的事,结束后在打车离开过程中,所乘坐的车辆与他人车辆发生碰撞,后双方发生冲突并报警。处置过程中,因为李某的两个朋友即将被带上警车,其突然从马路对面跑过来,用拳头殴打执法人员,李某被控制住时,浑身酒味,大喊“谁也管不了我,我有精神病”,言语混乱,口齿不清,兴奋冲动。
到案后在讯问中,李某称记不清楚,忘记了,而且自称有精神病,并提供既往就诊记录,故公安机关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案发时精神状态和袭警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进行司法鉴定。
经过调查与询问,得出李某患双相情感障碍,多年来坚持服药,病情基本稳定,案发前能正常聚会、给他人介绍工作,社会功能尚可,表明处于缓解期。案发当日,其在聚餐时大量饮酒,明显兴奋躁动,口齿不清,与人冲突,殴打执法人员,行为鲁莽,事后自称不记得当时情形,有自我保护意识,但其在实施行为时能准确地选择时机和对象,表明并未完全丧失意识,处于普通醉酒状态。综合考虑其所患精神疾病—— 双相情感障碍处于缓解期,又因饮酒属于自陷行为,故判断为完全责任能力。李某面临着法律的严惩。

案例二
郭某,女,65岁,已退休。1985年起间断出现情绪低落、害怕、发呆、不爱说话,哭泣等表现,担心家人的安全,觉得活得没意思,未发现情绪高涨、话多夸大等表现,长期服药病情好转。近十年情绪一直偏低落,活动少,不愿出门,不能遇事,有消极观念,想死,睡眠差,性格改变,变得固执,反应迟钝,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出门迷路,小便失禁,头颅MR显示脑内多发小缺血灶、缺血性脑白质病变、老年性脑改变,曾被诊断为多发性脑梗死。精神检查时意识清,言谈基本切题,反应显迟钝,未引出明确的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情绪略显低落,一般常识、记忆力、计算力差,理解表达和比较分析能力减退,记忆、智能受损。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轻度认知障碍。
案发当日,郭某与家人就餐后,骑行一辆路边未上锁的自行车回家,其解释为自己以前丢过多辆自行车,现在走累了,就可以骑一辆车,盗窃目的为满足日常出行方便,盗窃行为有一定现实性,作案没有预谋和准备,临时起意,顺手牵羊,且作案后没有销赃企图及掩盖犯罪行为的事实,仅仅是把车停放于自家楼下,没有藏匿,不符合一般盗窃行为的规律,其盗窃行为虽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原因显幼稚,行为轻率、不计后果,系认知功能损害的影响。事后知道行为不对,属于违法行为,但无明显悔意及压力,亦不关心如何处理,表明实施行为时受疾病影响,明辨是非能力下降,辨认能力削弱,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处罚稍减轻,需要家属加强监护,督促就医。
案例三
胡某,男,务农,51岁,子女在外地,其独自居住。1995年起出现精神异常,数次入住精神专科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有效,但其不能坚持服药,病情时有波动,迁延不愈。
2024年4月某日,胡某突然持铁棒殴打隔壁院邻居头部,致邻居重伤,颅骨骨折,事发后胡某欲逃跑,从邻居家二楼后窗跳下,摔伤致多发骨折。其被抓获后称,“我最近总嗓子疼,肯定是隔壁的人在饭里下毒了。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地震了,巴顿将军说弹道导弹正在飞过来。那时候隔壁的人在我干什么事时都要看着我,我好几次和他说‘不要看着,我做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但他就不同意。那天,我要乘坐飞机准备去法国国会,我把包、行李箱拉到院门口的时候,看见他在他院里房门口偷看我。我进去拿另一个包的时候,他在我耳边说,‘我去泄露你的消息’,当时我耳边传来了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话,‘你怎么办,打他’,于是我就用手上的铁棍打了他的头部。打完后我害怕,就跑到院子里,当时局长说‘去上面,警察要来了,警察来了抓你,会打死你,你去上面。’我从楼梯上去后,让我从二楼跳下去,我就从窗户跳下去。我打他没有什么意图,两个局长说,‘他泄露了你的信息,如果打他,我们做主,’我就把他打了。他说要泄露我上帝的任务,秦始皇让我做上帝十个多月了。他看见我干的事情就觉察到了我的秘密,我平时和他关系很好,有一次在一起喝酒。”事后,民警查看其院子里的监控录像,胡某行为异常,常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又装进去,把包放柜子里,用铁丝拧紧柜门,经常对着墙说话。
该事件中的被鉴定人有凭空闻声(幻听),自称为“上帝”(夸大妄想),疑心被害、被注视(被害妄想、关系妄想),行为异常,摔碗、收拾行李、对墙说话等,有连续长期的视频资料,表明其案发前已处于疾病期。其与受害人之间既往无矛盾冲突,案发当日,其受精神病性症状影响,认为即将被飞机接去法国国会,但被受害人注视,凭空听到对方欲将其是“上帝”的信息散布出去,又幻听到领导命令其打对方,遂持棍伤害对方。所释动机具有歪曲认知影响下的不可理解性,系病理动机导致。事后又在幻听支配下跳窗逃跑而受伤,表明受疾病影响,实质性辨认能力丧失,综合分析后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但是其后续需要接受强制医疗管理,同时其监护人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故事讲完,桌上一片安静,小虎伸伸舌头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可能。”小赵说道:“现实中法律上是严谨的,所以单纯理解为有精神病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是认识偏颇。这就是三个相对典型的鉴定案例,简单来说首先要判断这个人是否具有精神疾病,如果有精神疾病,需要明确疾病诊断。确定有精神疾病后,再根据目击者等反映和其在事发当时的表现判断精神状态,进而分析和评估其对事物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以评定责任能力。
以上三个案例是对《刑法》第十八条的具体应用。例如第一个案例中的李某,虽然诊断明确患有精神疾病,但是案发当时处于缓解期,言行正常,其对事务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存在,又是醉酒后发生的行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第二个案例中,郭某因为精神疾病影响,症状延续,事发当时其辨认能力下降,所以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第三个案例中伤人者因为治疗不规律,病情迁延不愈,事发时有大量精神病性症状,且在这些症状支配下发生违法行为,故虽判定无刑事责任能力,但是应按法律规定接受强制医疗,同时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部分。
小虎问道:“那过程中不会有人假装患精神疾病吗?”小赵说:“正因为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法条上说需要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也就是我们司法鉴定这个专业所做的工作。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其特有的规律,伪装出来的是会被识别的,同时我们也会大量调查被鉴定人周边的相关信息,根据客观证据去甄别,正所谓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是犯罪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既保护广大普通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患有精神疾病人群的正当权益。”
聚餐进入尾声,小赵举杯,以茶代酒,表示跟朋友们聊了这么多,希望对大家生活中的法律知识、精神和心理健康方面知识提升有所帮助,共同做好每个人分内的事,奉公守法,为国家法制化进程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