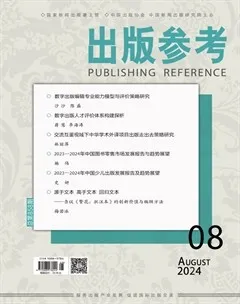源于文本 高于文本 回归文本
2024-10-14梅若冰
摘 要:《繁花:批注本》的选题策划以文本为中心,编辑团队反复思考、提炼书稿主题与核心特点,整体设计回归“复古”基调,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充分发挥编辑主体性,全面调动资源,积极回应出版价值,体现了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这部内容特色鲜明,排版形式和装帧设计颇具艺术感的图书,是近年来图书出版领域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成功探索。
关键词:文学出版 选题策划 编辑方法 《繁花》
2024年1月前后,受电视剧《繁花》热映带动,由金宇澄著、沈宏非批注、姜庆共排版的《繁花:批注本》发行约30万册,成为岁末年初文学图书市场的一匹黑马。
《繁花:批注本》于2016年签订出版合同,首版出版于2023年6月,编辑工作长达6年8个月。作为市面上唯一一部当代横排小说批注本,《繁花:批注本》拥有个性鲜明的内容、独特的排版形式和图书形态,是近年来图书出版领域一次颇具创新价值的选题策划尝试与编辑方法探索。
一、策划思路:源于原著的创新性文本再造
《繁花》2011年起连载于弄堂网,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图书长销不衰,又不断有舞台剧、电视剧、电影改编邀约,更让人期待的是王家卫导演加盟同名影视创作,《繁花》的IP价值不言而喻。
为《繁花》做批注本的创意来源,一是继承自文学传统形式。批注由来已久,自注、疏、说、笺起,到明清时期批注小说,千百年间,文人为经典作品加入自己的理解和相关资料补充,即成一家之言;以原著为基础,不同的批注者可汇集出文本更充实、风格更多元的作品。《繁花》获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道:“遥承近代小说传统……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繁花》的话本语言遵从“传统叙事”“中国式的简洁”,情节处理和人物塑造具备生活化的模糊感[1],加上贯穿全书的各种富时代感的细节与人物命运流转中的微妙联系,让这部小说以文学为起点往社会学延伸,成为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何平认为:“(《繁花》)如果真的要作评论,可能最适合的是张竹坡、金圣叹的点评路数,茶酒伺候,看一两行,点下批下。”[2]策划编辑提出为《繁花》做批注本,当属众望所归,也是作者欣然同意授予《繁花:批注本》版权的重要原因。
为《繁花》选择一名合适的批注者,成为选题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批注者选取的角度、采用的语言风格、个人特色与原著的融合碰撞,是否有足够的新鲜感以满足大众对《繁花》的期待,是选择批注作者的重要考量因素。沈宏非是电视节目策划人,制片人,专栏作家,美食家。他同时具备海派文化成长背景下的深厚底蕴、拥有专栏作家诙谐潇洒的语言风格,并对美食领域有着细致研究和实践,亦曾有小说创作和发表经历,从而成为担任批注者的不二人选。成稿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批注文本对原著涉及的文化背景、上海方言、艺术细节做了很好的诠释,消弭了《繁花》由上海方言写成的文本阅读障碍;同时,批注的语言风格与原著形成了生活化的呼应和风格上的碰撞,一个喋喋自语,一个插科打诨,以戏谑消解严肃,以精细考究注释粗粝生活,对《繁花》话语体系下的上海影像形成了很好的补充。沈氏批注特色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毛尖、欧阳江河、何平等学者对其评价颇高,陈建华教授认为:“批注展示广袤视野与深邃知库,囊括寰宇,笼罩三才,其释词之精详、疏通文理之精微,令笔者击节叹赏,然难言其涯涘……所谓五湖四海一家亲,显示出海纳百川的‘海派’风貌。”[3]
整体来看,《繁花:批注本》的选题策划灵感来源与《繁花》一脉相承,却在文本风格上另辟蹊径,突破学院派的批评模式,令批注文本反其道而行之,原著与批注交错纵横,交织出一种解构式的现代风格,不失为创新性文本再造的成功尝试。
二、图书呈现:海派情调与复古意味
图书呈现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内容与形式如何实现有机统一。出版物表现在艺术上的美,应当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4],编辑工作的重点,是概括提炼书稿的核心与特色,在文稿编排上理清逻辑,阐明核心;令版式设计服务于书稿阅读功能;同时确保封面设计突出本书主题,表达本书特色。《繁花:批注本》的设计理念基于“复古”的统一基调而来,正文通过细节阐释上海味道,并将版式设计、封面设计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1.高于文本的批注
在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过程中,内容起主导性作用。[5]《繁花:批注本》初稿成稿时间为2019年2月,绝大部分批注文本已经完成,在作者进行补充修改的同时,编辑工作同步开展。2019年2月至2020年6月,编辑与批注作者反复修改批注稿4次,才形成最终定稿。批注者必须站在比原著作者更高的角度俯视文本,才能体现出批注的独特价值。编辑工作同样以此为准绳,对批注进行编辑加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关于数量,批注不可过密以致影响阅读,不可过疏以致批注作用被忽略;第二,关于位置,以重点人物、重点情节、典型文化背景元素、上海方言首次出现等位置为主,结合数量原则,对风格不够突出的位置进行调整;第三,关于形式,全书批注共分为夹批、侧批、段批、尾批,功能各不相同,结合批注文本,编辑需在深度了解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与想象,并在审读过程准确说明批注形式;第四,关于内容,结合位置原则,突出批注作者创作特色,以“上海味道”作为批注文本的走向,大量精简冗余批注,整体把握批注文本与原著文本的碰撞感,以达到对照呼应却浑然一体的最终效果。除了进行修订、增补、删改等基本编辑工作之外,也可以认为,编辑深度参与了批注文本的创作过程,以编辑加工的结构性、整体性、经验性、综合性视角,对批注文本进行了全面组织和优化,为排版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2.服务文本的排版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横排长篇小说批注本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主,除另附脚注外,内文多以黑、红二色区别呈现,夹批以红色小字号、加注特殊符号铺陈其间,侧批和正文多不混排,在切口方向单列出现。借鉴古典小说批注本排版形式,版式设计师姜庆共先生延续了以黑、红二色和大小字号区别呈现正文与批注的做法。原著内容、批注形式,都与“复古”理念暗合,结合《繁花》的批注特点,版式设计也紧扣这一设计理念,让排版全面为内容服务。在全面保证阅读体验的同时,设计师提出了不同的正文排版方案,尤其是对侧批位置进行了多种尝试,例如侧批是否出血、是否跨页、是否以特殊符号标记、特殊符号标记规则等,并对比选择了批注错落于正文中、版心不出血的排版方案。在字体选择上,设计师坚持使用“汉仪新人文宋体”,因其笔画比20世纪的正文宋体略粗,具有“镌刻的手工感”;且文字和标点均各占“全角”一格,字字见方,与铅印时代排版方式对应,一字一字手工调整完善,[6]设计理念、呈现方法都颇具巧思和古意。书稿排版约耗时2年完成,期间作者细致构思、调整每一页版式,解决《繁花》原著存在的造字问题、字体变换、繁简转换等问题。截至目前,《繁花:批注本》作为市面上唯一一部当代长篇小说横排批注本,内文版式是为原著量身定做且难以复制的,也是当代出版物在内文版式设计上一次极有意义的艺术实践。因此,版式设计者也被郑重地在封面上署名,成为本书的作者之一。
3.回归文本的整体设计
封面设计是图书呈现的最直观环节,其设计方案应做到与文本风格统一。在设计元素选择上,应突出图书重点,令读者能够一眼抓住图书核心主题,且提示文本风格,从而让整个图书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美感。《繁花》版本众多,“繁花”二字多采用作者手绘稿,《繁花:批注本》同样延续了这一惯例,并以此作为《繁花》最重要的设计元素。此外,《繁花:批注本》再次统一了“复古”主题,暗红色封面庄重简洁,没有额外添加冗杂成分。为与其他的《繁花》版本相区分,批注本在封面设计上做了与众不同的尝试。来自材料触感与视感结合的灵感[7],经作者、编辑团队、设计团队多次打样对比,最终选用红色彩烙纸压凹印刷。压凹工艺部分颜色更深,手感立体;彩烙纸具备天然的白色驳杂条纹,暗合原著小说千丝万缕的生活化叙述;又因条纹形状位置随机,每本成品图书的条纹各不相同,使得每位读者手中的图书都是独一无二的。扉页模拟古书封面做大字竖排设计。为了满足发行需要,另配一腰封,对图书主要信息加以说明。《繁花:批注本》在延续《繁花》系列设计方案的情况下进行了改良和创新,在印制条件最理想的情况下,成品图书实现了封面触感、成书视感、文本统一、要素明确的结合。
三、编辑主体性:于繁琐中见繁花
编辑主体性,即编辑在选题策划、出版生产活动中充分确立主体地位,发挥自己的主体创造性并物化到编辑作品中的特性[8],是编辑主体的根本特征,由编辑实践活动得以实现。[9]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主动中介,编辑需明确主导地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能动性地创造高于原稿的价值;[10]通过主动调动所有资源,将头脑中的构想真正变成客观存在,将无形的意识变为人们可以想象和把握、理解和接受的传媒形象[11],并满足客观市场规律,引导文化传播向善向美。在《繁花:批注本》的出版过程中,编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让源于文本而来的“批注本”灵感真正得以落地实践,拔高文本的艺术价值,又回归文本的复古与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调度与目标实现
编辑不仅要充分利用既有经验、知识、技术手段以实现目的,又必须在原有经验基础上不断突破创新,设定一个高于市场平均审美水准的目标,并将其付诸实践。从《繁花:批注本》的选题策划和版权落地,再到批注文本审读、编辑加工、内文排版、整体设计、成品印刷,以及图书出版后与电视剧的IP联动营销,整个出版活动流程需要编辑团队调动庞大的脑力、体力、人力资源进行协调,以期令图书顺利出版,实现销售目标。例如,在编辑加工阶段,除遵循常规图书编辑方法和原则外,还必须关注原著与批注之间的动态联系,分析批注的位置、文本、作用和价值,对批注文本做出相应的取舍和修改,厘定批注所处位置是否恰当等,并对红样进行细致核对。在校对阶段,校对人员需按照编辑要求,“校异同”与“校是非”的思想活动交叉进行,“校异同”主要针对原著文本,原著文本存在大量有意识的字体变化和繁简转换,批注本所录原文需与原著一字不差;“校是非”主要针对批注文本,需审校批注文本自身、核对批注位置与原文是否对应、核对每一页的批注是否符合全书的既定排版规则、字体字号是否前后一致等。在印制阶段,编辑需要设定好内文的既定目标,包括内文字体颜色、特殊字体设置、插图呈现、封面印制效果等,并要求设计师、印刷厂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实现既定目标。其中涉及的环节紧密相连,繁复而琐碎,编辑必须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准确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进度和逻辑,才能达到最高效率地调动资源,实现既定目标。
2.人文探索和出版价值
从图书出版角度来看,《繁花:批注本》不仅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基础上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其出版过程更像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探索和实践。
一方面,现代传媒发展背景下,能实现“批注”功能的评价体系众多,量化评分、综合书评、实时弹幕等情绪价值更丰富的评价体系更受大众读者青睐。《繁花:批注本》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选择了一种最古典、最费时费力的形式出版新版本《繁花》,不光是因为《繁花》版权是高商业价值的稀缺资源,也或将成为出版业一次绝无仅有的传承和实验性创新。另一方面,图书出版需要接轨读者需求,更需要高于读者需求,以实现出版文化引领的功能。《繁花:批注本》借助热销,让读者看到一种当代文学耳目一新的呈现方式,或许会激发关于同类作品的创作灵感,为更多优秀文学作品带来新的演绎面貌,这也是编辑团队能够坚持完成这部作品的核心动因之一。
3.编辑的工匠精神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编辑的工匠精神被赋予新时代的要求,秉承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甘于奉献,同时拥抱变化,主动学习和创新。编辑是一个“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繁花:批注本》的重要价值注定其将经历繁复的编辑流程,编辑团队必须用长期训练而来的职业素养抵抗持续琐碎工作的厌倦感,并且甘愿退居台后,“依其复古传统,只在版权页和勒口上留名以作纪念,一声不响”。[12]《繁花:批注本》编辑工作期间经历诸多不可抗力的干扰,编辑团队始终在克服客观环境的不便,坚持既定的作品目标,对作品进行反复打磨,不厌其烦。“在一切形式都是内容的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这种工匠精神,如同一件艺术品的《繁花:批注本》是不可能诞生的。”[13]电视剧播出期间,编辑团队制作独家签章本,配合社内营销发行渠道,一举占据市场先机;与营销部门密切合作,推出了“用显微镜看繁花”系列文案,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编辑、发行、营销的一体化协作,充分发挥了“繁花”IP的联动效应,成为《繁花:批注本》能取得市场化成功的关键。
四、结语
几经更迭,传统出版行业的生态位从纸媒时代的唯一,演变为多媒体时代不可替代的产物,与出版人的坚守、继承和创新是分不开的。《繁花:批注本》作为沧海一粟,体现了编辑的职业素养和高度主体性,也为出版业带来了可复制的精品出版经验:源于文本的选题策划,高于文本的创新性再造,回归文本的整体设计。《繁花:批注本》的出版和成功证明,在快节奏的传媒环境下,出版人尽管踽踽独行,但唯有恒心方能恒久,才能打造更多传世精品。
(作者单位系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