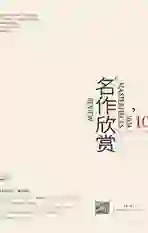孙荃和郁达夫的情书相思、诗词唱和(上)
2024-10-12张耀杰
孙荃和郁达夫的婚姻约定
孙荃,原名兰坡,小字潜媞,1897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宵井下台门村,比郁达夫小一岁。她的父亲孙孝贞早年苦读诗书,因为科举失败而弃文经商,经营着一家纸厂和一百多亩田产,在当地属于富绅之家。她的母亲是孙孝贞的续弦妻子,娘家住杭州拱宸桥,是一位读书识字的城市女性。孙荃同父异母的长兄孙灏,字贻清,又写作伊清,中过秀才,是当地名医。孙荃十多岁就能够和父兄诗文唱和,是一位裹了小脚的富家才女。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又名荫生,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绅商家庭。他的中学修业文凭上称“学生郁荫生,原名文”;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证书上称郁文,其英文证书上的名字是T.D.YUEWEN。
据1947年编撰的《萧邑郁氏宗谱》记载,郁家和孙家世代相交,清朝嘉庆十四年即1809年,郁大镛与孙氏签订合同,说是他的父亲郁宸章和孙天佑从少年结义一生,情同手足,胜若同胞,后辈不忍二君墓设两处,共同出资在富阳屠山购买田地作为两家坟地。
1918年4月14日,郁达夫在寄给孙荃的明信片上写道:“清明祭祀已毕否?文家亦有人来宵井耶?儿时文每来汝家宿,晓窗残月,东阁鸡声;旧梦重寻,已如隔世。”
按照郁达夫、孙荃的长孙郁峻峰的说法,1915年11月,郁达夫给孙伊清写信时的落款是“近作四律呈伊清表叔斧正”,郁达夫和孙荃订婚后于1918年10月2日给孙伊清写信时,称呼改为“外兄”。由此可知,郁、孙两家一直存在姻亲关系,在1917年订婚之前,孙荃其实是比郁达夫高一个辈分的“表姑”。郁达夫小时候几乎每年清明都随家人到宵井上坟,并且在孙荃家里留宿,他和孙荃其实是从小认识的。郁达夫的母亲陆氏1866年出生于宵井栗园里,与宵井下台门相距数里。郁达夫四岁时,父亲郁企曾病逝,陆氏主持经营全部家业,包括定时到宵井附近的祖坟烧纸祭祖、到宵井下塘村收缴田租。
关于郁达夫和孙荃的婚事,广为流传的说法出自郁达夫1927年3月4日写给王映霞的长篇情书:
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作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到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是长年地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的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地结了婚。
郁峻峰在《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发表的《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一文,依据孙荃所珍存的郁达夫早年日记、书信和诗文手稿,针对郁达夫和孙荃三岁订婚的说法提出两项质疑:
首先是郁达夫狂热追求王映霞的特殊情景。按照王映霞的解释:“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是怎样地被一个已婚的浪漫男人用诱和逼的双重手段,来达到了他的目的。”郁达夫追求王映霞期间的“诱和逼”,包括一部分夸张虚构的不实之词,以及情急之下的不择言词、不择手段。
其次,这种说法没有原始记录予以佐证。“郁达夫自1917年阳历2月16日开始记日记,在前4个月的记载中并没有出现有关婚事的片言只语,直到6月17日:‘……今日接家信谓将予完婚,明日将作复绝此事之信一封。’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史料中最早的有关郁孙婚姻的文字记录。”
掌握大量私家资料的郁峻峰,由于缺乏学术训练,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文字表述:“6月16日日记:‘今日接家信谓将为予完婚,明日将作复绝此事之信一封。’17日果然‘今日发家信一封’,说的应该就是此事。”
查阅郁峻峰执笔编写的《郁达夫年谱》,1917年6月16日项下的文字是:“午前交请假单,午后领来船票,夜赴隆儿处,与之谈一刻钟。同日,致函孙伊清(已佚)及赠隆儿花邮片。”该年谱对于“目前为止发现的史料中最早的有关郁孙婚姻的文字记录”,并没有给予明确说明,在6月17日项下倒是有“发家信一”的记录。由此可以断定,郁达夫日记中所说“今日接家信谓将予完婚”,是1917年6月16日的事情,他当天致函孙荃的兄长孙伊清,所要谈论的主要是完婚之事。郁峻峰《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所谓“直到6月17日”,是一处明显的笔误。
依据郁峻峰在《郁达夫年谱》和《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中提供的相关资料,郁达夫此前日记中虽然“并没有出现有关婚事的片言只语”,与婚事相关的文字记录还是存在的。
1917年5月31日,郁达夫接到杭州宗文中学孙树祺的来信。6月2日,郁达夫给孙树祺写了回信。孙树祺是孙荃的长兄孙伊清的长子,他的来信主要是询问到日本留学的相关事项,也免不了会提到家里情况,从而触发已经在日本留学四年的二十一岁的郁达夫的思乡情绪和本能情欲。
6月8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午前颇不振。夜雨,同学某来予正苦寂也。嗟乎!予自与曼兄绝后,予之旧友一朝弃尽,影形相吊,迄今半载,来访穷庐者二三小孩外只洗衣妇及饭店走卒耳。……今日颇思归,苦无余钱,只能作罢论耳。来年则无论如何欲归国一次也。”
这里的“曼兄”,指的是郁达夫的长兄、原名华又名庆云的郁曼陀。郁曼陀长郁达夫十二岁,他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岁时考取官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留学,毕业后升入法政大学专习法律。辛亥革命后,郁曼陀被任命为京师审判厅推事。1913年,郁曼陀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司法工作,便把郁达夫带到日本。郁达夫选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攻读文科期间,曾经按照郁曼陀的要求改入医科部特设预科,以便掌握自食其力的一技之长。1916年,就读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医学部的郁达夫,立志要成为一名爱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于是便改入德语法律科就读。郁曼陀针对郁达夫的擅自改科严加痛斥,并且中断了此前承诺的学费补贴。
1917年6月9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郁极思归颇苦,晚发信两封,一问经理员支费,一问家中索旅费也。”
6月10日上午,郁达夫前往邮船公司咨询,得知从长崎到上海的二等船票的往返价格是30元。他返回时路过开杂货铺的后藤隆子(隆儿)家,隆儿嘱托他代买《寮歌集》四册,他为此奔走了半天时间,并且开始和隆儿密切交往。
6月11日下午,郁达夫给邀请他回国的二哥郁浩写了回信。郁浩在来信中应该提到郁达夫和孙荃的婚事,这也是他邀请郁达夫回国的用意所在。
6月16日,郁达夫上午请假,下午拿到回国船票,并接到家里要他回乡完婚的正式书信。他于当天给孙荃的兄长孙伊清写信表达意见,并且连夜找隆儿倾诉。郁达夫在孙荃和隆儿之间所喜爱的显然是隆儿,于是就有了明天写家信拒绝完婚的决定。
6月20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表白了在孙荃和隆儿之间难以取舍的精神挣扎和情感纠结:“予已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为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
6月24日下午,郁达夫到隆儿家取英文诗集并话别,然后在日记中表示“此后不复欲与见矣”,并且在日记上加写了眉批:“自十日起到二十四日止,此十四日中予乃梦中人也。”
6月26日,郁达夫收到母亲附有20元汇票的来信,于第二天即6月27日启程回国,7月2日抵达上海,7月6日在杭州见到孙树祺。7月7日回到富阳家中。郁达夫在此后的半个月里不停地走亲访友、吟诗读书,直到7月22日,他的日记中才出现赴宵井相亲的文字记录:
晨起即往宵井,午前十一时顷午膳,膳毕偕树祺等至贝山寺,雨时方在贝山寺小饮也。入山里许至白纸槽,有劈竹使成细束者,再置细竹于灰水中者,有洗涤之者,有于槽中沥纸者,千工万苦始能造成一纸。创业之艰于斯可见矣!午后接陈某谈。拟明晨回富阳。夜不成睡,苦蚊子多也。
7月23日,从宵井回到富阳的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陈凤标表公以婚事来谈。”
7月24日,郁达夫写道:“晨起作书致陈某婉辞婚也。”
这里的“陈某”,自然是媒人陈凤标。郁达夫在随后十多天里,先和姐夫张兰生一起游览杭州西湖,然后依旧是走亲访友。8月9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媞手书也,文字清简已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孙荃(潜媞)的这封密信已经佚失,其主要内容并不是谈论婚事,而是向自己所仰慕的才子诗人郁达夫请教读书写诗方面的问题,从而激发出郁达夫充当精神导师的虚荣和冲动。于是就有了郁达夫标题为《云里一鳞》的长篇回信。
郁达夫在“八月十日旧历六月二十三夜书”的序言中表白说:“八月九日某以书来谒。予东行在即,欲作答苦无时,不答则又不足以报垂顾之盛意,于是每日于月落参横际,割一小时,依枕疾书,将所欲言者尽笔之于书,使闺中弱女子,亦得知二十世纪之气风若何。盲人行,须求助于相,否则亦必待行杖之扶。予虽无相者之指挥术,或者亦能代行杖之支助乎。”
《云里一鳞》第一段的警句是“过渡时代之危祸”:“我国古制,男女不相授受。近年来,西风东渐,男女交际自由之说,亦横流于中土。……近来男女间有种种离奇事者,要亦不外乎此耳。”
已经在日本享受到男女交际自由的郁达夫,要求于孙荃的却是遵守“男女不相授受”的“古制”。他讲解“虚荣不可慕”的第二段文字中,所强调的竟然是中国传统礼教社会不太文明的尊卑等级:
文明有益于国,人尽皆知。文明有害于民,人不察也。杭州风俗,旧尚纯朴,近则乞儿佣妇,亦衣绸帛,少年人皆戴金约指、金袖表矣,是则文明之害也。
接下来,郁达夫提出“女子读书当求真书读之”“女子不患多才而患无真才”的读书观。他在这封长信中,俨然是把孙荃当作抵制外来文明的女弟子来加以教诲指导的,他推荐给孙荃的经史子集的书单里面,就有一本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妾妇之道的《烈女传》。
8月11日,郁达夫日记:“晨起作《云里一鳞》寄孙氏,明日当有莫干山之行。”他在日记上方页眉处还写了“孙荃”二字,这是他给小字潜媞的孙兰坡起的新名字。如此改名意味着郁达夫已经回心转意,正在重新考量他与孙荃之间的婚姻大事。
9月2日,郁达夫乘船离开富阳前往杭州,入住华英旅馆。他在当天日记中补写了8月28日即旧历七月十一日打破“古制”和孙荃订婚的情景:
临行前陈某以未婚妻某所作书信来谒,翌日即乘舆至未婚妻家。时因作纸忙,伊父母皆在贝山寺。未婚妻某因出接于中厅,晚复陪予饮。时乃旧历七月十一日也。膳毕,予宿东厢。因月明,故踏月出访陈某,陈某出未归也。田中稻方割尽,一望空阔,到处只见干洁之泥田及短长之稻脚,清新畅达。大有欲终老是乡之意。翌日岳父归,与偕赴柳坞听戏,夜遇雨,归已迟……
所谓“因作纸忙,伊父母皆在贝山寺”显然是一种托词,目的在于主动放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权力,给郁达夫、孙荃提供直接相亲、自主选择的机会。郁达夫在孙荃家里住了两个晚上,经过男女双方自由交谈、自主选择,正式确认了婚姻约定,这样才有了“未婚妻”“岳父”之类的称呼。
概括地说,郁达夫、孙荃之间虽然不能确定是三岁订婚,双方家长早年的口头婚约还是存在的。1917年,郁达夫二十一岁、孙荃二十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郁达夫索要旅费回国返家的主要原因,是与长兄郁曼陀反目绝交之后的“郁极思归”,而不仅仅是双方家庭的包办逼婚。郁达夫对于由双方家庭代为选择的婚姻对象,在情绪上是有所抵触的。他先在6月17日的家信中表示拒绝,回到家乡见过孙荃及家人之后,又于7月24日通过给媒人陈凤标写信的方式,第二次表示“辞婚”。孙荃在关键时刻直接出面,用“文字清简已压倒前清老秀才”的两封温婉良善的书信打破僵局,换来男女双方的当面对谈。双方各退一步相互妥协的结果,是把完婚变成重新确立婚姻约定的正式订婚。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制”,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包办,在举行正式婚礼揭开盖头之前是“不相授受”的。郁达夫和孙荃之间虽然算不上现代意义的自由恋爱,却已经明显突破传统包办婚姻所遵守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不相授受”之类的“古制”。郁达夫认定孙荃为“未婚妻”的整个过程,足以证明这是一桩由家长初选、媒人传话,再经过男女双方当事人直接会面、自由决定的半新半旧的自主婚姻。
鸿雁池鲤的诗词唱和
郁达夫受孙荃父母及兄长的重托,准备把孙伊清的长子、小名关绪的孙树祺带往日本留学深造。他为了等待孙树祺一起上路,在杭州一直逗留到1917年9月7日。9月3日即旧历七月十七日晚上,郁达夫以《奉赠》为标题写作七绝五首,在杭州托朋友邦钧太转交孙荃,其中第三首绝句写道:
杨柳梢头月正圆,摇鞭重写定情篇。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
郁达夫为这首绝句加写的注解是:“预计返国,当在五年后。”
郁达夫在第四首七绝里,套用李清照的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表白道:“立马江浔泪不干,长亭诀别本来难。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回到日本,为前四首七律绝句加写题记“夜月明,成诗若干首,寄未婚妻某者也”,以《临行有寄》为题发表在10月14日的日本《新爱知新闻》第9431号,算是公开发布自己正式订婚的信息。
郁峻峰在《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一文中,首次公开了郁达夫“奉赠”孙荃却一直不肯公开发表的第五首七律绝句:“一纸家书抵万金,少陵此语感人深。天边鸿雁池中鲤,切莫临风惜尔音。”
郁达夫在这首七律绝句中,明确设定了男女双方内外有别的角色定位,真实展现了他这个飞到日本享受近现代文明的“天边鸿雁”,偏偏要求孙荃像“池中鲤”一样留在闺阁充当贤妻良母、管家主妇的男权底色。
1917年9月7日,郁达夫和孙树祺一起前往上海,入住吉升客栈。他们于9月10日下午乘船出海,9月15日在神户下船前往名古屋。9月22日,郁达夫在写给孙荃的情书中颇为动情地表白说:
举头见新月如眉,斜挂于碧天云影中,蟋蟀一鸣,万籁俱寂,西望故园,觉怀乡情切,不能暂耐,俯首凭栏,竟泫然泪落矣。予自去国迄今,五易寒暑,其中得失悲欢事颇多:祖母病报至不泣;姪儿死耗至不泣;去年因微事与曼兄争,曼兄绝交书至亦不泣;今日之泣,尽为汝也,然则汝亦可以自慰矣!
郁达夫一上来就把孙荃的地位抬高到所有家人之上,给对方吃了一颗定心丸。接下来,他提出要求说:“忆来时约各寄书,何以至今,尚未见汝只字?……前次关绪带来书一封,虽系汝手笔,然语气不合,当是汝兄草稿。此后无论如何,不可使人代作,若辞不能达意时,只可问一句二句,不可通篇求人改削也。予每日作‘起居注’,汝亦可效此。”
所谓“起居注”,指的是古代皇帝的贴身文官为皇帝逐日记载的言行录,这里指的是郁达夫自负满满的私人日记。为了让孙荃以自己为榜样每天坚持记录日记,郁达夫专门把自己的当天日记录入信中供对方效仿。第二天即9月23日晚上,郁达夫在信中写下一页用来写诗的题目,指导孙荃练习命题律诗。谈到孙荃的称谓,郁达夫郑重建议对方正式采用自己所赠送的新名字:“来书自称妾,固合于礼,然未免太拘,不若自称荃之雅而简也。”
9月24日,郁达夫给明治大学写信,帮助孙树祺咨询入学日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树祺一直住在名古屋补习日文。
10月2日,郁达夫给孙荃写了回到日本之后的第二封信,信里为孙荃修改了来信中附录的七律绝句《奉寄二绝》。
10月11日,郁达夫收到孙荃来信,信中附录了自己的习作:一篇《戒缠足文》和两首七律绝句。所谓“戒缠足文”,就是孙荃以自己的缠裹小脚为戒,劝告世人不要缠足。
10月15日,郁达夫收到孙荃的又一封来信,他在10月17日的情书中就祖母想见孙荃一事给出答复:“祖母欲见汝,自是老人望后辈之心。汝若赴杭,道经富阳,不妨暂至家中一坐,使祖母一见,安伊老后之心。”
10月21日午后,郁达夫收到孙荃来信,信中附有诗词六篇。10月23日,郁达夫为孙荃改写七绝四首,并且乘兴为孙荃写作一首唱和绝句:“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坡出楚词。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荃同荪,出自《楚辞》,是一种似石菖蒲而叶无脊的香草。郁达夫所谓的“离人芳草”,和前述《奉赠》第五首的“天边鸿雁池中鲤”一样,为孙荃设定了留在闺阁充当贤妻良母、管家主妇的角色定位。正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深意,郁达夫在10月25日的回信中,掐灭堵死了孙荃想走出家门到日本留学的人生理想:
汝欲东来颇妙……予意汝不若静居乡邑,研求文学为妙。大约予后年夏能回国一次,尔时或能至汝家,与汝同居月余。久别重逢,情当更切。较之日日相见,趣味应更深厚也。汝欲学医,亦颇妙。然予家中既无钱培植汝,汝家亦尚有钟祺、树祺各人。不使男子读书,反使女儿求学,恐汝父亦对汝兄及汝侄不起。
孙荃《戒缠足文》的写作和想到日本学医的愿望,足以证明她曾经有过依靠郁达夫充当精神导师引路人,而在人生路径方面有所超越突破的长远规划。郁达夫并不想在思想进步及人性解放方面与孙荃并肩同行、比翼双飞,而是宁愿她守在家里充当贤妻良母,进而维持一种“天边鸿雁池中鲤”“离人芳草最相思”的诗情画意和婚姻格局。
10月27日,郁达夫病情加重,接到未婚妻孙荃的情书家信才感觉到“稍轻快”。10月28日,他在写给孙荃的情书中信誓旦旦地规划起两个人白头偕老的婚姻生活:“予此后生涯,大约已定。不求富贵,不贸才名。唯欲博得微资,与汝偕老耳。”
10月29日,郁达夫因伤寒病住进名古屋附近的爱知病院,直到12月9日才病愈出院,期间停止了日记写作。
作者: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戏剧及民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