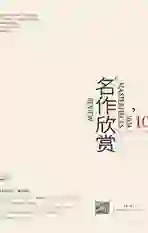三重孤独况味、三种复仇行动
2024-10-12姜异新
殳是一种木质的,无刃有棱,主要用来防身自卫的冷兵器。当鲁迅于1925 年10 月17日在稿纸上写下“魏连殳”这个名字时,身心两方面均陷入病痛的他持续不懈地向着无物之阵举起了投枪。在《孤独者》这篇他自己主动承认是精神自况的小说中,鲁迅说尽了精神界战士“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殳、枪、戟、矛、剑;壕堑站、瞎捣乱、肉薄;“拥有”各种兵器、巧妙采取各种斗争策略的鲁迅,在华盖之年“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于虚构世界营造了三重孤独况味,铺叙了三种复仇行动。
一
从社交层面看,魏连殳并不孤独,无论是作为S 城好管闲事的谈资,还是被寒石山村视为压力的新党,都说明他是被人群关注的对象。因为亲近失意人,客厅里经常有“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臜吵闹的孩子们”,临终前还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发表言论,虽毫无顾忌,仍能常常见诸报端,且一经发表就颇有流量,不但能引发S 城舆论的暗中算计——小报匿名攻击,学界流言四起,更是惹怒校长,以至丢了饭碗,可见影响力非同小可。
甚至,在理想追求方面,魏连殳也并不孤独。他是有所爱的,有真诚对待、为他而痛心的战友,而且为了他而死去——“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愿意他“好好地活下去”的人让连殳感到爱的力量的强大——“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
这样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吗?然而,孤身一人的魏连殳又的确孤独。
首先,身世孤单。连殳父母早亡,将其带大的祖母,虽是唯一的亲人,却也是父亲的继母。不会笑的继母,深味“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并将这独头茧的运命传递给他。父亲死后,本家夺屋子,逼小小年纪的连殳画花押。带着心理阴影成年后的连殳再不娶妻成家,拒绝做任何人的亲人,甚至将死后没有一个人来为他假惺惺地哭作为活着的终极目的。在房东母亲看来,他就是个“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的迂腐的哑子。
其次,百无聊赖。魏连殳在S 城的生存状态是“虽在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不能安住”。他本人学的是动物学,在中学堂却是做历史教员。平日对人爱答不理,成为S城的谈资与局外人、阴影般的存在。虽有很多访客,大部分是来拿他消遣,或者寻些谈资。连殳发表文章后,有人暗暗来“叮”,这在S城虽是向来如此,“并非这一回特别恶”,连殳因之被校长辞退还是令“我”感到突兀。失业后的连殳的客厅立显荒凉,“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屋中间的圆桌蒙着薄薄的灰尘,空空的书架散发着“淡漠的孤寂和悲哀”。书籍只剩了在S城绝没有人会要的洋装书。由此推理,洋装书《沉沦》是不会畅销到S 城的。那么,那些最情愿访问连殳的失意人——“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很可能都来自外城。他们曾“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连殳失业后,他们却再不来此间客厅主动寻觅无意味,就如同冬天不去逛公园以免不舒服。曾经拥打着争抢连殳口琴的孩子们见到连殳也马上悄没声儿地散开,不再吃他的花生米。连殳感受不到一点点赤裸裸的诚,更看不到世界的光明。
最后,自甘孤独。在几乎是求乞似的过了半年后,连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薪水现洋八十元,这是他深夜吐着血写信告诉“我”,即叙事人申飞的。然而,深陷名利场的魏连殳却在热闹声中更加孤独——“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连殳的失意人客厅成了顾问的雅集高斋。
读者在魏连殳给申飞的信中,读到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新——“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读到远远超过出身孤单、百无聊赖之外的心灵死寂,“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冲破亲手将自己裹在里面的独头茧,又是一种怎样新鲜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啊!
追随申飞的视角,读者眼中舆论界的连殳形象完全逆转。S 城的《学理七日报》接续寄到山阳,常有《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诗文。《学理闲谭》栏目还将其先前被传的笑柄反转为“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逸闻”。追蹑申飞的踪迹,读者一起离开山阳回到S城,晚饭后迫不及待地去看望连殳。然而,开篇奔丧的场景再次上演,未料想此次入殓的却是孤独中死去的连殳自己。
大良祖母得以有机会泉流似的涌出世俗闲谈——魏大人“一走红运,就与众不同”,“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人送他仙居术,他自己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就是这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人却早就瘦下去,吐过几回血,也没有看医生,“后来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说不出一句话”。不知是装的,还是痨病导致的。
还没有从耳边回旋着的大良祖母的絮叨声中反应过来,循着申飞的视线,读者蓦地看到连殳被不妥帖的衣冠包裹着,安静地躺在棺材里,“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身世孤单、百无聊赖、自甘孤独,三重孤独况味,交叠氤氲,融为一体,就如同欲雨不雨的天气,凝聚成沉重如铅的灰团,久久不散。
二
咀嚼着上述三重孤独况味的魏连殳,一再地“举着投枪”,撕下旧社会的假面,展开三种复仇行动。
第一,沉默应对,使族人无戏可看。
作为兴学20年来唯一出外游学的学生,魏连殳是老家寒石山村的异类。寒石山村中痢疾流行,连殳的祖母染疾病殁,连殳回乡奔丧。族长、近房及闲人们料定这位“吃洋教”的“承重孙”会争斗,便排成阵势,约定与“新党”对抗,然而沉默的连殳意外地一一顺从老例,使闲人无足观。申飞就是在这次丧葬仪式上第一次见到连殳,目睹了他不掉一滴泪地按规矩为祖母入殓,也目睹了他最后像一匹受伤的狼一样长嚎。连殳让伺候祖母的女工长期住着祖母生前住的破屋,任亲戚本家说到舌敝唇焦,也无济于事。堂兄不惜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带着小儿子辛苦辗转来到S 城找到连殳,要将孩子过继给他,以便继承破屋。连殳远远躲开了这对“不像人”的父子。喜欢孩子而不成家的连殳,带着对血缘宗亲束缚的极度仇恨,刻意一次性生存,花钱如流水,以对抗宗法制礼教成规,让惦记的人没得惦记,无戏可看。
第二,举起投枪,让士绅有戏可看。
与沉默应对不同的是,对于S 城士绅文化界的复仇,魏连殳全力出击,要使他们有戏可看。魏连殳以笔为矛,不断写文章,不断发表对于历史与社会的看法,常有奇警的议论,从与申飞的对话中看得出他因此而经常被“叮”。连殳明知自己被当作话柄利用,仍不放弃写文章,不放弃任何一个能够被启发的读者,即便被匿名攻击也觉得无足怪、无可谈,直至“彻底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威胁到士绅们的利益时,连殳终于失去了谋生的饭碗。最初因失业而失意的申飞常常访问连殳,以排遣郁闷,此次无意中看到旧书摊上摆着连殳的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知他变卖善本,生存定然艰难,遂前去安慰。“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便是失意人的治愈酒食。然而,连殳却不以自己的失业为失意,仍然发些与日见其困难的生活不相干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鲁迅没有正面交代魏连殳写了什么内容的文章,展开了何种观点的社会批评,而是以连殳与申飞喝烧酒发议论的形式带动读者参与思考了幼者本位问题。对于孩子的看法,二人争执不下。连殳觉得孩子全是天真,是中国的希望。申飞则认为孩子中也有坏根苗。为此,连殳三个月没理申飞,不过后来连殳还是主动和解了,因为他在街上看见一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道:杀!……
第三,主动入戏,横站于无物之阵。
除了宗法家族、士绅掌控的文化界,鲁迅最后让魏连殳涉足政界,去做杜师长的顾问,主动投向无物之阵。这样他所遇见的才能都对他一式点头,才可三日两头猜拳行令,才会放弃做一个独异的个人,与世俗同流合污。用魏连殳信中的话说,就是“现在已经‘好’”了。言下之意,不再似从前冷漠病态。
与家族、士绅空间里仅仅是摆出复仇姿态相比,政界空间的复仇行为似已有了具体的阴谋——“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然而,鲁迅什么情节也不涉笔,只留下魏连殳诗一般的语言,大良祖母世俗的闲谈,以至于让连殳的死扑朔迷离,让不明就里的读者不由地联想到自杀,甚至是他杀。
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连殳。但是奇怪!他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大襟上还有血迹,脸上也瘦削得不堪,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几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去试探他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
不仅是直接喊出奇怪!还要让“我”在看连殳最后一面时被两个穿白长衫的当面拦住,“瞪了死鱼似的眼睛,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当大良祖母兴奋地谈论连殳生时的情景,又让一个穿白长衫的人出来,使她住了口。这难道不十分可疑吗?
不过,鲁迅落笔的重心仍然还是无物之阵。譬如,礼教的虚伪,明明是不让看亡人,却要说成是“不敢当”。特别是从堂兄弟那一番山乡中人少有的套话,什么“舍弟”正年富力强、前程无限的时候,竟遽尔“作古”了,这不但是“衰宗”不幸,也太使朋友伤心。礼数之过仿佛是为连殳不该死而道歉了,不禁让人怀疑,从哪里雇来的人上演了这一出“无往而不合于圣道”的好戏!
因为有所爱,有真诚对待、为他而痛心的人,连殳可以躲在独头茧里“咀嚼孤独”的生存状态受到了挑战。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让他想多活几天,然而又让他感到负重——必须有所憎恶,有所反对,有所崇仰,有所主张。当所爱为了他而死去,魏连殳貌似陷入迷茫却终于明确了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所爱,倒是为了所憎。”“偏要为不愿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于是,他主动入戏,横战于无物之阵,同时也卸去了爱的负累,在自戕中感受到精神内在“快活极了,舒服极了”。
肉搏暗夜的魏连殳,直面被吞噬的运命,仍能以“横战”的姿态,冷笑着自己这具可笑的死尸,从而战胜了包括自我在内的无物之阵,成为失败的英雄,成就胜利的复仇。这种行为,在以大良祖母为代表的世俗人眼中,不啻为胡闹,浮而不实,不办一点正经事,不把人的好话当好话听,然而在鲁迅笔下的魏连殳那里,却是彻底撕下旧社会的假面、抉心自食的斗争哲学。
三
在1925年10月17日到11月6日这前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鲁迅接连写了四篇小说——《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这种密集创作的情况在鲁迅并不常见。这一组小说的主题均涉及家庭的分崩离析。其中,《孤独者》《伤逝》相隔四天完成,均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二者均没有在报刊发表,而是初刊于第二部小说集《彷徨》。
《孤独者》里的鲁迅痕迹是所有小说里最重的,从八道湾逐出,争夺房屋,到兄弟动手,喜欢孩子,教书欠薪,挑剔学潮,这些也都是鲁迅的生命经历。文末所署时间为1925年10月25日,由文本叙事中所说的兴学20年倒推上去,正是鲁迅留学日本的1905年。这些信息均可证明《孤独者》的叙事经纬由自传式回溯编织而成。
故事的开头带着浓浓的鲁迅气息,那是鲁迅最熟悉、最能信手拈来的追忆语调和嵌套叙事。整篇共分为五部分,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以狼嚎始,以狼嚎终。第一部分是叙事人申飞的回忆;第二、三部分是“我”回忆框架下魏连殳与申飞的对话;第四部分是魏连殳充满诗意的来信;第五部分是魏连殳的房东大良祖母的闲谈。
虽然小说的题目是《孤独者》,“孤独”一词在文本中却只出现了一次,“无聊”出现三次,“议论”出现四次,出现最多的是“哭”,共有二十次。况且还有不着“哭”字更动人心魄的描写——“兀坐着号咷了半点钟,铁塔似的动也不动。”真正与众不同的词语值得拥有自己的空间,它们的重复像鼓点一样重重地落在读者心上。
《孤独者》中出现的人物众多,幕后比之台前,配角比之主角,戏份丝毫不让。从寒石山到S 城,到山阳,所有的庸众暂且不说,房东家就有四个男女孩子来反衬魏连殳的孤独。另外还有几个不容易在文本中分辨的配角。以笔者管见,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要占寒山村破屋子的堂兄和小儿子并不是后来为魏连殳发丧的从堂兄弟和远房侄子。堂兄与从堂兄、侄子与远房侄子是亲疏完全不同的近亲与远亲之别。实际上,自占屋不成后,魏连殳很可能就与堂兄和侄子断绝了往来。
特别是,十三大人是谁?被敌人诱杀的人又是谁?尽管惦记魏连殳是否有存款的十三大人不必深究,权且可看成家乡某位有势力的见过世面的村绅,类似于《离婚》里知书达礼的七大人,因为普通村民大概还对何为存款无从思议。那么,被敌人诱杀的人难道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虚写吗?“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这句话分明是很具体的所指,有研究者指出“这一个”可能是“我”申飞,也可能是唯一爱连殳的继祖母,然而,魏连殳亲笔写的与申飞“究竟不是一路人”,说明二人交情达不到痛心的程度;继祖母远在穷乡僻壤,不会了解连殳的处境,更不会懂他的精神痛苦,她所有的应该只是牵挂——甚至永远是没有笑容的机械的牵挂,而远非痛心。能够痛心的只有同道知己,甚至更像是恋人。
申飞有两次想问连殳何以单身,当终于问出“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时,连殳先是很诧异地看着“我”,后来便盯着膝踝吸烟,没有回答。魏连殳的来信,释放了那个爱的讯号,“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一句话里隐藏了诸种情节、万千思绪,然而,鲁迅就此不再展开。连微妙的暗示性伏笔的功能都不赋予,仿佛故意让读者忽略过去。然而,等等,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孤独者,忽然深夜访“我”,哪怕找一个二三十元的抄写工作也行,申飞很诧异高傲的连殳会如此迁就。“我……,我还得活几天……”这句话出现了三次,“为什么呢?”“我”无端地这样问,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连殳这样的独头是不会为了谁而活的,恰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魏连殳的信及时到了,提到了为他而痛心的人。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动力何在?几乎是求乞的半年是如何度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具体的事件情节,脑中却更加明晰了鲁迅笔下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残酷而丑陋的动荡期,故事背后深藏着人性的无尽黑暗。
显然,魏连殳、申飞和吕纬甫一样都是生存于辛亥与五四之间的灰色知识分子,但魏连殳又与之有别。同样面对失业、流言与被攻击,在申飞那里只是生计问题,在魏连殳那里却是生死问题。申飞是躲——“极小心,照例连吸烟卷的烟也谨防飞散”,而魏连殳是直面。这就是二人“大概究竟不是一路人”的原因。又或者这是鲁迅的两个自我,一个现实自我,一个内在自我。文本的最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只有将其看成是两个自我,才能理解为何“我”在那样一个凄惨的时刻却能“心地就轻松起来”。那是因为内在自我终于破茧而出,实现了自我救赎,这狼嚎恰似呐喊的回声,这月光的清辉恰似无声的胜利号角。
文体家鲁迅绝非浪得虚名。《孤独者》将独特的文风、高超的叙事技巧和真诚投入的情感巧妙融合,用深刻细致的笔调,融合了讽刺性、摄人心魄的抒情性,营造出孤独的艺术氛围,锻造着经典的“鲁迅式”,是真正“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新文艺。
作者:姜异新,文学博士,研究馆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著有《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启蒙高潮为例》《沙滩红楼:新文化景观》《走读胡适》《读懂鲁迅》《〈呐喊〉导读》《别样的鲁迅》,编著《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合编)、《鲁迅致姚克信札》《胡适论教育》(合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