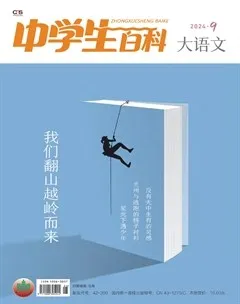我从不企图逃离忧郁
2024-10-12黎荔
无端地觉得,“忧郁”是一个阴性的名词。显然,它所呈现的是一个人格化形象,一个女性的人格化形象。如果忧郁是一个女人,她应该徘徊在水边,在像她一样平静的池水中映照着自己的面容,或是一只手托住下巴,在光影交错的走廊深处,因一种隐秘的痛楚而无言独坐。
这样忧郁的女性化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想到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代表作《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表现女神维纳斯从爱琴海中浮水而出,风神把她送到岸边,春神又从右边急忙迎来,正欲给她披上用星星织成的锦衣。鲜花漫天纷飞飘荡,维纳斯忧郁地站在象征她诞生之源的贝壳上,背后是平静而微有碧波的海面。她的体态显得娇柔无力,对迎接者以及这个世界似乎缺乏热烈的反应。她的表情告诉观者,爱与美的女神来到人间后,对于自己的未来不是满怀信心,而是充满着惆怅。
拉斐尔的代表作《西斯廷圣母》中,也有着同款的表情。在画面上方,帘幕展开,母亲抱着孩子走来。她的衣着有白、红、蓝三种颜色,分别象征着纯洁、爱和真实。她的脸上有一种柔和的凝重,这分明显现着母亲的忧郁和无奈,也昭示了孩子的命运。孩子受到母亲的感染,似乎已经预知了自己肩负的使命,稚嫩的脸上显出深沉的哀伤和忧虑。在母亲身后,弥漫的蓝光构成了深处的背景。
两幅名画中的人物,都不能避免忧郁的袭击。她们脸上无一丝笑容,完全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原来,谁也无法逃避迷惘、忧郁和恐慌,这些情绪都是人生所固有的。每次凝视这两幅画,看见那些命运巨轮下的忧伤和犹疑,我就感到自己的人生逃不出她们的幽幽沉思。忧郁本来是一种触不可及、虚无缥缈的情感,但是在画中,它已经化成了具体的、可感知、可触碰的图像,每每让观看的人坠落其中,如置身于绵绵不绝的秋雨中。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说过:“快乐乃是美的最庸俗的装饰之一,而忧郁则可以说是美的杰出的伴侣,以致我很少考虑(我的大脑是一面魔镜吗?)一种不包含痛苦的美。”是的,我也无法想象,笑逐颜开的维纳斯在浮沫中诞生。那样是缺少深度和内涵的,只有浮现在脸上的忧郁表情,泄露其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在那里,心灵的创伤呈现着繁复的花纹。
也许,艺术人物的忧郁与凡人的忧郁,英雄的忧郁与庸人的忧郁,强健的忧郁与虚弱的忧郁,积极的忧郁与消极的忧郁,都是不同的。现实中的忧郁,大多体弱多病、混乱阴暗,缺乏美感。而艺术中的忧郁,总是沉浸在一种永恒性的幻思中,将我们引向无穷无尽的生命的意味。
生命的意义特别美好,但同时也让人忧郁,而人在面对这一切时更需要宁静的状态。其实艺术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呢?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代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在逻辑上使我们必然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的反映,也是真正的生命欠缺的表达。所以,我从不企图逃离忧郁,我宁愿在写作中不断得以回返,成为离心力的那个深沉的中心。
黎 荔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高培中心主任、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专著《艺术导论新编》《视觉素养导论》《〈红楼梦〉与中国现代文学》《老子新学大全集》《易经的智慧》《道德经注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