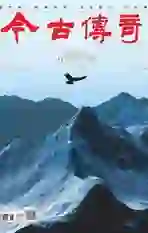一条长满野草的路
2024-10-08席星荃

席星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360余篇。出版散文集《沧桑风景》《记忆与游走》《祖先的村庄》,长篇小说《风马牛》《打呜吼》等。作品入选《1998中国散文精选》《200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等
一
回想起来,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当时是2018年深秋。
我是乘坐38路公交车去的。38路是通往郊区最远的公交线路之一。在民城路下了车,那里已接近终点。在深秋的宁静里,倒回几步,在十字路口拐上向西的关羽路。这民城路和关羽路都是近年修筑的新路,很宽,也很静寂,半天不见人也不见车。这一带原本有许多村庄,近年规划为高新区的拓展区,大力开发建设,村庄都拆迁了,建了一些企业,大部分土地还空着等待开发。兴修的道路倒是宽敞笔直,纵横交错,因为是古战场,命名都与关羽水淹七军之战有关:周仓路,关平路,庞德路……那些拆迁的村庄名字都有传说,比如官田,原本叫关田,是关羽大军驻扎的营盘。官田西边的村庄酒店子,传说是当时为军队提供后勤服务的商贸点。东边有个村子叫“回头”,传说当时关羽每日遛马,从关田出发,到了这里就掉头。南边的村庄鏖战岗目前还在,传说是关羽大战曹军,擒于禁、斩庞德之地。
这一带,近些年我来过几回了。每回来,总有陌生感——迅速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这片乡野(其实称乡野已不恰当,但又显然不是城区)当下最大的特征。
比起三十里外的市内,这里算得上旷野。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视野开阔、空旷高远。当然也滋生人间寂寥。向南望,目光越过层层的村庄,可以望见南山。南山与村庄之间,是站在这里看不见的低下去的汉水。汉水有宽阔的河床,夹杂着乱石沙滩和洲渚,大的洲上有村庄人家。南山是荆山的北边缘,这些山,有的壁立于汉水之滨,有的稍稍远离江岸,形成参差不齐的风景线。站在这里看过去,因为距离的关系,峰峦的脊线并不锐利,倒显得柔和,有点缠绵,平静里带一点儿淡淡的忧伤。越过这些峰峦再往西南深入,山越来越高,直到神农架深处。而往西去,晴朗日子可以望见武当山脉峥嵘的峰头;再往纵深走,是巴山和秦岭。
但只是隔了一条汉水,这里就不一样了,这里是狭长的冲积平原,平原沿着汉水北岸走。平原上是无尽的村庄,人家烟树,重重叠叠,无休无止,显得很平庸。其实呢,我知道,每一个村庄,无论大小,你走进去,都自成风景,各有趣味。鏖战岗村是其中一个。
向北望,情况又不同了,看到的是七八里外的冈岭,就像人们经常形容的——“像一道屏障”,陡然立在冲积平原的边缘,当地人称它为北山。其实它是一道东西横亘的冈阜,据说有一百余里,东到汉水的最大支流唐白河西岸,西到老河口市境内。这样的地理形势,每回到这里来,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词:关河表里。而且,这附近也有一条古道,古道上也走过无数的古代的军队,不是“潼关路”,如同潼关路。
现在是上午8时40分,我独自一人,沿关羽路慢慢往前走。关羽路的前身是不是一条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以前的乡村,这样的旷野上,有稻田、旱地、沟渠、田塍、阡陌、草径,各随天然地势而屈曲伸展、横斜或回环。这关羽路之前,即使有一条路,也只是田间土路,雨天泥泞不堪,天晴路干,可以拉牛车、送粪土、运庄稼;而眼前的关羽路却是这么宽阔这么笔直这么一副城市化的冷漠面孔。
这里是新区边缘,大道两边多半是已经圈占却未动工的荒地。天际线仍然很远,可以感受秋天的辽阔气象。路北依然保留着一大片耕地,种上了越冬作物,但尚未出苗。耕地当中有一片茂密的杨树林,当时我很奇怪它的存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鏖战岗村的坟场。杨树林北边是一座大型现代化厂房,钢架结构,塑料板的墙和屋顶,庞然大物,透着新贵的霸气与傲慢。崭新的围墙立在黄褐色的耕地上,耕地不情愿,不习惯,可耕地无可奈何,只能无声地喘气。
想起第一回寻访这个村庄的情景。
那是2013年12月的一个上午,在邓城大道韩岗站下了公交车,打听得知鏖战岗在西北三里处,于是沿着田野上一条斜斜的土路走去。土路是一条界线,路以北地势较高,微微隆起,然后是村庄。土路以南是低洼的田冲,田冲里一条大沟从西北来,向东南去,沟中可见细弱的枯黄芦苇(后来知道它叫普陀沟,下游汇入大李沟,再汇入汉水)。大沟绕村西而北上,村庄的地势就显得高亢,的确有“岗”的形貌。在村前遇到新开掘的施工沟,工人在沟里填埋粗大到可以直立行走的涵管,他们说这一带规划为工业新区,这是基础建设工程——地下排水系统。村里的老水井在村南洼地,一个汉子挑了一担水回村。跟他聊起来,他也说此地为关羽擒庞德处。到了村前,见一家院子大门敞开,院内坐一老人,戴眼镜,神态安然,遂进门访问。老人姓马,八十七岁,头脑清楚,言语表达清晰。但他毕竟年龄太大,不说是关羽,却说是诸葛亮挖开了上游的五堰二池,淹了庞德大军,乘小船在水上砍杀。老人说本村曾有“擂鼓台”,乃当年诸葛亮(其实是关羽)擂鼓进军之处。我正想说去看看,老人说前几年平掉了,在原址上盖了房,就是某某家院子,现在啥也没有了。老人说,鼓进锣退,是那时对阵打仗的“习惯”(准确地说是军队号令制度)。想起《水经注》云:“建安中关羽围于禁于此城(汉水北岸之平鲁城),会沔水泛溢三丈有余,城陷,禁降。庞德奋剑乘舟,投命于东冈。魏武曰:吾知于禁三十余载,至临危授命,更不如庞德矣。”这里的“东冈”,与鏖战岗的地形地貌相吻合,大沟就是当年关羽挖开上游五堰引洪水下泄的通道之一。
马姓老人还告诉我北边七里的马棚村有庞德墓——这座墓是有的,在马棚村前,小学院子内,数年后我去探访过,但看到的只是一个空场子——古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开挖,变成了庄稼地,小学是以后迁来的。那是一块二亩大小、稍稍低凹的方形平场,它就是庞德墓大冢子遗址,学校也没利用,长满荒草。查《三国演义》,第74回写庞德被俘,宁死不降,“引颈受刑。关公怜而葬之”。
告别老人,走向村西田野。村边有砖桥。桥下就是那条大沟,大沟在低洼的田野里蜿蜒南下。立桥上回望村庄,村庄再次显出了平冈的地貌。环顾四野,想象了一下暴雨成洪,顺着大沟汹涌而下,远近一片汪洋的情景。
时间又流逝了五年,马老人若健在,应该九十二了。
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距离2018年又过去了五年。时间真的很快。
二
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杂七杂八地回想。抬头望望天,深秋的气色是冷艳的。我沿着路南侧行走。
外侧是高高的围栅,内侧是宽阔的大道,围栅内,已被征收的土地荒芜着,暂未开建。围栅与人行道之间有一溜儿窄窄的隙地,不足两米,是预留的花坛,同样荒芜着。一低头,我惊讶了:隙地上竟然有茂盛的野草——原来,这是一条长满野草的路!
就是在这狭窄之地,野草们得到机遇,纷纷然,欣欣然,争先恐后,雀跃登场,共建了一个茂盛的野草乐园。
在围栅拐角处,好几种野草挤成一堆,形成一个繁茂的聚落,那气色,那景况,却像鏖战之后的战场。高高挺起的是一片结籽的藜,叶子落了一半,颜色深红,那是零落的残军的旗,那红是血的凝聚。几棵红杆铁扫帚苗有一人多高,威武得很,它的红更冷更硬,是经过酣战取得大胜之后的得意脸色。旁边的鳢肠却趴在地皮上,叶片萎蔫干枯,黑色的籽粒,当然是卧地献降的败军了。在这幅战场图上,大自然也安排了另外的内容:藜的脚下是几棵萹蓄,也结籽了,但茎叶仍是深青颜色,近似于蓝,有着深海的凝重。在鳢肠的一边,年轻一代的鳢肠又开花了,花小而洁白,是微缩的葵花。还有一丛细小的构树也混进草丛,叶子大半落了,未落的挂在枝上,黄得纯粹又明亮。这深青、洁白和明黄,给这个“战场”补添了复杂的色彩,其中有叹息,也有一抹暖色和微弱的希望。
我知道,战场的说法不过是我个人的感觉和想象。其实这些野草,只是处于各自不同的生命阶段,呈现出相应的生命形态。在冬天的天空下,它们同旷野一样宁静。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有闲心,如果你肯花时间注视它们,你就会听见生命流逝的声响,看见生命的颜色渐次褪去的演变。
一股强烈的久违的感觉冲撞着我的心。
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七八岁以前吧,我成天躺在这样的野草丛中,体验最初的对于人间的感受:原来人世有这么多丰富的、复杂的,只能感觉、不能说清的味道。
心底泛起遥远的往事,那是童年和家乡。就说藜吧,我的家乡并不多见,有一两年婶娘在菜园里种了几棵。初生时,顶端的嫩叶中心有胭脂一样艳丽的红粉;细细一瞅,是晶亮的微小颗粒;拿指头一捻,沙沙的,有说不出的异样感觉。这两株藜一直往上长、往上长,长到比人还高。因为稀少,村里人走过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少,总要一边走一边扭头瞅一瞅,被它的挺拔,还有它叶片的艳丽所吸引,这是一幅画,给朴素的乡村世界描上了一笔不同的颜色,给人间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采,于是,一生务实的种田人心头平添一种平时难得一现的情思。到秋后,藜的茎秆变得粗壮又坚硬,婶娘便用它做了一根拐杖。可是婶娘还年轻,家里没有老人,这拐杖派不上用场。倒是我有时偷偷地拿过来,学着乡村戏台上的佘太君,哈着腰,一点一点往前挪步,暗自快乐里带着一点点羞涩。后来我知道,在乡间,藜老了做拐杖是个古老的习俗;以前的日子里,种藜也相当普遍。
我的家乡也有萹蓄,人们叫它铁鞭草。铁鞭草是一年生草本,细茎如线,分枝紧紧贴在地上。它的特殊之处是喜欢生长在路边,如果是别的野草,早已被鞋底踩光了。而萹蓄却不怕,人踩来踩去,它依然故我,坦然躺在路心,坚韧又顽强,叶片展示着深海一般的蓝光。这独特的深蓝色曾使我深受感动。小学三年级时我曾失学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为了剜野菜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忧伤过早地侵上少年的心头;然而,走在荒凉的土路上,一看见萹蓄深海一般的蓝色,很奇怪的,我的心就平静了,失落和忧郁的痛苦减轻许多。灾荒过后,重新坐进草房教室读书的时候,我变得很用功,再也没逃过学。
那些年,舅舅的菜园里一直有铁扫帚苗。铁扫帚苗细长的叶片类似柳叶,无数的细枝密叶紧紧地抱住主茎,像一支巨大的绿色火炬。那天我去看舅舅,舅舅指点着铁扫帚苗,欢喜地说,你看它抱成一团,一个劲儿地往上蹿,看着就提精神呵!到了冬天,舅舅把铁扫帚苗砍下扎成了扫帚,扫院子里的落叶和门前的雪。有一天我又到舅舅家,舅舅送给我一本旧版的四角号码字典。当时正是特殊年代,十七八岁的我从学校回到家,在生产队下大田,泥一身,水一身,前途迷茫,心里苦闷。这字典是舅舅前天赶集两角钱从旧书摊上买的,舅舅说我读了十几年书,现在也不能丢了,是专为我买的。我忽然有点心酸,想起了舅舅园子里的铁扫帚苗,有了一点信心。在繁重的劳作之间,晨昏雨夕,光线昏暗,我抱着这本字典看个不休,以至翻断了书脊线,我拿母亲的针线重新装订好;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开始近视的。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的心开始沉稳下来,读过私塾的四太爷对别人说我:别看这孩子不言不语,可是有出息。
鳢肠则有一种实在的用处,在田野割草割麦,有谁不小心割破了手,血滴在土上;不要紧,就随手掐一点鳢肠,连茎带叶,揉出一点紫黑的汁水按在伤口,血就止住,不用管它,赶紧接着干活,你忘了伤口,再也想不起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乡下人把自己捆绑在土地上,脚踏泥土,与遍布大地的野草形影不离,相依相伴;每一样野草都与乡下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与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因此可以说,乡下人跟野草、虫子和鸟兽一样,是亲亲儿的兄弟姊妹,都是大自然里万物繁荣、共生互济的因子。
干活干累了的时候,腰酸背疼,浑身疲乏。我们会在草丛躺下,仰面朝天,摊开四肢;闭上眼睛,让太阳晒在脸上。我们闻着草的气味,嗅着草的花香。我们想着自己的辛酸。想一会儿,我们翻身坐起来,掐一朵野花举到眼前,与它久久地对视,默默地在心里说话。我们不快乐,但我们心灵得以平静安宁。
野草是野草吗?对乡下人来说,那时候,野草根本不是“野草”。
但现在,野草就是野草了。现在是2024年7月了。现在,不仅我成了城里的退休人员,日子真的有点悠哉游哉;即使在老家乡下,人们也不愁吃喝不愁穿,连当年做梦也不会梦见的小汽车,也是家家都有的,你说,野草还会是当年的野草吗?
三
那一回离开马姓老人后,我们去看了九冢村的大冢子。九冢村在鏖战岗西南四五里地。这个大冢在小学内,保存完好,高度与教工宿舍楼三楼的窗台持平,满坡密生杂树。这一带原有九座大冢子,当地人传说是某朝代一个公主的坟,为防盗墓,建一座真冢、八座疑冢,故得名“九女冢”。现在只剩下这一座了。但我觉得这个传说有些漏洞。古典小说和文献提到过这些冢子。《三国演义》第76回写关羽围樊城,徐晃前来救援,探马报说:“关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后一十二个寨栅,连络不绝。”徐晃设计赚关平出战,从背后劫了偃城,关平杀条大路,径奔四冢寨来时,早望见寨中火起……书里提到的地名是“四冢”而不是“九冢”。如果说小说家言不足为据,那么《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就相当可靠了: “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徐)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这里也只有“四冢”而没有“九冢”。查《三国志》,所记亦同。
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风霜里,时移事易,当年的古战场虽没有沧海桑田,却也远非原来形貌。比如说吧,当年的“偃城”“围头”已经不见了。当年的“偃城”,据胡三省转引《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安养县是唐代县名,县城即今邓城村,其北三里即现在的官田村一带。至于“围头”,一个推测就是回头村:二者音近,“回头”是“围头”讹音,进而导致误写。“四冢”也没有了,却出现了一个“九冢”。我的推测是,这些大冢子不是一次性垒建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冢子的数量不断增多,四冢、五冢……九冢,地名便随之改变。到大冢结束的时候,一个漫长的社会形态也就终结了。接下来,便是冢子的消亡。
四冢之战是本次蜀魏襄樊之役的转折点,战前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围困曹仁于樊城;四冢之战以后,失襄阳,丢荆州,败走麦城,势失而人亡。而今,烟云散尽。城郭化为村落,地名消失或演变,只有野草年年发年年绿,空留下民间传说。民间传说和野草,是乡村大地上的精魂,没有随风消散。一代代,一辈辈,口口相传——马姓老人在讲述传说的时候,头高高昂起,满面春色,声音响亮,让我看到他青年时代的影子——这些民间传说,是哺育本地人精神情感的母乳吧。
在鏖战岗东三里、韩岗村北野外的树林中,这样的大冢子现在还有一座。大冢像一座小山,满坡是稠密的荆棘杂树,我攀登时,头上不见天日,脚下落叶满地。顶上生大楝树一株,五根树枝像五根巨大手指指向天空,黄橙色的果实在冬阳下格外鲜明。最高的枝上挂着一个大葫芦形的马蜂巢。林间地上有卵形叶的蔓生植物,虽在严冬,茎叶犹青。我认识本地所有的野草,却没见过它。
是古冢就有传说。我进韩岗村去访问,78岁的汪文杰老汉给我讲,古冢坐落的这块地以前就是他家的,四岁那年,有一天他去玩耍,看见冢子边有一只金小鸡,追过去捉,金小鸡却钻进庄稼地里不见了,人们说,这娃子有见财命,没守财命。老汉又讲,村里有户人家,把冢子“东大门”的石碑(一块无字碑)弄回家做了房屋过梁,第二年就出事了:死了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人们都说这是皇姑的惩罚。老汉说,早年间冢子很神奇,村里谁家办红白事,缺桌子板凳之类,就到冢子前祷告,告知神灵所需物品,第二天再去,冢子前就有了所需家什,搬回去使用毕,再还回冢子。有这么回事吗?我不太相信,不妨姑妄听之吧。
我朝东南方向望了望,隐约里,看见韩岗村北有一点苍绿在天际微微突起,那就是那片古冢所在的树林。
四
现在,眼前是野黄豆的天下。这是耐寒的植物,虽是晚秋,依旧一派苍绿,稠密的藤叶一直爬到围栅顶上,使围栏变成一面绿叶纷披的墙,密叶间紫花点点,栅顶托不住繁花密叶,又一窝蜂地垂下来,却不甘心,茎梢又翘起高高的头,要在虚空中探寻一条上天的路。
这种野黄豆,少年时期我在家乡只发现过一棵,长在村中偏僻的长渠边,它很瘦弱,掩藏在草丛中,并不起眼。我到今天也不明白那棵野黄豆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村里村外、山冈野外从来没发现过它,我认定它是天外飞来的珍物。物以稀为贵,那一整年,从春到秋,每天我都去看它,悄悄地,不敢声张,怕别人发现了,拔了它,割了它,特别怕顽皮的孩子发现。好歹到了秋天,野黄豆结了细瘦的荚,我剥开豆粒,小心地保存起来,想在明年春天播种。可是,后来竟忘记了,等想起来时已经过了播种季节。跑到长渠边,好啊,原地又生出了一棵苗!我长吁一口气。这棵野黄豆在长渠边默默地生长了几年,后来又神秘地消失了,从此永不再见。我早就发现,在我们这个平畈上的偏远村庄里,有很多不知来历的植物,比如两棵野葡萄,比如一种冬天不凋的攀缘植物,比如一丛野枸杞……我知道它们自洪荒时代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亿万年没有断绝;它们比村庄更古老,比村里人的生命旅程更长。这棵野黄豆也是这样,它来自远古,现在又回到它之所来的时光深处。而人短暂的一生又算得了什么?那棵野黄豆,它的出现使我欢欣,它的消失又使我惆怅。通过一棵植物,人类看到了深远而神秘的世界,并因而知道了自身的微渺,减少了狂想和妄念,向谦卑靠近。
继续往前,这回爬上围栅招摇的变成了葎草,跟野黄豆各领风骚一段。它们葳蕤的绿看起来生机充盈,而我却从中隐隐听见凄凉的调子。长鬃蓼也一样,上一辈的长鬃蓼进入生命末期,叶子蜷曲、颜色焦黄,而下一代仍在开花,花穗像一条条半大的蚕,细巧而嫣红;但是,在深秋的土地上,在净而碧蓝的天空下,在无风自凉的气息里,花朵的红并不热烈,相反,它闪射出的是冷艳的光,向人,向这个世界,做出暗示。这暗示看起来是微暖的,而骨子里是悲凉的。
先后发现了两堆马泡瓜,早已枯萎的藤和叶已经半腐烂了。狗尾巴草的穗子轻飘飘的,只剩下绒毛,籽粒已不知去向。青葙被谁割下,扔了一堆,已经干枯;一边,几株年轻的青葙鲜花盛开,花朵像一枝枝蘸了红颜料的羊毫笔,打算书写什么浪漫的构思;但那红我总觉得是残红。一株龙葵正在盛年,枝叶和花朵都让人想起初夏;另一株已结了紫黑的果子,一串一串的,极像成熟的山葡萄。果实像山葡萄的还有绞股蓝,它将果实挂在围栅上,想炫耀,想让鸟雀们看见,这是它期望的最好的归宿,是它一生的完美。紫菀是彻底枯了,一片褐色,与小飞蓬一起做了迎接冬天的使者。野香草有两种,有一丛矮脚的完全老了,叶片卷起,显出美丽异常的胭脂红。我长时间地盯住这一抹红晕,目不转睛,它在眼前渐渐幻化成奇妙的深邃……
季节表达它的情绪。植物是季节的旗帜。人类通过野草看见季节,进而看见生命的消长与轮回。
一路走过,又看过了败酱草、鸡肠草、驴蹄菜、野西瓜苗……
五
到了关羽路尽头,尽头抵着南北流向的普陀沟。这条古老的沟近年修整过,取直了,挖深了,也拓宽了,很有点气派,却看不出原始的模样。有一座水泥桥横跨沟上,东岸的堤也就成了路,泥土路面被电动车、摩托车和鞋底碾得光滑平坦。
几年前我从这里走过一回,方向相反,是从普陀沟的堤上下来,由西往东走。那时候关羽路正在修筑路基,西端还留着一段黄泥路,矮棚里住着工地看守人,堤下的隙地上有水坑和野蒿丛生的砂石堆。看守人养的一群肥鹅嘎嘎叫着出来,也不怕人,在我脚前拥挤着向水坑走去。鹅群过去,我看见了南边的鏖战岗村。
老沟应该还有残留,现在我想看看它。近些年,我已经知道有关普陀沟及其上游的情况,乾隆《襄阳府志》载:“临川坡下有五堰,汉末(于)禁屯兵于罾口川,关壮缪(羽)决五堰以灌之,遂获(于)禁。今五堰俱存,为县西北水利要区。”所谓“五堰”,乃是北山峡口的五座古代水利工程,分别叫黑龙堰、白龙堰、青龙堰、红龙堰和普陀堰,都是关羽当年挖堤放水淹没曹军的水源地。普陀堰就在普陀沟的上游,距此五里地。我站在堤上观察了一番,发现东边百米之外田野上有一道杂树丛和芦苇形成的风景线,凭经验,我估计那底下应该是老沟了。我下了堤,横穿过抛荒的去年的芝麻茬子地,果然在树丛下看到一截老旧的沟,浅而窄,半干涸了,上下游已经不通,成了一条死沟。沟底长了一层鸡肠草,岸边有几丛细瘦的芦苇,风已经摘掉了它们头上旧棉絮似的绒毛。谁在沟里种了藕,枯荷缩着头。我沿东岸向北走,又看见了野草,野草沿着沟边变换品种,各占一段沟沿,形成聚落。有开花的紫菀,有鬼针草、马尾蒿、野香草,都老了,瑟缩或者苍凉。在这里,它们有着漫长的生命史,轮回着生命,也静观着人世的沧桑演变。它们是当年鏖战的目击者,它们是相关传说的证明人。
这些年,我无数回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无论走到哪里,随便找一个老汉闲聊,都会听到当地传说,有些故事让人不无惊悚。从这里往西北去十里是白龙堰。白龙堰下有一个堰口村,为纪念关羽在此掘堰放水,在西山上建了一座关公庙。于是,传说来了:有一年夏天,天上阴雨连绵,地上洪水泛滥,某夜,狂风大作,村中老人江伯半夜起来修补茅草屋顶,突然间看到一条白练从堰中卷起,携带着滔滔洪水冲向下游村庄,眼看洪水就要淹没下游人家,忽然从关公庙中飞起一道青光直追白练而去,电光一闪,劈在白练的头上,滚滚乌云应声消散,风息雨止,星光闪耀,洪水渐渐退去。第二天,人们发现庙里关公手持的青龙偃月刀不见了,原来那道青光就是关羽的大刀,那道白练就是兴风作浪的白龙。一时间,庙内香火极盛,每到三月三、九月九,方圆十里的百姓都来焚香祭祀。
这些传说塑造了另一个乡土世界,包括人的情感和精神。
现在是农历九月,如果关公庙还在,正是百姓举行祭祀的日子。
我走得很慢。现在,沟沿的野草换成了野胡萝卜——蛇床子,上一代只剩下干焦的秆立着,脚下的新生代却水灵灵的,撑开一片雪白的小伞。接下来看到了更多的两代共生:刺苋、野香草、扛板归……一边是衰败和死亡,一边是新生和成长。季节有点混沌,有点错乱,让人迷惑,疑虑,恍惚于人间的行走。
六
三年多之后,2022年2月15日下午,我旧地重游,仍旧在关羽路下车,仍旧沿三年前的路向西走。但是我却认不出眼前景了,站在路口发愣。以前路北的耕地和那片树林不见了,被栅栏围成一个厂区,耸起一座五层大楼,公司叫宇昂,栅栏和大门很气派。路南的荒地不见了,围栅里是一个企业,从东边的民城路开了大门,挂着两块牌子,一个是混凝土公司,一个是环保科技公司。
我仍然沿关羽路南侧走,想看看围栅下当初的野草。栅栏下的隙地已成正规的绿化带,栽了景观树和冬青。地面经过打理,野草不见了。一切都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那么平整干净。偶尔,会有一茎野草的孑遗,细弱得可怜,不仔细发现不了;我认出了其中一棵蛇床子,以及零星的小蓬蒿。一墙之隔,便是混凝土公司的车间,机器轰响。靠近公司北大门,有一段隙地还保留着,稀稀拉拉的越冬的野草趴在地上,叶子上盖着一层白垩灰尘,气息奄奄,它们在焦灼地等待,等待一场雨雪。
我也替它们焦灼起来。
三年前那条长满野草的路我是再也见不到了。还有传说和传承传说的人。
演变实在太快,崛起,消失;出现,离开;聚合,流散……
那位马姓老人的形象再次浮到眼前来,一位乡村老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笔直地坐在阳光下的矮木椅上,慢条斯理地说话……这是一介“草民”:终生与庄稼和野草为伴,也像野草一样贫贱的人。乡村这样的老人很多,对这样的“草民”我一直心生敬意。这样的人有一种特别的民间的禀性和人格。那个鏖战岗村已经不存在了。我也知道,拆迁的人家满怀喜悦,他们得到了丰厚的赔付,很多人成了富人,住上高楼,过上新的生活了。可是我也听说,许多上年纪的人,每天从高楼上下来,到沟边渠畔,找一些被遗忘的边角去开荒。更有甚者,在野草丛中搭了窝棚,重新过上野处的日子。
(责任编辑 王仙芳 3495728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