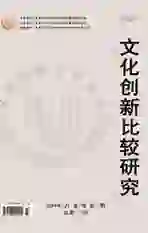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和治理遵循的三个基点
2024-09-30关盈盈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抓手。然而,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和治理过程中存在同质化、主体缺失、不均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和治理过程中偏离了对历史的遵循、背离了对人民性的坚守、逃离了对独特性的坚持。因此,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和治理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中汲取历史智慧,厚植治理经验;要坚持人民至上,发挥人民力量,坚守人民立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科学把握不同城乡的禀赋特色,以“差异性”彰显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地域特色。
关键词:城乡;人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治理;基点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b)-0159-05
Three Basic Points to Follow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GUAN Yingying
(Shandong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Socialist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ulture orien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more emphasis on the humanistic logic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To strengthen the people's cultural confidence is to firmly follow the socialist path and develop Chinese culture. The people are the main body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nd the promotion of people's cultural confiden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draw historical wisdom fro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s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and cultivate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put the people first, play to the people power, stick to the people's position,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highlight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with "difference".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areas; People; Public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Basis points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对物质文化需要转向对美好生活需要,这说明人民对物质文化有了更高阶的要求,不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文化强国建设归根到底是通过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使人民获得生活的幸福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不仅要注重文化设施建设等有形文化的提升,更要注重无形文化对人民精神生活的满足。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无可置疑担负着无形文化的塑造和传承功能。
1 汲取历史智慧,厚植治理经验
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为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所形成的空间框架。纵览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治理历程可以看出,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治理不是毁灭式地推倒重来,而是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时代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中应当充分利用历史资源,发挥人民历史主动性,洞察治理的历史规律。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宝贵资源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必须以此为基础。
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主体是人,只有在充分了解中国人的基础上进行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才具精准性。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对中国人的研究需立足于传统文化。中国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最早是农耕型文化,靠种植业为生,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人在一个小块土地上就地生产、就地消费,自给自足。农耕文化留下很多印记,比如中国人注重安土重迁、避险求稳。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伦性决定了中国人特别注重人际关系、人的道德修养、伦理纲常,这种文化留下很多印记,比如宗法性、群体性、人文性、道德性等。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固有的“文化磁场”,不仅是农耕文化的物质载体,还是中国人性格的体现,更是当地人民的集体记忆。祠堂是传统村落典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是传统文化中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的乡土文化是藏在居民心底的乡愁。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村落发展逐步趋同,传统村落面临空间破败、环境失调、文脉断裂等诸多问题。城乡因具有历史而厚重,城乡本身就是历史遗迹,承载着居民共同的情感。新时代进行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要坚定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沉淀,要挖掘与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之间的契合点,打牢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根基。居民长期生活在某一城乡空间中,经过长期的集体创造、加工、筛选和沉淀形成当地民俗,而相同或相近的风俗习惯、村规民约、道德规范、价值理念可以将同一地域人民紧密凝结在一起产生共同体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乡村文化才使居民具有向心力和归属感,有的甚至哪怕历经时间的流逝仍积淀为居民的共同记忆。城乡公共空间为城乡活动提供场地,使城乡地域文化得以保存、传承。王安石说:“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2]城乡公共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很多,在人生的历程中,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重要的礼仪,从出生时的诞生礼、成年时举行的成年礼、建立配偶关系举行的婚礼,到死亡后举行的葬礼。此外,还有民俗歌舞、民俗体育活动等这些民俗文化活动时时刻刻影响着居民,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居民的精神世界。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手机、网络的普及使多7f1372031e191e1feddce8c06b313bc22ef6e6f2b12677e13bf1956f01d5df6f元文化严重冲击公共文化生活。传统乡村的村规民约、礼治很难发挥调节乡邻关系的作用,而现代伦理观念在居民思想中又根植尚浅,不足以对居民的为人处事、言谈举止产生足够的约束力。城乡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过去”其实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原本的面目,记忆不仅重构“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3]。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要注重对居民城乡记忆的唤醒,比如,在传统节日中举办传统公共文化活动,正月十五的舞龙灯、端午节的赛龙舟等,唤醒居民对古老民俗的回忆,在潜移默化中燃起心底的乡土情感,激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霍布斯鲍姆说:“基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是国家开展行动的价值基础。”[4]因此,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需要立足于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1.2 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是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重要法宝
马克思认为空间不应成为个人追逐自身私利的工具,需要回归到人本身注重人文逻辑对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以列斐伏尔、哈维、索亚、卡斯特等为代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将空间与资本逻辑、政治权力、历史文化及情感等联系起来,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审视城市发展的空间生产研究视角。
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强调平等性,当前我国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农村大量居民搬到城市居住,农村缺少公共文化空间主体日渐衰败。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政策倾斜于环境好、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大的地域,忽视偏远、资源稀少、人口流失严重的乡村,造成城市成为中心区域,而乡村沦为边缘地带的非正义空间。我国公民是不存在区域界限的,这就要求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中要遵循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平等性原则,构建一个平等正义的公共文化空间,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2 坚持人民至上,站稳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立场
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体系中,人民无疑是高频词汇和核心概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5]新时代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依靠力量、坚守立场等方面要体现人民性本质。
2.1 发挥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人民力量
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是一项政府为主导,群众参与为辅的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群众参与意识不强、满意度有待提升[6],造成治理过程中主体缺失。实际上,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中,人民群众既是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的指向,也是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新时代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的动力源泉。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有利于加强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的资料都应该被合理利用。发挥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人民力量意味着人民不仅作为既成公共文化空间的享用者,而且还参与公共文化空间生产和再分配的实践,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者。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性必然要求民主性,即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各项过程居民应拥有表达利益要求和参与决策的渠道。若仅依靠政府或资本力量治理,公共文化空间难以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造成空间效用低资源浪费、民众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地位边缘化等问题。普通民众能否参与和是否参与是衡量公共文化空间现代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时,要广泛听取居民的意见,尊重居民的意愿,甚至将构建与治理权力下移到居民手中。
2.2 坚守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人民立场
吸取西方资本逻辑操控下城乡公共文化空间衰落教训,我国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中应注重“以人为本”。满足人对公共空间环境的需求成为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公众环境需求的深入研究,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提高环境质量和人们活动的质量,城市自然具备了温度和气质[7]。当前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的基层需求得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定期进行文化需求采集工作,保证供给在“最后一公里”精准对接。城市文化设施要根据不同层次人群对文化设施的需求不同进行设置,不能把高端的文化设施设置在人烟稀少的郊区,导致文化设施使用效率较低。创新文化活动形式,丰富文化活动内容,开展文化活动前充分做好实地调研,活动形式、主要参与渠道等按照城乡群众喜欢的方式进行策划、组织,使其与民众的需要相契合。
新时代,我国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要发挥主动性,紧跟时代步调。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已成为过去,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提升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的根本基点。简言之,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与治理就应该回应什么。
2.3 坚持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普及性
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所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8]。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必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在城乡治理过程中必须破除城乡二元对立壁垒,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虽然我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们对乡土产生了情感的背离,对乡土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9]。为此,必须加快城镇化建设,构建城乡共同体。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是构建城乡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公共性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本质特性,每个城乡居民都可以自由进入文化空间,这就要求建立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城乡居民共建共享共治的空间,强调空间的普及性。
在城镇化加速时期,乡村既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城市冲击,部分地区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断被弱化甚至丧失[10]。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中存在发展不均衡、文化要素分配分散的问题,难以保障公共文化空间的普及性。例如,许多地方实行“亮点村”的建设,其目标是“以点带面”实现公共服务的平衡发展,但实际很容易陷入政绩工程的泥潭。究其原因是资源分配不均衡难以发挥“以点带面”作用,“亮点村”自身资源禀赋好,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加持下更多优惠政策和资源向其倾斜,这些都是非亮点村无法比拟的,反而加剧了亮点村和非亮点村的村际差距。
保障资源的供给和配置的公平性是实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普及性的重要抓手。在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达到空间的普及性,需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要满足主体的需求性,在资源的初次分配和供给中注重农村特别是保障资源稀缺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配置,通过再分配引导城市优质的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建设。其次,参与文化空间的主体可划分成不同阶层、不同层次,人民的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需要发挥政府保障作用,保障每位居民平等、自由地享受公共空间的权利。最后,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及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利用科学技术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率、共享水平,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3 以“差异性”为目标,彰显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地域特色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特色化、差异化是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的必然。由于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长期由政府主导,催生了同质化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难以与人民文化需求精准对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的基层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精神需求动态发展向多样化、个性化迈进,因此,城乡迫切需要构建起差异化公共文化空间适应居民精神需求。构建和治理城乡公共文化差异化空间,一方面要对既有的公共文化空间的辩证传承,另一方面要重视从现有地域特色风貌中提取具有历史价值的素材与空间,留住街头巷角的文化基因。这就要求在进行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时不能将其他国家或其他区域的治理方式拿来就用,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身地域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构建和治理方案,以凸显城市的独特精神文化,塑造城市的独特魅力。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城市间的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和治理经验相互借鉴,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治理中的许多经验复制到乡村,使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中地域文化表达特征慢慢减弱或出现同质化现象,无法体现出城市独特的文化形象与特点。因此,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和治理时,要结合当地独特的文化底蕴,打造一个能让进入公共文化空间的城乡居民感到身心放松、心旷神怡,并且具有文化归属感、地方特色与审美格调的空间。
科学把握不同城乡的禀赋特色,要立足传统紧跟时代充分挖掘、开发、放大特色和有利因素。一是立足于时代发展,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原有的文化空间场域进行修缮保护。比如,利用虚拟技术把城乡居民集体记忆中的祠堂、宗庙、凉亭制作成虚拟化立体空间,通过现代媒体广泛宣传家乡文化,让人们跨越时间、空间的阻隔感受家乡文化的无穷魅力唤醒内心深处的乡愁。二是对于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治理,既要立足于过去又要紧跟时代特色,可以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中嵌入地方文化元素。比如,在新建的文化广场、文化大院可以摆放以前生活中能凸显当地文化特质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可以播放以前居民集体生活、劳动场景片段。建设文化活动中心,这些文化活动中心可以开展民俗表演,居民可以亲身体验,增强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日常生活的互动与情感交流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
4 结束语
总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须加强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治理。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治理既要汲取历史智慧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又要“以民为本”区别于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公共空间管理经验,更要立足于地域差异构建独具特色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1).
[2] 葛荃.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3]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6] 王家合,杨硕,杨德燕,等.县域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空间差异: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1,41(1):165-172.
[7] 余丽蓉.城市转型更新背景下的城市文化空间创新策略探究:基于场景理论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9(11):56-62.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吕宾,袁兰.乡村社会语境下乡村文化价值认同的困境与对策[J].宁夏党校学报,2021,23(3):98-105.
[10]陈波,耿达.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来自27 省(市、区)147 个行政村的调查[J].中国软科学,2014(7):7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