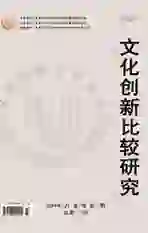文化制衡视域下的明清湘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2024-09-30黄建胜
摘要:“文化制衡”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是一个“偏离”与“回归”交替出现,不断再适应的推进过程,任何一个民族绝不会只对某一两个民族保持密切关系,而是同时要与众多民族发生不同程度的依存制约关系。该文运用文化制衡理论对明清两朝苗疆边墙的修筑历史予以解读,阐述了湘西苗疆各民族之间冲突、调适、耦合的过程。苗疆边墙的修筑,虽然达到了“民”“苗”分而治之的目的,但并未物理隔绝“墙内”“墙外”的社会联系。各民族以墙为“介”,打破了族群壁垒,重构了苗疆社会秩序,最终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局面,成为中国民族地区民族和睦的典范。
关键词:文化制衡;苗疆边墙;明代;清代;湘西;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b)-0056-05
A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Xiangx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straint and Balance
—Based on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iao Border Wall
HUANG Jiansheng1,2
(1.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straint and balances" holds that the existence of human society must be a process of alternating "deviation" and "return" and continuous adaptation. No nation will never maintain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one or two ethnic groups, but must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pendence with many ethnic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straint and balance to interpret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the Miao border wall, and elaborates on the process of conflict, adjustment,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Xiangxi.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iangxi Miao border wall, although achieving the goal of dividing and governing the people and Miao, did not physically isolate the social connection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wall.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ve used walls as a medium to break down ethnic barriers, reconstruct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Miao area, and ultimately achieve a situation of ethnic integration where "I'm in you, you're in me", becoming a model of ethnic harmony in Chinese ethnic areas.
Key words: Cultural restraint and balance; The Miao border wall;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Xiangxi; Associ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20世纪最早关注苗疆边墙的是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等民族学前辈于1930年在湘西开展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苗疆边墙的史料整理、学术专著、期刊论文等陆续出现。进入21世纪,苗疆边墙研究步入新阶段,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吉首大学主编的“苗疆凤凰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对湘西苗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罗康隆教授提出的“文化制衡”理论对今天研究苗疆边墙与国家治理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文化制衡论”认为,文化的稳态延续绝对不是按简单平衡的方式去实现的,而是一种制衡过程,“并存文化间的交互依存制约导致了人类文化总体系的平稳和延续”[1]。本文从文化制衡的角度对苗疆边墙的修筑历史过程及明清以来湘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以阐述。
1 文化冲突:“逃避统治”的湘西苗疆社会
元代以前,历代王朝在湘西地区的治理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间接统治和军事上的征剿行动。秦汉实现了全国性的大一统,设立郡县,秦在武陵山区设置黔中郡,汉改置武陵郡。三国时期,湘西境分属吴武陵郡和天门郡。南朝宋时,湘西分属荆州天门太守和郢州武陵太守。隋代,湘西分属沅陵郡和澧阳郡。唐代设置羁縻州县,在武陵山区置黔州道,后又置辰、巫、溪、锦、业五州团练守捉观察使和黔州经略招讨观察使。五代时期,湖南属楚,湘西州境分属辰、澧、溪三州。宋代沿用唐代的羁縻州制度,治理程度在唐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代设立土司制度,湘西地区的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是这一区域最高的行政建制。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三州安抚司被分置,永顺州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保靖州和南渭州则分别建制,并入湖广行省的新添葛蛮安抚司。安抚司统辖各蛮夷官,蛮夷官统辖各“溪洞”,形成了由“安抚司—蛮夷土官—溪洞寨首”的管理体系。明代土司制度在元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洪武元年(1368年),诏升保靖安抚司为保靖宣慰司。洪武五年(1372年),置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皆隶湖广都指挥使司。同时,为了控制土司,也经常派流官进入土司辖区,即所谓“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多流官”[2],经历、都事、吏目等一般为流官担任。而在“既无流官管束,又无土司制理”的“生苗”区则拥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合款”,这种组织实际上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农村公社组织。明代基本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度,全国范围内都设有卫所,明代湘西地区的卫所分布于各交通和战略要地,构成了严密的防守布局,与土司一道,成为明廷管控湘西的基本力量。
元明土司制度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以土司控制苗疆,以卫所控制土司,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控制链条,以保证土司的恭顺和苗疆的稳定。事实上,土司确实发挥了防御、控制苗疆的作用,如嘉靖十九年(1540年)五寨司苗民侯答保等起兵反明,永顺、保靖土司镇压之。凌纯声、芮逸夫先生认为:“湘西苗患,始于明代,然因对苗地使用封锁政策,故终明世二百七十年,未酿成大患。”[3]整体来看,明代对湘西苗疆的统治主要表现为封锁。苗族地区有苗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谚语,并认为“乙卯”为“苗变”之期。恰好咸同起义始于咸丰五年(1855年),距离雍乾起义(1735年)120周年、乾嘉起义(1795年)60周年,且都恰逢乙卯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当然,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也说明苗族地区所固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必然会激化。这是导致苗族人民周期性不断起义的根本原因[4]。有学者统计,从明洪武年间至乾嘉时期,仅在湘西苗疆地域内发生的苗民起义多达25次,成为当时明清疆域内冲突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5]。
毋庸讳言,历代中央王朝对苗疆地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以军事行动为主,“逃避统治”的苗疆人民居住在深山之中,基本上游离于王朝正统之外。他们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然而却屡屡成为中央王朝军事征剿之地,央地冲突、民苗冲突不断。苗疆地区统治方式历经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卫所制度,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改变对湘西苗疆社会族群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
2 文化调适:苗疆边墙的“界”与“介”
明代中后期,随着汉人的移民垦殖,苗民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反抗持续不断,苗疆多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彼时卫所制度衰落,朝廷不能有效地进行平叛,于是修筑了相对分离的哨堡,而后将哨堡连接起来成为边墙,试图利用这些堡哨建筑对以腊尔山“生苗”为主要对象的苗区构成军事封锁线,以此成为区隔苗民的特殊“界限”。后来明廷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边墙的数次修建。明代边墙以万历、天启间的修筑规模最大,是明代边墙的主体。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辰州知府刘应中曾奉命勘察明代边墙,在当地一位苗民家中得到其家藏《传边录》一帙,其中有关于明代边墙始末的记录。
清前期,朝廷内部曾有过两次重修明代“边墙”之议,但均无果而终,重修边墙自此又搁置了近百年。第一次即前述刘应中勘察明代边墙,发现边墙旧址“俱已残塌,所存废堵,百不一二”,刘应中对边墙修筑持否定态度。清廷根据刘应中的建议,暂时没有动工修建边墙。第二次是开辟苗疆设厅置县之后,根据记载,设置凤凰厅、乾州厅后,依然不断出现苗民反抗事件,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镇竿苗叛”,次年,镇竿苗民武装首领吴老吉等攻陷凤凰县德胜营(今吉信镇),被偏沅巡抚赵申乔率官兵剿灭[6]。鉴于苗民反复对抗清廷的形势,修复边墙以作为军事屏障的议题被再次提及。康熙五十年(1711年),湖广总督鄂海奏请依明代边墙旧址修筑镇筸边墙,随后康熙帝指示鄂海实地勘察,当鄂海一行所到之处呈现出一派苗民归附,成为输赋供役的“编民”情景之时,认为不必重筑边墙,在上奏清廷奏疏中强调了苗民的恭顺,这正和康熙帝“内外天下一体”的理念,于是要求湘西地方安抚苗民,不必修筑边墙[7]。
“改土归流”后,大量的移民进入湘西地区,促进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激化了苗汉矛盾。乾嘉苗民起义让清廷认识到有必要调整苗疆治理政策,厘清民、苗界址,解决土地纠纷,缓和苗汉矛盾,于是重修边墙再次提上日程。清代苗疆边墙于嘉庆五年(1800年)由傅鼐主持修筑完成,边墙全长110余里,是依明代边墙遗址修筑的“濠墙”,主要为石墙。“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扰。其险隘处增设屯堡,联以碉卡。”[8]即起于今吉首市乾州木林坪社区,止于今凤凰县沱江镇长坪村,并在凤凰、乾州(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县)、古丈坪(今古丈县)、保靖五厅县设筑碉卡、汛堡、哨台、炮台、关厢、关门等,边墙与碉卡汛堡等防卫设施共同组成了清代苗疆边墙防御体系。傅鼐所修筑的边墙,虽是为“防”而建,但事实上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已经不明显了,更多是作为厘清民、苗界址而存在。
明清两朝分别修筑了边墙,用以进行“民苗区隔”,然而,作为“界”的边墙,也成为调适湘西苗疆民、苗关系的“介”,重构了苗疆社会秩序。一方面,苗疆边墙成为空间上的界限,将湘西苗疆分为“墙内”的苗民社会和“墙外”的汉民社会两部分,并因大量人口聚集形成许多聚落,由此造就了独特的“边墙社会”。另一方面,苗疆边墙在厘清民、苗界址,调和苗、汉矛盾,基本达成“兵民一体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9]目的的同时,并没有物理隔绝“墙内”“墙外”苗汉区域社会联系,而在事实上却成为连接边墙内外的“中介”。苗汉人民以边墙为载体,兴起边墙贸易,边墙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盛,使得苗疆边墙成为苗汉交往交流的“中介点”,对清后期的苗疆族群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文化耦合:湘西苗疆族际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是湘西苗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完成了“改土归流”,从行政上将湘西地区完整纳入到国家的直接统治;另一方面,边墙的重筑成为解决苗疆问题的重要措施,基本实现了民、苗相安。清廷对“归流”的原苗疆地区采取派流官、劝农垦、兴水利、通道路、办学校、开科举等措施,使“新辟苗疆”与“改土”之地能够同步发展[10]。随着各种政策的实施,各民族之间加强了交往交流,以墙为“介”,打破了族群壁垒,逐步实现湘西地区各民族交融的局面。
其一,湘西苗疆基层组织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延续里甲制度。明代开始就在湘西苗疆尝试推行了里甲制度,据《凤凰厅志》记载:“厅属民里有五,即昔五寨土司所辖五峒地。”由此可见,当时的五里其实就是五峒,说明当地在里的基层组织管理中沿用了峒寨制度。清廷开辟苗疆之后,在设立府厅县等行政机构的同时,在基层社会中推行保甲制度,利用保长、甲长、寨头控制基层社会[11]。二是推行乡约组织。改土归流后,清廷在湘西苗疆大力推广乡约组织,如雍正六年(1728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在《条奏川省苗疆善后事宜》中就提道:“近卫者归卫管辖,近营者归营管辖,并择番苗之老成殷实者,立为乡约保长,令其约束。”[12]三是设置屯政与苗弁制度。明代军屯制度到清代也一直沿用,湘西苗疆地区在乾嘉苗民起义平息后推行了修边、练兵、屯田、办学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在“改土归”流后设置的百户寨长制度实施过程中,总结出现弊端的经验,并顺应历史和时代的需要设立了苗弁制度。清廷通过选拔苗寨中具有一定威信之人,借以处理苗民与朝廷之间的关系,维护苗寨稳定。
其二,湘西苗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改土归流”后,在流官政府的倡导和移民群体的影响下,湘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由原始粗放型逐渐演变为精耕细作型。流官政府出于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招徕外地移民进行垦荒,“凡逾期不开垦者,原荒地即按无主荒地处理,召农来垦。如原主持据阻拦,即按律处置”,“如有开垦百亩以上者,加重奖赏”[13]。为了吸纳移民开垦,给予方便和优惠政策,如配给牛种、分配房屋、银钱资助等。另一方面,选派一些内地有经验的农民帮助开垦,并将先进耕作技术推广到民族地区,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跟随移民进入苗疆地区[14]。并且,玉米、马铃薯、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引种促进了武陵山区农业经济发展。由于更多的汉人移民的进入及商贸水陆交通的逐步打通和改善,行商坐贾携带大量商品货物涌入,也给湘西苗疆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契机。以前“舟车不通,商贾罕至”的苗区,转变为“商贾络绎不绝”的地区。乾嘉苗民起义后,清代统治者开始“清厘”苗民界址,以边墙明确分苗、民土地于内外。而边地贸易即在边墙内外兴起,出现了一幅民苗互市的生动景象:苗民入市与民交易,驱牛马负土物,……以趋集场”“届期必至,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初犹质直,今则操权衡,较锱铢,甚于编氓矣。”
其三,湘西苗疆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偏沅巡抚赵申乔上疏言“苗民子弟宜设立义学教育”[15],建议在苗疆地区设立学校。雍正十年(1732年),地方官府在永顺的灵溪、勺哈、老司城三地各设义学一所,而后又分别在桑植、保靖、龙山等地相继设立12所义学。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及泸溪、麻阳、保靖等县各设书院一所,各屯分设义学五十馆,再于适中寨落增设五十馆[16]。傅鼐认为,要使苗疆长治久安,“惟有移其习俗”“格其心思”,而这必须“申之以教”,于是专门设立了苗义学馆70所。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政府资助盘费,设置奖励,且优待苗族生童。对苗民科举考生采取优惠政策,规定凤乾永保四厅县士子、苗生参加乡试,不与汉民竞争,而是另编字号,单设举人名额。伴随科举制度的需求,内地一些文人也进入湘西地区,并在当地开设学馆私塾,以执教为业,湘西苗疆逐渐形成了以私塾、义学、书院组成的教育体系。
其四,湘西苗疆文教融合逐步推进。首先,流官在湘西地区革除旧有习俗,推行符合儒学伦理道德的价值规范。雍正八年(1730年),永顺知府袁承宠在《详革土司积弊略》中,列举了21条应予革除的积弊,广泛涉及贺仪、节礼、婚俗、建房、跳摆手舞、祭祀、服饰等习俗。其次,尽管清廷在苗疆地区颁行苗民通婚禁令,但事实上无法做到,甚至在军队中苗汉通婚也屡见不鲜,出现“兵丁多与苗人联姻,……大干例禁”[17]。雍正八年(1730年),巡抚赵宏恩上《六里善后事宜疏》称:“永绥民苗兵丁宜结姻亲,以潜移习俗。查苗民既已化诲,则是与民无异。应如所议,准许民苗兵丁结亲,令其日相亲睦,以成内地风俗。”[18]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下诏“各苗俱令与兵民结姻”[19],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苗人“准与内地民人姻娅往来”[20],正式取消了苗汉不得通婚的禁令。到乾隆中后期,官方明确允许各族群之间的通婚,虽然在乾嘉苗民起义之后一度又重新颁布苗、民通婚禁令,但实际上已经不能阻止民、苗之间的交互融合了。
4 结束语
“文化制衡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是一个“偏离”与“回归”交替出现,不断再适应的推进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文化互动”,它是文化制衡的前提。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基本规律,明清时期的苗疆边墙发展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是我们审视苗疆边墙的基本视角。边墙对苗疆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多方面的,既有隔离的消极作用,也有增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边墙造成了苗疆与外界的区隔,但不是隔绝,只是将民、苗进行空间的划分,减少了民、苗的直接冲突,有利于苗疆地区社会稳定,为苗疆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社会经济得到不断发展,湘西各民族内外交往有序增进,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各民族亲密无间、相互包容,在不断交往交流中逐步融为一体,真正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的政治及文化生态,成为中国民族地区民族和睦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91-192.
[2]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4:1876.
[3]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76.
[4]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增订本)[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262.
[5] 陈曦.明清时期湘西苗族起义频繁发生的原因述论[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32(8):110-114,140.
[6] 翁元圻,王煦,等.湖南通志[Z].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7] 伍新福.清代湘黔边“苗防”考略[J].贵州民族研究,2001(4):110-117.
[8]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4093.
[9] 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354.
[10]李世愉.试论“新辟苗疆”与改土归流之关系[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19(5):12-17.
[11]郗玉松,刘永强.经制土司之外:清代贵州土弁与苗疆社会治理研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2,24(5):11-16.
[12]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1003.
[13]张天如,纂修.永顺府志[M].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14]孙秋云.核心与边缘 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0.
[15]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上)[M].长沙:岳麓书社, 1991:67.
[16]蒋琦溥.乾州厅志·卷六[M].同治十一年刻本.
[17]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M].光绪九年刻本.
[18]严如熤.苗防备览[M].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19]清实录.世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5:822.
[20]方志.凤凰厅志(合订本)[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14,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