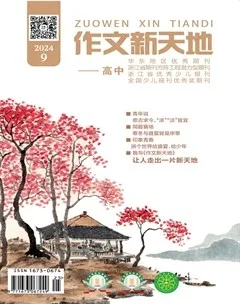文安
2024-09-30边建松
边建松,1970年3月出生,浙江省诸暨市草塔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浙江省绍兴市学科带头人、首届绍兴市名师、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省少年作家导师团导师、绍兴市作协理事,第九届绍兴市人大代表。曾在《诗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发表诗文100多篇(首),出版《海子传:幻象与真理》《戴思恭传》《高考作文突破与优化》等11部著作。
我不知道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村名的书面写法。记得儿时,隔壁满世界去养蜂讨生活的邻居们有写信回家,地址写“文安”为多,也有个别写成“文庵”。庵,确实有的,因为故乡有一座经堂。一个人、一座房子,成为一个标志,融化到一个地名里,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回老家,在阳台上就看到后山下的经堂,在毛竹林里露出一堵白墙,但已不再想进去看看内部的格局变化了。
经堂建在后山一个叫长弯的山脚。下面依次有三个池塘,老家分别叫小塘、上塘、下塘,三个塘似乎构成一条直线。从经堂到我家,有两条路:一条经过小塘直贯到我家后门;另外一条则由小塘往右面拐弯,穿过上塘的右面,再穿过下塘的左面,就到我家前门。我读一年级的时候,一天吃过了菜泡饭,正在大门口外,兰婆婆拐着脚,在窗口对着在灶头忙活的妈妈喊:“荷云,不好了,经堂着火了!”我妈马上丢下洗碗的笤帚,操起一个脸盆,跑到门外“当当”地敲起来——
“经堂着火了!”
我吓得跑进屋子躲起来,心里有不能着落的惊慌。妈吩咐我“不要跑来跑去”,转身就跑去救火了。兰婆婆拉着我的手,在椅子上坐下,我感到她的手绵软而温暖。过了很久,妈才回来,对兰婆婆说:“还好,没有烧到椽子,菩萨保佑的。”我不记得兰婆婆说的着火原因,但一直记得那个黄昏,天暗下来了,一个老婆婆握着我的手,绵软而温暖。小村的日子就是如此质直而紧致。
上文安、下文安以一条不过两尺宽的坑和坑边一条不过两尺宽的路分开。三个塘满溢出的水,经年不息地潺潺而流,坑底铺满小石块,有时还能够翻出石蟹和细虾。夏天发大水时,水就漫上来,最大的一次从后门进来,一直漫到家里。我还拿着脸盆往外舀水,没有大人的忧心忡忡,只是感觉好玩。现在干旱得几乎不再漫大水,就用水泥板蒙住了坑,再铺上水泥,变成一条可以开三轮车的路了。对我儿子一辈来说,他们已经不知道村子原先的面貌,而那些渐变,就这么不经意间成就了我们的当下生活。我们若回头看看,原初也会变得很不真实——这种幻灭感是很累人的。
一百年前,下文安真的没有几户人家,从“田”字辈算起,田银、田火、田生、田乐、田土等八九个壮年后生,算起来全村不到三十人。几列横竖的屋子,使村子的格局大致如同一个“旧”字,笔画疏疏落落,中间都是地垯,种些果树蔬菜。炒螺蛳时没有葱,一抬脚到屋外、到地垯里就有,露水清香的。下一辈“平”字辈又多出了好几户,后来村里搞了一个“光荣妈妈”,文安一下子旺盛起来,变成百多人了,壮劳力都有三四十个。原先村空窿的地垯,大约三十年前起,就都逐渐变为屋基地,建起楼房。到我们这一代,年龄差不多的上下年级的同学,单下文安就有十多个,七仙、风扁、培癞头、小芳、文英、燕秀……一个个穿着不知缝补了几次的衣裤,迎着朝阳,吵吵闹闹地、满足地走向设在边村祠堂里的边村小学。只是不知这个安静的村子为什么也会有怪病,而且居然是白血病。初中暑假时,我看到脸色苍白的燕秀躺在藤椅上,疲惫地大口呼吸。一旦回忆起来,每一种生命都是多有艰难,因为生命本身就要求自己有质量,你无法推远。
整个边村不仅水田少、旱地少,山林也不多。我们下文安大概每人一分多田;很多旱地是要走很远路的。到刀梢坞和九曲岭挑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路远而陡,只能将夵柱垫在肩膀上一步一步往上。而收获了马铃薯,又是一件高兴而麻烦的事,用长柄篮或者筲箩挑下来,山路刚好容纳一双脚,路两旁的灌木和茅草绊手绊脚。有一块田是在安华水库的,因为安华水库冬天放水、夏天蓄水,按此时令种冬麦,春天麦子一熟就推出双轮车带着冷饭包跑二十里地去赶紧收割。砍柴有时候要到边村最里面的大南井冈,也有十多里地。我们这一代都是父辈奋力在泥地里讨生活而存活下来的,这是一种社会体制下创造出来的奇迹,也许是只属于中国的奇迹。我对民间才有的隐忍不发有了自己的理解。
现在你若开车去文安,先到同山镇政府所在地高城头,沿大路再往里开。三里左右,左边有一个突出的山包,叫象鼻丘。下面的一条村路往上,百米左右,是边村的牌坊。在牌坊下远眺可以看见右边远处的高大墙壁,那就是边村祠堂,左边近一点建在高处的村子,就是下文安。到下文安,要先经过外井,这口井井水甘洌,远近闻名,我回家必带两桶回城。很多外村人甚至十多里外的解放村,也都来提水,用电瓶车、三轮车——有时候这些车很不讲道理,直接停在下文安路口,挡住村人出路。原先下文安是边村第一关口,到边村必先经过下文安,现在靠近前山另修一条大路,下文安下的老路车辆就少多了。我儿时就坐在村口的道地上,看老路上骑着自行车来往的人,萌生一种对远方的模糊渴望。
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些暑假,每早我都用大木水桶从外井挑两担水倒入水缸,傍晚,从屋角的里井挑两担水洒在阳台上以便乘凉。晚饭后,我们点起干艾草,坐在阳台上,看黑魆魆的后山岗和岗巅属于我家自留山的那棵松树,看向平榔头山边的几丛大樟树,看和尚山上的星星和偶然飞过的飞机的闪灯,看萤火虫在头顶飞,听故乡那些传奇人物在大人口中出没。有风吹来,吹来野鸟叫声和上塘的一丘田田边银杏树的沙沙声,一切都美好得那么不真实,惬意得似乎从来没有过饥饿、疾病、贫困和邻舍隔壁之间的龃龉——因此,这便可以写成“文安”吧?
离开老家读大学的那天,我是吃完早饭独自一人背着被铺出门的。一转出象鼻丘,漫天朝霞沿着南源溪,从远处的汤江岩过来,从高城头过来,从唐仁村过来,红红地笼罩了我全身,一时间我情不自禁泪流满面。我记得妈对我说过:边村人要有出息,一定要走出象鼻丘。这句话对我来说,更像是下文安留给我的一个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