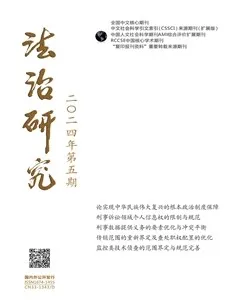《民法典》第1000条(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承担)评注
2024-09-25朱晓峰
关键词: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相当 非财产责任 比例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00 条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
一、规范意旨
(一)条文意义与目的
本条第1款是人格权侵权责任认定的辅助规范,主要目的是明确人格权侵害场合与消除影响请求权、恢复名誉请求权、赔礼道歉请求权相对应的责任承担应当符合民事侵权责任的填平原则,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旨在使因人格权侵害而导致的损害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属于恢复原状原则在人格权侵害场合的特别运用。①因为人格权与财产权虽然存在显著不同,特别是精神性人格权在遭受侵害场合事实上难以通过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赔偿在价值上予以等量恢复,但通过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承担方式,可以使特定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的受害人的处境得到改善、精神得到抚慰,②达到与损害赔偿等财产责任承担方式基本相同的恢复原状效果。③因此,本条第1 款要求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从而与民事责任的填平原则相协调。
本条第2款是关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承担方式或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在行为人拒不履行时适用替代执行方式时的构成要件及相应的法律效果的规定,明确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专属于人身权保护的责任承担方式,④可以通过转换为“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而予以执行,从而使其具有强制执行性,⑤解决责任人拒不承担民事责任时的执行难问题。
(二)体系位置
现行法中关于人格权侵害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既包括损害赔偿这样的财产性责任承担方式,也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责任承担方式,本条即是人格权侵害场合关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承担方式的使用规则及执行问题的一般性规定。⑥在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适用相应特别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11条、第23条等规定的商誉侵害场合的消除影响责任承担规则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第52条等规定的著作权侵害场合的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责任承担规则⑧等。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则应回溯到本条来确定相应责任承担方式的适用及执行方式。
本条第2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 年修正,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63 条规定的替代执行方式在人格权侵害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上的具体化。所谓替代执行是指由第三人代为履行义务,相应的费用由责任人承担的执行方式。《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这是民事执行程序领域关于替代执行的一般规定。而《民法典》第1000条第2 款规定行为人拒不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行为,属于前述第263条规定的“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具体情形,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承担。
本条第2款规定的替代执行方式与《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262条等规定的间接执行方式可以结合适用。所谓间接执行是指通过使责任人负担一定的不利后果,以迫使其履行义务的执行方式。其中,第114条第1款第6项规定“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266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这里的生效判决、裁定所确定的责任之外的因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所导致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其他相关措施,旨在迫使被执行人积极主动地履行生效裁判文书规定的义务。因此,若行为人拒不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的,法院既可以选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第6项以及第266条等使行为人负担一定的不利后果,迫使其履行义务。当然,法院也可以直接依据本条第2款选择替代履行方式。
(三)规范性质
本条第1款是人格权侵害民事责任认定的辅助性规范,旨在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以及第998 条等确定人格权侵害民事责任成立之后p/2hwiDa6jlcWBvlFzKkip4dNmUyJLWsB1QdINmsdK4=,明确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责任承担方式的具体范围与措施,保障人格权侵害场合的非财产性责任承担方式的具体适用与侵权责任场合的恢复原状目标协调一致。⑨
本条第2 款是在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手段性救济方式因行为人拒绝履行而难以实现目的时,赋予人民法院采取替代执行方式的权力,解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执行难问题,并使拒绝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行为人负有支付因替代执行而生之费用的义务。因此,本款是主要规范,⑩使实际采取措施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替代执行人取得向拒绝承担责任的行为人主张支付相应费用的请求权。
二、历史沿革
我国民事制定法上规定人格权侵害场合可以适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方式救济受害人的,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该法第120条即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或者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种做法在比较法上亦有迹可循。例如,德国司法实践以其《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为基础发展出来了恢复原状的撤回请求权,既有侵害名誉不实陈述的撤回及不当意见的更正或者补充说明等责任方式,也有将判决书进行全文或摘要刊登的方式。⑪《日本民法典》第723 条规定:对于损坏他人名誉的人,法院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可以替代损害赔偿或与损害赔偿同时命令其作出有利于恢复名誉的适当处理。依日本学理上的主流观点,该条的“恢复名誉的适当处理”主要包括公开的法庭上的道歉、报纸上的道歉启示、道歉状的交付、侵害名誉言辞撤回的通知等。⑫《韩国民法典》第764条同样规定:侵害他人名誉者,除命以替代损害赔偿或损害赔偿外,法院尚得依被害者之请求,命其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该适当处分包括谢罪广告。⑬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95 条也有类似规定。⑭法国《新闻自由法》第12条、第13条等分别规定了责令新闻媒体公开他人针对其具有名誉毁损性的报道所做出的回应、责令行为人矫正自己的陈述以及责令行为人撤回自己的陈述等。⑮与《民法通则》稍有不同的是,前述比较法上的恢复名誉等,主要适用于名誉权侵害场合。
考虑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种非以财产给付为内容的救济方式在具体适用上存在难以操作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 条第3 款规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该条规定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范围的认定问题上采相当性标准,该立场被《民法典》第1000 条第1 款所接受。另外,该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理。”⑯这就明确了行为给付场合的替代执行机制,为非财产责任方式的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该司法解释的做法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 条得到了进一步完善。⑰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些司法解释中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在具体承担和影响范围上应当满足相当性标准,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给行为人强加过重负担,与侵权责任填补损害、恢复原状的基本目标相吻合。⑱基于此,《民法典》在前述司法解释所取得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方式扩展至整个人格权保护领域,整体上有利于人格权的保护这一立法目的的实现。⑲
三、适用本条责任方式的人格权类型
《民法典》并未对何种人格权可以适用本条作出明确规定,这导致学理与实务上对本条的理解存在分歧。其中,非物质性人格权论认为,本条虽然没有和《民法通则》第120条一样,将适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人格权类型限定为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但通过文义、体系以及历史解释等方法的运用,可以得出本条适用范围及于所有的非物质性人格权而不包括物质性人格权。⑳名誉受损论认为,无论何种人格权侵害,只要导致受害人名誉受损,即可适用本条,其中赔礼道歉应主要适用于精神性人格权。(21)区分适用论内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应主要适用于名誉权侵害,不适用于隐私权侵害,赔礼道歉则主要适用于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22)另一种则认为,消除影响泛指人格权受侵害时,为消除对受害人造成一切影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的总称,于此的影响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因侵权行为致受害人自身精神上的影响,二是因侵权行为在社会上给受害人的名誉、荣誉等造成负面影响;恢复名誉系专门针对侵害名誉权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是消除影响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赔礼道歉的适用范围则主要包括具体人格权、身份权、知识产权受侵害的情形,不包括财产权受侵害。(23)本文认为,非物质性人格权论与名誉受损论在具体适用时固然存在着简洁且易于操作的优点,但其采用一元化的认定标准,模糊了人格权内部各种类型的界限,可能并不完全适应人格权侵害场合的复杂情形,难以满足充分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标。相比较而言,区分适用论考虑到了人格权内部的复杂情形以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三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具体特点而分别针对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确定其适用的人格权类型,整体上更具合理性。当然,区分适用论内部的二种观点亦有进一步改进空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为非财产责任承担方式,但其与财产责任承担方式的目的与功能是一致的,都是旨在使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属于恢复原状原则在人格权侵害场合的特别运用。(24)这就意味着,在人格权侵害场合,若损害可以通过财产责任方式的运用而恢复原状,则无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适用空间;若人格权侵害既使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又遭受精神损害,虽然精神损害依据《民法典》第1183条可以获得赔偿,但由于于此情形下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抚慰性质的,因此其可以与非财产责任承担方式共存,共同作用于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救济。并且,由于人格权侵害场合的损害并非都能满足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要件而可以通过赔偿的方式获得救济,此时亦可以通过非财产责任承担方式救济。
第二,对于因人格权侵害而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来讲,无论其何种人格权遭受侵害,不论是物质性人格权还是非物质性人格权,不论是具体人格权还是一般人格权,只要有精神损害,不论该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皆可以主张消除影响请求权;只要该请求权符合本条规定的相当性标准,通常即会获得法院的支持。亦即言,消除影响责任承担方式既可与精神损害赔偿共同作用于人格权遭受侵害场合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的救济,亦可以在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但尚不严重的情形下独立发挥其抚慰功能。在此意义上,消除影响责任承担方式原则上不受人格权类型的限制。唯一例外的是,在隐私权被侵害场合,由于侵害行为使私密信息等不再具有私密性,而消除影响通常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此时事实上难以通过消除影响来使已经产生的损害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25)亦即于此情形下只能采取其他责任承担方式救济受害人。
第三,相对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适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此种限制主要是因为恢复名誉以人格权侵害导致受害人名誉受损为前提,而非仅仅是遭受精神损害。对名誉受损而言,固然名誉权侵害场合通常会使受害人遭受名誉受损的不利后果,但并非所有的名誉受损都是因名誉权侵害而来,在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荣誉权、隐私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益侵害场合,甚至在物质性人格权侵害场合如当众扇人耳光、给人剃阴阳头等侵害身体权的场合,亦可能使受害人的名誉受损,此时即有恢复名誉责任承担方式的适用空间。亦即言,人格权侵害场合的受害人只要名誉受损,即可主张恢复名誉请求权,毋需考虑于此的名誉受损系侵害何种人格权。
第四,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强调通过外在的具有客观性的行为或者举措对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进行救济不同,赔礼道歉主要源于人的内疚感且与尊严感相关,(26)更强调行为人对自身错误的承认以及对因其错误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的歉疚与忏悔,因此具有内在性和主观性。赔礼道歉的这一特性一方面决定了人格权侵害场合的受害人只要遭受精神损害,即有权向行为人主张赔礼道歉,而毋需考虑何种类型的人格权被侵害;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赔礼道歉责任承担方式在具体适用时可能面临难以强制执行的问题。(27)因此,对于赔礼道歉应否作为责任承担方式而予规定,学理上存在分歧。(28)在《民法典》继续将赔礼道歉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加以规定的背景下,基于赔礼道歉的前述特性,在适用赔礼道歉责任承担方式救济受害人时应注意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之予以控制:一是请求权人只能是自然人受害人,不能是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并且受害人必需明确提出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法院不能主动适用;二是适用赔礼道歉原则上应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前提,至于过错是否严重则不做要求;三是法院在确定是否支持受害人赔礼道歉请求权时可以考虑《民法典》第998条规定的考量因素,其中损害后果是否严重应予重点考虑;(29)四是赔礼道歉是具有专属性的债务,在义务人死亡以及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形下,该债务虽不能让与或继承,但可以经由本条规定而采取替代执行的方式予以实现,从而解决学理上担忧的“无法强制被执行人真诚悔过并致歉,只能通过判决宣示正义”(30)的难题。
四、行为给付相当性的认定
本条第1款规定人格权侵害场合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具体适用上应与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相当,并且这些行为给付的影响范围亦应与侵害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由于本条规定的“相当”具有不确定性,在具体认定中需法官通过综合案涉诸考量因素进行利益权衡确定。
(一)与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相当
如前所述,与狭义上的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等责任承担方式目的相同,本条第1 款规定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亦旨在消除人格权侵害场合受害人遭受的不利影响,(31)使其遭受的损害尽可能地得到恢复或降低后续的不利影响等。这就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承担方式在具体方式和范围上具有相当性、适当性。(32)例如,就具体方式而言,行为人如以口头方式侵害他人人格权的,则通常亦应采取口头方式消除影响;行为人如果以书面方式侵害他人人格权的,则通常应当采取书面方式消除影响;(33)在微信群内(34)或微信公众号上(35)发布虚假信息或侮辱他人的言论,则应在该微信群内或公众号上发布澄清声明、赔礼道歉;如果行为人发表不当言论的载体为某网络平台上的某论坛,相应的不利影响系经由该论坛而造成,则行为人即应在该论坛上就其不当行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6)受害人要求行为人在其他主流媒体赔礼道歉的,通常会被认为超出了本条规定的相当性标准而难以被法院支持。(37)另外,如果人格权侵害的负面影响仅限于特定民事主体的亲朋好友之间,范围有限,此时,受害人若主张在大型媒体平台上赔礼道歉,则法院通常认为于此的赔礼道歉超出了“相当”的界限而不予支持。(38)
但要注意的是,本条第1款规定的“相当”并非相同,若完全以与侵害行为方式相同的标准来认定此“相当”,在特定情形下可能难以实现立法者通过该条填补损害、恢复原状的目的。例如,在微信群内发布侮辱、诽谤他人名誉的言论,若在法院所作裁判文书生效前,该微信群即已解散,或者侵权的网络平台已被封禁,等等,此时要求行为人以与侵权行为方式相同的方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几无可能,属于事实上的“履行不能”。另外,完全按照形式相同的标准来认定“相当”,并使行为人以与侵权行为相同的方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特定情形下恰恰可能无法实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目的。因为相较于赔礼道歉这种手段性责任承担方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主要从恢复原状的目的上强调责任承担的结果,如行为人在微博上发布虚假信息,该虚假信息引发社会关注并被新闻媒体客观报道,使行为人微博侵权产生的影响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得以扩大,此时若因与侵权行为方式相同而认定行为人仅在微博平台发布澄清说明并赔礼道歉,显然难以达到充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目的。于此场合,对于侵权行为方式与责任承担方式二者之间是否满足相当性要求的判断,司法实务中法院通常采取在综合考虑案涉各考量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利益权衡方式确定,如在望京搜候公司诉神棍网络公司名誉权案中,法院即认为:“考虑到涉案文章造成的社会影响,神棍网络公司之《致歉声明》不足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综合神棍网络公司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微信公众号被封等因素,依法确定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39)但是,由于法官进行利益权衡的过程通常难以在判决中以清晰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影响相应法律效果评价结果的可接受度。因此,学理上有观点认为应采比例原则的利益权衡方式,(40)将法官通过利益权衡认定“相当”性的过程以清晰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增强相应法律效果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可反驳性和说服力,值得赞同。
将比例原则适用于本条第1 款规定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具体承担方式与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之间是否“相当”的认定上,首先应当明确,于此的“相当”并不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手段与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之间保持形式上的一致性,事实上,只要是能够实现行为目的的方式,都因具备“相当性”而为法律所支持。当然,因为用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澄清声明的发布通常关涉行为人的不表意自由,所以不表意自由被干涉的程度也应以损失弥补为限,并在此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对行为人产生最低影响,否则即非为“适当的澄清方式”。(41)反之,如果相应澄清声明或道歉声明仅是将对行为人可能产生的影响降至最低而不能满足填补损害、恢复原状的目的,则该行为方式亦非“适当的澄清方式”。例如,行为人在其公众号发布侵害权利人的文章,法院判定其在该公众号赔礼道歉,但行为人将发布的《道歉声明》附在其他文章底部,不易被发现,此时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具体方式,与其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并不相当。(42)
其次,对具体责任承担方式是否“相当”的判断,可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四阶审查即目的正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来完成。(43)其中,目的正当性审查是比例原则适用的首要步骤,即要求首先查明和判断个案中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承担方式的目的是否正当,这是后续三阶比例原则的前提。在人格权侵害场合,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承担方式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行为给付解决财产性责任承担方式在非物质性损害救济上的先天不足问题,达到填补损害、恢复原状的目的。(44)在此意义上,人格权侵害场合,为充分救济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的受害人,让行为人在条件满足时承担以行为给付为主要内容的责任,符合目的正当的要求。
当满足第一阶的判断后,即进入第二阶的适当性原则判断,该原则要求对行为人之履行义务的强制适合目的的达成。对本条第1 款规定的三种责任承担方式而言,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属于目的性责任承担方式,通常情形下只要行为人的具体行为能够达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目的,即可认定该行为对目的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符合适当性要求。这也意味着,即便行为人以口头方式散播了虚假信息,但通过使其撰写书面澄清声明并予公开发布的方式来消除影响,也完全满足行为适当性的要求。毕竟,目的性责任承担方式场合的行为人具体行为给付义务的履行,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不良影响,而书面表达方式可以产生消除不良影响的结果;并且相较于口头澄清方式,书面形式具有一定的证明与公示效力,也是令第三人产生确信并消除不良影响的温和手段。(45)值得注意的是,在赔礼道歉这样的手段性责任承担方式适用中,即使让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并要求其履行该义务确实涉及对行为人不表意自由的干涉,但只要受害人接受,那么哪怕是行为人非真心实意的道歉,也符合于此的手段与目的相符合的要求,因为即使强制行为人赔礼道歉涉及侵害其之不表意自由,但赔礼道歉这项责任成立时的过错以及行为不法性等已将行为人赔礼道歉的责任承担正当化,强制行为人赔礼道歉,符合立法者通过承认赔礼道歉此种责任承担方式救济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的受害人的基本目的,不存在因赔礼道歉义务的强制履行限制行为人的不表意自由而使赔礼道歉此种手段性责任承担方式不适于此场合的受害人救济,(46)从而使其不符合比例原则第二阶“适当性”的判断要求。
满足第二阶的判断之后即进入第三阶最小伤害原则的判断。该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数个可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之间,选择对他人合法权益限制最小的手段。通常要求在既有的可选择的干预手段中,并无其他伤害性更弱的替代性方案,如有则应采用该替代性方案,否则即构成该原则的违反。对于人格权侵害场合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言,法院在具体的案件判决上无论是选择让行为人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样的目的性责任承担方式,(47)还是选择让其承担赔礼道歉这样的手段性责任承担方式,(48)抑或是不区分目的与手段的责任承担方式而让行为人全部承担,(49)实际上都要求行为人完成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义务,这就涉及这些责任承担方式在满足受害人充分救济目的的同时,也不能对行为人之行为自由、人格尊严的影响过大。即如果可以通过当面向受害人口头赔礼道歉的方式或者在微信公众号赔礼道歉即能达到救济受害人并使其遭受的损害恢复原状的目的时,则毋需在大型新闻媒体上发布书面澄清声明,(50)因为后者虽然符合第二阶的适当性原则,但可能造成对行为人的过重限制,不符合对其最小伤害原则的要求。(51)当然,如果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对其而言是最小伤害,如将道歉声明置于公众号最不显著的位置(52)而非显著位置(53),则该方式不足以充分救济受害人,亦不符合于此的最小伤害原则或必要性原则。
满足第三阶的最小伤害原则的判断后即进入最后一阶即狭义比例原则的判断。该原则又称均衡性原则,要求干预手段与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必须相称,二者在效果上不能不成比例。在人格权侵害场合,对于法院认定行为人应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责任的,由于现行法上并未明确规定对行为人不表意自由的保护与受害人受侵害之人格权益的救济存在价值位阶与次序上的差异,因此只要在通常意义上达到让社会一般f91d20961fa3d03c5d00751b192fefe9人认为并不存在“因小失大”的不良后果,即可认为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与对行为人的不利影响二者之间符合均衡性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消除影响来讲,原则上具体澄清方式的选择都符合狭义的比例原则。毕竟只要没有侵害行为人以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价值基础的人格权益,行为方式的选择本就应始终附随于恢复原状这一责任承担之终极目的之所在。
也正是因为对恢复原状的遵循与坚守,行为方式与侵害行为之间的相当性要求事实上仅是一项“底线要求”,只有当澄清声明公告等超出恢复原状的范畴而有损义务人他种人格法益时(如自我侮辱),(54)才会构成对本条第1款规定的相当性要求的违反。
(二)与侵害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如前所述,由于在责任承担方式的选择上通常不会违反本条第1 款关于和侵害行为方式相当的要求,所以对相当性的认定,事实上主要集中在侵害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与相应责任承担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范围这一结果的判断上。结合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赔礼道歉的特性,可以发现:第一,恢复名誉虽然与消除影响同为目的性责任承担方式,但恢复名誉通常表现为消除影响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即消除影响本就包括恢复名誉在内;(55)第二,赔礼道歉作为一种手段性责任承担方式,其主要功能及履行结果主要表现为教育、预防、安抚和制裁,(56)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仅表现为赔礼道歉的一种客观结果,(57)特别是让责任人当众赔礼道歉,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效果可能更为突出,但是除了这种客观结果之外,赔礼道歉更主要的还是满足受害人的心理需要,产生精神抚慰效果。(58)在此意义上,本条第1款要求行为人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应当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核心是指责任人承担消除影响责任的,应当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与前述行为方式的相当性判断方法一样,责任人承担的消除责任的影响范围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之间的相当性判断,亦可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四阶审查来展开。例如,通过发布澄清声明的方式消除影响,则该澄清声明应产生使之前受责任人之侵权行为影响而产生错误认知的社会公众知晓事情真相并因此消除错误认知的效果,达到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的目的。而澄清声明的影响范围如果小于因侵害行为产生的不利影响的范围,则难以实现消除错误认知的效果,与比例原则第二阶的适当性原则不相吻合。因此,删除错误的网络发帖、断开侵权网络链接等因不能令相关主体完全恢复正确认识,故应排除出消除影响的外延。相反,如为消除影响而采取的措施所导致的影响范围大于侵权行为产生的不利影响范围,则会违反比例原则第三阶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如侵权行为仅在亲戚朋友之间产生影响,若要求行为人在大型新闻媒体上发布澄清声明,则该责任承担方式的影响范围显然明显大于侵权行为产生的不利影响范围,违反必要性原则。(59)
值得注意的是,当侵权行为产生的影响范围因其他介入行为如第三人转述或者转载而超出侵权行为初始影响范围时,行为人是否亦应对因此产生的全部不利影响负有消除的义务?支持行为人对于此场合的全部不利后果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的观点认为,即便二次转载仅是事实报道,并不涉及对事件真伪的评价,但报道实有利于错误认知的传播,在客观层面难以完全遮蔽侵害行为本身的“违法性”,故对于造成的全部损害,对错误认知的产生有“过错”的侵权人均应承担消除影响义务,需要在转载媒体上刊登澄清声明。在该观点看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应作为消除影响责任承担范围的权衡因素,因为无论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要素的存在足以表明其未尽到理性人的注意义务,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其自然应弥补产生的全部损害,此乃“过错归责”固有的要义所在。并且,消除影响仅存在全有全无的问题,既无法根据过错程度而选择具体责任方式的承担,也不能因为权利人对损害发生与有过失而要求过失相抵,进而仅承担消除部分影响的责任。因此,消除影响的范围应着眼于客观的损害后果(范围)而非主观的过错状态。(60)该观点有斟酌空间。因为介入行为导致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扩大,此时的责任承担应考虑介入行为人是否因其过错而承担非财产性责任。若不考虑介入行为人的过错而让行为人承担全部非财产责任,亦违反过错归责原则之本质。具体来讲,在介入行为人无过错时,此时行为人应对因介入行为而使不利影响扩大的那一部分承担消除影响的责任;但若介入行为人在转述或转载时亦有过错,特别是在故意场合,则受害人既有权向行为人主张承担消除全部不利影响的责任,也可以向介入行为人就不利影响扩大部分主张承担消除影响的责任。
五、行为给付替代执行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本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给付替代执行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为人负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第二,行为人拒不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当满足这两项构成要件时,即产生使人民法院有权选择替代执行措施的效果,法院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替代执行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若法院采取替代执行措施并予以了实施,则发生消灭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债之关系以及产生因执行所生之费用由行为人负担的法律效果。
(一)行为给付替代执行的构成要件
1. 行为人依法应承担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
行为人负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系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结合第998条确定。在认定行为人人格权侵害场合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责任时,应当注意如下三点:
第一,《民法典》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的适用问题上相比较之前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在可以适用的人格权范围上作了扩展,并不仅限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非物质性人格权益类型,物质性人格权侵害场合亦有这些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适用空间。(61)另外,隐私权侵害场合通常亦不涉及通过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承担方式救济,因为隐私因披露而不再是隐私,难以恢复原状,(62)但可以使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以使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的精神得到抚慰。
第二,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的归责原则上,仍主要是过错责任。因为与这些责任相对应的请求权虽是非财产性的,但其本质上仍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债权请求权相同,(63)区别于《民法典》第1167条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绝对权请求权。另外,在个人信息侵害场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规定了过错推定,需要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区别于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过错责任。(64)
第三,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以及第998条等确定的人格权侵害场合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应当符合本条第1款关于相当性的要求。
2. 行为人拒不履行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
行为人拒不履行责任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就主观方面而言,本条第2 款规定的替代履行方式的选择及实施以责任人存在过错为前提。从本条第2 款的文义来看,“拒不”表明责任承担者主观上存在故意,即责任人知晓生效裁判文书等认定其负有履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若行为人主观上并不知晓其依生效法律文书所负之责任,则不符合该条规定的主观要求。就客观方面而言,“拒不承担”表明责任承担者未依法承担生效裁判文书等认定的责任,(65)既包括完全不承担责任,也包括不完全承担责任,如在庄宇诉郭敬明等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行为人郭敬明负有在侵权的网络平台消除影响并当面向受害人庄宇赔礼道歉的责任,但行为人仅在相应的网络平台采取了消除影响的措施,却拒不赔礼道歉。(66)
(二)行为给付替代执行的选择及具体方式
1. 行为给付替代执行的选择
依据本条第2款规定,在人格权侵害场合,如果满足前述两项构成要件,即依法负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责任的责任人拒不承担责任,则产生人民法院有权选择替代执行方式的效果。即本条第2款在特定条件下赋予了人民法院以自由裁量权,使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采取替代执行措施来完成责任人的行为给付。这一规定一方面有助于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强制执行,从而实现充分保护受害人人格权益的立法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灵活应对人格权侵害场合特别是名誉权、隐私权侵权的复杂现实。因为名誉权、隐私权侵权情形下发布公告或公布裁判文书可能会导致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扩大,如侵权行为已经停止且相关侵权信息已经删除,此时再发布公告或公布生效裁判文书可能将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此时,法院可以在尊重受害人意愿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67)在现行法律体系中,除《民法典》第1000条第2款外,《民事诉讼法》第266 条也规定了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选择包括替代执行等在内的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之义务的其他措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因此,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手段性救济方式在强制执行层面亦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间接执行,即通过使行为人负担民事、行政或刑事上的不利后果而迫使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二是替代执行,如本条第2 款规定的通过由第三人代为履行义务而使责任人承担相应费用的执行方式。若人民法院仅选择间接执行方式,则不存在本款规定的适用空间;若人民法院选择间接执行方式,同时也选择替代执行方式,由于现行法律体系下这两种执行方式可以并存,因此符合本款规定的构成要件,因此产生的费用自应由责任人承担。
除了《民事诉讼法》第266 条、《民法典》第1000条第2款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替代执行方式之外,202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1款还规定了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而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这实质上是在前述制定法规定的职权主义模式之外对申请执行人的选择权的尊重。因此,结合前述制定法规定及司法解释,对于是否采用替代执行措施的问题,整体上应由执行法院依比例原则等利益权衡方法决定,(68)同时也要充分尊重人格权受侵害人的选择权。(69)事实上,从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具体做法来看,其通常会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若行为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书中确定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义务,则法院将根据受害人的申请而在全国发行的媒体上公布相关判决内容,费用由行为人承担。(70)这实际上是对受害人选择权的承认与尊重,值得肯定。
2. 行为给付替代执行的具体方式
依据本条第2 款规定,替代执行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二是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生效裁判文书。其中,发布公告既可以是受害人发布谴责公告,也可以是人民法院发布判决情况的公告。于此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赔礼道歉,一般不采取受害人或者人民法院以被告名义拟定道歉启示并予公布这种道歉广告或道歉启示的方式,因为赔礼道歉具有人身属性,通常需要责任人自身亲力亲为,(71)若责任人拒绝履行义务,则通常的替代执行方式是人民法院将依职权(72)或根据执行申请人之申请(73),选择在报刊或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另外,为防范责任人所拟的道歉广告在内容上轻描淡写或因为受害人的压力而涉及自我羞辱等损及人格尊严的表达,(74)人民法院在认定责任人应承担赔礼道歉之责任时亦通常会在判决书中写明“道歉内容需经人民法院审核”。(75)公布生效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将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公布并使公众知晓,因此这里的公布既可以是在报刊、(76)网络(77)上的公布,也可以是以书面形式在特定范围内张贴公告的形式公布;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既可以是文书的全部内容,也可以是文书的摘要,只要能达到澄清事实、消除错误认知的效果即可。
(三)行为给付替代执行的法律效果
替代执行完成的法律效果有二:一方面,替代执行措施执行完毕后,责任人即无需再向受害人继续履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义务,因为作为执行机关的人民法院亲自或经由第三人如报刊、网络等媒体实施执行措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义务,使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全部消灭,执行程序亦因为前述执行目的的实现而结束。另一方面,依据《民法典》第1000条第2款及202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的规定,替代执行完成产生媒体公布产生的有关费用由责任人负担的法律效果。由于依据该解释第26条之规定,当责任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申请执行人也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此时因媒体公布而需要花费的费用应由申请执行人垫付。若申请执行人垫付了相关费用,则其可以因此而依据《民法典》第1000条第2款规定向责任人主张支付费用的请求权。在此意义上,本款也是关于替代执行场合的费用支付的规定。
依据本条第2款规定,于此的“费用”应当与人民法院选择的替代执行措施的实施相关,二者之间应当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非因替代执行措施之实施而发生的费用,不属于本款规定的应由行为人支付的费用。另外,从本款的文义看,“产生的费用”既指向前已述及的因果关系,也指向费用发生的具体性、客观性,排除抽象的、主观的费用。基于此种理解,“产生的费用”是指事前或事后向行为人收取执行的费用,(78)因此应当包括已经实际发生了的费用,也包括确定将发生但尚未实际产生的费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款虽然未对“产生的费用”在范围上作出限制,但考虑到本条的替代执行的目标主要是救济受害人并使其遭受的损害尽可能地因为执行措施的实施而恢复原状,并不以对行为人的制裁或惩罚为目的,(79)因此因替代执行措施所生之费用的支付,亦应以必要为限。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费用有诉前律师咨询费、案件调查费、证据保全费、公证费、律师代理费、法院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等,这些费用中的前三项通常是权利人为赢得诉讼所必需支出的费用,我国法律目前并未规定由败诉人负担,因此实践中若申请执行人主张这些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其通常的结果是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80)但对法院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有明确规定,由败诉方负担。要注意的是,这些费用均非因实施替代执行措施而生,不能通过本款规定而获得支持。从司法实践中获得支持的费用范围来看,于此的费用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的“媒体公布的有关费用”,亦即《民法典》第1000条第2款规定的“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产生的费用。
在司法实践中,为解决前述垫付所可能引发的执行难问题,在人格权侵害场合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赔礼道歉等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问题上,尽管执行标的是行为给付,但执行法院仍会通知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并通过财产查控系统查找被执行人名下财产。若财产查找无果且被执行人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如下落不明)赔礼道歉义务的,则执行法院就会将被执行人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并在征求申请执行人意见后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的方式结案。(81)
六、证明责任
本条第1款是人格权侵权场合非财产责任认定的辅助性规范,对于本款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与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是否相当的判断,由法官在个案中综合各案涉考量因素并通过比例原则的利益权衡方法进行判断,因此对于案涉相关因素的证明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各自完成,法官在双方举证证明的基础上依利益权衡方法认定相当性。
本条第2款的申请执行人提出行为人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后,行为人应当就自己已经承担法律责任举证,若其不能证明已经承担责任,则法院即可以依职权或被执行人申请而选择替代执行方式履行义务。若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选择替代执行方式,此时发生的费用由申请执行人垫付,因此其在向行为人主张支付费用的返还时,应当证明其已经因替代执行而支出实际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