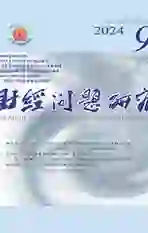农地经营权强度能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吗?
2024-09-22王家兴米运生徐俊丽




摘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然有着强烈的机构贷款需求,但因缺乏有效抵押品,正规金融机构普遍对其施加严格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三权分置”从法律层面激活农地经营权,是破解供给型信贷配给难题的重要契机。本文从法律维度、事实维度、感知维度对农地经营权强度展开维度化分析,厘清其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作用机理与具体路径,并使用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既能由法律维度、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同时具有较高强度而得以缓解,也能仅凭法律维度或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得以缓解,但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尚不足以单独发挥缓解之效。为进一步释放农地经营权改革的信贷效应,既要完善农地经营权的法律赋权与保障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利,也要强化主体对农地经营权的安全感知。本文既从理论上深化了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理解,揭示了法律赋权、事实拥有、先验认知等不同层面的产权排他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内涵,也在实践上拓宽了破解供给型信贷配给难题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农地经营权;产权强度;供给型信贷配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fsQCA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4)09-0103-16
一、问题的提出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为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国家不断提高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截至2023年,中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23万家,纳入管理的家庭农场超过400万个,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超过9万家,带动小农户超过8 900万户。在政策引导下,蓬勃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优势,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组f2380d2b9199b6dc1f1e101cbbfb5ba7织效率,其已经成为壮大农业经济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其进一步发展却因缺乏充足的机构贷款而受到极大制约。实地调研与经验研究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严重的信贷配给[1-3]。这无疑令人困惑。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农村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为农业发展带来了充裕的资金供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因其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而有着强烈的机构贷款需求[4-6]。那么,既然供需两侧没有阻碍,为何获得充足机构贷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十分有限,其遭受的信贷配给问题依然非常严重?显然,依赖于市场的资金流转出现了问题。
农村地区的资金供求市场虽然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但仍不能脱离市场基本规律运行。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需以借款方提供合格抵押品为前提。从功能实现角度来看,合格的抵押品必须具备法律层面权属明确和价值稳定容易变现的特征[7]。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有的最主要资产,是其为规模经营而转入的大量农地。“三权分置”后,国家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①意在从法律层面强化农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能。这为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与制度基础。并且,通过大量转入农地,土地细碎化、分散化的问题也得以缓解,进而提升了抵押品价值与变现能力。可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似乎不应具有担保抵押之忧。但是,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尚不完善。“三权分置”以来,农地经营权的权利内容与性质并未得到明确解释,“三权”之间的关系充满争议。这无疑影响到经营权的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8-9]。后续的一系列改革和法律修订虽初步实现了经营权法定化,但其权能不清、性质不明等弊病仍未从根源上予以解决。
显然,法定的土地经营权制度依然有待完善。但不完善的法律是否就意味着经营权改革完全是劳而无功?从全国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效果来看,经营权改革之效已初现端倪,一定程度上盘活了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这不由得引发思考:鉴于法律赋权的极端重要性,为何备受争议、存在明显缺陷的农地经营权制度,仍能够取得一定实践效果?现有研究并未察觉这一矛盾所在。农地经营权的合法性,并非取决于法律界定、土地合同、确权颁证等表象,其本质是法律赋予农地经营权的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即农地经营权强度。并且,产权在理论与现实上的割裂,也注定其理论逻辑势必是多维度的。因为即使制度不甚完善,法律具有的信号显示和政策引导功能,使其仍能够于实践中指导经济主体;干部认知、群众文化程度等多方面因素,也影响到制度的实际执行程度和实施绩效。这意味着,除法理层面的明晰界定外,还存在经营权主体实际行使权利的完整性,以及其对经营权排他、稳定、安全的直观感知。这显然无法从法律上予以表征。那么,对农地经营权信贷效应的考察,也不能局限于单一法律因素,而需充分考虑其实际执行情况和个体感知。现有研究大多仅从确权颁证等法律层面出发,其对经营权本质的认知并不充分。农地经营权的权能强度,由法律、事实、感知三个层面共同决定,其各自对机构贷款有不同的影响机理,三者协同作用构成的影响路径也必然是复杂多元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是否及如何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是有待解开的理论之谜和有待回答的实践之问。若无法深刻理解农地经营权强度的理论内涵,仅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单一因果判断,不仅缺乏理论根基,而且难以揭示内在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本文基于产权理论,从法律、事实、感知三个维度分析农地经营权强度,厘清其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作用机理,并采用基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 方法,探究由各维度农地经营权强度构成的组态集合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具体路径。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其一,立足于产权强度,从法律、事实、感知三个维度,建立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农地经营权的理论空间。其二,结合大国小农的中国农情,从多维度赋予农地经营权强度以丰富内涵,建立其与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既拓展了农地经营权理论的应用领域,也提升了其情境适用性。其三,在法律不完善或名义产权残缺的环境中,制度改革之效虽有据可证,但其具体机理与实践路径却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厘清多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影响机理,并使用有别于传统计量模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方法,揭示其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具体作用路径,为农地经营权改革提供了实践空间。其四,本文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为何法律层面关系不明、权能不清、界定不一的农地经营权仍能取得一定的制度实践之效这一现实谜题。这既强化了农地经营权研究的现实性,也能为经营权改革成效之论战提供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分析框架
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们必须有规则地占有与分配资源。若所有资源都被置于公共空间任人抢夺,社会秩序将不复存在。这种约束规则即是所有制,而产权则是所有制的核心[10]。土地产权也是如此。科斯曾指出:如果没有建立土地产权,任何人都可以占用一块土地,那么显然将发生很大的混乱。产权建立之后,混乱就消失了[11]。法律层面的明晰界定,如农地确权颁证,保护了农地产权的排他性与合法性。有了上层建筑与公权的保护,产权似乎变得明晰了。在受法律所规范、约束的文明社会,这确实是一个既定的认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除必需的正式制度外,非正式制度也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产权经济学之所以将产权赋权与产权行使区分开来,是因为产权总是不完全界定的,尚存在法律界定之外的,置于公共空间的剩余权利[12]。这意味着权利主体实际拥有的权利往往与法律界定有差别。例如,现实情境下,即使农地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但关于土地功能、面积和分配等方面的纠纷仍无法避免。因此,产权边界总是不甚清晰的,法定权利并不总是最有效的界定形式。那么,关于土地剩余权利纷争的胜负,则取决于实际的产权行使能力。权利主体实际能够获得何等程度的剩余索取权,构成了事实层面的产权强度。而且,产权本身的定义与内涵也是模糊晦涩的。考虑到不同产权主体的认知能力存在偏差,客观的法律界定与事实拥有并非总能得到充分的主观先验认知。特别是对于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且认知水平较为有限的农业经营主体而言,较之法律与事实层面的产权强度,其对于土地产权安全的主观感知,或许更加准确地代表了其实际产权强度的大小。
因此,产权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存在法律的事先界定与保护,产权强度也无法仅从单一的法律维度得以准确衡量,而是需要从法律、事实、感知三个维度进行综合测度。三者共同决定的产权强度才真实可信,且通过产权实施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路径也更加清晰。“三权分置”重构了农地产权。从农地承包经营权中独立而出的农地经营权,虽与母权同源,但有着更为明晰的权利内涵。同样地,在农地经营权的实践中,不完善的法律界定也导致经营权主体行使的实际权能与法律赋权存在差异。不同经营权主体对其权利的安全感知也是不同的。那么,农地经营权主体所实际持有,以及所能感知的经营权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同样能表征其农地经营权强度。基于此,本文参考Gelder[13]对产权的分析框架,从法律、事实、感知三个维度对农地经营权强度进行维度化的分析。
(二) 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
在零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中,产权初始界定并不重要[14]。科斯定理指出,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产权就可以有效率地在权利主体之间流转,直至消除负的外部性。因此,即使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无效率的,也总能够通过反复的零成本产权交易达成有效率配置。然而,在真实世界中,产权交易的代价却是昂贵的。这使得法律层面的产权赋权与初始界定,几乎决定了产权最终配置与社会总体福利[15],因而法律的初始赋权具有极端重要性。关于农地经营权,“三权分置”虽将其与承包权分离开来,但并不意味着斩断了农民与土地的法权联系,反而使其更加稳定、更加固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营权主体能够依法享有对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正式赋予农地经营权作为财产权的应有权能。201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 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经营权可以用于融资担保”,进而为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了法律依据。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的出台进一步明晰了农地经营权的权利内涵,并再次强调经营权的财产功能。在法律层面赋予农地经营权以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能够保障权利主体利益,降低交易风险与成本,构成了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
不过,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尽管科斯肯定了明晰产权的重要性,也注意到了通过法律进行产权初始界定的基础性作用[14],但法律作为政府意志的代言人,政府裁决中因信息不充分而引致的效率与公平损失,也导致了法律层面产权界定的不完全性。农地经营权也是如此。一方面,关于农地经营权的物权债权之争仍未有定论。《土地承包法》《民法典》均未明确界定农地经营权之法律属性,甚至在《民法典》中出现了自我矛盾的表述。《民法典》第三百四十一条中,赋予流转期限五年以上的农地经营权以物权属性,但在第三百四十二条中所规定的“允许以出租形式流转农地经营权”,却体现出债权属性。甚至在第三百三十九条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的表述,更是完全混淆了物权债权性质。另一方面,农地经营权的权能界定也是模糊的,不同法律所规定的具体程度与内容也不一致。例如,依据《民法典》,农地经营权人具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但《土地承包法》却规定农地经营权的权能包括流转、生产、再流转、担保、抵押和继承等。并且,《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均包含对土地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可见,不完善的农地经营权制度,导致经营权的法理层面关系不明、权能不清、界定不一,势必削弱了法律维度的经营权强度。
尽管目前关于农地经营权的法律赋权尚不完善,但作为正式制定并颁布施行的法律,不仅具有国家公信力予以背书,且其基本的指引、信号和明示等功能已然具备。自2014年“三权分置”政策确立伊始,不仅《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民法典》等基本法对其进行针对性修订,或纳入相关法律条文,且现全国至少17个省份也陆续出台了“三权分置”相关的地方政策文件。可见,国家积极鼓励开展经营权抵押贷款,释放其“德·索托”效应的政策意图,并依赖法律的基本功能予以推行。然而,出于客观条件不足、无为政府等原因,具体到地方的“三权分置”仍主要以县域、村镇试点的方式推行。当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至一定阶段,出现规模化的生产与资金需求时,地方政府自然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配套政策予以支持,“三权分置”则得以发挥制度之效。法律层面的强权赋能,显著缓解了信贷供求双方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法律效力的农地确权颁证,一方面,使得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的价值被正式认可,进而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以及事前甄别和事后监督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为农地市场交易的合法性、稳定性进行正式背书,提升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信心,进而缓解其所施加的供给型信贷配给。
(三) 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
在关于如何解决外部不经济的讨论中,科斯认为政府应当扮演关键角色,依据“能者居之”原则进行产权界定与配置,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其中暗含的两个关键假定:搜寻最优产权主体的发现成本为零和静态均衡,均是不真实的。一方面,完全识别不同产权主体的能力差异,需要更加高昂的界定成本和潜在交易成本,即使得以准确识别实现了效率,也无法兼顾公平;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和市场制度的演进,资源价值属性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15],进而导致旧的产权配置出现租值耗散,不再具有效率。
由此可知,现实情境中,虽然政府通过法律进行产权的明晰界定与配置,但因高昂的界定成本,无法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的产权配置也是低效率的,且加剧了制度的不稳定性。那么,市场化的私人交易、地位差距导致的权利侵占、价值判断下的自愿弃权等非法但具有效率的配置手段就无法避免。政治经济学派早已洞察法律与现实的差异。马克思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中所言:“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Besley[16]也提出:“正式的(法律上的) 权利可能与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事实上的) 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产权主体实际权利的大小,即事实产权,与其法律界定往往有差别。除产权行使外,产权价值不仅由法院系统、政策、合法的农地调查、登记和公告的代理机构等正式明确和强制执行的产权机制决定,还取决于社会规范、信仰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17]。同样,对于农地经营权而言,法律虽能够强化其权能,但也非行使经营权的充分条件[18]。原因在于:农地经营权的权能结构并不清晰;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不同地域的农地契约结构、权利登记落实、基层干部认知和纠纷处理机制等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主体对于法定农地经营权的实际行使程度,即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通常与法律赋权存在较大偏差。
在“法治”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民治”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农地经营权的权能与边界在法律层面的不完全界定,现阶段仅依赖法律去解决土地纠纷,显然脱离现实。自古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就存在着村庄自治。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的非正式约束,也逐渐发展成如法规一般的、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正式制度。在农地转型较为成功、土地流转需求较大的县域或试点地区,地方政府出台特色法规与配套办法予以支持。①更甚,在完全不存在正式法律的时空条件下,地方自治则依赖于长期形成的习俗惯例。例如,土地租佃关系中的永佃权及其衍生出的田面权,两者不受制于任何法典。在唐末农民战争后的三百年间,永佃权与田面权虽于时间与空间上形态各异,但其仍能持续作为承载土地流转与交易的“民法”物权而存在,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言:“使用者是对被用之物最了解的人,在使用过程中,他能发现事物的好坏。”可见,依赖于非正式制度的口头契约,俨然在正式法律赋权缺失的情况下,指导着实践活动。同样地,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境下,农地经营权主体是否实际拥有对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显然真正代表了农地的实际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进而影响农地的抵押价值与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决定。
(四) 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
感知上的农地产权是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农地产权的状况。产权主体之所以能够产生行使各项产权权利的自觉,是基于生活经验与习俗惯例所形成的认知[19]。对自身权利的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的直观感知,即心理学角度的先验认知,往往成为产权主体的行动准则。如Sjaastad和Bromley[20]所言:“无论一片土地的法律状况如何,都是产权主体认为的权利状况构成了可以预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础。”因此,感知到的产权状况往往并非与法律和事实维度的产权状况一致,即使在法律和事实产权相同的情况下,产权主体对其拥有的权利状况的感知程度也会不同。例如,是否会产生农地流转纠纷、转入农地被收回的担忧等。这种担忧,可视为产权主体对于可能失去具有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的农地产权的感知,进而构成了感知维度的产权强度。
对于农地经营权而言,经营权主体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感知与自身行为能力导致的约束相关。Barzel[21] 提出,产权主体的权利实施程度取决于个人保护、他人夺取和政府保护等方面。农村地区之所以土地纠纷频发,除模糊的法律界定无法带来充分的排他性保护外,还源于各权利主体对置于公共空间的土地产权展开争夺。产权实施能力不足的主体,因具有在争夺中失地的担忧,而无法产生良好的经营权安全感知。地方是否注重土地产权保护,解决土地纠纷也与之相关。“三权分置”、农地流转和经营权抵押贷款等土地改革政策的施行推广,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乡镇机关对政策的理解程度,以及改革工作的支持力度[22]。农业经营主体受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策实践情况直接影响其权利强度感知。
农地产权之所以能够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决策,实际上源于农业经营主体对实际产权状况的主观感知[19]。若农地经营权人对其所持有经营权的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存在较好的先验认知,那么其实践预期也会得到强化[23]。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定、安全的农地经营权认知会令其形成良好的经营预期,从而激励其投资行为,并更多地转入农地展开规模化经营。投资带来的农地产出率提升与农地规模的扩大使得农地作为抵押品的价值得以提高,有利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对还款能力与意愿的良好预期,从而缓解供给型信贷配给。
(五) 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
在现实情境下,农地经营权在法律层面的正式界定、事实层面的实际拥有和感知层面的先验认知并非单一存在,而是并存的。本文之所以从多维度分析农地经营权强度,正是试图从不同角度探求,为何不完善的农地经营权法律仍能取得一定实践效果。因此,本文探讨各维度经营权强度的协同作用,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影响。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经营权具有合法性、能够行使较为完整的经营权权能,且感知经营权是排他、稳定、安全的,则代表其不仅拥有法理层面的稳定经营权,且由法律不完善导致的经营权强度损失,也能因其完整的经营权权能与经营权的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感知而予以弥补。在多维度经营权强度机制的协同作用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得以缓解。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农地经营权同时在法律维度、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具有较高强度,能够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
法律维度、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协同作用,是在某一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其他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若能够予以补充,则仍得以实现一致结果。然而,三个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同时具有较高强度,虽能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但并不意味着三者的影响大小与重要程度等同。为提升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意愿,国家相应地出台“三权分置”、农地确权等配套政策,其作用机理正是从法律层面明晰农地经营权的权力边界,使农地经营权能够成为合格的担保抵押品。通过法律赋权建立的权力合法性与稳定性,赋予了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以客观性[24]。并且,由于农村长期开展法治教育,农业经营主体的法律意识与素养得到提高。这极大地强化了法律赋权的权威性。因此,法律维度的信贷效应仍是显著且极端重要的,即使它尚不完善。同样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行使的农地经营权完整性,以及完整性所决定的农地抵押价值,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由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约束,即“民治”赋予合法性。特别是在税费时代“去组织化”制度安排导致的公共空间主体缺失与公权真空下,精英治理、精英俘获的村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民治”。因此,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或许能够成为法权缺陷的有力补充。然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却并非客观。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经营主体尚未完全摆脱“生存小农”特征,进入“理性小农”阶段。即使是遵循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加之封闭村庄内部的信息壁垒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扭曲,农业经营主体不仅信息渠道受限,且获得的信息往往严重失真。那么,农地经营权的强度感知则可能并非是理性的客观判断,而是基于有限信息的无据主观臆断。因此,不仅感知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且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各方感知差异,进而发生农地纠纷,加剧产权不清。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即使事实维度与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较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仍能因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而得以缓解。
假设3:即使法律维度与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较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仍能因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而得以缓解。
假设4:若法律维度与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较弱,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无法仅凭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而得以缓解。
在农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农地产权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配给的重要因素。但除了农地产权外,还存在诸多影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决策的现实因素。其中,以借款方的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最为重要[9]。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收入、农地质量和农地规模等衡量农地作为抵押品价值的因素,分别表征其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一方面,收入的提升有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跨过最低收入门槛,也有利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其还款能力作出积极评价;另一方面,抵押品价值的提高,增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违约成本,进而疏解了正规金融部门对其还款意愿的担忧。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规金融机构施加的供给性信贷配给。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经济学领域,实证分析因其客观性、逻辑性、科学性而受到重视。基于理论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或某一现象的驱动因素展开分析,并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加以检验识别,是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范式。传统的实证分析方法,如计量模型,通常基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控制变量思维。在控制无关因素的前提下,集中于一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的单方面影响。这固然是合理的研究思路。但是,正如经济学家Leslie[25]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那样:“如果隔离出某一种因素来推导其对于国民财富的影响,即使这个因素是真实而非纯粹抽象的,也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种做法也是极其不科学的。”现实情境下,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某种现象的发生可能并非由单一因素所致。那么,是否有一种更加科学,且契合现实的研究方法,能够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在诸多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中,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方法打破了定性研究的特殊性与定量研究的普适性之间的界限。它强调条件变量组合的共同作用,分析多个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特定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进而解决以集合形式表达的多重并发因果问题。并且,fsQCA方法基于等效性原则,认为同一结果可由前因条件之间的不同组合而实现[26]。本文重点考察法律维度、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协同作用,即三者构成的条件组合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复杂路径。因此,较之聚焦于单一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注重条bAt2Z7ONEGVIkP9um7Potg==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因果关系的fsQCA方法显然更契合本文的理论逻辑。因此,本文使用fsQCA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21年5月至2022年6月针对广东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20个地级市展开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收回问卷102份。在剔除未申请机构贷款、数据缺失、不同题项前后矛盾、真实性存疑的样本后,最终得到46份有效问卷。为了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使用SPSS对问卷量表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标准化Cronbachs α系数为0. 803。这说明问卷数据较为真实可靠,问卷具有较高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 735,且Bartlett检验的P值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问卷的题项设计较为合理,适合用于因子分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农地经营权强度内涵的复杂性,现存公开可用的数据库均缺乏部分必要指标的测量题项。因此,本课题组展开实地调研,搜集数据。然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较少,分布也较为分散。即使在大型公开数据,如2015年CHFS数据和本课题组针对29个省份展开的“普惠金融与‘三农’研究”调查数据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仅占全部农业经营主体的2. 5%和2. 2%。因此,本课题组搜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样本数量较为有限。为了保证样本的可靠性与代表性,本课题组考虑生产型与加工型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定农产品加工业较为发达的广东省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多元化程度较高的湖南省中部地区和江西省展开调研。在确定调研区域后,综合考虑经营主体类型、土地流转市场发达程度、区位差异等多方面因素,采用典型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各个省份抽取5—9个代表县,在每个代表县内抽取4—6个代表性样本。最终,样本内包含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多个种养类型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此,本文所用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与代表性。并且,fsQCA方法并非如计量研究般需要庞大样本量提供普适性支持。杜运周和贾良定[26]认为,fsQCA方法不仅未囿于定量研究的相关系数依赖性,也兼具定性研究的样本容量宽容性,重视有限样本中的复杂因果关系,建议样本量为10—40个之间。因此,本文的有效样本量也较为契合其需求。
(三) 变量说明
⒈结果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满足程度。基于供给型信贷配给的定义,即申请贷款但未获正规金融机构批准或全额批准,通过两个问卷题项,“您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数量是多少?”和“您曾经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数量是多少?”,即能够测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程度。然而,本文所使用的fsQCA方法,其聚焦于前因条件组合与特定结果之间的非对称关系,较之传统计量模型具有更加严谨的因果逻辑。若直接使用信贷配给程度作为结果变量,则与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在逻辑上相悖。因此,本文使用机构贷款满足程度,即实际获得的信贷数量与实际申请的信贷数量之比作为结果变量,其数值越大,代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遭受的信贷配给程度越低。
⒉条件变量
(1) 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本文从合同签订、法律登记和流转补贴三个方面衡量。农地租赁合同是以转移农地经营权为基本内容的有偿合同,它包含农地流转的租赁规则、约定租期和租金等内容,用以解决流转过程中的土地纠纷[27]。正式签订农地租赁合同的农地流转,受《民法典》“合同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法》的保护。若未签订合同,则可前往相关部门进行土地流转登记,享受法律保护。《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外,农地流转补贴由政府或有关部门发放,受国家财政资助,其政策设计中包含依法、自愿、有偿等原则。显然,农地流转补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转入农地的合法性。
(2) 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本文从农地经营权的权能结构,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四个方面衡量。占有权方面,占有权主要在于主体对农地的占有,是否排他、稳定、安全。由于转入农地的排他性已由具有法律效力的流转合同所承认,在现实情境下,影响农地流转稳定性的因素取决于农地转入期限,安全性则在于转出方违反农地流转合同的可能性[28]。使用权方面,根据使用权的法理内涵,以及农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专用性,本文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农地开展农业生产的实际自主程度衡量。收益权方面,利用转入农地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所获收益的分配,通常由流转双方合同约定或口头协商。除此之外,转入农地后的应得收益还包含征地补偿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处分权方面,围绕农地的处分权指农业经营主体处置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力,从农地入股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两个方面衡量。
(3) 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表征了经营权主体对自身权利的排他性、稳定性、安全性的主观感知。排他性感知是主体对法律、政策、地方政府是否积极维护转入农地权益,或是否为此付出努力的感知;稳定性感知是经营权主体对转出方是否可能违反农地流转合同的感知;安全性感知则为经营权主体对农地经营权实际受保障程度的主观评价。
(4) 农业收入。农业收入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一年的农产品总销售额衡量。
(5) 农地价值。从质与量两个维度出发,用农地质量和农地规模衡量。
(四) 数据处理
由于各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均由多个因素衡量,调查问卷中各测量题项的计量单位不统一,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本文参考Ragin和Fiss[29]的研究,使用5%(完全非隶属)、50%(交叉点)、95%(完全隶属) 分位点作为锚点。其次,以熵值法处理过后的数据作为基本数据,计算所有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三个锚点阈值。最后,基于锚点阈值对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进行校准,得到对应的模糊集隶属分数。表1报告了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测量题项、变量赋值、熵值和权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前,需要检验是否存在引致特定结果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与结果变量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且必要条件存在于每一个引致结果发生的条件组态中。对必要性进行分析能够得到每个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数(Consistency) 和覆盖度(Coverage),二者均为0—1之间的常数。具体来看,一致性分数代表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隶属程度,而覆盖度则表示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本文参考Ragin和Fiss[29]的研究,若某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检验结果较好,即一致性分数(Consistency) 大于或等于0. 900时,则认为该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表2展示了各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数均小于0. 900。本文进一步对所有条件变量的非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必要的条件变量,进而提高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可见,各条件变量均对结果变量有较弱的独立解释能力,不足以单独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这说明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决策不是由金融机构主观决定的,而是基于其对借款人基本素质、贷款条件等多方面考察进而形成对借款人信用水平、经营状况、还款能力及意愿的全面评估而作出的,仅一个方面突出或许难以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青睐。
(二) 组态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不存在必要条件,那么,既然不存在必要条件,则需要进一步开展综合组态分析。组态是由多个条件变量及其非条件构成的条件组合,通过组态分析能够得到一系列的结果变量实现路径,它由条件变量组合构成。从集合角度来看,即判断某一个条件组合是否是结果的子集。
第一,构建布尔集数真值表。布尔集数真值表是进行组态分析的关键,它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所有组态单个条件的赋值情况、案例数量和满足结果的组态。本文共设计5个条件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理论上包含2^5=32个组态。然而,布尔集数真值表中通常无法包含所有理论上存在的组态,因为并非每个组态都有样本与之对应。Ragin和Fiss[29]将组态分为两类:一类是存在样本与之对应的组态;另一类是不存在样本与之对应的组态,即逻辑余项。为了提高组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剔除逻辑余项,并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6] 的研究,将原始一致性分数门槛设定为0. 800,确保组态对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布尔集数真值表如表3所示。
第二,利用布尔集数真值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按照fsQCA方法的基本原理,组态分析将输出三种类型解:简约解、中间解和复杂解,分析重点在于中间解和简约解。本文在进行fsQCA分析时,出现了四类内含于简约解之中的质蕴项。然而,本文未就各类简约解是否是必要条件展开理论分析,因而将所有质蕴项加入综合组态分析。经组态分析,由各条件变量构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缓解路径如表4所示,核心条件同时存在于中间解与简约解之中,其与结果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而边缘条件仅存在于中间解,其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较弱[26]。参考Ragin和Fiss[29]的研究,本文在组态路径中分别展示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本文中的核心条件为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边缘条件为农业收入和农地价值。
由表4可知,通过法律维度、事实维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以及农业收入、农地价值的条件组合,共得到8条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作用路径。从单条路径的一致性分数与原始覆盖度来看,参考Ragin 和Fiss[29] 的研究,若单条路径一致性分数大于0. 750,原始覆盖度大于0. 200,其揭示的结果就是可接受的,且较为充分地解释了结果。表4结果说明8条路径的一致性分数与原始覆盖度均高于此标准。可见,各路径的一致性分数均高于此标准;除路径7外,所有路径的原始覆盖度均高于此标准。这说明各条路径所示的条件组态与其对应案例样本的内在条件组合之间均具有较为紧密的逻辑联系。特别地,通过查询表3可知,路径7的对应案例数量仅为1个。受限于样本量,或是导致其原始覆盖度较低的原因。但是,其一致性分数却远高于标准,且为所有单一路径中最高。因此,路径7的所示结果仍是相对可信的,具有分析意义与价值。从总体一致性分数与总体覆盖度来看,总体一致性分数为0. 692,说明所有组态均是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有效路径;总体覆盖度为0. 659,说明所有组态共能解释约65. 9%的样本量。各组态的分析结果如下:
路径1(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业收入) 的结果表明,法律维度、事实维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且农业收入较高,能够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其中,法律维度、事实维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是核心条件,农业收入较高是边缘条件。这说明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或进行了土地流转登记,且对农地经营权的排他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感知较为良好时,其供给型信贷配给得到缓解。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比较分析路径2(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地价值)、路径3(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地价值)、路径4(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地价值) 可知,若农地经营权在法律维度具有较高强度,无论较高强度的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与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是存在还是缺失,其都能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其中,法律维度具有较高强度、事实维度与感知维度具有较高强度或不具有较高强度,在3条路径中均是核心条件,农地价值较高则均是边缘条件。这说明具有法律效力的流转合同,或相关部门登记与政府补贴领取凭证予以背书,是正规金融机构放贷考量的决定性因素,起到显著的“增信”作用。考虑到事实维度与感知维度农地经营权强度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这3条路径中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被“边缘化”的原因可能是,作为抵押品的农地已具有较高价值。法理层面的合法性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考虑到农地价值在各条路径中均为边缘条件,与结果变量具有强烈因果关系的核心条件仍是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当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缺失时,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发挥着关键作用。路径5(~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地价值) 与路径6(~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地价值*~农业收入) 表明,当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缺失时,若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即使农业收入与农地价值较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也能得以有效缓解。其中,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缺失、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缺失,在两条路径中均是核心条件,农地价值较低在路径6中是核心条件,在路径5中是边缘条件,农业收入较低在路径6中均是边缘条件。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若能够行使较为完整的农地经营权,即使其权利不具有法律背书、自身感觉土地权益不受保障、农业收入与农地抵押价值较低,正规金融机构也会给予其充足的机构贷款。这说明实际权力行使非常重要,当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缺失时,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能够成为其有力补充。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
路径7(~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业收入*~农地价值) 结果表明,当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与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缺失时,若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且农业收入较高,即使农地价值较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也能得以缓解。其中,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缺失、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缺失、农地价值较低是核心条件,农业收入较高是边缘条件。这说明在转入农地不具有法律保障,围绕农地的实际权利也不尽完整,以及农地质量较差、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转入农地是排他、稳定、安全的,且农业经营收入较高时,其正规信贷需求也能被正规金融机构所认可。虽然路径7结果表明,在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与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同时缺失时,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能够予以弥补,但农业收入较高这一条件的干扰是无法忽视的,原因如下:所有组态中,既不存在可以与路径7进行类比的路径,也不存在仅感知维度具有较高强度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路径。因此,仅通过路径7无法证明感知维度与结果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可能是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与高农业收入的组合所致。可见,现阶段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并不是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有力补充。甚至,在客观的法律赋权与实际权力行使均缺位的条件下,收入所表征的还款能力或是较之主观感知更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
此外,路径8(~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业收入*农地价值) 呈现出与其他组态不一致的实现路径。路径8结果表明,即使3个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均不高,且农业收入较低,但当农地价值较高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也能得以缓解。其中,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这三个维度的农地经营权缺失,以及农地价值较高是核心条件,农业收入较低是边缘条件。这说明农地作为可抵押固定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因农地质量较好、农地规模较大引致的高农业收益预期而得以释放。
(三) 稳健性检验
在必要性分析与组态分析中,本文已通过对所有条件变量的非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并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6]的研究,将一致性分数阈值由0. 750提高至0. 800来提高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与有效性。进一步地,本文参考张明等[30] 的研究,首先,将模糊隶属分数的转换锚点从5%(完全非隶属)、50%(交叉点)、95%(完全隶属) 调整至10%(完全非隶属)、50%(交叉点)、90% (完全隶属)。其次,计算条件变量以及结果变量的锚点阈值,并重复后续所有分析步骤。经检验发现,所得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变化。最后,将一致性分数阈值从0. 800提高至0. 810进行分析,得到表4中除路径3、路径4的所有原路径。新的路径3(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地收入*农地价值) 和路径4(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农地收入*农地价值) 较之原路径3和路径4 无显著变化,仍能通过与路径2 的比较验证假设2。并且,总体一致性分数提高至0. 723。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农业经营制度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与传统小农相比,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常具有规模化、长期化的资金需求。但是,其最主要的资产——农地,却因产权不清、细碎化、分散化等原因无法被正规金融机构所认可,面临严重的供给型信贷配给。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农地经营权的产权强度较弱。那么,厘清农地经营权强度能否,以及如何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遭受的供给型信贷配给,对于农业现代化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法律、事实、感知三个角度对农地经营权强度展开维度化分析,阐述各维度农地经营权强度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作用机理与具体路径,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方法进行综合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法律、事实、感知三个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同时具有较高强度能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其次,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是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核心条件,无论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是否存在,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足以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得以缓解。再次,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也是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核心条件,当法律维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缺失时,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对于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起到了显著作用。最后,在法律维度和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缺失时,仅凭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不足以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得以缓解,需要高水平的农业收入给予辅助。
(二) 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三权分置”赋予农地经营权的经济效应。多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互相协同,之所以能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遭受的供给型信贷配给,根本原因在于“三权分置”提供的理论与制度基础。因此,基于释放农地经营权的德索托效应之考量,进一步完善、创新现有土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明晰农地经营权的法理性质与权能结构,维护正式制度的绝对解释权。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强化,足以在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缺失的不利条件下缓解信贷配给。这肯定了经营权入法的积极意义,说明法律赋权在释放经营权经济效应方面的效果已初步显现。但是,经营权的权利性质不清、边界不明、权能结构混乱等问题,势必削弱法律层面的产权强度。因此,需要从法律定位、明晰权能等角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法律作为正式制度的强权赋能之效。
第三,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积极探索农地抵押贷款的多种实现形式。健全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地产权交易、完善土地纠纷治理机制,以切实维护农地经营权的完整性,提升事实维度的经营权强度。并且,正规金融机构也可适当提高除书面合同与法律登记外的抵押物价值评价因素的权重,进而得以在不违背市场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助力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本深化。
第四,注重土地政策宣传与土地纠纷处理,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产权感知。法律层面的产权保障缺失,事实层面的实际权力虚化,均会引致土地纠纷等集体维权事件,弱化产权主体的排他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感知。因此,需要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地经营权的法律界定与实际权能结构的认知,提升其排他性与稳定性感知。并且,政府应注重解决农地纠纷,保护置于公共空间的农地剩余索取权,提升其安全性感知。从感知维度强化农地经营权,赋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农地开展生产、投资、抵押的信心。同时,需要进一步提升农地作为抵押品的价值,进而增加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意愿。
参考文献:
[1] 王蔷,郭晓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研究——基于四川省的问卷分析[J].财经科学,2017(8):118-132.
[2] 周月书,王雨露,彭媛媛.农业产业链组织、信贷交易成本与规模农户信贷可得性[J].中国农村经济,2019(4):41-54.
[3] 陈军,帅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融资约束与融资担保——基于湖北省的数据考察[J].农村经济,2021(2):95-104.
[4] 张德元,潘纬.家庭农场信贷配给与治理路径——基于安徽省424户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5(3):59-63.
[5] 彭魏倬加,刘卫柏.种养专业大户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南4个试点县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8,38(12):176-182.
[6] 顾庆康,林乐芬.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能缓解异质性农户信贷配给难题吗?[J].经济评论,2019(5):63-76.
[7] 黄惠春,曹青,曲福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性及其约束条件分析——以湖北与江苏的试点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4,28(6):44-50.
[8] 刘守英,高圣平,王瑞民.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权利体系重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5):134-145.
[9] 米运生,石晓敏,张佩霞.农地确权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准入门槛视角[J].学术研究,2018(9):87-95.
[10] BARZEL Y. What are property rights, and why do they matter?A comment on Hodgson’s article[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015,11(4):719-723.
[11] 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4):1-44.
[12] 罗必良.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J].农业经济问题,2019(1):17-31.
[13] GELDER J L V. What tenure security?The case for a tripartite view[J]. Land use policy,2010,27(2):440-456.
[14] COASE 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2):72-74.
[15] 罗必良. 科斯定理:反思与拓展——兼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改革与选择[J]. 经济研究,2017,52(11):178-193.
[16] BESLEY T J.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5):903-937.
[17] 田传浩.土地制度兴衰探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38.
[18] 何一鸣,罗必良,高少慧.产权强度、制度特性与农地权益[J].贵州社会科学,2014(2):37-43.
[19] GELDER J L V. Feeling and thinking: quant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nure security and housing improvement in an informal neighbourhood in Buenos Aires[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07,31(2):219-231.
[20] SJAASTAD E, BROMLEY D W. The prejudices of property rights: on individualism, specificity, and security in property regimes[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2,18(4):365-389.
[21] BARZEL Y.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342-384.
[22] 钟文晶,罗必良.禀赋效应、产权强度与农地流转抑制——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3):6-16+110.
[23] 仇童伟,李宁.国家赋权、村庄民主与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基于农户的土地产权合法性、合理性和合意性认同[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3):71-88.
[24] 罗必良.产权强度与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个引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6.
[25] LESLIE 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am Smith[J]. Fortnightly,1870,47(8):549-563.
[26]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33(6):155-167.
[27] 崔梦溪.民法典时代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特殊性的立法实现[J].资源科学,2021,43(8):1628-1637.
[28] 胡新艳,王梦婷,洪炜杰.地权安全性的三个维度及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9(11):4-17.
[29] RAGIN C C, FISS P C. Net effects analysis versus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C]//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190-212.
[30] 张明,蓝海林,陈伟宏,等.殊途同归不同效:战略变革前因组态及其绩效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9):168-186.
(责任编辑:巴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