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灯塔
2024-09-21卢铭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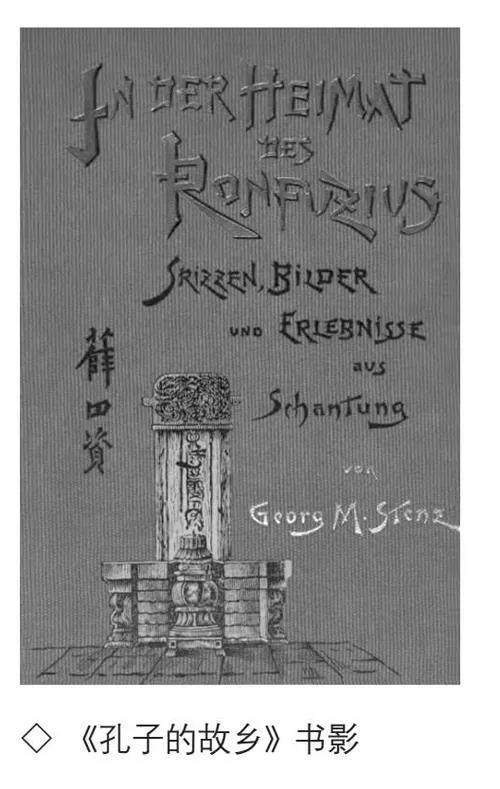
存世遗珍
来华传教士中文报刊肇始于1815年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传教活动解禁,传教士在华办报创刊与日俱增,至新中国成立前达近900种。
不过,传教士报刊林林总总,其语言多见于中文,外文少之又少,德文更是稀见。笔者在整理近代德人在华创办的德文报刊时,在德国发掘了《济宁德华学报》(Leuchtturm)。这是目前可知的传教士唯一德文学习刊物,存世量少,在中国和德国各大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未能得见,馆藏于德国圣奥古斯丁“华裔学志”研究所(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的藏书室,仅存13期,即第一卷(1914)第一、第二、第十期以及第二卷(1925—1926)的第一至第十期,且为孤本。
《济宁德华学报》1914年1月创刊,发行一卷后休刊。按该报主编、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传教士薛田资(Georg Maria Stenz,1869—1928)的说法,因当地有人“被挑唆”反对这份杂志。1925年10月复刊,然而这份刊物“定户太少”“损失太巨”,且“时值不佳”,战争让刊物雪上加霜,“邮途屡生不虞”“宣传亦倍多困难”。因无资金的支持,杂志难以为继,于1926年7月发文告别,彻底停刊。《济宁德华学报》孕育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之中,不仅涉及传教士在华报刊史,还牵扯到德意志帝国在华扩张史和德国人在华办学史。因此这份刊物虽创刊于20世纪初期,但若要究其创刊背景,必须回溯至19世纪末。天主教传教会圣言会于1875年在荷兰斯泰勒创会,1879年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93年薛田资接受派遣,于当年10月抵达中国,深入鲁西贫困地区布道。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大多扮演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全球扩张急先锋的角色。其殖民色彩引发当地民众的反感,激起民教矛盾。薛田资好斗和傲慢的性格加剧了与当地居民的冲突。经年累月的积怨于1897年11月1日在山东巨野爆发,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薛田资侥幸逃生,但同行的另两位传教士丧命。
然而,两名传教士之死为德意志帝国制造了一个绝好的借口。事件发生5天后,对中国觊觎已久的德国皇帝利用这一事件,下令出兵胶州湾,最终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实现了在东亚占领一个重要军事据点的野心。圣言会传教士从中获益,利用教案赔款,大兴土木,修建教堂,于1909年兴建“济宁中西中学”。薛田资担任首任校长,聘用外籍教师,雇佣中国教师负责国语课,意在提供“全面的通识教育”。1912年,这所学校获得民国政府的承认。
以知识启蒙为宗旨
1914年1月,薛田资集聚济宁中西中学的师资力量,主要针对“那些还不能讲j64VH5Wq0sLEtqsAyRn0I0EhTQBEVhyuM+Zl6gsrP0M=特别好的德语以及那些想继续学德语的人”,创办《济宁德华学报》,在青岛天主堂印刷,计划每月发行一期。
办刊源自薛田资在现实之下的内在需求。传教地缺学校,更缺书刊。薛田资等传教士面临着报刊匮乏的现状:“我们没有天主教日报,据我所知,只有可怜的小周报和两份月刊……”他自认办此刊可纾困:“至若竭吾等之时间与工作,以从事一种善举,岂非吾等所乐为。”对于德语初入门的中国学子而言,国内德语书籍稀缺,德文原版图书或杂志难度又太高,德语学习难度太高;另外,一些中国学子虽有一定基础,但离开课堂后,并不懂得“如何继续学习这门语言”。因此,薛田资断言《济宁德华学报》的重要性在于,读者“欲于德文内更谋深造”,“除一如此之刊物外,几无适宜读品”。为便于读者学习德语,大部分文章为德文,部分内容为中德对照。小部分文章为汉语文章,供翻译练习。中文部分横排和竖排混用。大部分文章附有尾注或脚注,解释难度较大的词语。
从知识传播角度来看,启蒙意图从刊名中便可窥知一二。刊物德文名为“Leuchtturm”,中文意为“灯塔”,并不能与其中文定名《济宁德华学报》对应。对取名的缘由,薛田资在创刊号首篇文章《总论》中有所揭示:“亲爱的读者,你是否曾见过一座灯塔?中国沿海地区有许多灯塔。它们耸立在海岸线和大海的危险地带。夜晚,灯塔顶部闪烁着光芒,为船夫指引前往港口的正确道路。”在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赋予了光和光线祛除知识蒙昧、启迪理智的作用。灯塔在此是种隐喻,喻示黑暗之中的引领之光。《济宁德华学报》试图起到暗夜灯塔的作用,给讲德语的年轻人“指明正确的道路”。
就封面设计而言,灯塔作为这份刊物的化身,经历从“隐”到“显”的过程。第一卷封面的设计类似中国对联的风格,采用框形结构:上方印德文主标题“Leuchtturm”,副标题为“Zeitschrift für Deutsch-sprechende Chinesen und Japaner”,意为“为讲德文的中日人士出版的杂志”,副标题下方以小字写着由济宁中西中学出版;第一期正中用繁体纵向列出中文刊名,第二期起,正中左边标明阳历时间,右边标明卷期;框形结构下方标明杂志的价格及订购点。
第二卷标题和封面均有变化。首先,封面设计仍为框形,但中文繁体刊名被放置在框外上方中间,左右两边分别是期卷信息。框内最上一行为副标题,“Monatsschrift für Deutsch-sprechende Chinesen”,意为“为讲德文的中国人出版的月刊”,缩小了读者范围,将目标群体锁定在中国。其次,框形结构的正中改印一座海边的灯塔,两边用繁体写着“灯塔”两字,灯塔上方飘扬着旗帜,向外发射光芒,下方是德文“Leuchtturm”,塔的下方两边分别标明1925和1926,显然是第二卷出版的年份。
边缘的宗教、中心的科学
知识启蒙的意图也贯穿于栏目编排中。《济宁德华学报》在内容上与济宁中西中学的课程配套,旨在帮助学生“复习课堂上学习到的内容”。中学核心课程有国语、德文、数学、物理、化学、算术以及选修课程英语。与之相适,杂志文章可分为科学知识、政治新闻、诗歌、散文、游记、轻松愉快的俗文学、以语言习得为目的的语法、会话、翻译及其他,另附有尺牍。
毋庸置疑,对一份传教士刊物而言,引人关注的是宗教与科学在其中的关系。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在来华传教士观念中,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正如《广学会年报》的宣告:“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补排斥的,他们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
对科学的重视确实能在《济宁德华学报》中得到印证。据《济宁文史资料》载,拥有教会背景的济宁中西中学也设置了教授天主教教义的“要理论证”课程,但这份报刊的宗教色彩甚为薄弱。这或许可从主编的文字中推断一二。薛田资在感慨传教士报刊稀少时,用一个转折“然而主要是宗教内容”指出现有报刊的局限性。显然,他对天主教报刊现状并不满意,这个“然而”也预示着,他所办刊物并不以宗教为重点,而确实他也做到了这一点。纵观现有史料,宗教与教会内容被边缘化了。
目前笔者仅辑录到第一卷第十期与教会相关的报道《教皇选举与和平追求》(Papstwahl und Friedensbestrebungen)。与之相反,科学知识在《济宁德华学报》大行其道,从创刊伊始便占据了核心地位,并呈现以下特点:从地理维度来看,观照中西;从内容来看,既有科普文章,又有现代技术的介绍。
物理、生物和科学是科学知识传播的重点。第一卷第一、二期连载科普文章《光学》(Lehre vom Licht),以问答形式介绍光的知识;数学专栏“给我们的数学家”(Für unsere Mathematiker)用德语传播数学基本知识;第二卷第三期文章《泉水、小溪、河流、溪流》(Die Quelle, der Bach, der Fluss, der Strom)、第二卷第四期文章《论太阳》(Von der Sonne)和第二卷第十期文章《我们植物的叶子及其意义》(Das Blatt unserer Pflanzen und seine Bedeutung),介绍了自然和生物知识;第二卷第八、九期连载文章《肺结核》(Die Tuberkulose),介绍了这种疾病的症状和预防;第二卷第十期文章《纸张及其制作》(Das Papier und seine Bereitung),简介了欧洲的造纸历史。
科学的发展不得不使传教士折服。在第二卷第一期文章《交通工具飞艇和飞机》(Luftschiff und Flugzeug als Verkehrsmittel)中,执笔的传教士不得不惊叹:“我们现在生活在20世纪,这个世纪经常被称为蒸汽和电力的时代。……蒸汽和电力这两样东西在现代人的生活、科技和交通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这两种技术极大地帮助世人克服距离问题。同样使写作更便利的是打字机,第二卷第九期文章《打字机》(Die Schreibmaschine)的作者以亲身经历介绍了这一机器的使用及其历史。此外,第二卷第七期撰文《孜孜不倦的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 ein Mann der Arbeit)和同卷第八期《德国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 Ein deutscher Mann)分别介绍了两位杰出的现代科学家。
诚然,科学和知识并不是唯西方独尊,对中国自然知识和科学的介绍也体现在第二卷第七至第十期的内容中。薛田资在第二卷第七期撰文《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研究》(Das Studium der Geographie im alten China),回顾了从周朝到清朝的地理学书、被他称为“科学考察”的国外远行以及早期旅行文献。他惊讶于中国古人向外探索的勇气,先进的古人和落后的清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文末慨叹:“向这些勇敢的人和研究者致敬!遗憾的是,后人将中国与其他世界隔绝开来,没有在古人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在一惊一叹之间,薛田资隐晦地批判了晚清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样令德国传教士唏嘘的是中国第一列火车的命运,虽然这列火车也经常使用,但由于顽固不化的官员,象征着现代技术的火车被停用和分解。这在第二卷第十期《中国第一列火车》(Die erste Eisenbahn in China)中有所简介。
除此之外,杂志在第二卷第八期通过数篇短文《漆树》(Die Firnissbaum)、《桐树》(Der Tungschu)、《五月》(Der Mai)、《杜鹃》(Der Kukuk)和《白虫蜡》(Das Wachsinsekt)介绍了中国的自然知识和气候。
对中国的表白
薛田资此时来华已逾二十年,滋生了两极分化的微妙情感。一方面,他受限于时代,内心固有的西方优越感使之抗拒和鄙视不接受传教的异教徒,即拒绝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人。其早期作品《孔子的故乡》(In der Heimat des Konfuzius,1902)产生于民教矛盾正严重之时,在书中薛田资在多处使用侮辱中国人的字眼,如“黄色辫子男”“中国流氓”等。
厌恶、藐视,是他对待反教村民的态度。至于其中国情怀的另一面,薛田资研究专家斯蒂芬·普尔(Stephan Puhl)十分有见地地指出:“毫无疑问,他喜欢‘他的’中国人,尤其是接受其传经布道的天主教徒,并努力保护他们免受欧洲人的成见。”同样可推断,薛田资将《济宁德华学报》看作“他的”场地以及启智园地,将刊物读者视为“他的”听众以及启智对象。
到20世纪20年代,薛田资对中国的看法有了较大的转变。日久岁深,他不得不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中国是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他在《学生与祖国》(Studenten und das Vaterland)一文中表白:“我在中国已逾我年龄之半……我很喜欢中国,而见这美丽富裕的国土,反侧这样贫困,也是与每个中国人感觉到一样的痛苦。”他认为“中国的福运”,必须依靠现代教育,因此寄希望于“求学的青年”。在这一点上,薛田资的见解呼应了梁启超之“少年强,则中国强”。他在杂志创刊号呼吁:
你们中国年轻人,学德语吧!如果你们想报效祖国,如果你们想获得渊博的知识,那就学习德语吧!中国是一个如此富饶美丽的国家,人民是如此善良。你们一定要为祖国争光!你们学得越多,可教的便越多。过去,你们的国家是如此闻名,你们的科学是如此发达;在你们的古书中,你们读到了父辈们的伟大发明。你们必须也能够重获这一切荣耀。
薛田资肯定20世纪初中国青年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运动,称赞之为“一种伟大而有价值的工作”,否定了“轻藐读书”的态度。面对外人办学缺乏“爱国心”教育的质疑,薛田资澄清道,如果外人所办学校着眼于学生的“根本”,以便他们将来报效祖国,那它们是“为中国有利益的学校”。他认为,中国青年学生救国有两个前提。一是获得“善治国家”的必备教育,而非“浮浅的学识”。二是拥有美德,“学识固然是好的,且是紧要的”,“但徒有智识,也是无济于事……”一个受过教育但道德败坏的人也会将国家“陷于败坏”。
具体来看,薛田资宣扬效法德国,复兴中国,“重现其昔日辉煌”。其中,民族自豪感起到作用。他举其他国家为例,力证德国科学的发达:“为什么日本的大学过去和现在都有德国教师?为什么日本每年都向德国派遣最重要的学者?为什么南美年轻的新国家、聪明的北美人需要德国教师、官员和商人?所有科学都在德国蓬勃发展。”薛田资力劝中国读者以德人为师,借助现代科学走出低谷,实现振兴。
结 语
知识启蒙,而非传经布道,为《济宁德华学报》之宗旨。从传教士在华所办报刊史来看,这份刊物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传教士办刊活动有重大的意义。从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来看,这份刊物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德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可起补益的作用。尤其是薛田资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争议的传教士,在杂志中呈现出对华态度的转变,可弥补学界目前对其晚期对华态度的观照不足。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近代中国德文报刊文学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VJX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