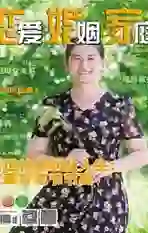“后现代老太太”陆晓娅:我就是我
2024-09-11潘彩霞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份温暖,在今天这个世界,像初升的阳光一样,一点一点地漫过无边的大地。”
从媒体人到公益人
新闻人、心理人、教育人、公益人,这是贴在陆晓娅身上的标签,她自称自己是“斜杠老年”,学生们则亲切地称她“后现代老太太”。
陆晓娅曾是《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是公益机构“歌路营”的创始人;近年来,她出版了《给妈妈当妈妈》《旅行中的生死课》等多部著作;她还是生死教育的先行者、践行者,安宁病房的志愿者,以及“墓地导游”。
面对诸多身份,陆晓娅调侃自己:“我不是学者,我有点学者气质;我不是作家,我也能写俩字;我不是旅行家,但我也四处晃荡;我不是医生,但我也穿着白大褂服务病人……我就是陆晓娅,一个独特的我。”
陆晓娅的一周从走进北京泰康燕园康复医院开始。早在2021年7月,她就以心理师的身份为生命末期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志愿服务。每个周一和周四的早晨,她都会坐50分钟地铁赶到医院,八点半准时进入安宁病房服务,一直到下午五点半才会离开。
穿行在病房,她身姿挺拔而优雅,声音清晰而有力,没有人相信,她已经71岁了。
公益人的身份,由来已久。2008年之前,陆晓娅在《中国青年报》做了27年编辑、记者。年轻时,因为一次采访,陆晓娅有了创办“青春热线”的想法。她去游说报社领导:“做起来不是很难,只需要一间办公室和一部电话,再招募一些志愿者。”
1991年,中国第一部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青春热线”正式开通。在这个“第二战场”,陆晓娅倾听年轻人的生命故事,了解他们的迷茫和困顿,在自问与他问中尝试回答“活着有什么意义”。
为了使自己更具专业性,45岁那年,陆晓娅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心理学,从硕士到博士,4年后,她成为首届注册系统的心理督导师。
“青春热线”的团队越来越专业,通过与青少年的对话,陆晓娅深切感知,很多问题在童年时就已经种下,于是,她把目光聚焦到随父母进京读书的“流动儿童”身上。
2007年的一天,陆晓娅去打工子弟学校访问,和学生互动时,有个孩子说:“北京太小了!”这让陆晓娅感到意外,同时,她也看到一些事实,这些孩子生活在城中村,没有坐过公交、打过电话,他们住的房屋狭小简陋,有的孩子甚至睡在父母的床底下。
脑海里,一个计划逐渐成形。2008年,陆晓娅从报社退休,带着“北京太小了”的故事,她和同事杜爽找到基金会。就这样,由“成长”的英文“growing”音译而成的公益机构“歌路营”诞生了。
很快,第一个项目“打工子弟城市学习与探索”应运而生。此后,陆晓娅每天通勤3个小时,去五环、六环外的打工子弟学校上课,通过室内课、情景模拟等方式,让“流动儿童”认识城市,融入城市。
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歌路营”又相继开发出多个项目,后来,他们将服务对象从城市延伸到农村。
“歌路营”的研发能力受到行业认同,作为创始人,陆晓娅非常欣慰,然而60岁生日那天,她却不得不对伙伴们宣布:“对不起了,我只能干5年,因为我妈妈的认知症已经发展到快要不认识我的程度了。”
“给妈妈当妈妈”
2007年,陆晓娅的母亲被确诊认知障碍。陆晓娅是长女,她必须花时间照顾母亲。尽管,只是出于责任,而不是“无条件的爱”。
长期以来,陆晓娅与母亲的关系是疏离的。父母都是驻外记者,她从小被寄养在外婆家,5岁回北京上幼儿园,全托,10岁见到母亲时,觉得母亲是个“陌生人”。青春期时到农村插队,父亲经常来信,满含温情,相较之下,母亲写的信“像报纸社论”。后来,他们从巴黎回来了——父亲罹患癌症。父亲去世后,陆晓娅对母亲例行公事式的探望,也大多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如今,陆晓娅却要把母亲当孩子一样照顾。当母亲情绪失控,大骂陆晓娅“什么玩意”时,陆晓娅难过地哭了。
有一天,陆晓娅陪母亲逛公园,回家后,她和保姆坐着聊天。一旁的母亲感到被冷落了,突然暴怒起来,使劲拍床表达不满。陆晓娅也生气了,多日来积累的情绪终于爆发:“我不是圣人,我受不了这种没事找事、假装耐心、没完没了的陪伴了。我想阅读,我想写作,我想备课,我想有精神上的交流……”
把母亲丢给保姆,陆晓娅仓皇逃离。
在地铁上,陆晓娅冷静下来,陷入自责。“她是你妈,她生了你、养了你,现在她生病了,你应该放下一切来陪她。”可是,潜意识又告诉陆晓娅,自己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恐惧与焦虑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陆晓娅看到一句话:“如果你仍然感到委屈、喜欢抱怨的话,说明你还在受奴役。”
“是的,我仍然被母爱缺失的心理阴影所支配。”陆晓娅被警醒了。母亲一生的影像开始浮现在脑海:童年时饱受家庭创伤,长大后投身革命建立家庭,可就在有机会实现女工程师梦想时,母亲因为怀了陆晓娅而不得不放弃。
“她不是故意的,这其中也有时代的原因。”陆晓娅不再纠结于母爱,放下怨恨,她陪母亲散步,为母亲读绘本,帮母亲洗澡擦背,在涂抹润肤露的同时,也揉进了自己的怜惜之情。
渐渐地,陆晓娅发现,一向强硬的母亲变得柔软了。散步时,母亲不再像以前一样甩开陆晓娅的手,而是紧紧攥着。终于有一天,母亲冲陆晓娅绽开“开花状的笑容”,那一刻,陆晓娅被治愈了。照顾母亲,也是在疗愈自己。可即使这样,衰退仍然不可逆转,母亲逐渐认不出儿女,她喊陆晓娅“妈妈”。
陆晓娅也不纠正,她问母亲:“我这个妈妈当得怎么样?” “还不错。”母亲说。
日复一日的煎熬与挑战,陆晓娅都记录下来,并在写作中找到陪伴的意义。2015年,母亲完全失去认知后,陆晓娅将母亲送到精心挑选的养老机构,交给更加专业的照护者。每周至少4天,陆晓娅和弟妹轮流探望,他们被称为“模范家属”。
从委屈、烦躁到谅解、接纳,陆晓娅认识到自我成长的重要性。63岁时,她开始自学英语,一来,据说学一门新的语言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二来,为独自出国旅行做准备。
一年后,她尝试阅读著名心理学家欧文·亚隆的原版自传,没想到,竟然囫囵吞枣地读完了,这让她喜出望外。两年后,陆晓娅已经能一个人去看世界了,短短几年,她的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2019年,在西班牙的旅行途中,她接到电话——母亲出现了心肌梗死症状,以最快的速度,她飞回北京。
患病13年后,母亲平静离世。在哀伤中,陆晓娅翻看自己的陪护笔记,几度泪流满面。最初的无奈早已化作对生命的观察,她将笔记整理补充,于2021年出版了《给妈妈当妈妈》,用文字去抚慰那些和她一样的照护者。一年后,她又把旅行笔记结集出版,这便是《旅行中的生死课》。
生死学的探索者
2024年5月,作为“墓地导游”,陆晓娅受邀带领一批学员远赴日本参观墓园,继续探索“死亡”这个深不可测却又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阅读、写作和旅行中,陆晓娅思考最多的就是生死。32岁之后,陆晓娅经历了几次“死亡惊吓”——她患了肿瘤,所幸每次手术都有惊无险;52岁时,大学好友突然去世,她意识到,“死亡永远比预期来得早”,于是,她写下了人生的第一份遗嘱。
“唯有面对死亡之时,一个人的自我才真正诞生。”可是,谈论死亡,难以开口,通过大量的阅读,陆晓娅为自己赋能。2012年,当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她开设一门通识教育课时,她首创了“影像中的生死学”。出乎预料,这门闻所未闻的“生死课”被学生们“秒选”。以电影为媒介,陆晓娅引领学生们“坦然直视死,纵身跃入生”。
在课程开始前,陆晓娅让学生们写下“死亡离我们有多远”,这时,有学生提议:“可以改为‘死亡离我们有多近’。”答案收上来了,结果让陆晓娅意外,“他们经历的死亡事件远比你想象得多。但是这些事情过去了,其实并没有机会说,没有人来和他们聊一聊。”
不知不觉中,改变发生了,有的学生说:“陆老师,上了这个课,我重新拿起画笔开始画画。”还有的说:“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通过“生死课”,他们收获了生命的热情。
这门课,陆晓娅一开就是5年,2016年,她将授课笔记一一整理,出版了《影像中的生死课》。
“思考死亡,其实就是思考怎么活着。”2021年,陆晓娅成为安宁病房的志愿者,在那儿,她和生命末期的患者上演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一位老人,腹部长了肿瘤,她没有告诉子女,独自来到安宁病房,她不怕死,只想“不给孩子们留下任何心理阴影”。
得知老人年轻时当过幼儿园园长,陆晓娅带着她做冥想。“您还记得吗?这双臂膀曾经抱过多少孩子,还记得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吗……”在舒缓的声调中,老人的面容宁静祥和。冥想结束,陆晓娅这才发现,不知何时,老人的女儿已从国外赶回来,此刻,她已泪流满面。
在安宁团队的安排下,老人在病房举行了家庭会议,那天,儿孙绕膝,她特意换了一件镶着花朵的黑色衬衣,语气平静而庄严:“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离开。”从容不迫地,她在预期的日期带着尊严走了,子女们没有恐惧,生死两相安。
另一位百岁老人,曾是中学特级教师,只要有空,陆晓娅和同事们就会齐齐喊一声“老师好”,然后围着老人听他讲新陈代谢。第21天,老人睡着了,眼角,一滴泪晶莹剔透,那是不舍,而非遗憾。感动之余,他的一个女儿说:“我在这里受到非常大的教育,原来死亡可以是这样的。”
死亡也可以温情脉脉,陆晓娅感慨万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份温暖,在今天这个世界,像初升的阳光一样,一点一点地漫过无边的大地。”
帮助老人回溯人生,寻找“自己的意义”,陆晓娅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必要的。
2022年的一个夏夜,陆晓娅捧读《一个人最后的旅程》,当目光触到“临终难民”这个词时,她猛然打了个冷战。从急诊室到ICU再到太平间,这是大多数人的临终程序。“留在亲人脑海中的,是仓促、混乱、隔绝和冰冷,爱与温暖,在临终过程中不断地脱落,让丧失之痛,痛上加痛。”
“我深刻感受到,有准备的死亡和没有准备的死亡是完全不同的。”为此,陆晓娅又把推广“生前预嘱”作为己任,积极宣讲。有位梅阿姨,在陆晓娅的协助下,豁达而亲切地完成签署。陆晓娅离开病房时,梅阿姨挥着手说:“我想通了,你放心吧!”
到了2024年,陆晓娅在安宁病房志愿服务已超过1000个小时,遇到的人、发生的事,带来哪些冲击和思考,她都会及时记录,“没准儿能写一本《安宁病房中的生死课》呢。”
这些丰盛而精彩的生命故事,让陆晓娅精神抖擞,勇敢前行。每年的生日,她都会重新写一份遗嘱,当作“自我革新,自我成长”。
“要不怕死,先得好好活,充分地活。”精神导师欧文·亚隆的话,她终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