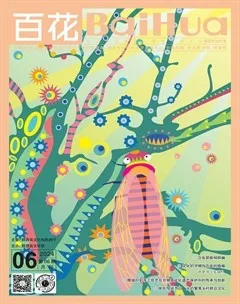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都市文化危机及拯救
2024-08-20管文慧陈曦
摘 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聚焦《星期六》中的都市文化危机,剖析西方现代都市社会的病态现象,揭示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及其生存逻辑,并提供了疗愈都市文化病症的出路。
关键词:《星期六》;麦克尤恩;都市文化危机
《星期六》是伊恩·麦克尤恩后期社会关怀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以高度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国际大都市伦敦为空间背景,讲述了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在星期六这一天的都市体验,折射出西方现代社会的病态症候。国外学者苏珊·格林借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麦克尤恩是如何通过聚焦任务描述和概念隐喻来凸显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思维,以此剖析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政治、伦理等主题。国内或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叙事学理论来解读作品中的道德叙事[1],或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解说小说《星期六》蕴含的交往思想[2]。多样化的阐述丰富了我们对该小说的理解,也印证了该小说所具有的恒久魅力。笔者从社会学的视角聚焦《星期六》中的都市文化危机,剖析都市社会的病态现象,由此传达麦克尤恩对都市文化的深入思考及其作为英国国民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都市文化主体异化
在资本进入都市空间后,都市人在资本之中发生了变异。[3]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来说,都市是异化的空间,“他人即地狱”成为都市生活难以摆脱的偈语。《星期六》设定在“9·11”事件发生后。尽管“9·11”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但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颠覆了人对生存价值的认知,冲击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秩序。个体在残酷的战争中变得渺小,这种生存境遇使自我无法顾及他人,个体的人性道德伦理崩塌。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加剧了个体异化,个体逐渐丧失伦理判断能力。对这种失序的都市生活体验,麦克尤恩从都市主体异化的两大方面——人与自身的异化和主体间性的异化,传递出他对都市文化危机的忧思。
第一,人与自身的异化。资本和权力构建下的都市社会加速了商品拜物教的盛行,人沉溺在消费中,沦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成为单向度的异己之物。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空虚的都市人如同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游走在都市空间之中,异化为无灵魂的独行者。小说主人公贝罗安是位颇负盛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他笃信科学,推崇进化论,拥护西方文明。贝罗安惊叹于工业进步,认为伦敦已经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机器时代”[4],绚烂多彩的商品世界更是让贝罗安欲罢不能,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贝罗安购买了一辆限量版奔驰S500,以奖励自己努力工作。处在资本消费的都市空间中,贝罗安消费的已经不是以物为代表的符号,而是被赋予的符号象征,是作为身份高低和财富多寡等区别的消费。不仅如此,对他来说,工作和效率就是第一生产力,“唯有工作才能让他专心致志,除此之外的事情都让他不胜其烦”[5]。工作和工作带来的物质享受驱逐了贝罗安对精神意义的追寻。他甚至忽视了亲情的重要性,与妻儿之间缺少交流,对岳父充满敌意,与母亲无法沟通。这种情感的麻木和默然体现了贝罗安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被金钱和物质的非理性精神所钳制,迷失在物质欲望之中,失去了文化内省意识。
第二,主体间性的异化。在人类共同生活的都市场域中,人与人的交往大多朝着自我利益的一方偏离,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价值追求。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导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裂。[6]工具价值与传统道德发生了严重冲突,带来了道德的滑坡和价值的衰微,“他人即地狱”成为都市生活难以摆脱的偈语。也就是说,主体之间缺乏理性和信任,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降格为主客体关系,从而使人陷入交往困境当中。小说中,中产阶级贝罗安和街头混混巴克斯特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差异和难以解决的交往矛盾。追根溯源是人际间的疏离感割断了二人之间的精神纽带。贝罗安作为中产阶级,举止投足间都流露出自满,这种虚与委蛇增加了两人之间的隔阂。在汽车剐蹭事故中,贝罗安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词,借其掌握的医学知识和话语,谎称有新的干扰治疗法可以治愈巴克斯特的亨廷顿舞蹈症。贝罗安并非真心实意治疗病人,而是为了逃避车祸引起的保险责任。贝罗安试图用谎言使巴克斯特就范,违反了人与人之间真诚交往的原则。同样,无论是在汽车剐蹭事故还是入室绑架案中,街头混混巴克斯特都以暴力和恐吓处理问题,隔绝了双向沟通,也丧失了向他人求助的机会。由此可见,异化交往下的主体间的关系是随时博弈状态,社会信任难以建立,人际交往逐渐混乱失序。
二、都市空间正义缺失
空间非正义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空间剥夺。也就是说,现代都市的发展是资本与权力不断融合和分流的结果,资本的趋向决定了社会话语和社会权力资源的社会配置导向,资本逐利性追求把都市空间变为商品交易的空间,都市空间异化为对空间正义的侵蚀。如此一来,都市空间生产背离了都市空间的属性,其本身应有的正当需求和空间的本真属性被破坏,继而产生相应的主流与边缘符号阵列。生活在英国工业发展和城市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麦克尤恩对伦敦空间具有独特的感知,他并没有着力书写伦敦的繁华与进步,而是强调都市化进程下的空间生产在资本与权力的角逐中逐渐背离正义的轨道。在《星期六》中,都市空间正义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对立与空间区隔问题日益突出,二是空间剥夺现象。
《星期六》中都市空间正义缺失的表现之一便是“中心”与“边缘”空间的对立。当下社会空间资源的分配以资本需求为核心,使社会结构形成“核心—边缘”的不平等模式,在空间资源分配要素的次序上,造成边缘群体越来越边缘的恶性发展现象。[7]资源分配不均扩大了贫富分区现象,人与人之间在居住空间上被贴上了“穷人”和“富人”的标签,强化了身份上的差异。于是,社会所需要的沟通、交流和尊重变得愈发困难。小说中,贝罗安的豪宅坐落在伦敦市中心费兹罗维亚区,“三只坚固的班汉姆锁,两条和房子同龄的黑铁的门闩,一个隐藏在黄铜外壳下的门镜,一个电子报警装置,一个红色的紧急呼叫按钮,警报器的显示数字在安静地闪烁”[8]。与贝罗安的豪宅形成对比的是,“这城市里还有要饭的、吸毒者和地痞流氓的存在”[9]。街头混混巴克斯特就是一个流落在伦敦街头的游荡者,但他与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身份有所不同,波德莱尔强调街头游荡者对城市现代景观的见证和观赏,而此处的游荡者的精神和意识是模糊虚无的。巴克斯特给贝罗安的印象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破旧的外套,满是虫蛀的羊毛衫,沾了油漆的裤子”[10]。由此不难推断出,居住在贫困和逼仄的生活空间里,巴克斯特不得不面对阶层划分与等级秩序的社会现实。巴克斯特私闯贝罗安的豪宅,看似是以暴力恐吓贝罗安一家,实则是在与他人的面对面中向贝罗安寻求帮助。同时这一行为也是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表现,旨在打破不平等的空间地位。
自然空间的剥夺是都市空间非正义的另一表征。都市空间发展伴随人类私欲的膨胀和资本增值逻辑,不断打破生态和道义的限度,无限制地剥夺自然资源,催生出都市生态危机。在《追日》中,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麦克尤恩就从生态哲理的维度考量了人类挥霍地球的现状和地球未来的命运。着眼于都市发展背景,麦克尤恩又将笔头指向城市自然生态空间的描写。在《星期六》中,从贝罗安的城市体验中,读者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城市生态加剧恶化,“清洁工人还在忙着清理游行示威者留下的垃圾……发电机支持的拱形的卤素灯照亮了成堆的食品残余、包装纸……这垃圾的构成很有挖掘价值……从一堆废弃的一次性杯子里探出头来”[11]。除此之外,都市空间建设更是使人与自然的直接交流与体验成为奢谈,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离。正如贝罗安在驱车看望母亲的途中,“一个长线的转弯让他经过一排排钢筋水泥的写字楼……看到里面工作的人们穿戴如同建筑的模板一样笔直,个个坐在桌前,面对着电脑,仿佛今天不是星期六”[12]。这种同质化、标准化的城市建筑展示出一幅忙碌的工作图景,个体被嵌套在资本构筑的空间里,失去了接触自然空间的自由和权利。
三、都市文化危机的现实拯救
在现代社会中,功利至上主义带来的货币文化逻辑滋生了人际关系的冷漠,导致了情感生存的异化。同时,现代人在都市文化和后工业发展的大潮中慢慢接受消费文化的洗礼,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日益丧失集体意识和文化认同。《星期六》中的都市文化危机书写精准地把握了现代性危机的症候,并且透露出麦克尤恩对拯救都市文化危机的思考:一是与异化的社会保持“距离”;二是关怀他者,重建都市伦理。
德国社会学大师齐美尔率先意识到“距离”的个体救赎意义,在这一点上,麦克尤恩拯救都市失落文化的途径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下,货币文化逐渐蚕食并建构都市文化,对主体内在的精神构成极大威胁。齐美尔指出,“距离”是现代个体对资本主义文明扩张所造成的个体本真体验被剥夺而找到的审美救赎之途。《星期六》中暗藏着“距离”对“两种文化”的平衡作用,即距离对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所代表的科学与诗人黛西所代表的文学之间的融合作用。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和信仰的贝罗安起初极力贬低文学的价值,认为文学作品充其量是作家的素材堆砌。在应对巴克斯特暴力入侵危机时,其女黛西通过朗读阿诺德的《多佛海滩》,控制了处在暴力和疯狂边缘的巴克斯特,消除了家庭危机。由此,文学的感化和疗愈功效“深深地触动了贝罗安的心灵,让其惊叹文学的力量,引发对于文学何为的认识与思考”[13]。借助小说,麦克尤恩喻指了两种文化的互补可能,即与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导向的物化生活保持距离,同时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以丰富内在的精神世界。
伦理的式微是现代性病症的形式之一,重建都市伦理对都市文化的保护作用在《星期六》中清晰可见。在“9·11”事件发生后,麦克尤恩曾发表言论,“如果劫机者能够站在乘客的角度思考,他们就不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想象成‘非我’的他者是人性的核心,这是道德的开始”。小说中,作为上层社会精英,贝罗安与街头混混巴克斯特产生交集,这类偶然事件是麦氏经典的叙事桥段。因为二者的对峙彰显了巨大的阶级差异张力,如何克服阶级矛盾,走向人际交往的和谐面构成该小说描绘都市伦理的一大亮点。小说结尾,贝罗安意识到自己拥有世俗公认的成功生活,而巴克斯特却一无所有且饱受疾病折磨。通过自我和他者伦理关系的建立,贝罗安成功打破了由阶级差异形成的区隔和边界,走出自我观念的循环,转变了原有中产阶级精英阶层的狭隘思维,最终选择挽救巴克斯特的生命。
四、结 语
麦克尤恩在小说《星期六》的序言中写道:“何为人类?我们,居住在某座城市,生于某个时代,蜕变无休无止,从属于某个群体,被科学改变,被政权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处在后机械化的环境下,激进的愿景接连破灭。”[14]《星期六》所关注的便是都市中人类的普遍生存问题,是高度机械化、高度现代化带来的都市文化危机问题。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对都市文化危机的描写,是反映21世纪初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面棱镜。同时作为国民作家的他还提供了两条疗愈都市文化病症的出路:保持与物化世界的“距离”,重视文学的精神价值;关怀他人,重建都市伦理。
参考文献
[1] 曲涛,孟健.解读后“9·11”小说中的道德叙事:评伊恩·麦克尤恩小说《星期六》[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5):90-93.
[2] 李菊花.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J].当代外国文学,2013,34(1):39-46.
[3] 刘钊.都市文化:危机及拯救[D].苏州:苏州大学,2014.
[4] 麦克尤恩.星期六[M].夏欣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5] 同[4].
[6] 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130-135.
[7] 张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正义的两重困境[J].伦理学研究,2018(3):124-128.
[8] 同[4].
[9] 同[4].
[10] 同[4].
[11] 同[4].
[12] 同[4].
[13] 尚必武.重访“斯诺命题”: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两种文化[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2):36-43.
[14] 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