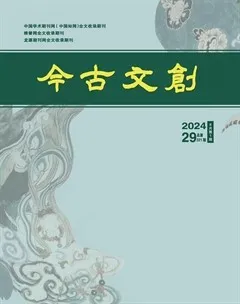唐高宗时期谏言问题研究
2024-08-20黄佩儒
【摘要】唐永徽六年(655)废王立武一事标志着高宗开始对关陇集团进行打击,逐渐收回权力,但其同关陇集团的政治斗争却对朝堂造成了不小的风波,导致权力收回后的高宗仍面对着朝堂冷淡、不积极上言的问题。高宗积极鼓励百官上谏,并通过修订礼仪、人事调动等措施平息废王立武的政治余波,试图建立上下情通的君臣关系。此外,政治制度上君主权力的集中也是君臣关系疏离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高宗;关陇集团;废王立武;谏言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7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23
陈寅恪曾指出永徽六年(655)废王立武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关键,西魏宇文泰之所创立系统至此改易,关中本位政策已不能适应大一统之格局,南北朝以来的贵族政治遭到破坏。①即关陇集团必须出让权力予山东集团,贵族必须出让权力予皇帝。孟宪实也曾指出:高宗在东宫旧部的支持下,凭借废王立武一事,成功打击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顾命之臣,实现了权力的逐步回归。②到显庆三年(658)时,反对废王立武的顾命大臣之一褚遂良卒官,第二年关陇集团中的长孙无忌、柳奭、韩瑗相继死亡,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受此牵连而遭贬官者二十一人。关陇集团已无力与高宗争夺权力,高宗同其的政治斗争基本走向结束。但废王立武的余波却继续影响着朝堂,“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 ③。重振谏言之风成为高宗收回权力后不可回避的任务。
一、重振谏言之风与平息政治余波
唐太宗贞观年间被后世成为贞观之治,尤以群臣积极纳谏、太宗从谏如流为后世所褒扬,但继之的高宗一朝却出现官场冷淡的迹象:
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④
在此之前,永徽元年(650)五月、永徽四年(653)四月和永徽五年五月都曾让群臣极言得失,以此看来显然没有收到群臣积极的反馈。对于群臣不积极上谏的情况,高宗也同当时权位最高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询问过,但长孙无忌只是含糊其词,没有为高宗分析原因所在:
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 ⑤
当时朝堂势力主要为关陇集团所把控,长孙无忌作为关陇集团的首要代表人物,既然不愿同高宗分析朝堂的实际情况,仅以政治套话来糊弄,可见正是其政治集团压抑着朝堂百官通向皇帝的声音。但当高宗从关陇集团收回权力后,官场冷淡的情况仍旧持续了近28年:
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⑥
可见高宗对关陇集团的打击使得原本压抑朝廷声音的关陇集团又转换成了帝王的威权,重振谏言之风成为此后不可回避的政治课题。
长孙无忌死后不到两年,高宗改百官名⑦,又自己自定选拔了一派官员⑧,似有一扫阴霾,别开生面之意,选官后高宗问李勣是否得当,对许圉师等新提拔的官员寄言,在他的一番称述中可见其所忧所愿为何:
朕所授未知允当与否?选贤任能,虽帝王之所务,然臣下之各进乃诚,举不失选,畴咨佥议,必尽是心。上下情通,何忧不理!但为永徽以来,颇闻朋党惩艾,此事实亦生疑。今不共公等商量,则自注定,自觉专固,以为愧也。勣等引咎拜谢。及许圉师等入谢,帝谓曰:构大厦者,必藉群材;理天下者,必资良佐。比来食禄之官,多不称职,或遽相朋附,或忘公徇私,庶政未康,或由于此。我所以就中拣择,亲注此官。各宜用心,勿踵前弊,无令后人嗤失鉴也。⑨
从“然臣下之各进乃诚……上下情通,何忧不理”可以得见,高宗一是希望百官们积极进言,打破废王立武前官场冷淡的局面。二是疑心朋党一事,早在永徽二年,高宗便对朋党一事生疑,只是那时向长孙无忌问得比较含蓄,仅说“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长孙无忌也以“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为由而含糊回答过去。在结束与长孙无忌的政治斗争后,心中仍有担心。最后则表露出来对百官的不信任,所以亲自选拔了一批官员。但高宗还是向往父亲的贞观之风,所以自定官员后反思专固,希望臣下可以各进乃诚,上下情通,藉群材,资良佐,共同治理好国家,可这一用意似乎没有被臣下体会到,臣下体会到的更多是高宗对朋党的忌讳和对百官的疑心。龙朔三年(663)八月诏百僚极言正谏⑩,自然也就没有收到百官的积极回应。麟德二年二月,又再次提无人谏言一事,但臣下李勣的回答就像当年长孙无忌的回答一样,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⑪,是因为陛下做得够好所以无可谏言。同年十二月,原本因反对废王立武而遭外贬的裴行俭征拜司文少卿。第二年乾封元年高宗东封回来后,就下诏恢复祭祀南郊感帝和神州,原本二者的取消就是因为高宗想强调礼学上更能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的“一天说”,而感帝和神州祭祀的礼学理论基础为“六天说”,认为天有六个,显然同独一无二的皇权不相符,换言之感帝和神州的取消是显庆二年高宗和关陇集团政治斗争的产物,现在被重新恢复,很可能是面对官场冷淡做出的一个政治信号,表达对关陇集团的打击已经过去,鼓励群臣共治,积极进言。第三年即乾封二年高宗实行了总祭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的改革,对此《通鉴》胡注:此兼用贞观、显庆之礼。⑫《贞观礼》的重新起用也正符合高宗想要在新的政局下重唤贞观时积极上谏、君臣共治之风的需求。同年高宗的所作所为终于有了一点回应:
上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
“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矣,是以各各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为然。⑬
从李安期的话语中可以看到百官不积极谏言的原因正是因为怕坐朋党之罪。当初在打击关陇集团时,便多用朋党之名牵引相杀,龙朔二年高宗自定官员时仍担心朋党一事,众官员也心有余悸不敢进贤,怕坐朋党之罪。可见废王立武后高宗虽然从关陇集团中逐渐收回权力,但此事的余波仍影响着高宗和百官的关系。
总章元年(668),高宗继续表达积极纳谏的政治态度:
夏四月丙辰,有彗星见于毕、昴之间。乙丑,上避正殿,减膳,诏内外群官各上封事,极言过失。
群臣对此并未真正上言过失,而是以政治套话讨好高宗,认为这是高丽将灭的天象,高宗不必对此负责,但高宗面对群臣的开解之言没有推避责任,而是做出万国之主的表率和风范,希望群臣可以极言正谏,而非敷衍搪塞之词。
第二年,高宗欲巡视凉州,大臣们多在私下议论,以为未宜游幸,却不敢面陈皇帝,于是高宗又一次因上言一事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这一次来公敏直言独进,高宗采纳其意见并擢升其为黄门侍郎,以示鼓励上言的政治态度。 ⑭总章中,裴行俭也升为吏部侍郎,或许正是高宗进一步向百官们传递平息废王立武后的政治余波的信号。
咸亨元年(670)十月,诏官名皆复旧。同年废王立武的重要功臣之一许敬宗致仕,且在两年后去世。许敬宗去世不久,即咸亨四年(673)三月,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之故,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上元元年(674)九月,下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的官爵,以无忌曾孙长孙翼袭爵赵公,并让长孙无忌陪葬昭陵。上元二年裴行俭加银青光禄大夫。上元三年(676)二月,追复于志宁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仪凤元年(677)擢升曾因反对废王立武而被贬的来济的兄长来恒同中书门下三品。仪凤二年(678)八月裴行俭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朝廷之中高宗反躬自省,平息废王立武余波的趋势越来越强,但另一方面由于高宗晚年病重,太子身体欠佳,其余皇子政治能力又不足的情况下,需要提高武则天权威以为身后事做准备。⑮于是上元元年高宗推动武则天建言十二事,上元二年提议武则天执政,此时但若百官不明高宗本意,可能还会联系到废王立武一事上,对谏言有所忌惮。
二、以制度史的角度看高宗一朝官场冷淡的原因
高宗一朝君臣关系的疏离在制度上也有迹可循:
贞观初……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郞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高宗临朝不决事,有司所奏,唯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郞、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⑯
据袁刚对唐宰相表的补订,可知许敬宗最早于贞观十九年(645)2月以太子左庶子同掌机务之职为副宰相,高宗即位后,许敬宗于显庆二年8月以侍中之职为正宰相,李义府最早永徽六年7月以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许敬宗此年则为礼部尚书,显庆元年李义府被贬为莱州司户,到显庆二年3月以兼中书令之职为副宰相⑰,也就是说“许敬宗、李义府为相”这个条件最早要等到永徽六年7月后才成HWJwtmSvqoiRCroKdIZGtQ==立,若要满足二人同时为相,则需等到显庆二年8月才成立,自此以后,高宗打破了贞观时起居郞、舍人参加仗下面奏的旧制,他们不再能知机要之事,直到大和九年才恢复贞观故事。资治通鉴对此事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屛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⑱
不仅起居郞、舍人参加仗下面奏的贞观故事被打破了,谏官、御史也随仗而出,“於御坐前屛左右密奏”可见奏事者与天子的距离之近,御史和待制官也要远远待着防止偷听。“仗下奏事”本是常朝退朝后君主和宰相等高级官员商议国事的一种形式,其议政和决策过程却逐步以皇帝为中心变得私密化,皇帝的专制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其与臣子的关系却也进一步疏远了。
“唐武德、贞观时期,朝政决策的主要渠道是宰相政事堂会议,两省给、舍在禁内封驳判案,执笔室相可以随时入见皇帝,取旨画敕,决策机构与皇权紧密结合,能够高度发挥其自身的职能。” ⑲然废王立武一事却多次撇开法定的议政场所与程序,其过程也常依靠私密的解决手段,高宗先是选择长孙无忌家这样私密性较强而非礼仪烦琐的宫禁,来劝说长孙无忌支持废王立武,并授予长孙无忌三个儿子以朝散大夫之位,后又秘密遣派使者以赏赐长孙无忌金银宝器,再动用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进行私下劝说。废王立武的重大功臣李义府、李勣在参与此事中也带有秘密性色彩,此时多数大臣还不知高宗废王立武的意图,许敬宗的侄子王德俭不知是否从许敬宗处得知,于是才有了李义府的机遇: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⑳
《资治通鉴》记此事于永徽六年7月,同李义府以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之职成为副宰相的时间点正相符,这意味着他可以加入中枢决策机构的议政活动中,帮助高宗实现废王立武。从一月后“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由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俭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 ㉑中的“闻”“私议”“告”字眼来看,此时知道高宗仍未公开与大臣讨论废王立武:
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帝后密访绩,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㉒
“畏大臣異議,未決”也可说明在李义府请废王皇后前,高宗未向大臣公开透露废王立武的意图,“密访”二字,可见李勣并非在正式的君臣议政或宰相议政场所支持高宗。武后的册立礼虽是有唐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可废王立武的决策过程却较为私密化,再加上它所造成的政治余波,君臣的关系便不能不疏远了。
永徽六年废王立武后,君臣关系在制度上的距离仍继续被拉大着:
显庆二年二月,太尉长孙无忌等奏以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㉓
高宗一朝之初本为每日坐朝视事,自此改为两日一常朝,胡寅评价其为:“高宗春秋鼎盛,天下一日万几,乃无故献谀,请隔日视事,得非取媚于房帷间乎?” ㉔前已论及显庆元年长孙无忌因废王立武失势而有向高宗低头示好的态度,但不论长孙无忌奏请的主观动机为何,减少君主与大臣的议政次数,总是在实际上便于君主个人意志的发挥,加强君主的专制权力。
龙朔年间(661—663),政治心中从太极宫移到大明宫,并因此撤销了中书和门下两省的内省建制而移至外朝,宰相要见皇帝,就有了更严格的规程,除皇帝定期在宣政殿视朝,完成礼仪性的正衙奏事外,皇帝与宰相的主要议政方式是入阁到紫宸殿议事㉕,宰相和皇帝的距离也因制度的变化而拉大了。此外,由于中枢决策机构移出宫禁,在宫禁之中紧密围绕皇帝的决策班子便出现了真空,不久后的乾封年间(666—668),我们便看到了北门学士的形成:
开元初置。已前掌内文书。武德已后……时召入草制。未有名目。乾封已后。始号北门学士。刘懿之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以苏味道。韦承庆等为之。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睿宗即位后。以薛稷。贾膺福。崔湜为之。其院置在右银台门内。驾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驾在大内。院在明福门内bf2e51badeec2c320e26a4e9a18842f5。㉖
《旧唐书》对此有进一步的补充:
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㉗
据孟宪实对北门学士的考证,“从武德、贞观以来,个别文学大臣待诏北门,是一个未曾中断的传统,除了上官婉儿独揽其事的时期以外,这个传统一直存在,并最终发展成了翰林院” ㉘,废王立武的大功臣许敬宗也在永徽时的关键时刻召入禁中驱使而非以正式途径同皇帝见面,再次可见废王立武事件的私密性。待诏北门虽是有唐以来的传统,但在乾封时形成有所名目的北门学士,当有其发展的必然性,而龙朔移宫后内朝决策班子的空缺恰好给了北门待诏之臣发展的空间。其后竟能发展为新的内朝决策机构即翰林院㉙,可见制度的变革往往起于青萍之末,正如汉武帝时召选一批文学之士出入禁中参与议政,其后竟发展为内朝中枢机构尚书台一样,君主专制集权制度下,君主的个人意志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进入宫禁、靠近皇帝、掌握机要,往往能参与进国家的中心决策中,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依靠档案文书运作的官僚政治,“公文书的运行也就是各种指令、情报的流动,在这个信息流动的网络中占据了节点的位置,也就等于占有了一种权力,进而是一种政治地位。” ㉚北门学士没有法定地位,却越过宰相同皇帝议政,越过中书省为皇帝草诏,进而掌知机要参与决策,皇帝的决策过程也进一步私密化了,君臣间的关系自然也进一步拉大了。
撇开法定议政程序,破坏原有议政和决策机构,再将决策权移于宫廷内禁,在制度的发展轨迹上我们可以看到高宗一朝君臣关系疏远的制度性因素,而另一面,则是君主对决策权的进一步控制,是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态势,也因此官场的冷淡是高宗收回权力后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三、结论
唐高宗时期,君臣关系的疏离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朝堂谏言不积极问题,一方面是由影响颇大的政治事件即废王立武和随后对反对废王立武的关陇集团的打击所造成的,一方面则是政治制度上君主权力的集中与加强所造成的。高宗积极平息废王立武的政治余波,试图建立积极谏言的环境,但却并没有在制度上有所创造以保证言路畅通,反映出自魏晋南北朝入隋唐以来,中古贵族政治的色彩逐渐淡化,皇权逐渐突破贵族政治下“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强大起来。
注释:
①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3-279页。
②孟宪实从旧臣的角度认为支持废王立武的朝臣皆为东宫旧部,认为这是政治斗争的基本单位,并以上官仪为例子,其出身关陇集团,但却也是高宗东宫旧部,在废王立武时选择了支持高宗。但出身山东的崔玄义非高宗东宫旧臣,仍支持废王立武,似更符合陈先生的地域集团说。今兼取两位先生的观点,同时认为兼取二说能更好地解释废王立武背后复杂的权力斗争关系。参见《武则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1-200页。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0-6411页。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五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86页。
⑤宋祁、欧阳修等编著:《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54页。
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0-6411页。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0,高宗龙朔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6页。
⑧王钦若:《册府元龟》卷69《帝王部·审官》,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35页。
⑨王钦若:《册府元龟》卷69《帝王部·审官》,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35页。
⑩宋祁、欧阳修等编著:《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5页。
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二年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43页。
⑫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乾封二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53页。
⑬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乾封二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51-6352页。
⑭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总章二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59页。
⑮关于高宗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安排,详见孟宪实《武则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4-342页。
⑯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新唐书》卷47《百官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8页。
⑰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重庆出版社2023年版,第272-273页。
⑱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五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28页。
⑲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重庆出版社2023年版,第223页。
⑳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六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88-6289页。
㉑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六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89页。
㉒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新唐书》卷93《李勣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20页。
㉓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07《帝王部·朝贺》,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6页。
㉔胡寅撰、刘依平点校:《读史管见》卷18《唐纪》,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61页。
㉕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㉖唐会要、王溥:《唐会要》卷57《翰林院》,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77页。
㉗宋祁、欧阳修等编著:《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43页。
㉘孟宪实:《武则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8页。
㉙翰林学士院成为内朝新决策机构的过程,详见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重庆出版社2023年版,第102-112。
㉚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孟宪实.武则天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3]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23.
[4]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黄佩儒,女,汉族,四川雅安人,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