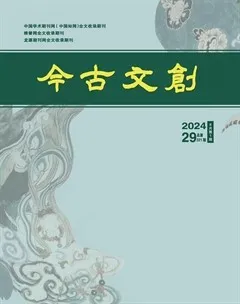王阳明思想与贵州明清文化的关联研究
2024-08-20陈欢
【摘要】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主张“心即理”,强调“致良知”“事上练”的主张,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正德元年(1506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在贵州期间开设学院著书讲学,对贵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王阳明思想与贵州明清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促进贵州省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贵州;贵阳;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6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20
一、贵州地区的历史文化
贵州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夜郎国在此建立政权。夜郎成名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据《华阳国志》记载:楚国顷襄王派“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今贵州福泉),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这时,人们方知西南有一夜郎国。“公元前227年秦朝建立黔中郡,黔东北一带纳入了行政管辖”[1]。秦汉时期,贵州境内各民族的交流不断加强,形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以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进行改土流归为契机,设置八府,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正式建省,明清之际被称为“黔中地”[2]。在清朝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包括移民、改土归流、平定叛乱等措施。
(一)贵州地区的人口和民族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全省共有民族成分56个。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各民族之间趋于交流和融合。清代“自元代军屯、卫所、官户、戍卒以及负贩商旅,来自各方,移民渐众,而苗夷同胞,遂多移居深山野谷之中,自成风俗,与世相远”[3]。“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家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黔北历史上长期受播州宣慰司管辖,杨氏土司地区汉化较早,汉族移民人口多。而黔西南地处偏远,清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反客为主”,客民逐渐超越少数民族土著。
(二)贵州地区的社会经济
贵州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地形多山、多丘陵,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明末到清初,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和手工业。到了清康熙年间,出现了商业贸易,但规模很小。乾隆年间,贵阳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农业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在手工业方面,以织锦为主,贵阳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当时,贵阳是贵州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之一,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主要的商业工业有织锦、染布、制糖等。随着改土归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以及贵州地形原因,贵阳地区也逐渐处于封闭状态。
二、王阳明与贵州
在明中叶以前,贵州称之为“鬼方”“夜郎”,属世人眼中的“蛮夷”之地[4]。据《黔记》记载:“元以前,黔故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地理上的闭塞和未开化,造成贵州经济文化的落后。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封闭性,贵州地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明代中后期(1506年),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今贵阳修文)当龙场驿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地区的文化状况。他在思想上的巨大成就之一,便是创立了“心学”,提出“知行合一”的传世哲学思想,而王阳明悟出此道,与贵州有着重要的关系,可以说,贵州龙场是阳明心学的发端之地。
贵州贵阳修文县东北部的龙冈山上,有一处清幽的石洞,洞口提有“阳明先生遗爱处”的石刻,便是王阳明先生曾经悟道的地方。王阳明先生虽然仅在贵州两年,但不论是贵州这片土地对于他来说,还是他对于贵州人民来说,都影响深刻,意义深远,对贵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王阳明在贵阳的讲学活动
王阳明的讲学活动是其学说传播的重要渠道,王阳明在贵阳地区讲学活动的开展情况,对于研究贵阳地区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龙岗开讲后,王阳明声名日隆,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主管贵州教育的官员)多次拜访王阳明,对他的学问佩服不已,并以正式书面邀请的形式,请王阳明来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从全省各地招收了二百多学生。王阳明在明正德四年(1509)来到贵阳时,席书还“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这使得王阳明的声名广为传播。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期间,对当地教育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贵阳兴办了书院、学堂等教育机构,并积极倡导民间办学、普及教育的活动。
王阳明在贵州地区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通过对王阳明著作的收集整理,王阳明在这一时期内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学术活动:
(一)整理并刊印王门著作
在王阳明讲学过程中,贵阳地区的士人对阳明心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仅向王阳明请教问题,而且还自发组织起学习阳明心学的团体。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阳明心学研究和传播的学者,他们将自己所整理的阳明心学著作出版刊印。此外,出现了多部研究王阳明在贵阳地区形成的思想和学说的专著。如明代著名学者刘宗周所著《阳明先生行状》,是研究王阳明生平及思想的重要文献;明代著名学者胡居仁所著《阳明心学集传》、王廷相所著《阳明先生年谱》、周积所著《阳明先生年谱补证》等文献均记载了王阳明在贵阳地区讲学活动的相关情况。王阳明在这一时期内在贵阳地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讲学活动,这些活动对于阳明心学在贵州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二)讲授王学
王阳明还对王学进行了系统讲授,并在贵阳地区的多所学校教授王学。据《明史》记载,王阳明在贵阳开设“龙岗书院”,讲授王学。在《明儒学案》中,记载了王阳明在贵阳开讲《大学》《中庸》等的情况:“龙场道上,阳明讲学,四方学者趋之”。“讲习数月,讲毕,有数人欲留宿。先生曰:此二日亦当来此。余曰:已为二日矣。先生曰:只今日已为二日矣。”
王阳明在贵阳地区讲学活动期间,注重对王学的弘扬,并以王学思想为指导,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念。这些思想主张为贵州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王阳明在贵州地区积极弘扬王学思想,开展讲学活动时,还大力倡导民间办学、普及教育,促进了贵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发展。
四、王阳明与贵阳地方文化
王阳明三十六岁时(1508年),被贬谪到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驿,其地“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仅有“驿丞一名,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王阳明只能暂结草庵,权且栖身,仍读书求道,矢志不渝[5]。历经磨难,终于在“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学说,是为思想史上的一声惊雷,五百年来,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影响深远。今天,贵阳的城市精神“知行合一,协力争先”,正是来源于王阳明先生的思想资源。王阳明除了对贵阳的儒学发展贡献良多外,在贵阳的许多地方也留下了王阳明的足迹。王阳明曾说:“吾今住此,盖欲为黔而无他也。若为黔而不为吾,则吾与汝皆非我也。今以吾所居而治黔事,则无不可为;若以我所居而治黔事,则无不可为。”在他看来,贵阳虽远离京城,但这片土地却是王阳明的理想之地。
贵阳市修文县的龙场驿,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传播之地。《王阳明先生年谱》载:“龙场在贵阳府城东南十五里,今名龙场驿,山环水抱,形势险阻。”在王阳明看来,贵阳既是他的理想之地又是其精神之地。
(一)贵阳的“龙场驿址”
明代,贵阳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代,贵阳已成为贵州省会,人口更是激增至四五十万。当时贵阳的工商业、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据《贵州通志》记载,“贵阳旧城设七个驿铺,每铺有驿丁七名。”当时贵阳的交通十分发达,到贵阳的人不仅能享受到较好的交通条件和服务水平,还能从贵阳运来各种货物。
龙场驿是贵州最早设置的驿站之一。《黔记》载:“建驿于龙场,以其地有龙而名”。“龙场”即是指如今的龙场驿址。在明清两代,这里一直是贵州的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当时这里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旅云集之地,还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自明代起就有不少文人来这里游历和居住。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在龙场驿内又陆续建起了“飞来阁”“观澜亭”等建筑,并在这一区域内发展出了“四大书院”等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
(二)王阳明贵州龙场驿悟“致良知”
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到的到底是什么,王阳明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因此,心即是理,理即是心,心理本是合一的,“心即是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6]王阳明在龙场悟道 (“心即理”) ,乃是精深恢宏的心学体系。此心学体系之所以能得到建立,一方面,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7],使他脱离了程朱理学的牵绊;另一方面,使他得以回到方土人生,吸纳民族,返本得道。不久,王阳明移居距玩易窝三公里的龙岗山“东洞”,并将之命名为“阳明小洞天”,开始授徒讲学。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是王阳明对人的心学思想的概括,也是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王阳明先生年谱》卷五载:“弘治六年,(阳明)复讲学于龙场,时弟子从游者亦众。”王阳明晚年在贵州龙场驿讲学,弟子们从各地赶来听课,一时兴起,又有百余弟子相继而至。此时王阳明在龙场驿讲学已有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龙场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致良知”学说。
“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王阳明先生年谱》载:“正德十二年冬至明年夏,先生至贵阳讲学。”王阳明于这段时间到贵阳讲学,也正是由于他在龙场悟出了“致良知”学说。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的观点是对“心即理”的否定和对“物即理”的肯定,也是对儒家理学的超越。“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为阳明心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阳明心学与贵州地方书院教育
地方书院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教育机构的一种,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书院是一种通过讲学、学术研究等方式,把儒家思想传播给社会大众的一种教育机构。与官办书院不同,地方书院则主要是由士绅或学者在民间创办的,办学目的是培养人才、弘扬学术、倡导道德。
贵阳作为王阳明先生的重要思想发源地之一,其地方书院教育也与阳明心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时,便开始创办地方书院,培养当地人才。其创办的贵山书院位于贵阳西南30公里处的花溪河畔,是王阳明先生在贵州最早设立的两所书院之一。在贵阳创建贵山书院期间,王阳明与弟子们在花溪河畔、青岩古镇等地做了大量讲学活动。贵阳贵山书院的设立与王阳明先生有关。
《贵州通志》载:“明初,贵山环山而建,周回三百余里,为贵州四大名山之一。”贵山书院作为贵阳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所地方书院,其创办宗旨是“以崇实德、以明体达用为宗”,王阳明希望通过贵山书院来培养“贵德者”,也就是社会中最有道德、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人。他在贵山书院“大讲朱子理学”“为朱子所不容”。为了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王阳明在贵山书院还提倡“读经以明其志”的学习方法。王阳明认为读书要有目标、要有志向,而立志则是读书最重要的一点。他在《致良知学行录》中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体顺于道者,志之所趋也;趋之所无者,志之所在也;故志于道者,路不拾遗;行于义者,人不害其所为;居是邦也,无求备于人。”
王阳明所倡导的立志教育是培养君子人格、引导君子向善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贵山书院在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中承担着重要任务:
第一是培养君子人格。王阳明在贵山书院的教学活动中要求学生们要学习圣人之道、要做到“良知”。他在贵山书院对学生们说:“夫圣人之道者也,吾性自足矣!”意思是说:圣人之道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境界,不需要通过学习就能达到,就像是每个人心中本来就有的东西一样,我们只要让自己内心保持本真状态就可以了。所以王阳明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而良知不需要通过学习就能获得。
第二是引导学生“知行合一”。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后,在学生们中兴起了“知行合一”学说的学习热潮。《贵州通志》载:“(贵山书院)学生多从阳明先生学问于此而得之……先生为明、清以来讲说工夫之始也”。因此在贵山书院中强调要学生们“知行合一”“致良知”。
王阳明在贵山书院的讲学活动对贵州地方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贵阳地区的书院教育与王阳明先生的讲学活动有着紧密关联。在贵州地方志中就记载了不少王阳明讲学活动的情况:“明初建贵山环山而建……嘉靖、万历年间两度重修”“明末清初书院仍在贵阳府城内及贵阳郊区”“贵阳城内还有几处书院……如:云岩书院、黔中书院等”。这些记录都反映了王阳明在贵阳对地方书院教育发展所做的贡献,为贵州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繁华的都城被流放到偏远的闭塞之地,成为一名最底层的官员,然而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让王阳明就此消沉,他依旧追求着心中的大道。在谪居贵州的几年时间里,王阳明汲取内在的力量奋发有为,创立了“阳明心学”,终成一代圣贤。
阳明心学作为一门新的儒家学派,对倡导仁义道德、治国齐家的儒学理论具有卓越贡献。“王阳明一生留下的600多首诗,其中六分之一作于贵州,贵州因此被称为“王学圣地”。
六、结语
王阳明在贵阳讲学,并在此创办书院,培养人才。他倡导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对贵阳地区的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王阳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因子。王阳明一生都在致力于心学的研究与实践,而贵阳是其重要的研究阵地,在贵阳传播心学思想,不仅对贵州地区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当时贵州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王阳明在贵阳传播心学思想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个方面。而这些思想对后来贵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通过研究王阳明思想和贵阳文化之间的关联,能为贵阳文化建设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唐莉.明代贵州省建置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7.
[2]周妮.政区与区域之间:“黔中”名实变迁考[J].贵州文史丛刊,2022,(02).
[3]张祥光.明清贵州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
[4]周春元.贵州古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5](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明)王阳明著,于自力注.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7](日)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8]雷成耀,汪勇.龙场悟道与讲学化夷——王阳明对贵州民族教育的推动[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09).
[9]彭恩.清代贵州区域人口与城镇地理分布[J].农业考古,2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