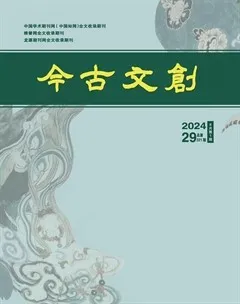夏秉衡戏曲《八宝箱》与小说中杜十娘故事对比分析
2024-08-20蒋乐乐



【摘要】杜十娘故事流传甚广,华亭人夏秉衡在小说基础上创作出戏曲《八宝箱》,通过分析对比小说中的杜十娘故事与戏曲《八宝箱》在人物情节上的不同,探析杜十娘故事的流变,并对《八宝箱》中的人物形象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戏曲《八宝箱》对小说文本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杜十娘故事;小说;戏曲;《八宝箱》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4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14
基金项目:国家级课题培育项目“庚子事变时期文人交游图谱及文学地图之建构”(项目编号:GP2021007)的阶段性成果;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晚清报刊所载庚子事变诗歌资料的汇辑与整理”(项目编号:1451ZD010)。
杜十娘故事流传甚广,而在小说故事基础上出现的杜十娘戏曲作品,也广受欢迎。清人夏秉衡在创作《八宝箱》时,就参考了宋懋澄的《负情侬传》和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过对比小说中的杜十娘故事与戏曲《八宝箱》在人物情节上的不同,分析杜十娘故事的流变,由于这两个小说在情节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而冯梦龙所作杜十娘故事影响最大,因此主要将《八宝箱》与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对比,分析人物情节的不同之处,以及《八宝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小说中人物的异同。
一、杜十娘故事的流变
杜十娘故事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真实事件,杜十娘确有其人其事。最早将这个故事付之于笔端的是明人宋懋澄,他偶然间在友人处听到这个故事,援笔而成,创作出了文言小说《负情侬传》收录在他的《九籥集》卷五,这也是最早的杜十娘故事文本。作者自述其创作情由为“余于庚子秋闻其事于友人。岁暮多暇,援笔叙事”[1]。此后,关于杜十娘故事的改编层出不穷。其中,最受欢迎的杜十娘题材小说作品就是明朝冯梦龙的白话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收录于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此外,在他的《情史》卷十四中也收录有《杜十娘》一篇。
冯梦龙的白话小说是在宋懋澄《负情侬传》的基础上改编的,该文本在情节结构上和《负情侬传》基本一致。但是对于人物的描写有一些差别。
首先,对主要人物的描写有了偏移,《负情侬传》可以从题目看出侧重点在于“负情”,创作意图在于斥责负心郎,主要描写的对象也是男主人公李生。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描写的对象主要是杜十娘,在他的描写中,杜十娘是令人赞叹、同情、惋惜的对象。也因此,两篇文本的主旨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抨击负心郎,一个是赞美女主人公的坚贞刚烈。
其次,在角色设定上,对原有的主要角色赋予了名姓。《负情侬传》中男主人公为李生,设计谋取杜十娘的为新安人,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生“姓李名甲,字子先,浙江绍兴府人氏”,新安人“姓孙名富,字善赉,徽州新安人氏”[3]。原本帮助李生筹银的“亲知”也变成了新的人物柳遇春,帮助杜十娘妆饰、保管百宝箱的教坊诸姊妹,也成了有名有姓的谢月朗、徐素素等,人物更加具体形象。
最后,小说在结尾部分也做了改动,在《负情侬传》中,杜十娘投江后“李生与新安人各鼓船分道逃去,不知所之”[1],而冯梦龙小说中的杜十娘投江后,孙富受惊“终日见杜十娘在傍诟骂,奄奄而逝”,而李生“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3],二人都受到了更严厉的惩罚。此外,由于一个是文言小说,一个是白话小说,所以在语言风格上也有所变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语言更偏向口语化。
夏秉衡的《八宝箱》是由杜十娘故事改编而成的戏曲作品,于乾隆十四年(1749)创作,共二卷三十出。浙江图书馆藏有乾隆清绮轩刻本,清绮轩是夏秉衡的书斋名。卷首署有“秋水堂八宝箱传奇”,附有序言两篇,一篇是廖景文书写,另有一篇作者自序,还有赵虹等七人的题词。夏秉衡在自序中提到他的创作缘由:“尝读《情史》至杜十娘沉江事,为之感愤者累日,思欲并未作传,以幻笔补造化之缺陷,而属稿未成。”“余欲故《情史》所载,叙其始末,谱为新曲,使千古慧心淑女,一段精光,永永流传于鹅笙象板间。是则余作《八宝箱》传奇之志也。”[2]从中可以看出,夏秉衡读过冯梦龙所作的杜十娘故事后,对杜十娘不幸的结局感到气愤,因此,“以幻笔补造化之缺憾”把杜十娘的身份由青楼妓女塑造成了下凡历劫的天宫仙女,在历经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后得道成仙。但这并不是夏秉衡的独创,在《负情侬传》中,宋懋澄记述他在写完这个故事之后,夜梦一妇人对他说道:“妾自恨不识人,羞令人间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见怜,令妾稍司风波,间豫人间祸福。”[1]并且不让宋懋澄作传奇,否则“妾将使君病作”,后来宋懋澄果然生病,但他不肯折笔,行舟过河时,家中一女奴堕河而死,这也应了前面“司风波,豫人间祸福”的话,给故事增添了一抹奇幻色彩。夏秉衡从这里得到启发,又创造出了很多情节。这些细微之处,也可以看出夏秉衡作《八宝箱》,是受同乡前辈宋懋澄《负情侬传》的影响。
二、戏本《八宝箱》与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对比
夏秉衡的戏曲作品《八宝箱》脱胎于小说。通过将戏本与小说本相比较发现了一些异同,从故事的核心情节来看,戏本与小说本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主要的情节都是:李甲进学——遇到杜十娘,二人情投意合——杜十娘想要从良,李甲钱财用尽,老鸨想要赶走他——杜十娘与鸨母约定三百金赎身,李生借贷——借贷无果,杜十娘交付李生一百五十两,嘱李生另谋其半——柳遇春帮助李生——杜十娘赎身,老鸨后悔无果——杜十娘与好友告别——泊船瓜洲,遇孙富——孙富设计骗取杜十娘——公子吐露实情,杜十娘假意答应——杜十娘示宝沉箱,怒骂孙李,投江自尽。
不同之处首先是人物,不像小说那样只有几个主要人物,戏本出场人物众多,此外还增添了小说中没有的人物,例如杜十娘的丫鬟桂儿,李甲的同窗宋如玉、相以金,还有为杜十娘仙女渡劫身份所增设的碧霄夫人、吹笙仙史、水判官等,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戏本与小说本的人物差别,列表格如下:
除了出场人物不同之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夏秉衡的创作体现了传统戏曲中的度脱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被度者通过度人者的帮助,经过度脱的过程和行动,领悟到生命的真义,最后得到生命的超升——成仙成佛。” ①在戏本《八宝箱》第二出《谪凡》中就点明了杜十娘的身份:“说话间,只听得仙音嘹亮,不减钧天,想是女侍们在内奏乐了,呀,你听她正五音,调六律,节八风,成九奏,众声皆和,独有洞箫之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似有尘凡之想。原来是吹箫女子,孽缘未尽,应劫降生,定数难逃莫能救挽,不免唤他出来,嘱咐一番,使他虽落火坑,毋忘本性。”[2]杜十娘原本是天宫的一位吹箫仙女,碧霄夫人听到她的箫声呜咽,似有尘凡之想,察觉到了她孽缘未尽,必须要勘破劫难,天意难违,所以决定将她谪落凡间。这也十分符合度脱剧的模式。杜十娘是被度者,碧霄夫人是度人者,仙女思凡被贬凡间成为青楼妓女,后来遇到了李甲,本以为得遇良人,结果却遭到了李甲的伤害和背叛,沉箱投江而死。经历了一系列磨难,最终在《迎仙》一出,作为度人者的碧霄夫人吩咐水判官“今有杜美,向系本官仙史,因吹箫而暂谪人间,能守节而复归天上。中秋乃脱凡之日,花朝为复位之辰。咨尔江神,小心接待”[2],杜十娘被救下,并且迎回了天宫。由此,被度者经受了种种磨难,完成了死亡的仪式,终于大彻大悟。在结局《仙圆》一出中,杜十娘被封为花苑真妃,渡劫完毕,重回天宫。
除了杜十娘与小说本不同的身份之外,剧作者还增设了其他不同于小说本的情节,这些情节有的是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还有的是度脱传统模式中度人者对于被度者的引导情节。例如碧霄夫人以梦度人,在梦中告知了杜十娘后面发生的事情;李甲突发疾病,杜十娘只能典衣卖饰,为李甲延医请巫,向上天祷告,碧霄夫人再一次托梦,李甲最终痊愈。比较戏本与小说本的情节列表格如下:
戏本与小说相比较,在核心情节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主要区别在于杜十娘的身份,以及柳遇春婚配,不同于小说作品中的柳遇春直到结局都是单身,《八宝箱》中的柳遇春与义妓梅楚楚喜结良缘,梅楚楚也将杜十娘的丫鬟桂儿给柳遇春纳为妾室,妻妾双全,感情美满。李甲的结局也与小说中不同,小说中杜十娘投水后,李甲“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而剧作中,李甲感杜十娘情义,也随之赴水,和杜十娘一起被水判官救下,回到天宫后,判官点明李甲身份,在杜十娘还未成仙时,他就是杜十娘身边的一只燕子,今日依旧判他做燕子,也算是受到了惩罚。
三、戏本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对比
(一)杜十娘形象
杜十娘在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与小说中有些出入。小说中的杜十娘“自十三岁破瓜,今一十九岁,七年之内,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3],是风月场中的高手。而在《八宝箱》中,杜十娘是一位卖艺不卖身的贞洁女子。教坊妈妈向李甲和他的同窗说起杜十娘时道:“这个女儿,吹弹歌舞,件件聪明,诗词歌赋,般般伶俐,那些豪华子弟,那个不想去梳笼他,只为自小娇养惯了,十分作怪,莫说接客二字,抵死不从,说重了些话儿,还要寻死觅活哩。”[2]杜十娘坚守贞节,鸨母要她接客,她以死相逼不愿接客。“赋桃夭,同守蓬蒿,只恨那梁鸿已死冀缺难遭,我愿井臼亲操,只不许琴心墙外挑。”[2]她反对“琴心墙外挑”的行为,向往操持井臼,与心上人同守蓬蒿的生活。在见到李甲之前,杜十娘就久有从良之志,直言“常深跨凤之思,未遇乘龙之客”。托身李甲后,也有“妇人之道,从一而终”的誓言。遭到李甲的伤害与背叛时,痛斥孙富与李甲,最后投水自尽,这些都体现了杜十娘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念。除此之外,夏秉衡还增设了杜十娘前世因为守贞节义可彰,得以升做吹箫仙史的情节,这一世虽误落尘网,依然坚贞自守,终于又重返天宫。由此也体现出剧作者本人的情结和当时社会对妇女贞洁守志的要求,也可以看出剧作者创作时对杜十娘这个人物形象做出的改动,她的形象已经逐渐脱离妓女,而是成为更符合明清士人所期盼的世俗意义上的良家女子形象。
(二)柳遇春形象
《八宝箱》中柳遇春的形象也有了一些变化。小说中,柳遇春形象是更接近于唐传奇中“黄衫客”的侠客义士。柳遇春是李甲的同乡,一开始听说李甲要借三百两为杜十娘赎身时,认为这是烟花逐客之计,劝告李甲早日脱身,但是在见到杜十娘拿出一百五十两时,大为震惊,因此感念杜十娘真情,代李甲出头借贷,并对李甲说:“吾代为足下告债,非为足下,实怜杜十娘之情也。”后杜十娘得以赎身,拜谢柳遇春时,柳遇春说道:“十娘钟情所欢,不以贫窭易心,此乃女中豪杰。”[3]他不因杜十娘的身份而轻视她,反而盛赞她为女中豪杰,可见其豪爽热心,侠义心肠。而剧作中柳遇春虽是一个寒窗苦读的书生,但品行出众,在李甲为杜十娘借钱赎身时,亲朋好友都不愿借贷,只有柳遇春典书卖琴凑足银两,帮助了二人。后来得知杜十娘身死,还带着梅楚楚及桂儿去金山寺祭拜她,可见其为人善良。小说中柳遇春最后得到了杜十娘的百宝箱,而剧作中夏秉衡对柳遇春也十分厚待,柳遇春调任为扬州知府治理水灾,在南下任职之时,夜梦杜十娘,此时的杜十娘已经被封花苑真妃,为感谢之前筹钱的义举,把百宝箱赠予了他。柳遇春妻妾双全,和睦美满,仕途通畅,得到了世俗意义上的圆满结局。
(三)李甲形象
夏秉衡笔下李甲的形象与小说中的李甲形象基本一致。小说中的李甲是杜十娘千挑万选出来的“忠厚志诚”可堪托付的人,剧作中的李甲对待感情专一,想要与杜十娘结为夫妻,积极为杜十娘赎身。但是他同时也非常矛盾,心性摇摆不定,他惧怕老父,又被孙富设计,最后还是决定抛弃杜十娘。剧作中判官审李甲时,他还把责任都推到孙富身上,并且还怨杜十娘隐瞒实情,可见他的懦弱和没有责任感。此外,在小说和剧作中都有关于李甲哭泣的描写,小说中,李甲筹集不到银两,无颜见杜十娘,杜十娘只得唤小厮把李甲拉回院中,回答杜十娘问话时,“公子眼中流下泪来”“公子含泪而言”。第二次是李甲答应孙富要将杜十娘卖给他,与杜十娘诉说完毕后“泪如雨下”。而剧中也哭了两次,正是与小说相对应,第一次是李甲筹不到钱“(小生大哭介)(旦)李郎,银两曾否到手,奈何只管啼哭(小生)真惶愧有无莫通,好教人羞惭满面返江东”;第二次是李甲答应把杜十娘卖给孙富,心中有愧,不敢面对杜十娘,“(旦)呀,李郎,你有何心事默默无言(小生掩面泣介)(旦)为何悲泣起来(小生大哭介)(旦背介)这是什么意思(小生)咳,十娘,我四海空囊,一贫徹骨,今带你回去,如何见得爹娘”[2]。李甲遇事没有办法解决,只能掩面哭泣,这都体现出他懦弱无能的性格特点。
通过对戏曲《八宝箱》和小说文本的对比,可以看出杜十娘故事的流变,杜十娘的身份从一个性情刚烈的妓女,变成了因为动了凡心被贬到人间历劫的仙女。与小说中投江而死的悲剧结局不同,戏本结局杜十娘因为坚守节义而得以超脱升为花苑真妃,冲淡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对于正面人物,剧作者也给出了最理想圆满的结局,柳遇春仕途通畅,获赠珍宝,家庭美满,杜十娘的朋友梅楚楚和丫鬟桂儿也都有了归宿。对于反面人物,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孙富绝嗣,李甲被惩罚变成燕子。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式结局,也可以看出《八宝箱》具有的社会教化倾向。
注释:
①荣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宋懋澄撰,王利器校.九龠集[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4.
[2]夏秉衡.八宝箱传奇[O].乾隆十四年(1749)刊本.
[3]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冯梦龙.情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3.
[5]焦循.剧说[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6]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7]王文照.清代戏曲家夏秉衡及其戏曲作品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20.
[8]陈旸.“杜十娘戏”研究[D].华侨大学,2021.
[9]张中.论杜十娘[J].明清小说研究,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