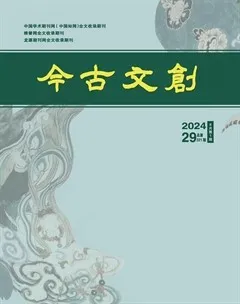论21世纪辽宁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技术型女工形象
2024-08-20孙嘉悦
【摘要】工业题材小说中有大量用男性主人公视角讲述的工厂故事,女性在其中的登场极为碎片化。21世纪辽宁工业题材小说与现实接轨,展现了辽宁女工追求技术进步、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物特色,联结着女工的精神生活境界。
【关键词】辽宁工业题材小说;技术型女工;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4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12
在很长一段时间,女性的劳作领域在家庭,作为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失去了社会属性和自我革新的能力,即使进入到工厂工作,也会作为陪衬角色,成为男性主人公恋爱时登场的工具性人物,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正如戴锦华在《女工故事与主体之名》一文中提到的,“女工们的,也是今日世界劳动者、生产者、供养者与服务者的故事。无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她们的故事记述并展示了今日世界多数人——在主流媒体上状若无声的多数人的生命境况;必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是强韧底层中的强韧者。”聚焦现实背景,辽宁省女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专业素质也有明显提高。女工在认同自我劳动者与匠人身份的基础上创造着个人故事,独立而自信,生发出人格尊严。21世纪辽宁工业题材小说遵循现实主义原则,于文本中呈现了以技术进步为目标、追求独立精神的辽宁女工群像。
一、以技术进步为目标
女性的工厂境遇大多相似。在男性工人的主导下,劳动分工不单纯依靠职能划分,还会附加上性别因素。女工在持续寻找和证明自身价值中希望获得更多话语权,因此她们普遍存在价值焦虑,在劳动过程中逐渐觉醒性别意识,并开始对父权秩序自觉反抗,在承担“技术女工”这一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展露生命底色。“多了洒脱恣意,也多了已然失根的飘零,同时或更自觉于别样的出路与价值。”
《热流》中的女工陈铁花,如其名般坚毅,自入厂到退休始终坚守岗位,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下书写人生。出身长门村的她,因农民身份只能做长门电厂的清洁工,但内心始终磨不灭成为技术工人的渴望,“清扫工算不得真正的工人,我想当像你一样的,能拿着锤子、扳子在厂房里干活的工人”[1]。她把爱情当作“晋升”筹码,用情感绑定大学生施其山,计划通过他来接触到汽机分厂主任施玄山,在功利与真心的矛盾情绪中,陈铁花在技术大赛“巧合”登场,向在场所有人证明“钳工手锤并不是专属于男人”,并在实际操作中发掘自身优势,依靠“巧劲”完成技术展示,赢得大家关注。
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对技术痴迷的陈铁花迫切地想要转变为城市身份。为了更加融入工厂,她不断超越自我、精进技术,最终凭借自身本事成为一名汽机分厂检修工人,从初级技工不断成长进阶。在工人干部邵振军的眼里,“外表似乎与其他女工并没有区别,都穿着肥肥大大的工作服,头发全部压在工作帽里……陈铁花的皮肤虽然已不像乡下女孩那般粗糙,但神态中流露出的气息依然是乡村的,是没有经过修饰和过滤的,属于纯天然的那种……越是工业化、城市化了,这种气息旧越珍贵”[2]。陈铁花身上既有工业化的气息,又保留着乡土社会中的生存欲望本能。在现代社会,知识即是权力。陈铁花急于在外表和心灵层面脱胎换骨,她将技术看作是公平展现个人价值、掌握话语权的力量手段。于是她为提高技术能力毅然选择拜声名狼藉的尤大海为师,在看重男女关系问题的年代,她放弃了真挚爱情和名誉,选择了“手艺”。“这段时间,除了早上她还梳一下头,平时几乎难得拿一下木梳,总是穿着松松垮垮的工作服,是真正的不修边幅了。学了很多,练了很多,但绝技还没触碰到,她当然是不甘心的。”[3]强烈的欲望驱使她从只会基础工作的检修工进化为掌握“直大轴”技能的技术女工。
作者李铁喜欢将手艺与情调关联,与性别挂钩。“设备也是有雌雄的,大轴就是雄性的,只能由男人来摆弄。自从有了发电厂,还没听说有女人直过大轴”[4]。“直大轴”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代表顶峰技术,它是陈铁花心中至高无上的“武林秘籍”,也是尤大海终身的“拿手好戏”和傍身之术。尤大海断定直大轴是“雄性”的,只能由男人来干,激起了陈铁花的野心,促使她用贞操换“秘籍”,抛弃做人的尊严,得到了“工人的尊严”。技术对劳动者主体性的越界,激活了潜意识中需要被认同的价值诉求。陈铁花的无数次后悔,换来的是她对“手艺”与日俱增的执着。相对的,在手艺人师傅对技艺保守的年代,尤大海选择用自己的手艺交换短暂肉体欢愉,任凭欲望战胜理智。在这场师徒较量游戏中,尤大海溃不成军,充分印证了“雄性由雌性掌握”[5]的论断。
李铁在采访中曾提到,“在这个场所里,被高压的东西往往会发出强有力的反弹。人情、人性、命运、心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人们把娱乐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到性。那也是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工人的最高荣誉就是手艺。为最高荣誉献身,是个别人能接受的,也是我能接受的。于是,小说情节就这样诞生了”[6]。陈铁花“献身”的行为动机是充分的,但当她真正成长为技术大拿后,“重文凭轻技术”的价值理念成为主流。陈铁花不愿相信“技艺至上”的时代已然过去,于是将“个人牺牲可以成全大局”的意识贯彻到子辈身上,固执地阻碍徒弟的前途和女儿的婚姻,最终酿成悲剧。结尾处,当重视技术的新时代重新到来时,当将要亲身展现“直大轴”技艺时,陈铁花晕倒在了现场。这位名副其实的“铁姑娘”终其一生为学习技术奉献,却在即将达成理想时遭命运戏弄,为小说笼上荒诞的色彩。
而在《杜一民的复辟阴谋》中,张连萍作为水班的技术员,始终不得志。她自愿又自信地去到生产第一线,期望学习技术,大展身手,但却被迫到了生产二线的水班。不满于此的她,关注到新任总经理高总和水班班组长杜一民之间的“救命”交情,权衡利弊后她选择献身,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被生活无情地击溃。表面上张连萍是趋炎附势的,但其内心深埋的是对理想技术能力的执着,表明了女工想要在复杂工业生活中自我实现面临的重重困难。
技术女工将灵魂嵌入工厂,以此深植劳动根系,甘愿成为生产“零件”,用劳动参与着、创造着美好的新时代。《北爱》中,刚毕业的苗青奔赴辽宁实现航空梦,在父辈熏陶下继承伟大志向,架起小志向与大情怀的桥梁。在外人看来,东北是一个人口外流的地区,苗青却决心逆流而行,坚定热爱黑土地,在她身上寄寓着年轻一代技术人才精神返乡的立场。“乡”并不仅指客观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延伸至情感上的归宿地。苗青从被动到主动,逐渐直面内心深埋的“工匠之心”,深耕飞机制造技术研发,为了东北航空业,更为国家航空业尽一己之力。从“我,尚不知答案”的迷茫到最后毅然决然放弃飞鹰集团总经理职位回到国企鲲鹏集团,苗青与周围一批年轻卓越的技术人才一起制造精品,致力打破西方大国的制造垄断,不断超越自我,攻克难关,发出女性的时代回响。
如果说辽宁女工对机器的感受是滚烫的,南方流水线女工则触摸到了另一层女性工业体验。郑小琼在《铁·塑料厂》中谈及女工们对铁的知觉,“在南方,进了一家五金厂,每天接触的是铁,铁机台,铁零件,铁钻头,铁制品,铁架。在这里,我看到一块块坚硬的铁在力的作用下变形扭曲,它们被切割,分叉,钻孔,卷边,磨刺头,变成了人们所需要的形状、大小、厚薄的制品。”[7]“铁”的锋利与坚硬在心上撕裂开一道口子,这股伤痛犹如巨兽,在内心深处不断冲撞。
城市化、工业化的“腐蚀”既使女工飘零无根,却又让她们重新开始体认自我,开始共享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生命肌理,在这一层面上回望辽宁女工的劳动观向度,能够发掘出彼此联结的女性命运。两类女工,不同的劳动态度,生动演绎着别样鲜活的真实故事。
二、追寻独立精神
辽宁女工在为工业化服务的过程中怀揣伟大志向,传递坚定女性力量,追寻精神出路。她们在劳动中体认自我,努力与悲惨人生抗衡。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和工厂父权话语遮蔽了沉浮的女性。女工即使技艺超群,也逃脱不了被男性凝视与轻视的命运。
《出墙的红杏》中,天车女工红杏故步自封,囿于操作天车的成就感,“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工,能有这样一个岗位应该知足了。别人这样认为,红杏也这样认为”[8]。她安于现状,又为保护这片舒适区而“疯魔”,作为一个技术娴熟得无可挑剔的女工,她在职业工作中受制于车间主任吴大手,用“性”换取坐在天车中受人“仰视”的权利。她深知这美好的一切都源于吴大手的偏袒,于是当更年轻漂亮的钳工小叶出现时,她自惭形秽又诚惶诚恐,在患得患失中身陷泥沼。小叶就像她的“镜像”,反射着过去的红杏为学习技艺付出过的泪水和汗水。红杏在养家糊口的重压下,无法忍受被一个极像自己的女工取代而下岗。她顽固抗争,状若无意地透露吴大手与小叶的私会地点,无意识地想要摧毁迫害她的男性话语权,期待有一天能够摆脱束缚,单纯依靠过硬的技艺征服男性、机器,实现自我。女工在环伺的危机夹缝中生存,努力寻求社会认同和自我价值。
《彭雪莲的第二职业》中,经历丈夫入狱、女儿病倒的纺织厂女工彭雪莲只手撑起整个家,屈服于生存欲望,选择豁去名誉从事“第二职业”。虽然她被迫出卖身体,却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仍坚持在纺织厂做工,代替男性承担家庭经济重任。但彭雪莲的内心并没有生发出鲜明的独立意识,她的自主权是外在因素赋予的。在接待客人老徐时,彭雪莲产生了道德羞耻,但在市场逻辑的同化下逐渐丧失道德底线。她的梦想是努力活着,在对抗生存危机的过程中,她陷入“哈姆雷特式”困境。用强大心性独自应对支离破碎的生活,仅仅是独立思考的一步。要达到精神独立,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们在两性关系中浮沉,成长。《热流》中,女工莫静兼有外貌和技术,让工厂的众多男性都为之着迷,其中就包括了厂长邵振辉。莫静没有选择厂长夫人这条注定高升的捷径,转而投入无法见光的地下恋情,深陷复杂的三角关系中。莫静迫于权势与邵振辉例行相处,同时秘而不宣地与施玄山恋爱,处在情感漩涡的中心,不停追问爱情的真谛。施玄山干部与已婚的双重身份,注定两人爱情的不伦和悲剧结局。明明是有技能的女工,莫静选择了与技术女工截然不同的道路。她不争不抢,有强烈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在他人对陈铁花的名誉指指点点时,她避而不谈,给予陈铁花无声安慰。作为女性个体,莫静游走在人群之外,在隐秘黑暗的空间释放自身欲望。她既叛逆,又清醒,在旷阔的工厂中漂泊不定。在奸情被发现后,她从工厂中“逃走”,并在数年后以私营企业老板身份强势回归,以爱国和爱厂的心注资支持长门厂转型。在选择企业管理者时没有偏袒旧情人的儿子,而是选择了有更强管理能力的孙兆伟。她不计前嫌的奉献,是其成长轨迹的最终一环。
在《纪念于美人的一束玫瑰花》中,追求于小雨的男人破坏了她的声誉,让她失去了前景大好的爱情和事业,成为下岗工人。面对周围的流言蜚语,技艺是她心中仅有的慰藉,也是拯救精神困境的唯一解药。在劳动中她改变了先前不屑一顾的态度,提升了精神境界。在抛下脸面做了公关小姐后,于小雨长期利用身体去换取对工厂有利的发展机会,在旁人的不理解中做着有意义的事。
同样,《热流》中合资工厂的公关小姐苏丹从容地周旋在男人之间,貌似唯利是图,却在觉察到施大伟想要损坏长门厂利益时力挽狂澜,勇敢维护集体利益。长门厂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以劳动为荣、无私爱厂的女性,是她们用悲壮的姿态撑起转型中摇摇欲坠的工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坚守本心,展现女工独立的精神内核。作者一方面突出精描她们的外貌,又在字里行间细致诉说其外貌之下更为纯净高尚的内心和隐匿的大爱。
《锦绣》中的古小闲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被主人公张大河抛弃,致使古小闲产生了身份认知障碍,她期望通过转变身份重新获得爱情,又被真爱受阻的现实打击。在另一位男性角色吴远山的示爱下,她开始在理想与爱情之中摇摆不定,最终在争夺话语主导的强烈欲望驱使下,古小闲用身体牟取来“医生”的身份,但闲言碎语纷至沓来,很快让她从“云端”掉落。在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调到车间当工人后,古小闲不怕脏累,不顾危险地跳入泥浆槽守护工厂公共财产,她真正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地——工人群体,并在劳动中成长蜕变,获得极高的价值感。
她们建立独立事业,为理想付诸行动。《工人村》中的英莲一心办工厂,“英莲要办小工厂的事在工人村已传得沸沸扬扬了。英莲通过王婶,找到老于家的女人、楼上的张婶,还有对面楼的小丽妈等十几个家庭妇女,说要和她们到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建个小工厂。那些妇女表示,有英莲带头,她们一定好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9]。她带领一批妇女“白手起家”,迎合时代搞技术协作,为祖国创造财富,拥有不输男性的魄力和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使命感,凭借着创新开拓的精神,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随后,接管小工厂的兰儿在面对停产裁员危机时,并未独善其身,而是选择与工人共患难,用行动表现人道主义关怀,展露舍己为人的“英雄”气质。《钟爱一生》中因国企改制,三分厂的工人大批下岗,在工会主席陈重望对下岗再就业问题一筹莫展时,女工胖嫂勇敢站出支持其工作,挑起家政组的担子,为下岗女工们探索出路,为证明“女性不都处于弱势”,她带领女工穿梭大街小巷,自力更生,展现乐观坚强的精神气质。
综上,女工特有的细腻洞察力,为书写工业生活提供了全新视角。辽宁技术型女工以技术创新为目标,不拘泥于一方天地,不依附他人,她们从人性幽微处见证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并将自身融入普遍劳动世界和广阔历史的深邃处,自主能动地大胆实践,与时代接轨。21世纪辽宁工业题材小说中塑造的女工形象具有强烈劳动价值感和进取心,突破了传统女性脆弱易碎的形象,以一种挺拔、勇敢的姿态闯入大众视野。
参考文献:
[1]李铁.热流[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8:7.
[2]李铁.热流[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8:26.
[3]李铁.热流[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8:62.
[4]李铁.热流[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8:89.
[5]李铁.热流[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8:331.
[6]鲁大智.李铁:生活底子深厚,写作便成为一种流淌[N].中华读书报,2018-3-16.
[7]杨宏海编.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散文、诗歌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2.
[8]李铁.出墙的红杏[J].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 (7):89.
[9]温恕.工人村[M].沈阳:沈阳出版社,2012:90.
作者简介:
孙嘉悦,女,汉族,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202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