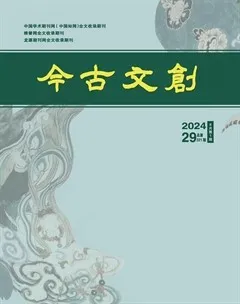橱中的巨婴:麦克尤恩《与橱中人的对话》的权力解读
2024-08-20倪烯瑞
【摘要】《与橱中人的对话》是伊恩·麦克尤恩早期作品《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其中一个故事。本文跳出对于该小说集中不可靠叙事、伦理学以及性别冲突的研究思路,从“橱中的巨婴”如何养成入手,采用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理论以及拉康的镜像理论,发掘和讨论主人公成长过程中三个不同的微观环境,从微观家庭权力的扭曲到走上社会的不平衡,再到最后主人公放弃主体性走向自我封闭的压抑过程,探究了微观权力病态与不平衡的格局之下,如何压抑和消解成长的主体性,最后使其“瘫痪”而主动选择放弃成长,只能永久停留在镜像想象界的悲剧。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与橱中人的对话》;权力结构;镜像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2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07
《与橱中人的对话》(Conversation with a Cupboard Man)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Last Rites,1975)中的一篇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压抑的成长故事。叙述者是一直被母亲过度照顾到17岁,成为一个“巨婴”,其间其母一直控制他的成长,不让他长大。当母亲终于决定迎接新生活之后,叙述者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被母亲抛弃,于是他被迫离家自力更生。在酒店厨房工作时被人欺侮,而现实的局限又让他去偷窃。最后叙述者渐渐地把自己关在阁楼上的衣橱中,拒绝与外界产生联系。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恐怖伊恩”(Ian Macabre)时期的代表作,学界对于这部作品的讨论大多数集中于作者对于暴力、恐怖、惊悚与荒诞的书写。《与橱中人的对话》是其中一个压抑又痛苦的成长故事,叙述者在自我对话的过程中努力挣扎着,到最后却并未走出象征着母亲子宫的衣橱。苏梅拉谈到了女性与权力的问题,她认为这篇小说是麦克尤恩在新领域的尝试,一反之前父权对于女性的支配,制造了一个“母亲对儿子绝对控制”[1]128的情景。
国内学者房文静从经典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探究了叙述者和母亲、社会的复杂关系,苏玮的论文从文学伦理学“斯芬克斯因子”的维度出发,讨论儿童成长过程中“伦理身份确认、伦理意识构建和伦理选择的困难”[3]70,从而揭示出该小说的伦理批评内涵。这些角度都探究了对于不同群体的意义,但从本质上来讲,由于家庭伦理失序,个人话语被过分挤压,给成长个体带来“身份认同焦虑”的这种机制是如何出现的,又如何解决,仍然还可以继续讨论。
本文将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拉康的镜像理论出发,剖析伦理失序下导致成长过程中的主体性如何消解,以及主人公站在社会底层和人性底层的边缘向主流群体融入失败后,缺失身份认同而走向迷失,最终只能停留在婴儿的镜像想象界的矛盾局面。
一、福柯权力话语下的《与橱中人的对话》
《与橱中人的对话》采用独白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故事。这种叙事手法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叙述者在个体角度对自我身份和环境的认知。他大概经历了三个环境的变化:在家和母亲生活、被迫出门工作以及最后回归阁楼上的衣橱。在每一个微观的权力话语之下,叙述者都经历了内心的斗争和主体性的挣扎。而这三个微观环境的出现更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循环的逻辑蕴含着底层哲理的普遍性。然而,叙述者最终也没有走出他的镜像阶段,把矛盾留在了他最初始的状态。麦克尤恩通过这个故事发出对“人”的反思和叩问。
二、家庭权力的扭曲
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他的母亲一个人把他带大。然而,母亲却成为家庭中知识与权力的唯一掌控者。她阻止他长大,让他“十八岁才学会说话”,并且不让他上学,固执地认为“学校是个野地方”[5]108,切断主人公和外界的知识联系。除此之外,母亲也对他进行了身体上的限制。她一直都抱着他,把他当作婴儿对待,当他需要睡正常的床时,她却去医院的拍卖会买了护栏床,所以他没法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在普通的床上睡觉。而这样一来,母亲成了主人公世界里唯一能言说的主体,他生活状态的操纵者,她就是他认知中的一切。在叙述者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母亲这种行为的愤恨:“没她我简直动不了,她却以此为乐,那个婊子。”[5]108但是实际上他的想法却又非常矛盾,在后面受到了挫折之后的一段叙述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母亲的不合理行为的怀念:“我开始回想过去和妈妈一起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回到那时”[5]117。因此,在主人公的潜意识深处,他是仍然深信着且迷恋着母亲的绝对而又病态的控制。母亲的这种无处不在的权力显然已成为一种对他的规训。
在福柯眼中,规训的作用相当微妙:“‘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4]241。这种权力类型无声之中监视主体,也塑造主体。母亲这种行为对主人公的规训已经无形之中化为了对他一辈子的监视,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形成了另外一种自我约束,本质上心甘情愿地接受母亲无处不在的监护,自我的身份认同却难以成长起来。因此叙述者在自述中说,自己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候非常快乐,在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之前,根本就没有起过逃离的念头:
……我从没起过那念头。我不知道生活还有其他样子,我不知道自己与众不同。话说回来,我那时在街上走不出五十码,就会害怕得拉一裤子,又怎么逃跑呢?我又能去哪里?我连鞋带都不会自己系,别提打份工了。我现在听起来恨恨的是吧?但我告诉你一件滑稽的事情。我那时并没有不快……是的,在我发现别人如何看我之前,我没有不快乐过。我想我本来会一辈子都一再重复生命中的头两年,而且不会觉得不开心。她是一个好女人,真的,我的妈妈,只是搭错线。[5]109
从叙述者的视角来说,他有一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态:渴望成长、憎恶被控制的感觉,却又无法逃脱对这种情感的依赖,当只有主体与监视者时,他期待自己的突破和成长;然而在主体遭受外部世界的冲击时,他无法应对外部的矛盾,从而又对控制他一切的摇篮产生了依恋。从第一阶段的叙述中,麦克尤恩在一个家庭里展示了微观权力的能量:它可以让人厌恶和产生叛逆感,同时它最强大的一点是在其管束下的个体不管有多大的违背意愿,最终却割舍不掉对于婴孩般生活的依恋。
这种病态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主人公17岁时,母亲选择了迎接她的新生活,迎来了她生命中另一个男人。这也就意味着权力的监视者即将抛弃她一手打造的权力监护机制,这片“监狱”即将变为废墟。她不愿意再管他,但是主人公的主体性已经瘫痪了。他无法割舍掉对于监护的依赖,离开了无处不在的监管,他将无法独立在社会上生活。更可怕的是,母亲急于追求自己的新生活,期望在两个月之内让他完成前十几年的成长。
成长的急剧到来以及被压缩,让主人公出现了不适应的症状。在微观权力不平衡的病态格局下,问题开始出现:叙述者开始“头疼”“抽风”。而这些症状既是病态养育之下遇到变故后的应激反应,又是出于对权力回应的渴望。平衡的被打破让他需要自己的身份得到确证,获得身份认同,确证自己的主体性。然而,掌控一切的养育者一旦离开,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叙述者一个主体,且在自我意识没有建立起来的前提下,他感到无所适从。此时的环境并没有对他的诉求做出回应,于是他带着主体性的困惑,进入下一个新的环境。而从主人公与养育者的关系来看,自我意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他注定无法与社会形成正常的互动。
三、社会关系的边缘化
失去了家庭支持的主人公不得不离开到社会上谋求生计,而他本身作为一个“低能”的成年人也被主流排除在外,只能被酒店的厨房接受。酒店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厨房却是一个“肮脏的粪坑”[5]114,而这也暗含了叙述者的状态。他只能属于边缘、肮脏、阴暗的角落。同他相处的同事们也都是底层的边缘群体,靠对彼此的倾轧为乐。其中,大厨“脓包脸”是这个微观环境下的权力网络核心。当他欺负其他人的时候,另外的人都只能附和他而不敢说话。没有道德,没有规则,只有在底层下欺压他人的独裁者无限膨胀的个人权力和欲望。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体系下,主人公也无法获得正确的身份认同。他单纯因为不想附和脓包脸说的笑话就被针对,脓包脸趁他不注意把他关在了铸铁烤炉中两次。他第一次选择了忍气吞声,第二次当他经历了火热的烤炉中缓慢煎熬的炙烤和带来的身体问题时,他决定反抗,将滚烫的油倒在了脓包脸的腿上。这种做法让读者在阅读体验中有了一种荒诞和惊悚的感觉。引起这个矛盾冲突是叙事的关键,主人公报了仇之后,也失掉了工作。他并没有因为反抗他人入侵自己的边界获得任何对他的肯定,相反的,他更知晓了外界的恶意和第一次独自面对、发起反抗的恐惧和不安。因此,和外界冲突带来的并不是主体性的确立,在这种同样病态和不健康的成长环境下,这样的矛盾进一步消解了主人公的主体性,让他对整个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趣。他开始怀念母亲监护一切的生活,他才发现他并有点想被关进那个差点要命的烤炉,他反思道:“我想要呆在一个出不去的地方……当我真正被关在烤炉里的时候,却太担心出不去,太生脓包脸的气了,而没能体验到内心的需要”[5]119,这个烤炉对他来说就像是母亲的子宫,封闭、温暖、安全。在他的叙述中,他甚至认为自己真正的需要就是被关在烤炉中,而不是与脓包脸对抗。他主体性的建构彻底而又不现实地走向了一个终点:回到婴儿状态。因此,在社会上作为底层边缘的流浪者的他开始拒绝工作,拒绝与外界沟通,选择偷窃为生。
偷窃行为私密、封闭,只要不被发现,就很安全,非常适合他的人格特质。但他还是因为这种行为被发现而入狱。回忆监狱生活中其他的种种怪人,有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人叫“聋子”,又聋又哑,这人有一个自己的小隔间,主人公非常喜欢到他的房间里去坐。“聋子”无法言说自我,像他一样,独自待在自己的环境中。在“聋子”创造出来的空间里,同样是安静、封闭、无需沟通的,因此叙述者找到了熟悉和稳定的感觉。
在不得不出狱之后,他找到了一个阁楼,其间有一个衣橱,他做了格外多的叙述:
我觉得里面很不错,不会感到无聊什么的……有时我希望衣橱自己会站起来走来走去,忘记还有个我在里面……后来我就彻底不去上班了。我这样有三个月了。我讨厌去外面,我情愿呆在橱柜里。[5]123
衣橱已经完全成为母亲子宫的象征。他希望衣橱可以自己移动,潜在的话语即是指向衣橱有自由的行动力,就像母亲,而他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没有自由行动力的人,主动放弃构建主体的机会,“我不想要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嫉妒那些我在街上看到的被妈妈裹着的婴儿”[5]123,将自己的身份认同视作是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婴儿,把主体性完全移交于外界。叙述者的自我确证彻底走向了不健康和病态的迷失。一方面,他执迷于回到不可能回去的婴幼儿状态;同时,他也对外界暗自渴望,但这种渴望的联系也变得奢侈,他感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对主体性的主动放弃让他只想在橱柜里怀念他最初和母亲在司登斯的生活。畸形的权力压迫个人话语成长空间,导致主体性的完全萎缩。所以最后主人公选择把壁橱当作母亲子宫的替代品,“我希望重回一岁。但那不会发生。我知道,不会的”[5]124。
他把自己塞到阁楼上的橱柜里去,彻底与外界隔绝。橱柜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但他也知道这是他在这格格不入的社会中唯一能找到的慰藉,而他自己终究成了社会的弃儿。
四、结语
在《与橱中人的对话》中,主人公并不拥有姓名,他是麦克尤恩笔下刻画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的“怪人”。文中,并没有第二个人与主人公对话,而一直是个人独白。这种镜像式的幻象就如拉康提出的婴儿的镜像阶段。处于镜像阶段的婴儿看到镜中的自己会兴奋不已,与其他的动物完全不同。拉康认为,这是由于婴儿认识到了一个统一体的存在。但是,这个存在并非是自然的,“像弗洛伊德的‘自恋的自我’观一样,拉康亦认为自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幼儿主体与自身之镜像认同的‘自恋的激情’的产物”[7]876。叙述者迷恋、沉浸于自我的镜像,就是他的母亲呈现给他的作为一个“婴儿”的镜像。而叙述者一直只能通过母亲给他营造的想象确证自我,一直停留在由母亲的权力建构出来的想象界中,而在没有正确的引导下,努力进入大他者的象征界的期望也因为遇到挫折而被无情地毁灭。而让他一直停留在镜像阶段的原因则是由于他所处的各种病态、失衡的权力结构,让他难以获得正确的自我认知和对外界的认知。因此叙述者很难接受母亲的变化和社会的残忍,愿意主动放弃自由和自我,回到温暖舒适的牢笼,断开与外界的联系,把自己寄生在一个想象的、虚无的子宫之中。
麦克尤恩正是通过这样压抑的笔触,描写边缘、病态的社会关系,书写了社会上共同隐藏着的肮脏、阴暗又无处解决的问题,从伦理、社会背景等方面提醒读者这样残忍又压抑的存在。
参考文献:
[1]Sumera,.A.“Woman and Authority in Ian McEwan's
‘Conversation With a Cupboard Man’ and Its Film Adaptation”. Text Matters:A Journal of Literature,Theory and Culture, no.1,Nov.2011,123-34.
[2]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4):84-90.
[3]房文静.经典精神分析批评视角下的《与橱中人的对话》[J].文学教育(上),2018,(08):70-71.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麦克尤恩伊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潘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苏玮.成长中“永久的划痕”:麦克尤恩《与橱中人的对话》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今古文创,2020,(26):38-39.
[7]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8]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 (01):118-127+15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