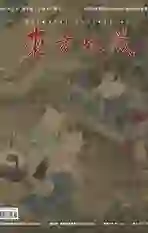黄河流域汉代陶灶图样考略
2024-08-17吴佳雯
摘要:陶灶作为陪葬明器,承载着古人对死后“大象其生”生活的想象,也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及庖厨相关行为特点。文章结合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从图史互证的角度出发,探究陶灶作为陪葬明器的原因,并研究陶灶上装饰纹样与汉代民俗的关系,研究内容涵盖随葬陶灶与汉代灶神祭祀传统、灶面与画像石食物炊具图样、灶门图样上的器具与人物形象三个部分。
关键词:陶灶;汉代;民俗
自春秋战国起,就出现了以陶灶作为陪葬品的风俗。在汉代,以陶灶作为陪葬明器的情况较为普遍。“西汉中期以后,作为明器的灶变化很大,装饰不仅仅局限于火门周围,在灶的四壁和灶面都出现了生活化的精美装饰。”从出土陶灶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带有装饰图样的陶灶大多出现在黄河流域,南方的陶灶装饰性较弱,且器型与北方具有明显区别。本文论述的陶灶以黄河流域出土模印庖厨饮食图样的陶灶为主,出土的陶灶主要见于河南、陕西、山西、宁夏和内蒙古。
一、随葬陶灶与汉代灶神祭祀传统
陶灶在汉代成为一种流行的随葬品,与当时的灶神祭祀活动脱不开关系。汉代祭祀活动较为丰富,且在典籍记载中说法不一。汉代祭祀活动有“五祀”“七祀”以及祭祖等,祭祀的执行者与祭祀的对象在不同的记载中都有所不同。①不管是“七祀”“五祀”还是“三祀”,灶台都在祭祀对象之列。祭祀时间集中在夏季,主要是在农历的四五月份。每个季节的祭祀对象不同,与阴阳五行有关。秋天是阴气渐长万物收的季节,冬天为阴寒之气,春天的阳气才开始生养,而夏天阳气积聚。灶与火、红色、夏天相对应,因此夏天要在灶台前进行祭祀。
在举行灶台祭祀时,祭品的摆放也有所讲究,这体现在汉代陶灶明器的纹样上。在灶台前进行祭祀时,东西主要摆放在灶台前突出的位置;另一种说法是“设主于灶陉也”,也就是将灶神摆放在灶台突出的位置。从宁夏固原博物馆馆藏的黄釉陶灶(图1)来看,应是将祭祀物摆放在灶沿前,而不是将灶神摆放于此。该黄釉陶灶在灶陉处运用乳丁纹表现祭品,排列整齐。宝鸡市谭家村四号汉墓出土的陶灶也采用这种表现手法,东西排列整齐有序,乳丁纹表现的应为动物内脏。《吕氏春秋》指出:“其祀灶祭先肺”,肺脏被选择作为祭品也是与其五行属性有关。《春秋繁露》同样提到祀灶祭品:“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又设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由此可见,祀灶祭品由心、肝、肺向外延伸。
除了夏季固定的灶神祭祀环节,如有祈雨、搬新家等情况也可以进行灶神祭祀,可见灶神祭祀在汉代的流行程度。“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灶台祭祀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而将灶台制作成为明器带入墓葬中,可能隐含着在往生世界中也能复刻生前祭灶祈福的行为,从而同样得到保佑。
二、灶面与画像石食物炊具图样
在《风俗通义》中提到南阳有一个名叫阴子方的人,他平时行善事积恩德。这个人喜欢祭祀灶神,传说在某个腊日早晨做饭时灶神出现了,刚好灶台边有黄羊,他就拿来做祭祀。后来他的子孙都封官进爵,为此,其后人就常在腊日用黄羊祭祀灶神。灶台上黄羊图像的出现,可能就与此传说有关。
可以看到,出土带有羊头纹样的灶台主要集中在河南与山西两地,陕西出土一例,但羊头纹样较为模糊,仅可从其卷曲的羊角进行辨认。笔者通过对收集到的带有羊头纹样的九个陶灶进行分析后发现,河南出土灶台中的羊头纹样位置较为不固定,居中摆放的羊头纹样只有一例,其余三例摆放较为随意。而山西出土的四个带有羊头纹样的灶台,羊头纹样都垂直摆放于靠近灶门的一侧。河南辉县赵庄墓地M50出土的陶灶,其羊头纹样的摆放方式与山西出土陶灶羊头纹样的摆放方式较为一致,都呈居中摆放。通过查询,发现两地的直线距离约为200 km,该地出土的陶灶纹样布置方式可能受到山西地区陶灶制作范式的影响。
羊头纹样除了与灶神祭祀仪式有关以外,可能还与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有所关联。虽然“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但在丧葬仪式这种大事中,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也会选择宰羊。在山东画像石中可见许多露天庖厨场景,有学者分析其为汉代丧葬仪式中宴飨宾客的环节,在这些图像中,羊也作为一部分出现。汉代的食物谱系已经相当丰富,虽然这些肉类食品的普及程度尚未可知,但是证明了这些动物有被作为食物食用的迹象。
在黄河流域的汉代陶灶中,鱼是最经常出现的一种动物图像。在河南、宁夏、河北、陕西、山西等地都有刻画鱼纹样的陶灶出土,在笔者收集的资料中,以陕西出土的刻画鱼纹样的陶灶数量最多。通过对笔者收集到的带有鱼纹样的陶灶数量进行分析:河南出土的七个陶灶中,有五个陶灶上的鱼纹样为独立出现,两个陶灶上的纹样漫漶不清;宁夏出土的两个陶灶上的鱼纹样为两条及以上;河北出土的一个陶灶鱼纹样为单独出现;陕西出土陶灶上的鱼纹样有三个为单独出现的情况,有五个为成对出现的情况;山西则是出土了一个单独出现的鱼纹样陶灶。由此推断,刻画鱼纹样的陶灶更多流行于陕西与河南,刻画鱼纹样的陶灶在这两个地区相比其他地区更受青睐。山东在临沂白庄汉画像石、五里堡汉画像石等画像石中都能看到鱼的身影,鱼或对半置于盘中、或于砧板上,还有呈悬挂状。可见,汉代人将鱼作为一种食物进行处理、烹饪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方式,鱼是汉代黄河流域人民较为常见的一种食材。
“在中原地区的陶灶上,常见有大量模印的食物和炊具,这与当时的经济富足紧密相关。”在宁夏、内蒙古、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出土的陶灶上都能见到烤串或烤串工具叉、钎的身影。呈直线状的是“钎”,而呈“Y”字形的是“叉”。通常叉都伴有环首,详见1978年宁夏吴忠市关马湖汉墓出土的双眼灰陶灶。而钎有时带有环首,有时不带环首。环首钎可参考河南新乡赵庄遗址出土的陶灶,而不带环首的钎可参考河南郑州巩义北窑湾M20:6出土的陶灶,以及陕西咸阳织布厂汉墓M3:12出土的陶灶。钎、叉纹样上一般还带有烤串图像,作为一个完整的食物图样被安置在灶面上。烤串图像在汉代各地的画像石中都可以见到,为常见的庖厨图样,乌海市三坝汉墓M3、山西临汾天马曲村M5221:2出土陶灶上均见有烤串图样。汉画像石中表现烤串的场景也非常多,五里堡汉画像石、孝堂山汉画像石都有烤串场景出现。
除了烤串工具外,还有多种庖厨工具也模印在陶灶上。如乌海市三坝汉墓M3出土陶灶表现为一长方形物体承托一些圆形物体,这些圆形物体大小不一;郑州博物馆馆藏新乡赵庄遗址出土的陶灶,可见一些大小相对一致的椭圆形器置于长方形盘子上;山西临汾天马曲村M5221出土陶灶上也见有该种表现形式;河南洛阳烧沟 M120出土陶灶上似有该种表现,但是图像模糊。印制该图样的陶灶分布较无规律,其应为当时常用的饮食器物耳杯,在汉代随葬品中有实物出土,如山东朱鲔石室画像中有两处表现耳杯的图像,均出现于人物类宴享图像之中。耳杯的出现,可能寄托着墓室主人期盼在往生世界中也能享受和生前同样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
三、灶门图样上的器具与人物形象
甘肃泾川县博物馆馆藏多个汉代陶灶,其中很大一部分陶灶的灶门上刻画有宝瓶与一人物形象或刻画宝瓶与宝瓶的组合图案。泾川县博物馆馆藏汉代陶灶中多能看到完整的宝瓶图案,宁夏博物馆馆藏绿釉陶灶(图2)和昭君博物院收藏的绿釉陶灶的灶门上也均刻画宝瓶形象。宝瓶形象在西汉中期以后多流行于关中地区,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陶灶图像之一。宝瓶图应属当时庖厨器具的一类,在汉画像石的庖厨场景中多次出现宝瓶形象,因而作为庖厨器具的代表,在陶灶灶门上有所表现。
宝瓶除了作为庖厨用具来进行表现之外,可能还与灶台的“火”属性有关。“五祀”的主要区别在于祭祀对象根据祭祀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夏天是阳气积蓄的季节,因此要祭祀灶神,同时灶台是火神的附身之处。在汉代警世故事中多以灶台失火进行隐喻,《吕氏春秋》与《战国策》中都有提及②,可见失火为当时的人们所警惕。因此灶门前的瓶,也可能是预防失火的水瓶。
在西安白鹿原汉墓 M35:6 陶灶前壁、咸阳织布厂 M8:2 西汉陶灶前壁两处陶灶的灶门边,我们能够看到清晰的人身蛇尾形象,这里应该是刻画人在灶台前添柴火的场景。在五里堡汉画像石、嘉祥蔡氏园画像石等画像石中,添置柴火的人都呈跪坐的姿势,因而身体蜷曲,在衣物表现上像人身蛇尾,宁夏博物馆馆藏的绿釉陶灶展示的可能也是这样的形象,但在制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扭曲。西北国棉五厂 M35:6陶灶的图案形象比较模糊,但也应为人物形象。
西安白鹿原汉墓 M35:6陶灶前壁与咸阳织布厂M8:2西汉陶灶前壁,这两处陶灶灶门边的人物头饰有明显不同:西安白鹿原汉墓M35:6陶灶前壁人物头戴高冠,并有一条巾子后垂,而咸阳织布厂M8:2西汉陶灶前壁人物左右梳理两个发包的造型,与密县打虎亭一号墓北耳室西壁南壁石刻画像中的侍女形象相似,应为侍女图。在山东画像石中表现添置柴火的基本为男性形象,其中所戴帽饰前侧表现较为倾斜,帽型高耸,顶部较窄。西安白鹿原汉墓M35:6陶灶前壁上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明显与山东画像石不同,而且关中地区所表现的与庖厨相关的人物多为女性,因此推断在西安白鹿原汉墓M35:6陶灶前壁上所表现的人物形象为一名女性。西安白鹿原汉墓M35:6陶灶前壁人物形象,应与灶神的传说有关。
汉代《驳五经异义》认为,上述情景的出现可能是妇人常参与饮食的制作活动,而灶神主饮食,所以汉代就流传灶神是一位妇人的说法。如果汉代人在灶面上塑造老妇形象是为了进行灶台祭祀,那么前文所提到的宝瓶图案也与灶神祭祀有关。“灶者,老妇之祭,尊于瓶,盛于盆。”宝瓶图案可能是为了让灶台祭祀仪式更加完整,而与老妇一同出现。《春秋繁露注》也提到了灶神形象,并提及《庄子》所记载的“浩,灶神也。如美女,衣赤”。对于陶灶上的人物形象是否身着红衣,我们无法判断,但这能够作为灶神是一位女性的说法的论证。还有陶灶灶门边出现两个妇人形象的组合,郑州博物馆馆藏禹州市新峰墓地出土的汉代釉陶灶,刻画的是两个妇人的形象,这应该就是庖厨场景的表现。
从上述材料可以发现,汉代黄河流域的主要饮食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羊在重大场合中会被作为食物,鱼类作为食物的情况就比较常见,肉串则是黄河流域比较普遍的一种饮食方式。在从事庖厨人物的表现上则有很大的不同,关中地区从事庖厨的人物形象大多为女性,这可能与地区的文化有所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汉代陶灶图样表达了黄河流域人民对于庖厨饮食的认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汉代饮食文化材料。
参考文献:
[1]周俊玲.“器”与“道”——汉代陶灶造型、装饰及其意蕴[J].文物世界,2009(06):24-29.
[2]蔡邕.独断[M].四库全书本.
[3]佚名.太平经[M].明正统道藏本.
[4]郑玄. 驳五经异义[M].四库全书本.
[5]高诱.吕氏春秋[M].毕氏灵岩山馆刊本.
[6]董仲舒.春秋繁露[M].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皇清经解续编本.
[7]班固.前汉书[M].武英殿本卷二十七下之上.
[8]许慎.淮南鸿烈解[M].景钞北宋本.
[9]应劭.风俗通义[M].四库全书本.
[10]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 [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
[11]冯沂. 临沂汉画像石图册 [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
[12]朱津.论汉墓出土陶灶的类型与区域特征[J].中原文物,2015(02):43-51+67.
[13]傅惜华等. 山东汉画像石汇编 [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14]杜赟清.泾川馆藏汉代陶灶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17):9-12.
作者简介:
吴佳雯(1999—),女,汉族,福建厦门人。宁夏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美术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