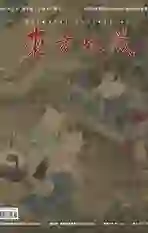廖迎晰:哲理、诗情和艺术的感性呈现
2024-08-17刘登翰

廖迎晰是一位有思想、有诗情、有自己大追求的中生代艺术家。以往虽在她的工作室里零散地观赏过她的一些作品,但这次借助其即将出版的画册,才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她几个系列的创作——尽管这远不是她创作的全部,但这个印象仍十分强烈地震撼着我。中国有句老话,说的是“知人论世”,用在文论或艺评上,是指只有了解其人,才能深入地评论其文或其画。其实这只是一面,还有一面则是“论世识人”,用在文论或艺评上,同样是说,对于作家或艺术家,只有深入了解其文或其画,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人。读文和读画一样,都是在读人,读作品背后那个执笔的人,这是不同于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开放性的东方文化批评。我对廖迎晰的认识,经历的正是这样的过程。
廖迎晰给人最初的印象,很“女人”。是的,在她泡一杯氲氤的冻顶乌龙,或煮一壶浓香的南美咖啡,静坐一旁聆听朋友们大声谈笑的时候,或在她居家和爱女嬉闹的时候,日常生活中的廖迎晰是个端丽、娴静、优雅的女性。然而只要来到她的工作室,看其专注、果决的工作状态,或者进入她的艺术世界,从她于作品中寄寓的深奥的哲思和诗情,以及严峻理性的观察和思考,就会感受到她艺术思维中强烈的男性化特征:一个“很女人”的艺术家“很男人”的创作。难怪当年闽晋台艺术家在前往山西采风途中,一位画家诧异地问她:“听说你也做雕塑?”那弦外之音,仿佛雕塑这种艺术“重工业”,是男性的专利,而不是她这样一个优雅的女性做得了的。事实恰恰相反,雕塑在廖迎晰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只有当你细心地欣赏这些作品,你才会发现,这些看似“很男性”的作品,其实都是她以“很女性”的方式来表现和处理的。艺术本就不该有“男性”和“女性”的分野,只有艺术个性的不同。廖迎晰恰恰是在“很男人”的艺术理性和“很女人”的艺术感性之间,建立起自己的艺术个性。
这或许是许多女性艺术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和有过的共同经验,只不过廖迎晰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会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对事物外在形象的描摹上。这样的作品,即使画得再精细、再“像”,那也是一种缺少灵魂的匠人作为。艺术家在描绘事物形象的同时,总会有自己更为深沉的蕴藉。无论写实还是变形,或者具象、抽象,艺术家画笔或塑刀下的造型,已不是作为描绘对象的那个客观物象,而是艺术家主观对物象的“再创造”,融入了艺术家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温度。廖迎晰的一系列作品,从“人之初系列”“亚当夏娃系列”到“幻·山水系列”,她所关怀的是生命:生命的源起、存在和困境,是一个关于“人”的大命题。她以爱为核心,向着生命的诞生和生存的困境两端展开。作者开阔的视野以及对于艺术的大追求,关注的不只是具体事件和细节的道德评价,而是整个“人”的生命原本形式,以及生命的起源和生命诞生赋予这个世界的意义。
廖迎晰的艺术世界,是一个符征化的世界。无论是爱意的表达、生命的创造,还是追怀万古而思索今天、由微4R6fp34VSARvgYfiO/Nujg==观而达致宏观,符号化的意象和象征是她最重要的艺术手段。这使她的作品,无论平面的油画还是立体的雕塑,都蒙上了一袭朦胧、神秘的面纱。(节选)
(刘登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廖迎晰简介
廖迎晰,出生于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美术研究所毕业,比利时列日大学在读博士生,公共艺术家。现为华承国际艺术总监、安徽铜陵铜雕艺术研究院艺术顾问、深圳欧古轩艺术中心公共艺术顾问、台湾墨海艺术协会理事长。作品多次在国内、国际大展(赛)上获奖,荣获“福建省雕塑大师”等多个荣誉称号。
艺术家以对生活经验的反思,并借传统经典作品,作为转换媒介,以当代手法表现古代经典题材,进而引申出观赏者意料之外的一个表现。作品多以“爱、希望、圆融”与“现在、过去、未来”之时间的意象,将其个人对于当今社会环境的关注显现于作品当中。迄今为止,先后在日本、德国、比利时、韩国、意大利、泰国、英国、印度、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的北京、上海、台湾、深圳、成都等地举办个展二十余次,参加国际、国内联展百余次。作品陈列于多个知名场馆,并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知名机构,以及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私人藏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