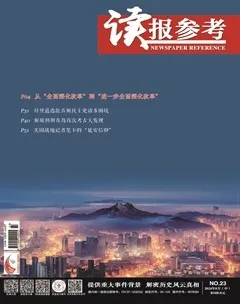徐州热粥苏轼赞
2024-08-15张小勇
热粥是徐州特有的早点。年纪大些的徐州人都知道,热粥是“拐”出来的。
卖热粥的人家,头天晚上要将精选的黄豆与粳米,按一定比例用水泡上,子夜过后,再将黄豆与粳米捞出来,在小石磨上慢慢磨,磨成浆沫沫。怎么说是“拐”呢?早年间,早晨卖热粥的人家,都是小本经营,在家中制作;每天制作的热粥分量有限,大都是装盛一瓮而已。所以只用一盘小石磨加工即可。小石磨完全靠人手工推动。磨浆的人坐在小石磨旁,一手攥着小石磨上盘的木把手,绕着磨心旋动上盘;另一只手攥着一勺子,不时将身旁泡过的黄豆与粳米舀起,倒入磨眼中。人攥木把手的那只手臂在转动中绕来拐去,年岁大些的徐州人,就说“热粥是拐出来的”。
拐动小石磨,石磨上下盘之间就不停地流下浆沫沫来。磨完了,将浆沫沫倒在锅里添水熬制,就熬成了几乎没有颗粒的热粥——处在稀饭与稠粥之间的一种糊状粥。由于熬制的主料是黄豆与粳米,所以熬成的热粥,散发着黄豆与大米混合后特有的香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热粥,历史很悠长。北宋年间,苏东坡诗里就出现过“热粥”二字。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东坡在徐州任知州。一次与朋友宴饮,高兴中喝多了酒,人有些醉,一个叫艾贤的农民端了一碗热粥给他喝。苏东坡喝了热粥,浑身舒畅,即兴赋出了《豆粥》,诗云:“身心颠倒自不知,更识人间有真味。”热粥的可口与宜人,可见一斑。
1957年,我在老黄河畔的大马路读小学,冬天上学早,家中还没烧早饭,出门前,娘会给我三分钱,叫我到大坝头南巷的巷口喝热粥去。寒风中,临街卖热粥的是一老头儿,热粥装在裹着棉褥子的大瓮内。大瓮旁摆着低低的木案板,木案板四周地上有几个小木凳,喝热粥的男女老少就围坐在木案板旁,盛了热粥的碗摆在案板上。有的端着碗喝,有的低头将嘴凑着碗沿喝。有的光喝热粥,有的另买两根油条,将油条撕成段儿,泡进滚烫的热粥里吃。那时热粥一分钱一碗,油条两分钱一根。七八岁的我,早晨一根油条一碗热粥就饱了。
人到晚年,往往思念故乡的小吃。虽然常年生活在南方,每每说起热粥,面前就浮起热粥那独有的香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