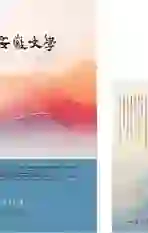经验、想象的过剩与整体意义的匮乏
2024-08-12陈振华
本雅明曾经将经验区分为无意识的经验(体验)与理性的经验。前者所指的是经验沉淀在人的无意识深处被偶然唤醒,后者则是主体的人对经验有意识地记忆与保留,从而成为人的生命经验与理性。其实,在这两个维度之外,还有第三重维度,那就是想象性的经历与体验,它带有梦幻与超现实的意味。《火车驶向虎兰礁》即是以陈海伏的无意识经验、有意识经验以及想象性体验为主体编码的一篇小说。从文本自身的审美风貌而言,乍一看,似乎有着别样的风味、形象的比喻、陌生化的修辞以及些许异质化的诡谲。然细读之后会发现,这些杂花生树的叙述背后,给人的阅读感受是经验与想象的过剩,它们像碎片一样被编织在缺乏有机性的叙述话语之中,文本匮乏整体的意义建构或象征隐喻题旨。
陈海伏(小说中的阿伏)是一名未成年的码头船工,漫长的禁渔期,他无事可干,百无聊赖,仰躺在渔船的甲板上,终日漂荡在望耶港的海湾中,浮想联翩,心思漂移。阿姐的呼喊和踢打将他从神游的状态拉回港口世俗生活的现实。周围漫漶着的是常年的鱼腥味、腐烂味,长久生活在这样的气息与味道之中,即便年轻的阿伏也感到窒息、沉闷和绝望。母亲的形象就是阿姐未来生活的镜像:一个悲哀的句号,一根慈悲的火柴,身体在经年累月的劳作、风雨的侵蚀下逐渐凋零、衰朽。舅舅的形象则是阿伏未来的写照:肩负起家庭的重担,在出渔期出海打鱼或捕获其他海产品,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勉强度日,日益变得沉默寡言,最终苍老如版画一般。这些生存场景、氛围、经验,阿伏从小就浸淫其中,已变成其无意识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循着这样的生存经验,阿姐和他的未来就是照着母亲、小姨和舅舅的葫芦,依样画瓢,继续重蹈人生大致相仿的命运轨迹——整个望耶港的居民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凡俗、平庸,充满咸腥味、汗臭味的时空里。
终于,挤过嘈杂、混乱、拥挤的人流,阿伏登上了开往虎兰礁(仅仅是小说的标题所指,小说的叙述并未明确)的绿皮火车,火车启动,在海水中劈波斩浪,远方的大海以及充满乌托邦色彩的虎兰礁渐次敞开了它的胸膛。小说在叙述火车行进的过程中,又不失时机地穿插对阿伏既往日常生活的回忆。叙述人以“你”“你们”为叙述视角,试图拉近叙述者和主人公的距离。这些叙述是有意识的回忆,因此可以视为本雅明所言的“理性的经验”。在“理性的经验”中,你离开母亲和小姨,和舅舅一起驾驶着桁拖渔船前往你舅舅三番五次念兹在兹的虎兰礁,据你舅舅的描述,那里有俯拾皆是的海产品,那里人们踩着鮸鱼的脊背就可以上岸。这是你最为开心、美妙的人生时刻,你在闷罐子火车里、在依稀的梦里,很清晰、有意识地回忆这些场景,这说明,这些经验(经历、体验)不仅仅内化为你的理性经验,更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或觉得最有意义的经历、体验和感悟,你从枯索的禁渔期中得以抽身,你从窒息沉闷的生存环境中得以短暂逃离,你义无反顾地冲向心中的乌托邦,你也在妈妈、小姨、阿姐的眼中逐渐成长为可以独立的真正男子汉。然而。文本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桁拖渔船朝向的神圣目的地虎兰礁,还是绿皮闷罐子水上火车开往的乌托邦家园,在文本中都没有现身,它变成了一个无限延宕的存在。就像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中的戈多,始终没有显现真身,舞台上的各色人等永远在等待他的“过程”中。由此,《火车驶向虎兰礁》的叙述就只能停留在对你既往无意识经验、理性经验的不断交叉出现的循环中,从而导致叙述上对“你”的经验的不断闪回、重复、回忆、梦幻的过度演绎,最终形成了无意识体验和有意识经验叙述的过剩、冗余。
不仅如此,小说的叙述重心逐渐过渡到你的想象性体验。你跟着舅舅踏上了水上火车,火车驶向何处?舅舅闷声不响,更令人诡异的是,你从舅舅的衬衫里摸出的五张粉红的车票,居然通往五个不同的地方,并非如小说名字所锚定的“虎兰礁”。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反复皴染了火车上的拥挤、混浊、混乱、嘈杂。之后小说的叙述转入超现实的想象性体验与回忆性经历、体验的交替出现。尤其是在超现实梦幻般的想象性体验中,出现了很多奇谲的现象和场景,给你带来既往无意识体验和理性经验所没有过的观感和震撼。火车车窗一夜间长满青苔、火车蔽明前行、孔洞外的海水幻化为蓬勃世界、幻化为一个斑斓的花园。火车在藤蔓编织的热带雨林之网的缝隙中穿行。而你的行为更加匪夷所思:激情已被消耗殆尽,浑身上下的力气无处安放,便翻过车窗跃上了车顶,在火车的车顶上来回狂奔、跳跃,你在车顶看清了这里不仅仅是绿草如茵,还有死水、沼泽、赤链蛇。火车一路向北,超现实的想象叙述中,又嵌入你父亲陈步坦的故事以及你在父亲墓碑上将自己的名字完完整整地书写一遍的经历。火车诡异的前行依然继续,火车车厢被冰封了几近三分之二,你们不下车,火车就只能一直向北趔趄前行,直至完全脱轨,跌落山崖,石破天惊地破冰入水。而你则在海底的丛林和花园里看到了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并最终被水母温柔地从脚底板托举出海面。小说的结尾,你舅舅雇用的两个湖南人,一个左撇子,一个跛腿爬上岸后的第一句话是:“老天,我这是在哪里?”无疑,更是增添了小说亦真亦幻的超现实色彩。和前述无意识体验与理性经验的叙述呢喃一样,“丰富”的想象性超现实的搭乘水上火车的经历与体验,究竟在文本中承担怎样的叙事功能?火车的倾覆具有隐喻意义吗?垂死的母亲对你的谆谆告诫,要你听舅舅的话,是临别遗言?火车驶向虎兰礁,虎兰礁究竟在哪?抑或仅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甚至是一个臆想的异托邦?叙事没有朝向,逻辑关联与因果链条被切断,叙述中无意或故意留下了许多“空缺”,而这些“空缺”不是我们习见的潜隐的草蛇灰线、艺术的留白,而是关键逻辑连接点的缺失。这样的叙述颇具先锋性,而致命的缺陷导致文本意义整体性的空无。文本叙述只剩下一堆经验、想象的碎片、语句、段落散落在文本的各处。
为了避免行文的过度枯燥单一,叙述只能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对主人公“你”的经验感受的反复摹写以及不厌其烦的修辞。撇开整篇总体立意看,单看一些粼光闪闪的句子与修辞,这个文本颇富一些文采。这里试举几例:“你的眼底陡然激荡起无数鱼鳞样的灿烂光斑,你知道无数的云在你眼底咕嘟咕嘟冒泡泡。”“无数缆绳如海的脐带伸向陆地”“许多苍老如版画的渔民蹲在门边,长久地凝视着来去缤纷的腿”“你流出的两股眼泪好像两道铁轨直达天际”“车轮嘎吱嘎吱前行的时候,一种类似脊椎一节一节断裂的声音顺着车轮就弥漫上来了,你的尾椎骨马上响应起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形象的比喻、夸张的想象、神奇的通感让小说的叙述充分感觉化。中国古典诗论者认为,中国有不少古典诗词,“有句无篇”,单看句子,佳句频出,然则整首诗词,却无“整篇”。王国维甚至认为:“五代词有句无篇,南宋词有篇无句,有篇有句唯后主之作。”这种观点对当代小说创作同样适用。有一些作家过于注重字词、语句、修辞甚至段落、章节的精彩纷呈,却忽略了这些精彩的话语、修辞、句段与整部小说的布局谋篇、整体立意之间的深度关联。部分先锋小说极端到创作仅仅停留在话语狂欢的表层,彻底放逐了文本意义的指向,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义链条被截断,意义通道被阻塞,文本叙述悲哀地沦为能指的漂浮。
学者、评论家黄子平早在1980年代就说过:创新犹如一条疯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小说叙事的创新也莫能例外。《火车驶向虎兰礁》试图在叙事方面有所创新,现实与超现实的交织、真实与梦幻的真假莫辨、无意识体验/理性经验以及想象性体验的互嵌、小说叙述的充分感觉化、话语修辞的多样性、海岛码头人情物理的呈现以及后现代的叙事风貌等,确实给人带来一种异质性的阅读体验。遗憾的是,表层经验、想象的叙述给人以过剩的观感,并没有导向文本核心意义的有效生成。小说的书写也许受到时下流行的网络类型小说的影响,在玄幻、想象、纯虚构的叙事背景下,部分延续了先锋小说的余绪,由此形成了这篇小说的审美形态。而我想说的是,无论叙事形态如何花样翻新,文本都需要一个核心意旨作为面向,需要一个整体性意义作为归趋,读完《火车驶向虎兰礁》,无论从写实、象征还是隐喻等层面都无法形成总体的意义建构,而这正是这篇小说的致命伤。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