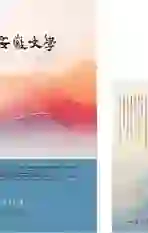人类挚友在自然中
2024-08-12钱红莉
小满未满
小区十余株枇杷树,一夜间,所有小果子一齐黄了。无须查看日历,小满想必到了。
许是上了年岁,立夏以后,凌晨即起,小区漫步。走着走着,抬头间,一树榴花的嫣红,辉映一树枇杷的橙黄,清风徐徐,花枝果叶微拂,我的心颤动一下——真是美咧。
美为何来?说不出,唯默默感受。
冰箱里明明存有余菜,总是拦不住自己,执意往菜场去,来来回回逛一圈。水果摊前,波罗蜜的香气弥漫,异国大樱桃红里透紫,圣女果散发着迷人光泽,红黄魅人,怎能忍住不买一些呢?
蔬菜档位上,忽现一个牌牌,上书:“皖北人的乡愁”——到底,荆芥上市。拈一株,放鼻前闻嗅,沁人心脾的药香气,我这个皖南人一样喜爱。
荆芥上市,夏天确乎来了。藕带、南瓜、丝瓜、黄瓜……如若钢琴曲的急速回旋,一样样叮叮咚咚而出。
买回满满一兜菜,太阳尚未升起,将小电驴停驻于门前柿树下,长风忽来……站在树下,仰望巨大而深绿的树叶层层叠翠翻滚,心为之静。
久站树下,不舍离开。南风虚怀若谷地吹啊吹啊,吹得我乱发穿空卷起千堆雪,所有感官次第打开,每一寸皮肤每一根发丝全部复活——我想坐在树下包几斤粽子。
糯米浸泡一宿,赤豆、蜜枣于水的浸润下变得松软。两片粽叶,仔细叠好,挖一勺糯米,添一颗蜜枣和几粒赤豆,粽叶闭合,麻线扎紧。十个粽子连成一串,拎在手上宛如一串绿茵茵的动词……
做手工活,耳朵也不闲着,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轻缓流淌,我家门前倏忽一条大江流过……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嗯,我的故乡瞬间于杜甫的诗中复活。
小区门前一辆皮卡,装有百余斤蚕豆荚、豌豆荚,来自皖北临泉,十元四斤。我剥开一只豌豆荚,豆米处于青黄之间,用来煮糯米饭,正是时候。絮话间,陆续围拢几位老人,每个人均称四五斤。老人教我:你把豆米剥出,冷冻在冰箱,春节吃也不碍事。
家务琐事料理完,终于可以歇息一下。坐在客厅剥豌豆,初夏的万籁俱寂之中,一颗豌豆粒掉落地板滚动的微响也能听得见。
豌豆有多种烧法。瘦肉剁末,取胡萝卜一根,切细丁,与豌豆粒一起爆炒,略微激点水,铺上肉末焖煮四五分钟。起锅前,撒一点孜然、胡椒粉,入嘴甜而软糯,下饭神器。
冰箱存有一小块腊肉,特意留待小满时节,烧一道豌豆糯米饭。
腊肉切丁,与姜粒一起,热锅煸香出油,糯米、豌豆洗净倒入,翻炒入味,一齐移入砂锅,加适量滚水,中火焖煮四五分钟,熄火停顿数时,小火焖煮……待砂锅内发出噼里啪啦脆响,饭熟。
腊肉豌豆饭适合热吃,咸香扑鼻,糯而不腻。最惊艳的是锅底那一层焦黄锅巴,如若金不换,唇齿间流淌小农经济的异香。末了,喝半碗丝瓜鸭蛋汤顺顺肠胃,静静摊在沙发养养神,窗外大风,把绿树吹得翻起,浪一样涌动,如行海上,四野茫茫,无际无涯。
樟树花刚刚凋落,香气尚未走远,合欢便开出了第一朵,蜀葵也不甘落后。忍冬沿着路灯杆攀缘直上,黄的花,白的花,香风细细。金丝桃如火如荼……花讯,一场接一场。高大的广玉兰革质叶丛中,“砰”一声,忽然怒绽一朵ef1238bd054fd24d338a0456b9e138fa白花,复瓣花朵大如蓝边碗,于五月的艳阳下唱着浩荡的歌。
立夏以来,恢复黄昏散步习惯,日日有晚霞可看。
居所附近那一片荒坡,是我眺望宇宙的唯一窗口。
天空变幻不定的云朵,时而巨鲸横陈,时而城堡耸立,如梦如露亦如电……夕阳余晖中,当我伫立高处,眺望壮阔无边的晚霞,橘黄、玫瑰红、苍灰相融相和,将天空洇染得立体广大。众鸟归林,大地沉寂,夏风无所不在地吹啊吹啊……芦苇于低处沟渠急速生长,香蒲葱茏一片的绿里,深藏默默思君的惆怅……
我在青草的香气里疾步,无所止,而无所终,耳畔隐隐约约响起罗大佑、陈百强、蔡琴、邓丽君的歌声……忽然觉知,我的一切链接均是旧时代的了,但古典乐永远是簇新的,当倾听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直至晚霞一点一点被黑夜吞没……星挪辰移,亘古未变。
到了《火星》一章,定音鼓追随小提琴的森林,黑管、双簧管、大提琴、中提琴、长短笛适时加入,轰隆喑哑如急行军,使我不觉加快步伐频率,直至累得精疲力竭,仿佛早早获悉人类的命运。
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我们DNA里的氮元素,我们牙齿里的钙元素,我们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的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的万千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星尘。
是的,人类渺小如微尘,但,人类又是伟大的,这些有着炽热想象力的优秀灵魂,正不断创造出各类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绘画……他们犹如一个个永恒的发光体,与星月同在。人类困于局限,而又勇于超越,当真了不起的。
我常常劝告自己,不要急,慢慢写,尽量多读书。
读书的过程,是逐渐走向开阔的过程。接纳自己,接纳别人,接纳发生着的一切,宛如一年接纳春夏秋冬,接纳二十四节气,逐渐地,人便不会陷入焦躁、忧惧,融入风一样的平和之中。
前阵,整理餐边柜小屉,发现一只小包裹,打开,摊开一小把黑炭样花子,恍然有悟,是去年秋天收集的晚饭花种子啊。开春时,忘记把它们撒到楼下空地。接下来的盛夏黄昏,没得紫花可赏了。但,错过一季,又有什么关系呢?留着明年,它们还会一样发芽的啊。
对门邻居姐姐家,白兰花新开一朵——每日清晨,在我们两家共用的外阳台晾衣裳,总是被这洁白清澈的花香氤氲着,真是福报。今年,她养了一缸荷。哪天我去买回几尾游鱼,与这一缸荷结结伴吧, 像把一个词放在另一个词后面,组成一个踏实流利的句子。
昨夜,邻居姐姐敲门,打开,她赠与一袋豌豆,说是刚回了一趟故乡。
故乡,是一个令人意动的词,像小满一样让我们终生热爱。
花花朵朵,杯杯盏盏
芒种后,一日热似一日。晨起推窗,鸟鸣之声,寥寂寡合,仿佛欲言又止,始终懒懒恹恹的。
万物似都提不起精神。唯花花朵朵,兴兴头开着。这无穷无尽热烈奔放的天性,颇为感染人。
屋后山坡上,一丛又一丛夹竹桃,万花怒放……白衣胜雪的白。
夹竹桃的花,还是白色的好——远望,雾气袅袅,如白丁香开在细雨中,恰好一阵风过,微微晃动,梦一样的质地。
其次蜀葵,广布于小区底楼庭院旁,一株株挺立着,不分杈。蜀葵的气质,近于舞者,长身玉立,有着天鹅颈似的。然,世间物事总逃不了二律背反原则。蜀葵如此好身段,开出的花,却不尽如人意,颇为俗气了:暗红、浅红、桃红、紫红、粉红……红颜料泼翻,独缺洁白色系。各样浓烈的红花,犹如上上下下被按了多只喇叭,一声声嘶鸣着,热啊热啊热啊……酷似大红裙女子,走哪儿都自带一阵熏风,简直大白天点灯。
酷夏时节,红色系衣服,不太合宜,无论男女,不仅热,还额外显出呆傻之气。小区广场舞的红扇子除外。
我喜欢看妇女们跳民族舞,红绿相间的蜡染布扇子于头顶身畔袅娜,弯腰,侧身,转体,右脚绕至左脚后,下蹲,再一抬头,群扇“唰”一下散开,如飞龙扶摇直上了,像极了巫术里一个神秘的仪式,也是生命刹那的完成。伴舞音乐是老旧的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要么: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
中国的民族舞里有流水潺潺的自然,也有嘈杂热烈的俗世,总归都是叫人热爱生活的。
周末夜里,喜欢带孩子去小区附近的某商业广场。广场极大,自动分成三组民间舞团。其中一组交谊舞,男伴黑衣黑鞋,女伴上黑下红,百褶裙随着她们陀螺一样旋转,花一样散开,足下皮鞋踢踏有声,一派往复不休你中有我的和谐。交谊舞很好地诠释着两性关系,彼此赏悦,互为成全。
另一组舞团,自动围成一个偌大的圈子,与老鹰抓小鸡游戏相若,音乐节律始终摇摆着的,近于疯癫,男男女女,一会儿张开双臂,一会儿耸肩扭胯,望之粲然——可又说不清笑为何来。
最后一组舞团,乐声冲天,肢体语言炽烈似火,近于街舞,旋律如密集鼓点,亦如急行军,无所不在的律动感。最惊奇,团队里两位大爷,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驾驭得了如此激烈迅捷的舞姿……人人衣服湿透,趁间隙,喝口水。夜空昏灰,不见星月,唯有音符永不停歇,直跳到天荒地老……
整个夏日,金银花始终幽秀低回,像一个人辗转细腻的心思,敏感,纤巧,素淡,又长情,永远开下去,一直开到初秋。
然而,比金银花更加长情的,还数复瓣栀子。
有人看栀子花,村气,嫌其香气浓烈,我则以为亲民。
栀子花的香气里,始终有一份与生俱来的大老实,也是一种稀世的趋真精神。年年端午前后,栀子迎来花期,热烈又真挚,不分黑夜白昼地开。
栀子最美的状态,当数含苞待放蓓蕾期,像春风少年,世间的一切都是簇新多姿的,蓓蕾鼓胀着,随时蓬勃而出。这青白相间的蓓蕾,被莲花状青柄托起,顺时针旋转,一瓣一瓣紧密相连,心手相牵。
栀子蓓蕾的香里,是泉水调蜜的气息,淡淡复浅浅,月光一样柔软,小鹿一般怜爱。待整个花朵张开,香气馥郁起来了,有酒至微醺之感,待沐浴几日阳光,花朵锈黄,枯了,落了。个别的,结一个两头尖的果实。中药里,被称为“黄栀子”的,莫非这种家常品种?在古代,黄栀子可用来染衣。
这些年,去过各地,见到各样古朴的茶盏,总是爱不释手。苦于神经衰弱,不能饮茶——这些茶盏就都一直寂寞地被关在书柜里。每年栀子花期,它们一齐被派上了用场。
不能实用,何不审美?
黑釉茶碗,适合蓄养栀子花苞。清水半碗,浮两三朵蓓蕾。黝黑底子上,飞了一点青白,如国画留白,以少胜多。甜香气稍被水稀释些,浅淡若无。
有一只茶盏,颇为拙朴,印的是浮世绘。日本大和时期女子,云髻高耸,脖颈颀长雪白,被一袭黑和服包裹住……这样的器物,适合喝一杯明前的西湖龙井,恍惚活在了南宋。可是,没得西湖龙井,插一朵盛开的栀子花吧。黑白配,极尽嵯峨之美。
南京作家黎戈曾赠我一只玉杯,常年置于书柜间,微微泛了幽光。这样的时节,拿它出来,注满清水,一朵栀子蓓蕾随性斜靠于杯沿,空疏,简洁,遍布寂静……搁窗台,望之良久,像菩萨。杯身刻有四字:平淡之喜。像禅语。
我们的一生,大多囿于困惑迷茫、焦虑无奈、追念痛悔之中,少有平淡、宁静时刻。
迷你型紫砂壶,也可用来蓄养栀子花,最好带长枝,绿叶三两片,配两朵白花,当清供,有宋时案头山水的清气。
磨砂质地的茶宠里,也插一朵栀子花,搁鞋柜上。黄昏,身心疲惫旋开家门,一股暗香扑来,像孩子的拥抱,末了,还在你额上浅浅碰一下。
栀子花这样纯洁无邪的白里,有一个幼童的向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吾乡女子大多拖着两条麻花辫。清晨小河边,一朵朵白栀子在她们黑发上跳动。年老女性将花别在鬓边,姑娘们将花绑在辫梢或插于辫根处。
小河淌水清悠悠,两条黑辫搁在她们胸前,随着双手揉搓衣物的节奏而耸动着,栀子花也一同雀跃起来了,白鸽一样灵动。她们挎了一篮蔬菜自河边走过去,香风细细,万物寂静,一种无所不在的荷尔蒙气息,河水一样遍布,是簇新的甜气,沁人心脾。
幼童是混沌的,一日日置身于山风月色之中,却浑然不觉,反倒一派漠漠然,非得隔了许多年,才会被一朵朵白栀子点燃,仿佛短暂的童年都拥有着一生的落日与晚霞。
置身城市,少见落日、晚霞的机会。城市没有地平线可言。
夏日黄昏,有着木质的光线,似叫人看得见纹理。
一次,我与孩子站在小区一株高耸的合欢树下仰望——成千上万羽状叶片渐收拢,露出一线瘦天。彼时,一大一小两人即刻幻身为两条游鱼,静置于河底,河面为水草所覆盖而露出的一点罅隙,安静而微妙。
翌日,熹微时分,合欢叶子渐次舒展开。重站树下,天空不见了,唯余一地浓荫。合欢花永远开在枝巅,喜欢压过叶子一头。羽扇一样的花,天生不怕热,烈日下开得欢洽,有茸茸之美。这些花花朵朵,枝头停留三五日,悄悄落下,比微风还轻。地下堆积层层残花,由红渐黑,幻为无形。
昨日,东北朋友发来两种我不认识的花:山丁子、黄刺玫,一白一黄,充满蓬勃的野气,令人向往。
责任编辑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