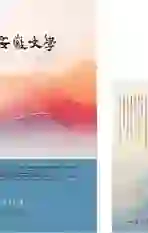古树札记
2024-08-12赵丰
枫
枫,左木右风,一曰为树,二曰喜风,叶如人掌,极易招风应风,稍有轻风,摇曳摩擦,哗啦哗啦。
秦岭北麓牛头山上长着许多枫树,覆盖了整个山坡。庞光镇在牛头山下,间距一公里许。霜降一过,更显山高水长,从我家的位置望牛头山,枫叶呈现一抹火热的金黄。
在古人那里,枫叶是被蚩尤的鲜血染红的,文字记载源于《山海经·大荒南经》,“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说的是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尾声,低吟的秋风轻拂蚩尤披散的长发,冷冷的急雨叩击蚩尤赤裸的胸膛,战败后正在受刑的蚩尤血浸桎梏,化为秋风里的枫树。神话赋予枫叶以精神因素,让杜牧喜爱有加,诗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杨万里的眼里,枫叶是偷喝天酒而被染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
南唐李煜亡国,遭后世斥责非议,用史学家公正的眼光审视,李煜并非懦弱无能之辈,亡国为时势所致。我非史学家,只是喜爱李煜的词,尤喜他《长相思》的上半阕:“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一重又一重,谁知多少重的枫树,相映着苍茫寒冷的天地,是思妇还是忧国,岂能说清?
古籍里的文字,枫叶总是美好。少年哪懂审美,见到喜爱之物,只会说好看,但“好看”二字蕴含审美之意,秦岭北麓面坡之树,大多是杜甫诗中所言,用以“伐薪烧炭”,我没有烧炭的阅历,但有的是背着竹筢搂树叶的生活体验,杨树、柿子树、核桃树、梧桐树,这些落叶适宜烧炕,也搂枫叶,红黄兼备的叶子铺地,举片枫叶,细察形状,呈掌状,正反两面均为金黄色,叶脉背面有几圈回旋的花纹,中间点缀着或大或小、色泽有深有浅的圆点。片片叶子,几乎一个形状,也会念想,人的模样各有区别,枫叶为何长着相同的脸。显然,这是少年的思维方式,大人也许不会有这样的念想。
渐渐年长,审美便进一步,忽然发现枫叶的花纹隐约透露出一些高山流水的痕印,像极了一幅山水素描。我曾珍藏过牛头山的一片五角枫叶,夹在《青春之歌》的书页里,和女主人公林道静一起呼吸,一起诉说心事。一片树叶,如一叶舟,足以负载生命前行,那本书后来找不到了,我忧伤了许多日子。
牛头山初秋的季节,暄气初消,月正圆,天透明,枫叶嫩黄,宛若油画,可惜那时没有相机,无法留下它的倩影。人到中年,忽然对草木情有独钟,潜意识觉得拜访植物便是参禅,对少年时偏爱的牛头山枫树,更是念念不忘。每次回家乡,脚步牵着我不由自主地走向牛头山。不知何故,坡上的枫树剩下孤零零的数十株,为一面山坡坚守着风景。秋深,绕枫树转圈,脚踩松软的枫叶,仿佛棉絮做的地毯,舒心惬意。仰头,望依然挂树的金黄之叶,竟生清雅芬芳之情怀,浮闪迷人的怀旧。风卷落叶,接住一片枫叶躺在掌心,欣赏着它的流韵,奢望用文字轻唤它的诗意古色。其实,按《幽梦续影》“山树宜画”的说辞,我应当去学作画,为牛头山枫树涂抹出最好的情韵。
枫叶有传说,谁如果能够接住被风吹落的枫叶,会获幸运。若与心爱之人一起目睹枫叶飘落,便可永不分离,此为枫叶赋予人生的况味。岁月轮回,生命沉淀,情感永恒,汇聚于一片叶子。
尼采这样说:“寻找的人容易迷失。”在牛头山寻找枫叶,我的意识陷入迷离,常常忘了回家。六十周岁那年霜降的节气里,仿佛冥冥之中的约定,我爬上牛头山,与枫叶在一面山坡谈心怀旧。天空澄澈高远,树上已无枫叶,皆铺展在山坡上养生,我不忍心踩踏那层层堆积的枫叶,怕听见它心碎的呻吟,怕惊动了藏匿在它体内生命的韵律。喜欢山野读书,坐于树下,捧出《小窗幽记》,山风乱翻书,掀开卷五“素”篇,书页有句:
霜降木落时,入疏林深处,坐树根上,飘飘叶点衣袖,而野鸟从梢飞来窥人。荒凉之地,殊有清旷之致。
如此文字,自是润心。
六十一过,该是奔老而去,那是我中年的最后一个秋天。
槐
槐树,我称老槐,亲人的感觉。祖父告诉我,咱家的老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来的。
某些草木,在古代文人那里是人格理想的化身,就如槐。槐的祖先在华夏,称之国槐,历史久矣。最早的文字记载为周代宫廷外的三棵槐树下,恭敬地站着朝见天子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后人依此用三槐喻三公,故成为宰辅官位的象征。古代大臣多在门旁植槐,名曰槐门,祈望子孙位列三公。《花镜》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园艺专著,清人陈淏子所著,发黄的书页有这样的文字:“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荫,一取三槐吉兆,期许子孙三公之意。”宋代东坡是有气节、有情怀之人,在《三槐堂铭》中提及一个官至晋国公王祐的人,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槐落民间,多在老宅生长,树上架着鸟巢,树下有竹凳,老者坐其上,手捧《论语》念念有词,不再妄想官爵,只是祈望家业兴旺,后人遵规守道。所谓院中一棵槐,清风自然来。
槐芽可食,有清凉收敛、止血、降血压之功效,主治便血、血痢、痔疮出血、衄血、高血压。《本草纲目》云:“槐初生嫩芽,可炸熟水淘过食,亦可作饮代茶。或采槐子种畦中,采苗食之亦良。”《抱朴子》云:“此物至补脑,早服之令人发不白而长生。”《名医别录》与之说法相似:“服之令脑满发不白而长生。”槐之花蕾,俗称槐花,生吃熟吃,皆是美味。生吃清香润口,拌面糊蒸,甜绵滋润。熟吃,叫蒸麦饭,从祖母到母亲,再到妻子,个个好手,我从小吃到老。人食之外,也可提取精油,材质可制农具、家具。
古代文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浓郁着国情的树,《太平广记》中槐树的文学意象,继承宋代以前古人对槐的认识。元明之后,洪洞大槐树成为移民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在明清时民俗内涵又添新意,黄梅戏《天仙配》的董永,在槐荫树下与七仙女结为百日夫妻,在傅员外家男耕女织,百日期满,夫妻辞工回家,途中七仙女告知董永实情,并赠罗裙、白扇宝,约定来年二月十五日送子相会后,在槐荫树下重返天庭。虽是神话情节,槐树却成虚幻中的真实。唐宋诗词中,槐却不多见,这让我纳闷。少有的几篇,白居易的“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是意境不错的两句,贾岛的“槐花风处蝉”那句也有点意思。
在我居住的小城,行道树十年上下就要新换一茬,常常是刚长到正好时却被砍伐,让我质疑某些人的用心。欣喜的是,长虹十字路东北角的那棵古槐,几十年来一直站在那儿,身围很粗,枝叶弯绕,陪伴小城时已久矣。下班或远出归来,看见它,就知道到家了,久而久之遂成家之象征。做县政协委员时,我曾数次提案,建议把小城的行道树换成槐,但未被采纳,理由是落叶太多,清洁工忙不过来,我哑然。
人生有沧桑,草木也有。寒露,秋渐深,草渐黄,秋风扫落叶,老槐不起眼的叶子在地面堆积了一层深黄,与深沉的秋色和谐融合。脚尖轻踩,沙沙细响,宛若生命的耳语,像静静流逝的时光。蹲在树根下,握一把槐叶,黄叶应声而碎,碎叶流沙般从指缝落下。
晴好的日子,树冠下的阴影里总是围着下象棋的摊子,两人对弈,围观者众。有时,我会靠在树身,眯眼伸脖,看他们对弈。偶尔,仰头看一眼树叶,仿佛听见了它的心跳。
那夜风轻,月也圆,我却无所事事,于是,捧一杯茶,提一小凳,来到槐树身边赏月。它的月影下已坐了不少人,大约与我一样的心境,让一棵树慰藉属于自己的时光。
树影月色,宁静绽放。
赏月,赏树,皆为品味,皆脱世俗。
柳
古人吟柳之诗,尤喜贺知章的二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细叶为物,剪刀为像,组合一起便为柳树的物象。细长优雅的叶片,被叶脉一分为二,尖端微翘,达·芬奇的肖像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应当就是那样的神韵。
柳分两类:垂柳、旱柳。若再细分,还有大叶柳、白皮柳、圆头柳等。我之所见为垂柳,从我现在的寓所步行五分钟,上了涝河岸会见它,垂着叶,沿河堤站了两行。涝河赏柳,是多少代户县人的闲情逸致。老城曾有西门,出门即景,曰“西郊花柳”,为户县八景之一。户县前几年改名了,叫鄠邑区,河边之柳,依然如故。
我之钟情,在于那个“垂”字。树叶之形,要么上扬,要么平行,这一垂,便有了别致之味,生发出阴柔,娴静若少女,在一缕微风里轻盈浅笑。即便无风,也微颤摇曳。此情此景,白居易也喜欢,咏出“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有花,有柳,这是多么好的春天啊,就连孔夫子也与弟子畅快地“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从华佗老先生将“花”和“柳”组合一起,写进《华佗神医秘传》,这“柳”就变了味,成为人皆不齿的性病用词。在汉语里,寻花问柳,本指赏玩春之景色,不知何时被改为嫖娼,杜甫的《严中丞枉驾见过》就有句:“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明清小说的书页里,“寻花问柳”几近泛滥。
花之容,柳之形,具女人味,令男人生出遐想。
让柳回归它的自然属性吧。清明,日丽,风轻,摇出婆娑。风若轻,雨便柔,柳叶挂雨滴,滴出曼妙。水与柳,为大自然绝妙之配,柳尖轻扫水面,水起丝丝涟漪,若轻诉,若抚慰,若啜泣。在西方,柳树被视为失去之树,从古老的民间歌谣到爵士乐,关于柳树的歌皆为悲伤之调。二战时期,犹太人被歧视、驱逐、屠杀,离家前,他们将竖琴挂于巴比伦水边下垂的柳条,那一刻生命的悲伤系于柳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摇滚民谣潮流中,美国音乐家哈利·尼尔森恳求听众倾听柳树的哀号。莎士比亚的作品,柳树既是背景,又是情调。在《威尼斯商人》中,洛伦佐想象着,当埃涅阿斯扬帆启航的时候,迪多被留在他身后,手里只拿着一根柳枝;《哈姆雷特》里,在格特鲁德描绘的一棵倾斜生长在小河旁柳树下的画面背景下,奥费利娅跌进她水中的坟墓。令人悲恸的是,《奥赛罗》中,苔丝德蒙娜被杀的那天晚上对歌曲《绿柳树》的演绎。《走进莎莉花园》温柔的歌曲中,柳树柔软、摇曳的树枝,在爱情失落之前倾诉甜蜜的心事。
柳之忧郁、悲情,在西方似乎只是文人的象征,而在中国,那就成为大众情结。清明坟头插柳,离别时折柳,沿袭成寄托情感的普遍心理,诗人们没有放过这独特的意象。《诗经·小雅·采薇》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抒发的是伤怀之情,生命流逝。唐诗宋词中以柳寄情的诗作不少,我以为李白的《劳劳亭》独出心裁。全诗四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送行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诗人突发想象:春风之所以成心不让柳条发青,是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世人折柳送行。这是诗人的联想兼奇思,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化物为我的艺术呈现。
柳,不止美目,不止传情,其芽可泡茶。柳芽柳叶可入馔,芽儿洗净,沥水,装盘,淋上酱油、芝麻油,便是一盘鹅黄淡翠的凉菜。还有一种做法,焯掉苦味切细,和上面粉、鸡蛋,油煎,翻烤,做成柳叶饼。淮扬一带,柳芽食法颇多,为春之美味。
柳木硬实,可做箱盛物,柳条可编织用具,柔软舒适。柳编制品始于元末明初,有六百余年历史,从最初的簸箕、箩筐、箱子、凳子、篮子、盘子,发展到衣柜、沙发、床、茶几、柜橱、屏风,其实用价值为人青睐。
《圣经》里八次提到柳,其中三次指向垂丝柳,分别在《创世记》《撒母耳记上》两卷。垂丝柳,中文译为柽柳,长于沙地,高度可达二十英尺(约6.1米),细叶、树皮、树身皆有实用价值,白居易在《有木诗八首》里言之:“纵非梁栋材,犹胜寻常木。”
无论东西方,柳皆为风景之树、意象之树、灵感之树。
椿
椿,古字为橁,汉字里,还有一个字与它通用,此字为杶,从木从屯。《易·序卦》曰“屯者,物之始生也”,万物初生,即有椿。《山海经》称它为櫄,言之:“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櫄,《辞海》有解释:櫄,古同椿。
椿为长寿木,《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言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八千年,才是它的一个季节,这就非自然之木,而是神灵也,故此古人视椿为灵木,有仙气,可静心养神。传说吕洞宾在单州赛仙台仙居时,以椿木为枕,以吸收和汇聚天地灵气。
香椿可食,香味可口,香气通透。民间食椿,汉代已有记载,《本草图经》里有“椿木实,而叶香,可啖”的文字。饥荒之年,香椿可救饥,被徐光启写进《农政全书》。古代传说中一位皇帝战败逃亡,孤身逃入深山老林,七天粒米未进,奄奄一息间一丛香椿树枝落在头部,被椿叶救得一命,东山再起,再夺天下,于是昭告天下,封赠椿木为“百木之王”。
查阅《诗经》,总是喜欢在古老的文字里赏读那些古老的植物,《小雅·我行其野》开篇二句便是:“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樗,古义专指臭椿,其果实却有凤眼子、椿荚、樗荚、樗树凸凸、樗树子、春铃子等多个美妙的名字。凤眼子一名尤其神似,臭椿长椭圆的翅果,正中是一粒圆形鼓突的种子,横看宛若美妙的凤眼,恰如《诗经·卫风·硕人》里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臭椿叶虽不可生吃,但经开水轻焯、冷水浸泡,调盐拌蒜,仍是美味。
椿芽可入药,民间流传有“常食椿巅,百病不沾,万寿无边”的说法。《唐本草》称“主治症疥,风疸”,《本草纲目》说香椿叶温煮水洗疮疥风疽,消风去毒。臭椿根皮有收敛止痢、清热利湿、止泄等功效。香椿散是中医方剂,民间用它治痔疮出血、跌打肿痛、恶心吐酸、不思饮食。
草木也有乡土记忆,安徽太和一带人迁离本土时,随身带些干香椿,如遇水土不服,用它泡茶,饮之可缓解。
椿为佳木,材质通直,结构细致,无节少疤,耐腐蚀,防虫蛀,不渗水,材色微黄深褐,古人喜用它做乐器,《左传》里,记述着孟庄子斩橁做琴的故事。我小时,故乡很多人家植椿,成材后做家具,木香淡雅清香,气味芬芳。若是建屋,或梁或椽,总要用上一根椿木,甚至一个木楔,用以镇邪。
椿有香臭之别,香者曰椿,臭者名樗。一种树以香臭分之,在植物里实属罕见。椿流落到民间,便具备了确切的人性指向,以椿喻父,最早的文字很可能是东汉牟融《送徐浩》的此两句:“知君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满头。”椿为坚硬之木,萱为柔弱之草,椿喻父,萱喻母,椿萱双双白发,双亲健康长寿。古人作联,以“椿年”“椿令”祝贺长寿,“筵前倾菊酿,堂上祝椿令”,“椿树千寻碧,蟠桃几度红”。将椿萱二字嵌入联者,至少是乡下秀才。
在情感的平台上,草木可以视为人类的衣食父母。
童年生活的情景若迷离梦影,但碾儿庄外婆家院子那棵香椿树的记忆,却是那般清晰。母亲带我去外婆家拜年,我不想回去,母亲说等开学了来接你。我不想走的原因外婆一家人和母亲都知道,我喜欢吃香椿。
没上学前,春天我多是住在外婆家,舅舅有许多小人书,被外婆放在炕箱里,我一去,外婆就开箱,抱出一堆。香椿树,贴着窗户成长。春分日暖,椿香穿窗而入,外公让舅舅上树折下枝叶,外婆洗净煮熟,拌进小米饭,撒盐,搅拌,就是香椿捞饭,是我记忆里的美味。及至老矣,方知香椿可成菜肴:凉拌香椿、香椿辣子、香椿煎蛋、香椿炒鸡蛋、香椿芽拌豆腐、香椿芽油泼面、香椿酱、香椿鱼、香椿蚕豆炒春笋,味道各异。曾有人问我香椿的吃法怎样才好吃,我无以对答。中年里读清人顾仲编著的《养小录》,看到此二句,“物无定味,适口者珍”,方才悟出天下没有最好的食物,不同情境下,适之口味便可视之为“珍”,譬如凉拌香椿,夏日食之最宜。
童年的无数个春天,香椿树的枝叶上长久地悬挂着我的目光,那是我成长的插曲,如帕斯卡尔所言:“人的天性,是完全自然的。”
成年后再去外婆家,香椿树一看见我,宛若多年老友,摇晃起枝叶,仿佛欢迎的掌声。渐老,往昔时光喜入心头,皆是美好影像,香椿之香,成为岁月深处的芬芳。
古树是有情怀的,默默守住这千年积淀的内涵。
柿
北方常见柿子树,秦岭终南山下甚多。公元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四月及第,授盩厔(今西安周至县)县尉。盩厔县东临鄠县,白居易常来游走,留下诗作《朝归书寄元八》,诗中有句:“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瓶中鄠县酒,墙上终南山。”描述的是在一户王姓人家的柿树下品味鄠县黄酒的情景。
柿子为落叶乔木,身高可到十几米,树干直立,树冠庞大,叶子椭圆或倒卵形,背面有绒毛,花色黄白,果色橙黄,果形扁圆,一般熟软生吃,也可下锅煮熟,除去涩味,叫漤()柿子。汉语里“漤”是专用词,柿子放在热水或石灰水里泡,除去涩味。这个字生僻,一般人不会写,写成“懒”或“烂”,意思大不一样。
柿为佳果,《酉阳杂俎》谓之“七绝”:果多寿,叶多荫,无鸟巢,少虫囊,霜色可玩,佳食可啖,落叶可书。“霜色可玩”之表述,似杨万里的两句诗:“冻干千颗蜜,尚带一林霜。”诗词里寻柿,望的是金黄,赏的是秋色。“落叶可书”这句更好,有意境之美。笔记小说集《尚书故实》里载有例证,诗人郑虔学书无纸,取慈恩寺的柿叶练习写书,久之,写尽几间房里的柿叶,练出一笔好字,唐玄宗赞其诗书画为“三绝”。
柿入古诗,南北朝时期庾仲容的《咏柿诗》有可能是最早的,“发叶临层槛,翻英糅花药”的含义是,拨开叶子,一层层的柿子挂在枝条上,柿子花可以做药。宋人单人耘《野柿》里的二句不错:“谁知秋在北山裹,野柿如花万颗丹。”杨万里写到了风干成熟的柿子,“冻干千颗蜜,尚带一林霜。”冻干的柿子像蜜一样甜,上面还带着白霜。刘禹锡的五绝《咏红柿子》,诗面无一字“柿”,诗人是惊叹于火晶柿子的莹润有感而发。“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秋风起,落叶飞,唯有高挂枝头的柿子带着落日的光辉,依然火红炙热。柿熟,自然有人来采摘,可是诗人偏偏遇见了一个被人们遗忘的柿子,从早到晚红彤彤地悬挂枝头。这涉及一个问题,柿子到底是被人们采摘,以供品尝,作为一个有用之物好,还是被人们遗忘,以保全天年,作为一个无用之物好?诗人在“有用”“无用”之间选择了后者,有了人生之味。
在中国,柿子品种有二三百,分为南、北二型。南型类喜暖,果小,皮薄,色深,多呈红色;北型类果大,耐寒,皮薄,多呈橙黄色。如此之多的品种,大概谁也见不完,以我所见,秦岭山里山外有火罐、面蛋、牛心、灯笼、磨盘、乌柿、面柿、水柿、金弹子等,其中有些是方言称呼,学名不详。
秦岭的柿子树,其形貌是所有树种里最具风韵的,亭亭玉立、虬枝错杂、盘虬卧龙这些词,在柿子树的身上皆可领略。秦岭地区的气候,尤宜柿子树的生长,结果树龄在百年以上,鸟儿喜欢这种老树,也喜欢吃它的果,在它的高处筑巢。霜降,天渐冷,霜也白,树叶渐落,柿果的红彤与鸟巢的乌黑,在树的身上形成色彩分明的比照,为自然天成的杰作。
碾儿庄站在秦岭北坡上,坡上有杏、石榴、核桃、柿子,也有不结果的杂树,柿子树最多,品种有牛心、火果、面蛋三种。牛心个头大,适合漤熟吃;火果和面蛋小而圆,挂在树上就软了。火果无核,可以一口吞咽;面蛋有核,汁液少,味却甜。
“谁知秋在北山裹,野柿如花万颗丹。”此二句,好像是专为碾儿庄的秋天写的。柿子熟了,村里人聚到山坡的最高处俯视红满坡的柿子,大人牵着孩子,娃娃搀着老人,一路吆喝:“看红柿子啰——”夕阳下,霞光映红柿林,也映红人脸,古人崔护有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在碾儿庄却是“人面柿子相映红”。
此情此景,我笔涩,写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那样的传世之句。
柿子下果,仿佛碾儿庄的盛典,前一天晚上,要“请”场电影,幕帐挂在柿树上,放映前放一串鞭炮,影片是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第二天一早,男女老少拥进柿林,青壮年上树摘果,老人在树下用长竿子勾果,女人娃娃捡果入筐入篮。
柿子不能打完,每棵树的高枝上都要留些喂鸟。
我的意念里,碾儿庄是柿树最好的家乡,怎么长都顺眼。这也是它最好的乡愁,生死不弃不离。人也一样,老人们不愿去远方,看不见柿子树,心不静,即使出去几天,也是匆匆赶回,看一眼坡上的树,心才踏实。
柿子红了,碾儿庄的姑娘就该出嫁了,这是乡俗。出嫁时必备的嫁妆是一篮柿子,牛心在底层,火果和面蛋在上层。篮把上拴着红绸,娘抱篮于怀,伴着女儿走向迎亲车。
碾儿庄深秋的柿子,一树树红灯笼悬挂于我记忆的深处。
责任编辑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