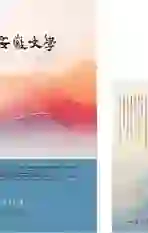母亲的忐忑
2024-08-12徐贵祥
一
我的母亲八岁那年,姥爷给她取了个名字叫胡馥声,把她送到公立小学读书,读到初小毕业,就不让她读了,要把财力集中用在我大舅身上。我母亲后来说起这件事情,心里还很难过,但是她并不埋怨姥爷和姥姥,因为她是长女,家里需要她干活了。
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认字,她用硬纸板剪成“字丁”(我母亲发明的教辅工具),上面写着“天、地、日、月、人、树、花、田”等等。母亲教一个字,我能认识很多字。比如,她先让我认“一”,然后认“十”,依次是“寸”“木”“又”“权”“对”,等我最后认得了“树”,实际上我已经认识了七个字,而且对每个字的含义都有了印象。母亲的教学法,让我受益至今。
母亲参加工作之初,在老家小镇公私合营的商店当营业员,商店原先有我姥爷的股份,后来没有了,我母亲就成了集体企业的职工。当时的商店党支部,认为我母亲工作认真,把她当作进步青年培养。我母亲的性格是“一根筋”,单位有个领导虚报“损耗”,我母亲二话不说就揭发了。后来组织上讨论发展新党员,这个领导找我母亲谈话说,现在我们党支部有两个小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左派小组人员已经很多了,你参加“右派”小组怎么样?我母亲说,那我就参加“右派”小组吧,反正是入党。结果是,我母亲党没入上,不仅稀里糊涂地戴了一顶“右派”倾向的帽子,还被查出了贪污的劣迹,实际上是被栽赃了,定性为错款,开除公职。
这以后,我母亲就开始了人生的艰苦奔波。后来我听我老舅经常讲起一个故事。那正是饥饿年代,我刚刚出生不久,为了糊口,我母亲在姚李镇卫生院谋到一份保健员的临时工作,正在叶集读中学的老舅也住在我家,吃饭的时候,家里有白碗黑碗之分。所谓白碗黑碗,说的并不是碗,而是碗里的内容,我的碗里是白米汤,舅舅的碗里是白米稀饭,而我母亲的碗里是薯叶和杂粮,颜色是黑的。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在老家洪集汽车代办站当代办员,人称胡站长,其实就是一个合同工。为了笼络司机,多载几个乘客,我母亲下班之后走村串户给司机们采购鲜鸡蛋。有些老弱病残乘客当天搭不上汽车,我母亲会把他们带到家里,管吃管住,我们家里一度就像收容站。我记得,因为这件事情,我、姐姐、妹妹,甚至还有我父亲,都和我母亲吵过。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母亲把一个挺着很大肚子的孕妇带回家,把我父亲吓坏了,生怕出事。我母亲说,有什么办法呢,她没有搭上车,离家还有十多里路,我总不能让她摸黑回家吧?
接受这篇约稿,我最初不想写我母亲如何善良,怎样帮助他人。我知道,对于子女而言,自己的母亲都是伟大的、无私的,所以子女眼中的母亲,往往都是不客观的。我把我原先写的初稿发给我的表弟任家杰,他很直率地告诉我,我写的大姨不像他的大姨,他心目中的大姨就是一个善良慈祥而又坚持公正的人。家杰问我:“有一年冬天,姥姥见大姨穿得少,给她缝了一件新棉袄,很快,大姨把这件棉袄给了另外一位更冷的旅客。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我母亲能够做得出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所在的洪集镇没有中学,读中学要到五十里外的叶集,就是我老舅当初就读的那个学校。每到周末晚上,农村的孩子要回到家里背粮食。那时候生活艰苦,学生们营养不良,一天之内徒步来回两趟,非常劳累。可是乘车吧,又没有钱买票。我母亲对此很是同情,经常替他们拦截货车。要知道,我母亲的工资是靠营业额提成的,学生乘坐货车不买票,就意味着我们家的收入会减少。但是我母亲有她的原则,她能设身处地地体会穷孩子读书的不易,宁可减少收入,多费口舌,也愿意帮助他们。
前几年我到河南出差,我的洪集同乡、原河南省军区司令员袁家新回忆他上中学的时候,我母亲帮他们那批穷学生搭车的情景,还充满深情地说:“你妈妈可真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帮我们搭车,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我母亲做的好事可以写一本书,以至于我后来写小说写出一点动静,又调到北京工作,老家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他有什么本事?还不是他娘修行修来的!
老家人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小时候读书不用功,加上正赶上“特殊年代”,月上东山,街头巷尾,哪里有孩子打群架,哪里就有我。一句话说到底,在老家长辈的眼里,小时候的我就是个混世魔王。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孩子,长大后居然能够写出“七侠五义”来,实在不好理解,他们只能把这件事情归功于我母亲的功德。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母亲做的好事都回报到我的头上来了。
二
母亲去世之后,我经常在梦里见到她老人家,每次醒来都是泪流满面,除了思念,更有愧疚。我一直怀疑,我的母亲是被我吓死的。
母亲被我惊吓,从我的童年就开始了。
我父亲和母亲都有一份工作,白天很少在家,我和妹妹是跟着我奶奶长大的。奶奶年纪大了,眼神不济,根本管不住我,所以我经常逃学,基本上是个野孩子。
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年家乡发大水,我家房后西马堰河水陡涨,房根后面出现几平方公里的水面。那几天不用上学了,我高兴得很,就像一只上足劲的发条,白天一会儿也不肯停下来。有一天上午,下着大雨,我把邻居的鱼桶——比小舢板还小的打鱼工具——偷偷地拖到岸上,到对面陈真家的河湾偷梨子。
有人很快报告了母亲。母亲三步并作两步,匆匆赶到岸边,隔岸喊了一遍又一遍:“回来吧孩子,掉到水里就淹死啦!”
母亲的声音是颤抖的。
我那时玩得兴起,哪里理会母亲的呼喊?我在水里充分表演技术,一会儿金鸡独立,随波逐流;一会儿弯腰弓背,展翅如飞。母亲无奈,急中生智,大喊:“孩子,你要的铅笔盒给你买回来了,你要的盒子枪也给你买回来了。”
我没想到我的撒野还会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我站了起来,两腿一蹦一蹦,很快就把鱼桶拱到岸边,一个亮相,跳到岸上。我正要跟母亲讨价还价,不料斜刺里窜上来两个黑脸大汉,分别是我的堂兄和表哥,一左一右,像缚小鸡一样把我擒住,按在地上。我可怜的母亲这才回过神来,举着一根青竹竿,照我的屁股猛抽起来。我疼得哇哇大叫,挣扎着反抗:“打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投降,‘革命者’是不会屈服的!”
那一顿暴打,是我平生挨过的最疼的一次打,母亲手里的竹竿都打裂了。当天晚上,我父亲下班回来,察看我的屁股,已是皮开肉绽。父亲同母亲吵了起来,父亲哭了,母亲也哭了,后来我也哭了。
三
我给母亲带来惊吓,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譬如在学校肇事,把人家的红油纸伞捅破,人家告状告到家里,母亲只得赔礼道歉,赔人家的雨伞——自然,这些都是小事。
依稀还记得一件事情。母亲在车站当“站长”期间,有一次一辆大客车因为故障,停放在车站对面的粮站大院里。我那时候正读小学,放学回来,看见空荡荡的客车,喜出望外,居然拉开车门爬了上去——小时候,当一个汽车司机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好像是司机下车时没有拔钥匙,我七鼓八捣,居然把火点着了,而且车子启动了,照直向水塘驶去,大约走了十多米,我手忙脚乱再也没有办法让车停下来,幸亏车子速度不快,被水塘岸上几棵大柳树挡住。母亲闻讯赶来,吓得说不出话来。
那一次有没有挨打,我记不得了。
我成年后给母亲,也包括父亲,一次比较大的惊吓,是1979年春天。那时候我刚刚参军一个月,部队就到前线作战了。我的父亲是当地的公社书记,人前人后谈笑风生,鼓励安慰那些同样有孩子在前线的家长,可是转过脸去,就是热泪长流。据我父亲的一位同事说,那一年春节,公社干部互相拜年,大家都害怕在我家吃饭,我父亲一端起酒杯,话没出口,泪已涌出,搞得满桌子沉闷。我的母亲表现得反倒比我父亲坚强,我母亲经常用一些诸如好男儿志在四方之类的大道理宽慰我的父亲,可是,我姐姐后来说,她发现,我母亲经常半夜起来烧香磕头,菩萨也拜,道士也求,连灶王爷也不放过,只要是跟神仙沾边的,她都跪在人家面前,一遍一遍地求。
而在过去,我母亲是一个无神论者,那时候她只信仰共产党,她四十岁以前不知道写过多少入党申请书。可是,唯一的儿子在前线,她就再也不敢忽视神仙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好在我后来活着回来了,并且立功提干,当了军官。就在那一年,我母亲的所谓错误被甄别了,入了党,恢复了公职,补发工资一千多元。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娘要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我觉得母亲有点好笑,她把自己等同于那些平反昭雪的大干部了。但是我没有反对,全家人都没有反对,反对也没有用,我母亲的主张通常都是很坚决的。
几年后我才知道母亲的真正用意。母亲说,我一个儿子在外面当兵,经常动枪动炮的,一下子拿这么多钱,我心里慌。我把钱送出去,保佑我儿平安。
我想,可能每一个母亲都是迷信的。
继上次参战之后的第四年,云南边境烽烟又起,我们部队组建侦察大队,指挥组需要一名政工干部。那时候我血气方刚,一听说有这样的任务,立即向领导请缨,要求上战场。因为我有过战争经历,领导同意我随侦察大队赴前线轮战。
出发前我接到父母联名来信,里面措辞相当生涩,既有白话文,也有文言文,拐弯抹角,云遮雾障。后来我还是揣摩出来了,他们的意思是暧昧的,一句话说到底,不能装孬,但是也不能逞匹夫之勇,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子弹不长眼睛。我想,盼望我活着回去,才是这封信的核心意思。
部队很快就开到云南省麻栗坡县,驻扎在一个叫下金厂的地方,那里常年云雾缭绕,汽车硬着头皮开进去,就再也不敢乱动了。交通不便,通信不便,再加上保密要求,一连几十天没有音讯。我的父母又陷入恐惧之中。
我后来听说,当时在我老家,关于我的传说很多。一则消息说,徐贵祥作战勇敢,军用水壶里面装的都是烧酒,喝一口酒打一个冲锋,就像当年的杨国夫。杨国夫是我老家洪集的传奇人物,红军英雄,开国中将,曾经担任过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把我和杨国夫相提并论,让我的父母心情很复杂。还有一个传说说,徐贵祥带领一个排深入敌境,被对方包围在一个山洞里,徐贵祥身负重伤,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对方活捉,投降了。这个传说就不那么让人自豪了。
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父母受着怎样的煎熬,一定是心乱如麻,百口莫辩。我相信,无论是褒义的传说,还是无意的诋毁,传过去的讯息,都不是我父母希望见到的结果。
当时,家乡小镇还有几个当年参军的新兵,所在的部队也到前线去了。后来我听表弟家杰说,我的一个街坊老弟,名叫王启军,他所在的部队比我们先从前线撤下来,很快家里就收到他的来信,信封的背面有三行一样的字——“我回来了”,字一行比一行大,后面分别是三个感叹号。启军的姐姐在街上读信的时候,街坊邻居雀跃欢呼,我的母亲特别为他高兴,可是回到家里,我母亲和父亲相对无言,转过身,各自抹泪,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得到我的消息。
真实的情况是,我那时候写了很多信,只是没办法投递。后来麻栗坡县政府采取有效的拥军行动,把邮递员冯大爹调到我们那个方向,凭借人工传递,这才有几封信陆续寄到家里。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报道,题目是《子弟兵的贴心人》,我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麻栗坡的冯大爹,当年就是他凭借双肩和一双铁脚板,为我们传递家书。
父亲收到我从前线发出的第一封信,欣喜若狂,当晚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把我的舅舅、姨妈、姑妈一干人等都请到家里。客人走了之后,我的父母又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在油灯下仔细地研究我的那封信,从邮戳日期到笔迹,研究得十分仔细,就像法医鉴定证据那样一丝不苟。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封信不能说明我还活着,因为这封信是一个月以前写的。
那天夜晚,我的母亲又自作主张,请了一尊菩萨,在家里烧香磕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人们的集体意识里,宗教和迷信是一回事,都是党政干部忌讳的。而在那天,过去一向反对迷信的我父亲,假装没有看见,待我母亲离去,我的父亲也在菩萨前面,恭恭敬敬地跪下了他的双腿。
好在,没过几天,我的后续家信陆续到达,父亲和母亲这才稍微放心一点。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我负伤的事情——人活着,不等于没伤着,在没有见到我本人之前,他们是不会彻底放心的。
1985年夏天,我所在的侦察大队完成了边境作战任务,顺利归建。父母言辞恳切,迫不及待地催我回家探亲。我到家的当天下午,小院里人声鼎沸,父母迎来送往,不用多说。
客人散尽之后,母亲让我姐姐打来一盆热水,就像小时候一样,母亲督促我洗脚。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说现在是夏天,干吗用热水洗脚啊,况且一会儿还要洗澡。我看着父亲,父亲看着母亲。父亲说,洗洗吧,热水洗脚解乏。没办法,我只好从命。就在我洗脚的时候,母亲突然走到脚盆前,弯下腰,两只手一上一下地捋着我的腿杆。我一下子急了,我说干什么干什么,我都这么大了……再说我跑了这么远的路,脚臭……
母亲还是一言不发,上上下下地捏我的腿肚子,捏我的膝盖,捏得生疼。这时候姐姐在一旁插话说,家乡传说你的腿被打断了,安了一个美国假腿,俺娘俺爸不放心,要看看你腿上的那些血管,是不是美国电线。
我顿时明白过来了,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泪水滚滚而下。
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我本人结婚生子,求学调动,日子渐渐安定下来。前线一年的经历,关于战争的体验,在我的胸膛发酵多年,终于变成文字,后来我渐渐踏上文学小道,成了一个作家。
父母得知我当了作家,既高兴,也担心。用我母亲的话说,我的“文化程度”有限。
1991年,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调到解放军出版社工作,家属随军,我把父母也接到北京小住。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上街,路过天桥的时候,有一个衣衫褴褛模样吓人的残疾叫花子伸手乞讨,我拉着母亲快速逃离,结果,母亲一路上数落不停,说我没有同情心。我只好又返回跑了二百多米,给那个叫花子送去一元钱,母亲才说,这就对了,做好事,有好报。
1996年秋天,我们家里发生重大变故。
继我大姑妈去世之后不久,1994年到1995年,我的小姑妈和她的独子、我父亲最器重的亲外甥又相继去世,父亲终于被击倒了,也于1996年秋天撒手人寰。
我记得那天清晨,当母亲赶到医院,听说父亲已经去世的噩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你爸去世了,我可怎么办啊?我说娘,我对不起你,是我无能,没能把爸爸救活,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的。
父亲去世之后,我把孝心都集中在我母亲的身上,我在老家小镇给母亲买了一套房子,母亲在里面住了十年。
二十一世纪初,我在单位当一个有点职权的小官,母亲的心里又悬上了一块石头。有一次回家探亲,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娘老了,不用花啥钱,有钱多花,没钱少花,有口饭吃就行了。咱们是穷人家的孩子,有了今天不容易,你要珍惜。
我说娘,你怎么想的?你是不是担心我贪污受贿啊?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来的。我有稿费啊!
母亲说,那就好。母亲虽然这样说,其实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她老人家不相信我的稿费够我挥霍。
后来我姐姐悄悄地告诉我说,俺娘的箱底攒了很多钱,连毛票子都聚着,一捆一捆的,你知道是为啥?我说不知道。姐姐说,俺娘说,贵祥手大心大胆子大,手里不能有权。他给我的钱我得留着,万一有个啥事,我得把我的儿子赎回来。
母亲的担心,直到我辞去那个职务为止。
母亲住在新房子里,照样吃剩饭剩菜,极其节俭。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先后给母亲找过几个保姆,但是我前脚刚离开,母亲接着就把保姆辞退了。探亲期间,有一次我看见母亲买了一只很大的鸡,是那种速成的大洋鸡,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我说我千里迢迢回来,你就给我吃这个?难怪姐姐和妹妹都不愿意回家吃饭!母亲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左邻右舍不都是吃这个吗?你小时候能吃到这个就不错了!人啊,不能忘本。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母亲曾经一度挂在嘴边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名人伟人的话,我母亲记得不少。
还有一次,我喝了两杯酒,高谈阔论,讲了一句很不着调的大话,我说如果我爸还活着,我让他每天都喝茅台!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看我的眼神就像看陌生人,忐忑不安。母亲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你就吹!
母亲还有一件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收破烂。还有一次探亲回去,我把母亲堆放在楼梯拐角下面的坛坛罐罐、旧书废纸统统清理掉了,我的理由是那些东西离厨房近,容易引起火灾。母亲当然反对,我在这边扔,她在那边拣,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我胜利了,我发动姐姐妹妹一起扔。那次把母亲气得不轻,老人家差点儿就离家出走了。而那次,我也感到寒心,当母亲的,怎么就不理解儿女呢?为什么老是唱反调?
我本来以为,只要让母亲衣食无忧,儿子的孝心就算尽到了,可是我想错了。孝顺孝顺,我在孝道方面还算做过一些实事,可是在“顺”的层面上,确实愧对父母。我是不理解老人啊!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从二十世纪末到母亲去世,我给她老人家的钱不少了,平均至少每个月一千元,加上她本人每月有近七百元的退休金,足够她花了。可是,我的母亲永远都是个穷人,永远都是省吃俭用。那么,她的钱哪里去了呢?我的舅舅曾经向我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全都是母亲接济别人的。受我的影响,我的妹妹曾经说过一句话:“俺娘就是运输大队长,把俺家的东西都运出去了,给了不相干的人。”——愿母亲在天之灵接受子女的忏悔,我们都知错了——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原先居住的小镇上有几个孤寡老太太得到噩耗,当即凑钱包车到县城为我母亲送行,她们伏在玻璃棺材上号啕大哭。感觉我的母亲,也是她们的亲人!过去的岁月里,我的母亲就是她们的主心骨。
其实,母亲就是再无私,她又能给别人提供多少接济呢,毕竟是杯水车薪,但是她不屈不挠,不改初衷。我现在经常回忆《安徒生童话》,一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心里就痛,就想我的娘。
五
最近几年,我常常反思,检讨我对不起母亲的种种,但是也有一些略感安慰的事情。要说我是个不孝的儿子,那不是事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老舅到北京,告诉我,我母亲幼年的时候,我姥姥就给她扎了两个耳洞,可是快六十岁了,母亲还没有戴过耳环。我当时并不富裕,但我立即拉着老舅直扑王府井,几乎倾其所有给母亲买了一对很大的耳环,还有一个镌刻着“寿”字的戒指。重要的是,我让老舅转告我母亲,买的东西就是预备给她老人家丢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备受打击,精神受过刺激,记忆力不是很好,经常丢三落四。我想,给她买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她万一在洗菜的时候丢到水里,或者忘记在哪里,或者被别人骗走,那岂不是害了她老人家?所以我有言在先,不丢更好,丢了也好,破财消灾。从这件事情上看,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还算粗中有细。
还有一件事情。有一年我休假回去,发现母亲卧室里的床腿很高,母亲上下很不方便。我立即找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阶梯脚踏,放在母亲的床前。我并且以这件事情为教材,把我姐姐和妹妹都叫到家里,现场演示。我至今能够记得,母亲试用这个脚踏的时候,笑得非常开心。也许,我为母亲做过的最有意义,最让母亲感到高兴的、温暖和踏实的事情,可能就是那个阶梯脚踏。可惜,这样的事情我做得并不多,我忽视了母亲的精神需要。
2005年,我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的母亲颇感惊讶。接二连三的赞扬向我母亲涌来,当地政府也往家里送米送油,让老人家惴惴不安。在通电话的时候,母亲疑惑地说,孩子,茅盾文学奖是什么奖?我说是比较重要的奖。母亲说,你也没好好读过书,没有多少文化,你怎么就能拿到那么大的奖呢?我说,可能是沾了电视剧的光,那个剧本不是我写的,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老百姓喜欢,我就获奖了。母亲半是明白半是糊涂地说,哦,那就对了!有了成绩,千万不能忘本。
那段时间,当地市县有一些记者跟踪到我家采访,扛着摄像机、照相机,在院子或者二楼架起来,有点吓人。我母亲没有感受到多少荣耀,反而诚惶诚恐。她经常提醒我,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
有什么讲什么,是我母亲的一句口头禅。
在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母亲会在院子里忧心忡忡地走来走去,远远地看着我,特别是我高谈阔论的时候,母亲会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因为只有母亲和父亲最清楚,我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生怕我说漏嘴了,让人家笑话。
有一天晚上母亲看我屋里灯光亮着,进屋对我说,别那么累了,你一个农村孩子,文化程度不高,有了今天,应该知足了,往后,不要那么写了。
我诧异地看着母亲问,娘,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母亲说,名利都是身外之物,有名有利会更累,你也是奔五十岁的人了,该歇歇了。
在我踌躇满志的时候,别人都认为我应该乘势而上,而最早打击我积极性的就是我的母亲。我记不得在哪里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别人都关注你是否成功了,只有母亲,关心你累不累。现在,我对这句话的体验太深了。
2006年,我在老家县城买了一个庭院,盖了一幢两层小楼,把我母亲从小镇接到县城,由我妹妹一家和她同住。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在那个小区里,隔壁还有我的表舅和我的战友,可以互相照应。哪晓得母亲一看院子很大,惶惶不安:我的妈呀,这要花多少钱?
我说没有花多少钱,农村地皮便宜,再加上贷款,前期投入不大。你老人家就放心住吧。
母亲说,你就吹!
母亲在晚年,经常说我,你就吹!
那一年秋天,从十月一日到十一月一日,我陪母亲在新家住了一个月。几乎每天早晨,我起床后都能看见母亲的身影。她的腿不好,一瘸一拐,拿着火钳,在院子里翻拣,薄膜袋、铁皮、塑料桶、旧报纸……但凡可以回收的废品,她老人家都要拣回来。我感到奇怪,下楼问她干什么,她不回答。我指挥妹妹把冰箱的包装箱扔了,她老人家趁我们不注意,又拣回来,蚂蚁搬家似的将笨重的包装箱从一楼拖到三层阁楼上。妹妹后来告诉我,母亲搜捡这些东西,准备卖给回收站,她要为我还贷款。
一个月后,我要返回北京了。临行前的一天早晨,我陪母亲散步。院子里,我让人沿院墙修了一条周长近百米的防滑小路,刚刚竣工。我指着这条路同母亲开玩笑说,我把这条路命名为胡馥声小道,以后你就在这里散步。母亲高兴地笑了一下,突然皱起眉,不安地问我,修这条路,花了多少钱?我回答说,没有多少钱,地砖是降价的,工钱打了折。母亲说,你就吹。我说我没吹,是真的,霍邱的房价比北京便宜多了。母亲说,我这里还有一张存款,一万三千多块,你要用就拿去。我说,好,先用这个钱支付修路的工钱。母亲二话不说,就到屋里找出一个存折交给我。
我回北京之后,才过了二十多天,妹妹打电话说,母亲病了,让她去医院,她高低不去。我问为什么,妹妹回答说,怕花钱。
我当即给母亲打电话,我说一定要去医院,别说你有医疗保险,就是没有,给你看病的钱,你儿子有的是。
母亲说,你就吹!
好说歹说,母亲终于答应去医院治疗。经诊断,母亲患有轻度脑血栓,需要住院输液。可是母亲一听说挂一次水(输液)需要五百多元,又坚决不干了,当天下午就回家了。其实,医药费并不多,仅仅是前几天需要多花一点钱而已。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解释,母亲就是不信。
此后的两天,简直就像战争,我发动姐姐妹妹、表弟表妹、外甥外甥女、亲戚战友,一起做工作,可是统统无效,母亲坚决不去医院,只同意在家挂水。
到了第四天下午,隔壁表舅妈到家看望母亲,正好我打电话回去,我趁机请表舅妈做工作,还是动员母亲住院治疗。我们三人来回说,讲了半个多小时,我谎称已经同母亲原单位说好,医药费全部由单位负责。母亲说,你就吹!母亲其实并不糊涂,她知道她原先所在的供销社穷得要死,根本拿不出钱来。但是母亲见我着急,还是答应次日去医院。母亲最后对我朗声说,好啦,明天我就去,你放心,你娘死不了。我说那好,我该下班了。
放下电话,我匆匆奔向即将开动的班车,坐在车上,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岂料,车子从平安里启动,还没到新街口,噩耗就传来了,我的母亲溘然长逝。
我无法形容那个下午在班车上、当天夜里在火车上的心情,我只记得,在天快亮的时候、在快要回到家的时候,我终于停止了饮泣,我的心里居然涌过一丝解脱的感觉:好了,终于,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事了,母亲的胃病、关节炎、脑血栓等等,我全都不用牵挂了。回到家里,我扑向一动不动躺着的母亲,哭天抹泪,使劲地抚摸母亲的手掌,可是,那手掌再也暖不过来了。
事后表舅妈对我说,母亲放下电话之后,到卫生间刷牙,好像打算晚上去看一个亲戚。可是就在卫生间里,母亲滑倒了,颅脑出血,抢救无效。
表舅是建筑工程师,事后告诉我,卫生间没有必要建那么大,要是小一点,你母亲也不至于摔倒。
这句话让我悔恨交加——就算母亲不是被我吓死的,也是被我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害死的。今生今世,我是没有办法挽回我的过失了。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