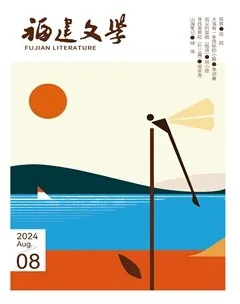寻找张草纫(外三篇)
2024-08-11庞余亮

作者简介:庞余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著有长简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散文集《半个父亲在恋》《小先生》《小虫子》《小糊涂》,童话集《银镭子的秘密》等。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柔刚诗歌年奖、汉语诗歌双年奖、万松浦文学奖、孙犁散文双年奖、扬子江诗学奖等。现居江苏靖江。
1984年,我17岁,我在扬州做着我的文学梦。
这个梦于我,有点好高骛远。没有多少阅读积累,没有多少创作经验,当然,也没有任何文学导师在身边。还是不甘心。于是,就疯狂找书,找能够“辅导”我的书。
学院图书馆里的书实在太陈旧了。我盯住了扬州新华书店。扬州新华书店在扬州最老的一条路上——国庆路。
我去国庆路新华书店总是步行着去。买书的钱都是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然后,和写作一样,我的阅读同样没有“导师”。我还没有学会阅读的辨别,只知道热爱,只要是诗与散文的新书我都要想方设法地买下来。
在扬州国庆路新华书店,我盲目地买了一大堆价格不高同时也良莠不齐的书。幸运的是,在窘迫的、盲目的购书中,我误打误撞选中了一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俄苏名家散文选》。
这本薄薄的即将成为我的文学校音者的散文选,封面相当朴素,上面仅有两株白桦,青春的白桦。封底上仅仅署“0.31元”。
打开这本书,我掉进了炫目的宇宙里了。
这本仅有79页的散文集一共收录8位作家18篇灿烂的散文——当时我们读多了类似杨朔的散文,类似刘白羽的散文——我一下子有点目眩。这是一片多么蔚蓝的天空,蓝得连我怯弱的影子都融掉了。
我过去的关于“起承转合”的散文写作方式一下子被冲垮了。我学习(或者叫模仿)着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雾》,想想多稚嫩——“雾走了,留下了一颗颗水晶心。”——多年以后我只记住了这一句,而再看看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我感觉到了我的矫情,但我跨出了我面前最关键的一步,我从我的身体中不由自主地跨了出去——这蔚蓝的王国里有一朵矢前菊的诱惑。
普里什文和万事万物平起平坐的目光像雨露一样浇灌着我的文字。
我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文学嗓音,这嗓音后来也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小先生》中。
其实还不只普里什文。
还有柯罗连科的《灯光》,屠格涅夫的《鸽子》,契诃夫的《河上》,蒲宁的《“希望号”》,高尔基的《早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黄色的光》。
我一直没有丢弃这本书。我有多次搬书的经历。从扬州到黄邳,又从黄邳到沙沟,在沙沟又经历了几次搬书,再到我现在居住的长江边的小城靖江,而这本薄薄的《俄苏名家散文选》,它是跟着我时间最长的书。
是时候说出这本书的翻译家了:张草纫。我的文学嗓音最值得感谢的人。或者说,他就是我文学嗓音的塑造者。
当代翻译家。上海市人。又名张超人。1949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肄业。后入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文。1951年毕业后留校边编教材边教课。1957年主持《汉俄词典》编辑室业务工作并从事翻译,后任编辑室副主任、副教授。
这是仅可以查到的资料。
没有多少人知道张草纫,好在我陆续买到了张草纫先生翻译的书:《浆果处处》《老人》《俄罗斯抒情诗选》《人类幸福论》。我还是最喜欢薄薄的《俄苏名家散文选》,当年印刷了30000册的好书。
后来,有了孔夫子旧书网,我用了搜查功能。查阅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张草纫先生不仅是出色的俄文翻译家,他还是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大家。
《纳兰词笺注》《黄仲则选集》《二晏词笺注》……
我赶紧下单买回。
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校音者。
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喜欢张草纫的嗓音,为什么不可避免地模仿并学习了张草纫的嗓音,因为张草纫先生已在翻译的同时把优秀的汉语化为乳汁哺育给我了。
多么了不起!17岁的我遇到了这样的大翻译家。
我决定继续寻找张草纫。
有人告诉我,张草纫先生后来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应该是俄文教授。我很想当面向这位无意中给了我文学嗓音的翻译家致敬。我拜托了上海同学。上海同学一番寻找之后,没有任何下文。
1949年大学肄业,估计20岁左右。
20世纪20年代生人。
现在,快100岁了。
年轻的翻译家陈震知道了我寻找张草纫的事。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他为什么从事翻译这个行业的动力。他的动力就是一个被改装的成语:“凿壁运光。”
翻译就是凿壁。把有光的墙壁用翻译之笔凿开来,然后把光运给寻找光源的人们。张草纫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凿壁运光的人。
这世上许多翻译家都是凿壁运光的人。
中国文学的光,外国文学的光。
听了这段话之后,我再捧起《俄苏名家散文选》时,就觉得捧住了一盏明亮的灯。灯光深处,端坐着那个给我校准了文学嗓音的张草纫先生。
露珠闪烁的日子
清晨时分,红彤彤的太阳从远处防洪堤外缓缓升起,从学校里看去,像是系在高大梧桐树上的一枚气球。从学校门口冬青丛中走进学校的孩子首先看到了一个逆光中的校园。
无数颗露珠在泥操场上闪烁。看到校长匆匆走向铜钟时,多少小鞋子就急急地奔跑起来。到处都是露珠浸入灰尘的味道,一股新鲜的泥腥味就溢满了整个校园。
仅过一会儿,树叶上的露珠就被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一一震落,泥腥味似乎越来越淡,而露水的清香就开始荡漾。整个校园像一桶刚提上来的清亮的河水,在晨阳下晃啊晃啊,然后渐渐地静住了,一个夜晚的睡眠就被露水们澄清了。
快下早读课了,我会从教室里踱出来,走到教室外的走廊上,等待铃声敲响的那一瞬间。教室里读书声停住了,第一个黑乎乎的脑袋从教室门里钻出来,迟疑了一会儿,像一条探出河面的小鱼,最后还是蹿出来了,游到了歇了一个夜晚的操场上。
泥腥味又溢了出来。
如果逆着阳光,我可以看到灰尘在阳光下升腾着,起伏着,欢乐着。孩子们可不管这些,在追逐,在跳绳,在踢毽子,我都看到他们面颊和脖颈上细腻的茸毛了,像还没有长成的黄瓜似的,也像初春。
下午放学的那一瞬间,幼兽们会急不可待地从教室里杀将出来——尤其在冬天寒风凛冽的黄昏里——一股只有孩子才有的混杂着纯正泥腥味与汗腥味的气流就包裹了我,我就觉得我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钟声是最不甘寂寞的,它们平时像芝麻一样坐在芝麻壳一样的钟壳里,每40分钟放一次学。
一旦把这钟声之门打开,这些钟声就会毫不犹豫地往田野里奔跑,跑过棉花地,跑过稻田,跑过打谷场,准备偷渡另一条大河时,却被后来赶上来的一群气喘吁吁的钟声抓住了,回去!回去!要上课了!要上课了!
课间十分钟怎么这么短啊!
有时候,钟声就这么跑掉了,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像一些逃学的学生。女孩子最瞧不起逃学生,她们一起甩着羊角辫,一边跳着皮筋,还唱:“逃学鬼子,板凳腿子……”
一张板凳长了四条腿,板凳长了腿肯定是逃得快的,钟声驮着板凳跑到哪里去了呢?
黑板呢?
乡村学校的黑板是用水泥抹在墙上的,然后用黑色的漆刷一下就成了。这比不上木板底的黑板。水泥底的黑板不太好写字,粉笔在上面走有点滑,更是难为了那些黑板擦,不论值日生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有点糊在上面了。女生的责任心很强,下课用手绢沾了水来洗,黑板洗是洗干净了,但黑板上的疤痕都露了出来,像多了皱纹似的。
孩子们说:黑板老了!
每一学期,总务主任都亲自用油漆漆一遍,漆完后的黑板黑是黑,但只写一遍,值日生来擦,又糊起来了,就像漆黑的天空突然起了万里风云似的。黑板真的是老了。
怎么能不老呢?黑板都有30岁了,比我的年龄还大呢。
30岁的黑板该退休了,可它还在坚持着,它总是越过我的后脑勺去迎接孩子们的黑眼睛,它在孩子们的眼里,依旧是那种新鲜的漆黑。
寂静是乡村学校的耳朵,它总是替我们收集白日里最令我们容易忽略的声音,比如一阵拍巴掌的声音以及两个人的合唱:“你拍一,我拍一……”比如一个声音在对什么说:“快快,听话,睡觉。”
我猜了半天,猜不出。
脚步奔跑的声音,先是急促的,然后放慢了,扭成一团,快乐飞溅的声音。还有一个女童音在喊她的伙伴,声音脆而尖。一个少年在领读,一群孩子在跟读。
我原先的声音有了皱纹,而孩子们的声音像春风似的,渐渐地,我声音中的皱纹就没有了。
那些脚踝上银铃铛的声音。破风琴的声音,又像哭又像笑。口哨声,广播体操的声音,眼保健操的声音。校长在大喇叭上说:“下面播送一个通知,下面播送一个通知……”
这肯定是紧急通知了,否则会写在小黑板上的。
到了星期天(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乡村学校就会一下子静了下来。我依旧在清晨醒来。没有读书声,只有鸟叫。
一串一串的。
像一串串露珠。
再回来,这露珠闪烁的日子,被我写成了一本《小先生》。
晚饭花开了
1985年于我,是一个最值得记取的年份。18岁的我,师范毕业,从扬州去了乡下做了小先生。
同时跟着我去乡下的,还有一本好书,汪曾祺的小说集《晚饭花集》。一个人的读书,就像爱上的第一个人,她会奠定我们一生的品位。这本淡绿色封面的《晚饭花集》就是我爱上的第一本书。
说句实话,这本书第一个打动我的,并不是汪曾祺先生的文笔,而是书名:晚饭花。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花。”
这是汪曾祺先生一开头就告诉我的话。我想了一会儿,终于在我的头脑中找到了对应的花朵,这不是我父亲口中的“懒婆娘花”吗?父亲的意思是这花太懒了,像一个懒女人,一直睡到黄昏才起床梳头开花。
同样一朵花,两个不同的称呼,就有了不同的意味。我觉得汪曾祺的“晚饭花”真的太恰当了,“懒婆娘花”实在太粗鄙了。
这是我秘不示人的自我教育。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文学的成长同样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晚饭花集》给了我很多次这样的自我教育,还有自我暗示。
非常庆幸的是,在那所非常偏远的乡村学校,我的行囊里有一本《晚饭花集》。我们的校园因为没有绿化的经费,一位老教师给校园的各个角落遍种了晚饭花。每当放学的时候,晚饭花正好开放,在空旷的校园里,我就捧着《晚饭花集》,对着正在开放的晚饭花读书。
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是知道少年李小龙的。
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也是知道那个王玉英的。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美的时光,我以为,我一生中最美的时候就是18岁的我,在晚饭花前读《晚饭花集》的那个时光。那时候,有忧伤,有寂寞,但那忧伤是纯粹的,寂寞也是纯粹的,热爱同样是纯粹的。
我爱上了汪曾祺的文字。
我悄悄去了趟高邮。
从我的乡村学校去高邮得绕道界首,也就是高邮的那个界首镇。我在界首镇停留一个小时,看了会儿小镇,也看了会儿大运河,大运河的水很浑浊。开始很失望,后来想通了,浑浊才是有历史的大运河啊。
到了高邮已是黄昏。但不是夏天的黄昏,是冬天的黄昏。冬天的高邮给我的印象,和我老家兴化城差不多,但是高邮的面条的确好吃啊。
吃完了面条我去找我的李小龙。那时候的大淖已快成垃圾场了,竺家巷上空全是不同形状的电视天线。
我依旧闻见了晚饭花的芬芳。
我的行囊里还是那本《晚饭花集》。
这本《晚饭花集》跟我走了多少个地方啊,也跟着我做过许多有关晚饭花的梦。
有了微信之后,每个夏天,我都会拍摄晚饭花。天南海北的朋友都会跟着回忆,说起了晚饭花在他们那里的名字。北京的朋友叫它“地雷花”:晚饭花的果实就像小小的地雷。山西的朋友叫它“考试花”:每当它开得最盛的时候,升学考试就要到来了。也有叫“烧汤花”和“洗澡花”的:每当花开的时候大家就需要洗澡了。也有叫“潮来花”,这是住在海边的朋友说的,晚饭花唤来了大海的潮汐。还有直接叫“五点半”的。当然,叫得最多的还是“胭脂花”和“紫茉莉”。
我热切地回应着,同时也在回应我心中的李小龙和王玉英,当然还有那个好玩的老头汪曾祺,与我的文盲老父亲同龄的汪曾祺。
那一年,我又带着《晚饭花集》去湘西看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故居里的人很多,像凤凰的姜糖一样,多而诡秘。我在故居买了一本《从文自传》,准备去沈从文的墓,可熟悉吊脚楼的导游并不清楚先生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出门打听了一位当地老者,她给我们指点了方向:城东南岸。
我们立即过桥,穿越长长的小巷,出城,找到了先生的墓地,这是12岁就离开家乡的凤凰游子的终点。在小小的半山坡上。墓碑上有16个字: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令我惊奇的是,墓碑边就是一丛灿烂的晚饭花,不是我常见的红色、黄色或者紫红色,而是白色晚饭花。
我在白色晚饭花前停了很久。
我要记住这芳香寂寞的白色的晚饭花。老师的晚饭花,先生的晚饭花,学生的晚饭花。
那个有月亮的晚上,我又来到了高邮,来到了竺家巷,敲开了汪曾祺先生家的门。汪曾祺先生的妹妹和妹夫在。他们请我们都在签名簿上写行字,我想了想,写了五个字:
“晚饭花开了。”
渐 渐 靠 近
那个梦。还是那个梦。
渐渐靠近你了。
这是我在暮色里的抚河上,在心里对抚州说的话。
刚刚在心中默念完这句话,抚河大桥上的路灯就亮了。
有8个字也跟着亮了。
“汤翁故里”。
“才子之乡”。
在路灯的照耀下,我再次眺望初见到的抚河,灌溉出那么多才子的抚河,波澜不惊。
波澜不惊,也叫深水静流。
谢灵运、王安石、曾巩、晏殊、晏几道、汤显祖……灌溉的力量,痛饮的恩情,清冽而明亮的抚河有这个自信。
我的梦,开始在扬州,梦圆在抚州。
所以,“渐渐”这个词,有时间的长度,也有空间的宽度。1983年,一个16岁的师范生,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来扬州,就穿着一双老布鞋在扬州城闲逛。
那时扬州的道路和古巷实在是太老了。
老文昌阁、老四望亭、老石塔寺。
当然,还有老的树。
道路两边不是梧桐,而是高大的榆树。
最高大的榆树都长在汶河路上。
在榆树和老房子中间,当然有老银杏树、老苦楝树、老玉兰树,当然,肯定有老槐树。
怎么可能没有老槐树呢?
在驼岭巷里闲逛的我,就这样和那棵著名的老槐树迎头相遇了。
满枝头的槐豆叮当叮当响。
为什么要说到槐豆?
为什么槐豆会在老扬州的古巷里叮当叮当响?
相遇就是击中。
首先,我有一个与老槐树有关的成语“南柯一梦”。
巷子里肯定养过骆驼。这个不稀奇。1983年的扬州,骆驼们已被关在瘦西湖动物园里了。但动物园的外面,全是驴车。每当我想到1983年的扬州,耳朵里还会响起那悠长的驴叫。
驼岭巷里竟然有成语。
而且是我们高中语文老师常常用来讽刺喜欢上课睡懒觉的学生的成语。
“你是不是做了个南柯一梦?”
驼岭巷10号。昔日的古槐道院不见了,但是“南柯”还在,那是一株国家级保护的千年古槐啊。
南柯一梦的主角,那个成全了淮南节度使门下小官淳于棼的好唐槐啊。
也许,那年成全的力量耗尽了全部的能量。1300岁的唐槐只剩下半圈树皮了,但它的梦还在继续,槐树荫落在我的头上,槐花已谢,满枝头全是饱满的槐豆。
槐豆叮当作响。
淳于棼梦醒之后,那酒依旧温热。我俯视地上,有蚂蚁出没。就在那个下午,我就这样无师自通地理解了另外的时间和空间。
似蚁人中不可寻,
观音讲下遇知音。
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阴。
——《南柯记》
我的阅读就这样开始了。先是找到了唐朝李公佐所著的《南柯太守传》。读完之后,我又去了离我的师范不远的驼岭巷。那已是冬天。槐叶落尽,蚂蚁无踪影,清冷的巷子里,我吸着两根清水鼻涕,越想越兴奋。
在时间之外有时间。在空间之外有空间。
比如,在冬天的扬州之外有冬天的大槐安国。
然后就是汤显祖的《南柯记》了。读完了《南柯记》,又去读《邯郸记》,再后来是《牡丹亭》和《紫钗记》。很多人喜欢《牡丹亭》,但可能心中有了那一棵唐槐,我更加偏爱《南柯记》。我一点点读,一点点悟。从一棵槐树开始的文学启蒙是那样的神奇。
槐花开的时候,我是捧着书去的。
淡黄色的槐花落在我的头上。
时空叠加。
时空穿越。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淳于棼:我们的名字中间的音是相同的。
骥子书有隔,
鸾俦镜乍辉。
绿槐无限好,
能借一枝栖。
——《南柯记》
再回来就去乡下教书了。像梦一样的15年。在那个15年的蚂蚁洞穴里,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成长。我写诗,写童话。寂寞的时光里,最爱做的事就是和邮递员去河边等待每天抵达的邮包,因为太渴望远方来的好消息了。邮递员后来直接把剪开邮包锡封的事交给我了。不大的邮包里有信件、杂志和报纸。报纸是两天前的,到达乡村的时候,还算是新闻。这也是另外的时间和空间。很多时候,是没有消息传递到我的“小槐安国”的。世界把我遗忘了。
好在还有文学慰藉着我。
书本上那些寂寞的文字多么像蚂蚁啊。我的蚂蚁王,我的蚂蚁兵,在反复搬运着我的时空。友人送了一套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厚厚的8大本。说是非常难读,但我觉得好读。里面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和解构。梦与梦,梦之梦,梦里梦,梦外梦。
现代派=天才汤显祖。
多么神奇的古今中外的时空链接啊。
临川四梦。
我记住了一个词:临川。
上天如圆盖,
下地似棋局。
淳于梦中人,
安知荣与辱。
——《南柯记》
现在,我也进入临川了。这个“川”,就是抚河。越过抚河大桥,我就渐渐靠近了40年前的那个梦。玉茗堂里,那天才般的汤显祖必定芬芳绽放,他的文学经历,他的人生准备,他的人生境界,他灵慧无比的悟性……我还看到了泰州——他是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学生。
不乱财 手香
不淫色 体香
不诳语 口香
不嫉害 心香
多么好啊,纯正的二度桂花的香气。渐渐靠近了那个梦。我不知道我是在做梦还是在醒来。我几乎深陷在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馆名的汤显祖纪念馆里了。
临川四梦,又不止四梦。
几乎概括了中国人所有的梦。
有限的梦,无限的梦。
《紫钗记》初版和完成版之旅里的妥协和包容。
《牡丹亭》里后花园的青春和爱里的明亮和绝望。
《邯郸记》里那碗永远无法醒来的黄粱饭。
当然,还有亲爱的《南柯记》里的槐树,从山西大槐树下开始流浪,一直流浪。
我们共同背负着扬州驼岭巷里的槐花树。
那仅剩了一张树皮但依旧枝繁叶茂的唐槐,现在已经是扬州002号古树了。001号,是一棵相隔不远的古银杏。著名的“饭后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棵银杏树下。
人间君臣眷属,
蝼蚁何殊。
一切苦乐兴衰,
南柯无二。
——《南柯记》
我低头寻找纪念馆里的那些蚂蚁们。还有那些我们,那些书本上的蚂蚁们,那些我们藏在电脑里的蚂蚁们。他们爬行,他们搬运,他们的名利,他们的喜悦,他们的崩溃,还有我们共同的欢乐和悲哀。
文学多么好,抚州多么好,有汤显祖,还有纪念馆里和汤显祖比肩的莎士比亚,还有带来了出生证明的塞万提斯。
谢谢文学和抚州,还有深水静流的抚河,请继续关爱我。
责任编辑 韦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