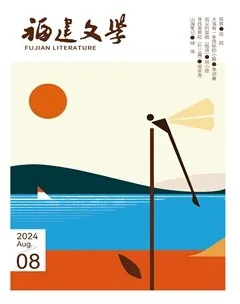炊爨
2024-08-11张金湘
柴火灶的构件有:灶炉,灶门,灶壁上掏的火柴屉,灶膛,灶腔,灶台,前鼎,后鼎,鼎盖,鼎盖垫,灶公,竹鼎扫,油光,柴角,竹火钳,硬木火耙,烟囱。真是麻雀小,五脏全。
烟囱的通畅关系到顺利起火、火烧旺、会不会倒流烟的问题。柴火不干,或者风向不对,屋外的风穿囱而进,烟火倒流,熏得你头昏眼花、泪流满面不说,还会弄得整个灶衙底乌烟瘴气。煮一顿饭,气都气饱了。它是呼吸器官,呼吸顺畅,身体健康,家和万事兴。“一溜烟”这个词语,原义应该是形容烟囱的通畅,后来赋予另外的释义。假如烟囱堵住了,张公慌不择路,钻进灶腔,能否“一溜烟”从烟囱里出来而成为黑脸神呢?我们一日三餐养着“一溜烟”,“一溜烟”喂着我们的一日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一溜烟”中一溜烟长大了。鼎盖是杉木的,不易变形,揭盖轻便,小孩子都能操作,向阳山坡上又枯又老的杉木是材料的首选。母亲挑来一种沙灰土,掺进松针,舂白粿似的鼓捣,做灶膛。果然耐热,不善导热,不变形,不脱层,顺滑,扒火灰容易,母亲的智慧可见一斑。灶台的长宽高与前后鼎吻合,讲究比例,美观大方。这样一个烟火圣地,每户人家都要精心打造。做前要堪舆,看时动工,牙节要上香,平时要维护,分家时办盘贺灶——四个盘,开科的猪脚,肝尾肺,八宝饭,一担水桶——娘家人必定要花去一笔不小的开支。贴“灶里出黄金,鼎中生白玉”对联。每个隆重而庄严的细节里都充满祝愿和期盼。
灶膛里塞进杉刺或蕨草,盖上薄、细、小的柴火,划亮火柴,点上油灯,点燃竹火把或松油块,探进灶膛……起火的流程像火炬传递。
火苗养大,添柴,火筒探进灶膛里,轻轻吹。火大了、火炉热了才能大点力鼓吹,当然还是要小心行事,不可吹灭了。一个熟练的“厨公”是不愿意第二次去起火的,自己费事不说,还惹人笑话。添上大柴,关紧灶门,火势形成了合力,火烟拉着火苗呼呼地往烟囱里奔跑。火苗伸着长长短短的舌头,舔得大锅饭激动翻滚,有时会发出一阵灿烂的笑声。嚯嚯嚯笑得真真的,母亲就说,有客呢。然后说,会是谁呢?便若有所思地猜测。嘻嘻哈哈像个瓜女子在傻笑,母亲会说,笑得这么花,不会有客。母亲的猜测,有时不准,有时准。笑得真没客,笑得花来客了;有笑无客,没笑居然有客。猜得准,是因一些确定的走亲,母亲心中有数。猜得不准,也要猜。人客来或是不来,母亲都在时刻准备着,以免措手不及。无论来谁,母亲都表现出一份惊喜和忧心。一个家庭有人来访肯定不是坏事,说明人家心里有你。你家里,有人敢来,你家拎得起,过得去。但是来人了,要不要煮点心,煮什么点心,客人会不会真吃点心,围绕点心的话要怎么圆,是伤脑筋的事。站得了灶台,立得住桌前,是每个当家女人的追求目标。
煮。蒸。炊。煎。炸。感觉柴火灶没闲过,每天都在吞柴吐烟。前鼎煮饭,后鼎闷番薯芋头地瓜干。前鼎煮,后鼎热水洗刷。前后鼎就是两个大窟窿,多少东西扔进去,永远填不满。而我们的肚子就是个无底洞,似乎通海。人人都是“做得不会,吃捧大盆”。母亲看着我一根大衣针就可穿透的肚皮,说我“杀牛也吃不饱”。我们偶尔趁独自在家的时候,炒一把黄豆、煎一勺粉心煎偷吃,偷吃剩饭,以期“牛无夜草不肥”。找到黑糖的藏身之处,撮一撮配口水咽下,那是透到肺里去的甜。母亲对我们的偷吃不是不知道,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饥不择食。煮啥吃啥,没有人抱怨过啥,没有人单独开小灶,每个人吃啥都要努力填饱肚子。犁田、耙田等大累活前,母亲要捞干饭给父亲吃,连续几天的重活后,母亲给父亲吃个鸡蛋淬小酒以助恢复精气神。父亲的胃病发作了,母亲会买个猪肚给他以形补形。父亲的“吃独食”是公开的,家里没人眼红嘴馋口水掉。母亲是砖瓦,父亲是梁柱,他们是我们家的高楼大厦,他们的勇健是一厝人顶天立地的保证。当然,哪个感冒发烧了,母亲煮碗米粉汤给他当药吃,哪个咳嗽了,母亲给他烧个白豆、熟姜、红糖汤吃,也不是偷偷摸摸做的。母亲头疼发作了,几天没吃饭,我掏出卖松油块、柴火悄悄攒下的“私房钱”给她买瓶“枇杷胶”吃,也是公开的行为。家里有点好吃的,总要孔融让梨推让一番,总要等到母亲发话说,不要夹来夹去了,下象棋似的,某某吃了吧,某某才不再推却吃了。每顿饭,吃多吃少没有限额,由着大家的肚皮。一大缸稀饭,够够。也有饭做得欠缺一点的,母亲会大量地说,吃吃吃,不够了再煮米粉汤。大家听了,心照不宣地放下饭碗,母亲见稀饭还有剩余,就说米粉就不用再煮了,大家心照不宣地附议。口粮丰富之后,偶尔遇到吃得缸底朝天的时候,母亲坚持要再煮米粉汤。大家都说饱了,不要再煮,母亲坚持煮好米粉汤,每人一小碗,没人说吃不下,都是几口扒完。多少年来,母亲就相信一个事实,一定要把饭做得一厝人全吃完了留有缸底才算饱。三十暝的隔年饭是每个大年夜必须要的,一生节俭的母亲,不心疼在这一个细节上的浪费,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那年。
炊烟从烟囱里遁逃,厝瓦顶升起云朵,老屋弥漫着“遥看近却无”的烟火气息。不一会儿,香气充盈灶房。我凳子垫脚,小饭碗举过头顶,高昂小脑袋,对母亲急切热盼地说,给我一“鼻屎珠”“饭饭”吧。母亲一边把饭舀到饭缸里,一边顺手给我舀了一碗底,然后继续一瓢一瓢舀饭。她没有直接把饭端给我,是因为她要放着凉一凉。但我哪里等得——那时我并不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更吃不得热稀粥。我急着要端起灶台上的饭碗,但是我的身高无法支持我的想法——“矮伍连高,跟灶平齐”,便用手去拉碗沿。碗一倾,热气腾腾的稀饭倒在灶台上,倒进我的脖子里。脖子喉结处揭开一层皮,剥地瓜皮一样——想想就心疼后怕。幸好是那里,伤疤也被下巴巧妙地遮掩住。要是脸、头皮或是眼睛呢?至于碗有没有摔破,更不知道了,我不可能“十二岁记二十四代”。那时候,家里人的外伤是被人威胁说“把你家的水缸、鼎灶都捅了”,内伤便是打破碗。碗若是摔破了,别说受伤,我还有可能吃“竹枝炒肉”。
谜底在母亲人生最后那些时光里揭开,我在她跟前撒欢,给她看伤疤,她想起来时揭开的。母亲看着我脖子上的褶皱,一句话就说完故事,淡淡一笑,却瞬间愧痛,眼角溢出难以掩饰的含辛茹苦。这么一个“多子女,困难户”,上有老,下有小,口粮有限,自留地不多。父亲疲于工作家庭两地奔波,母亲顽强撑起一片天。供“大小人”吃穿,供“大小人”上学,要起大厝每个兄弟分一柱,要做眠床三合桌讨媳妇。一分钱掰成两片花,一粒米都要塞进牙缝。事无巨细,样样操碎心。母亲常常自豪自己做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孩子的上学还算争气,肚子不怎么饿着,偶尔还能吃上一些杂粮打牙祭。只想着养活,不承想还能养好,母亲的快乐愈发表现在勤俭持家上。她是家里高速运转的动力头,丝毫不敢停歇和出现故障。每天眼睛一睁,就爬上飞快的时光之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厝前厝后,远山近山,是她挥汗如雨的战场。但她总感叹自己没有三头六臂,不能做得更好。而今,母亲的生命在倒计时,时间一分一秒逝去,将被一起带走的还有她的许多念想。我忽然发现,几十年的光阴在不知不觉中就“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么长的一截时光,原来只是一瞬之间。这一瞬间,是我与她46年共同光阴的缩影。这一瞬间,是父亲母亲带领一厝人,在有限的田地上精耕细作,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苦各自尝,笑与大家分享,风雨同舟。
母亲常常嘲笑我吃得猴急。表现在两点上:一是吃得急。什么东西,哪怕刚从油锅里捞起,就可以塞进嘴里。二是吃得快。母亲说我,一海碗饭,滚烫烫的就有本事一下子倒进肚子里。她用“塞”“倒”这两个猛字的同时,还用上带贬义的“有本事”。对于她的宝贝儿子,她完全可以换上一些调侃的字眼,或是修辞得委婉一些,减少我的难为情程度。可惜她大字不识一个,根本不知道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故事。她进一步具体地说,我一端起海碗,嘴巴就搁在碗沿,一口气扒完,不洒汤漏水——想到吃相就自觉好笑,我把碗联想成海,筷子是龙舟比赛的双桨,食物“飞流直下三千尺”滑落肚子里。还说我放学到家,一手挂书包,一手拿碗筷。不管冷天热天,必定都要吃得汗流夹背,整个人从水里捞起一般。这些笑谈说得我一点儿都没法反对,我确定是那样的,我吃的时候,经常嘴唇被烫去一层皮。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们谁也没有笑话我,因为母亲说我也是说大家,他们心知肚明,不会笨得五十步去笑一百步。没办法,一个要长大的孩子,在饥饿面前是无法优雅的。现在,我已体会到母亲所说的“年轻时爱吃,啥都没有;现在啥都有,已吃不下”的年代和年纪。但习惯难改,我就喜欢大碗吃饭。我很想当这个画面里的主角:捧着一大海碗汤面,半蹲在厝埕沿,大汗淋漓地吃着,一条小狗在不远不近处盯着你看——多惬意啊!我觉得这才是“吃”。老婆告诫我不要那样子,不良饮食习惯会得病的,再说又没人跟你抢。植物生长得那么缓慢,咱得慢慢享用,才对得起它们。你“见鼎熟”“生吃番”,又吃得狼吞虎咽,是暴殄天物。我讪笑说,不然我不会吃啊,再说,吃在先,死在后,不烫不快吃得不香不畅快啊。老婆无语,吃她的“财主妈”饭去——我们把吃得又细又慢的人称为“财主公,财主妈”,碗在手,慢慢摆,慢慢进,爱吃不吃的样子。一次在单位,同事给了我一海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汤吃,我几口就搞定。把碗还回他时,他的夫人说她筷子都还没动呢,你就吃完了?我的快速让她大为惊讶——我让她长见识了。同事倒是淡定,叹一口气说,穷人家的孩子呀!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没有素食主义的素食者。粗茶淡饭,是生活常态。每日盘中餐,大抵无油无鲜。桌上没有一碟菜,母亲说,随便配一碟。于是我们吃稀饭配稀饭,有时悄悄加点盐,有时偷偷加勺糖,便是囫囵一餐。生活好了后,还是简单吃。偶尔加葱,肉饭配肉片汤,蛋饭配蛋汤,干海蛎饭配生海蛎汤,无非多两三根葱,施几滴油,没啥新花样。老迈的母亲上街购物,往往空手而归。问她为何,她说东西那么多,不知道要买啥,也没想过要吃其他的什么东西。她常常抱怨父亲上街只会买块豆腐,而她自己兴冲冲去了半天,也只带回一包盐。父亲母亲的购物现象没有口传身授,我夫妇二人已得到真传。我进超市会迷路,要买的东西如果不记在纸条或手机上,到街上就茫然。面对小摊小贩的叫卖不知所措,他们问要不要买,只会说好,于是他们把东西称好了纷纷挂在我的摩托车的前架上。我提一大堆东西到家的时候,老婆在分类时白眼随即飘过来,说我要买的没买,乱七八糟的买一堆。她自己呢,“嘴红红,说别人”,上街只会买一块肉或者一条鱼,添油加醋煮好,劝我趁鲜一顿吃了。一顿吃了,又没下顿。
总而言之,如今,很少对吃的怀有期盼了,不像小时候。
小时候,我们天天盼牙节,牙节到,口福也就到,母亲就会备有好吃的东西等着我们。所谓好吃的东西,无非是借助磨、臼等工具,把米加工而成的另一种东西,添加一些佐料,加油盐糖葱蒜姜等做成。年暝红团白粿,头福“番薯起”,端午包粽子,七月半爆豆早米粿,米粉栽秋,冬节搓汤圆。遇有家事,炊甜粿,打松糕。偶尔煮菜饭、锅边糊,炝粉心。这些,便是乡下美食的全部,是我们家的千滋百味。就是乡村办酒,七谷华八谷华,除了米加工成的各种食品外,吃来吃去就是吃一头猪。变着花样,从猪头吃到猪尾,从猪皮吃到猪内脏,吃完肉啃骨头。曾听到有人自嘲说大吃是因为嘴大,说嘴大好,嘴大食四方,好命。害得小时的我常常用家里唯一的一个小镜子看着自己的嘴巴发呆。
那时候我们还老觉得冬天特别漫长,老觉得肚子饿。冬天的漫长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而削短,饥饿感一直伴随我到仙游师范毕业。我时常想,要是石头能当饭吃就好了,有没有营养放一边,至少硬实、扛饿。我不喜欢吃面包馒头类发酵食品的原因是觉得它们虚假,不硬实,又容易吃得撑。工作后,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我的胃肠顶住了两大考验。一是没被啤酒浇灌成啤酒肚;二是整日呷茶,没被茶水清洗。而它们似乎习惯了加工五谷杂粮,无法消受美味佳肴。小时的食欲得不到满足,没觉得痛苦,现在的食欲得到了满足,也没觉得幸福。都说我是茶喝多的原因,肠胃受到破坏,影响功能。茶我是喝多了,什么茶都喝,一天会喝几泡。哪天不喝喝茶,就觉得哪天的生活有严重不满。但我觉得未必是喝茶的原因。
我知道我的肠不是在故意作梗。它习惯了对粗茶淡饭的加工。为了给肠道减轻负担,面对珍馐,我只敢浅尝辄止,没多大欲望。去吃酒宴,回家必定要再进一碗稀饭才觉得肚头肚角踏实。母亲瞧见了会质疑说,吃大块肉去,没吃饱?我回她话说,你自己不也是!
母亲无言以对。大家都是如此,不愿再为一口吃的而费劲。
可是当年,为了一餐饭,人人都是劳力,人人都是砍柴仔,人人都是厨工。
每一天都是忙碌的。为了不使家里穷得“大鼎扛起来只有一把火灰”,在有限的田地里,母亲带领一厝人刀耕火种,精耕细作,恨不得把土地捏出油来。播种,除草,施肥,杀虫,收成,归仓,不放过一丁点的细节,以期把收获最大化。然后一天、一天,一点儿、一点儿抠回家,一餐一餐往大鼎里填。
忙时砍柴是顺手牵羊。一边放牛一边砍柴。田间山间劳动回家,肩头没担子就不能空着,肯定要撸些柴火带回家里;就是有担子,路边见到了中意的柴火,就要连挟带拖捎带回去。农闲时的专门砍柴是件很快乐的事。没有约定,小伙伴们在村里的某个地方集结出发。和谁去,去哪里,砍多少,什么质量,都没有要求。在砍柴的时候,我们是一只只快乐自由的小鸟,林深任我钻,路远任我飞。渴了饮山泉水,饥了饮山泉水,饥渴一路,一路牛饮。一家人都是柴火的供应者,厝前厝后堆满了柴火。柴火烧不尽,有空就砍回。没有谁下达命令,所有往家里运送柴火的行动都是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行为,因为我们的心底都存着一个念想——柴火的尽头是香喷喷的食物。柴火堆是每户人家除了谷堆、地瓜窖、咸菜筒、草垛外的一大财富。母亲常常会在被人家评论家里的柴火又多又好看、五百年都烧不完时笑盈盈的。
母亲是家里的主厨。早饭是她做的,美食是她做的,点心是她做的。物资那么匮乏,母亲总能沿着季节的方向向贫瘠的自留地“讨”到瓜、菜、杂粮,然后精心加工成美食塞进我们的嘴腔。她还善于做豆腐,善于酿酒,红酒水酒酒糟。无论什么时候来人客,她都能变出一碗又多又好看的点心。如果说母亲是一位魔术师,那么灶衙底便是她的魔法小屋,在牙节或客人来临的时候就弥漫着一股香气。这股香气叫作母亲的味道,在全家人的血液中流淌,生生不息。午晚饭谁做不固定。一家人都在家,一起做,看火的看火,煮菜的煮菜,谁都有能力去露一手。当然,大部分还是母亲在做,孩子们坐享其成。农忙时节,那要根据劳动强度、出工人数及饭菜的成色来定厨工。一般情况下,只要够得灶齐,就能胜任。饭煮得够不够吃,不在米的多少,在于加一瓢水。菜够不够,在于加一勺盐。煮得熟不熟,在于加一灶火。正因为平常烧火做饭的技术性和工作强度不高,所以我们骂人“当厨使”,表示被骂之人笨,只会做饭,别的都不会。因为人人都会做饭,所以把饭做出差错,就显得特别差劲,就会遭人贬“当厨都难使”。
事实上,做饭没有那么容易。粗平直谁都会,高精尖不是谁都会的。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火烧大了,煮开水都会烧鼎底;火烧小了,饭没煮熟,那你又会被人骂作“欠一灶火”(欠灶);火烧得靠前,前鼎熟了,后鼎的食物还是半生熟,那你这人有被定性为“半生熟”的危险了。乡村里的厨公,地位很高,他的口碑是办酒好坏的关键。谁家办酒,得隆重相请,新人答拜,第一个要拜厨公。相对于煮饭,大家更热衷于烧火。看吧,天寒地冻的冬天,围在灶炉前,一手拿着火筒,一手拿着杨排风的烧火棍,一边烧火,一边烤火。有时烤地瓜,年节时烤白粿,烤得香喷喷的,吃得香喷喷的。寒冷把我们塞进灶膛里,温暖已比食物抢先一步进入我们的身体。
只有经常给前后鼎“丢盔弃甲”,才能让它们“轻装”烧饭。每天清晨,乡间都悠扬起扒鼎的晨钟。抬起大鼎小鼎,倒趴在大埕的黄土地面上,紧握一把锄头,紧贴鼎身,由下往上,转着圈刮锅灰。刮好抬起大小鼎,地面黑了一圈,像过度熬夜的地眼。锅底灰可是好东西,父亲用它来磨墨,母亲用它当消炎止血药和肥料,我们蘸着它朝小伙伴的嘴边画去,画上八字须。而掏烟囱是一项高空作业。须晴日,爬楼梯,钻楼井,到楼顶,开天窗,站在厝瓦顶,收拾瓦片,通达烟囱处。两片长长的竹片探进烟囱,竹片盘旋转圈搅着,黑烟纷纷扬到后鼎窝。
火,是人类的朋友,又是人类的敌人。做家事,年暝时节,偏偏用火高峰期撞上天干物燥,一不小心,天火落进烟囱里——走水了。一声声某某家火烧厝的急促叫喊声,就是集结号。闻讯而来的乡亲们立即投入一场无人指挥的战斗。挑水的,泼水的;挑粪池水的,泼粪池水的。一时咋咋呼呼,手忙脚乱。火很快扑灭。主家望着臭满满的房子,感激涕零。
现在的老家,年暝才能见到闹热。然而越暖和的地方年越短。今天初四,明天初五,元宵改到初六举行。初六之后就把日子过回正轨。该做买卖的做买卖,挣钱没有一个嫌早的,人们“一溜烟”走了。“烟囱嫑熏”曾是一句恶毒话,意思是没有了烧火做饭的人,瓦房被钢混建筑替代后,却变成过上好日子的代名词,说明住上新厝,用上新能源,有能力外出挣钱,有能力进城买套房。乡村里的炊烟袅袅娜娜了几千年,如今已变淡变少。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可是,“爨”这个字,要怎么写好它呢?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