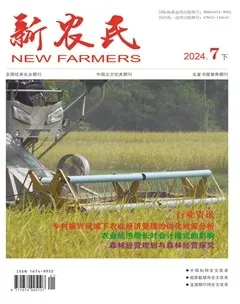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践样态、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2024-08-08董鑫王梓桢
摘要: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乡村教育振兴,而乡村教育的基础在义务教育阶段。现阶段,我国乡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呈现以保障效率公平为前提、以优质发展为理念、以共享为根本遵循的实践样态。乡村义务教育发展存在着生源数量和质量面临挑战、人才供给制度存在短板和乡村特色教育起步较晚等问题,制约乡村教育的全面发展与提升。本文通过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义务教育的行动对策,提出全面提升乡村义务教育供给效能、完善乡村教师成长体系、打造乡村教育振兴共同体等改进策略,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可行的路径与思路。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通过义务教育事业,特别是乡村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对国家建设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发展教育为偏远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为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提供基础和条件。2023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下文称《意见》)提出建立优质均衡义务教育服务体系的要求,以更为有效地适应教育强国建设的复杂需求。文件明确强调,全面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城乡整体协同发展,确保各群体在教育领域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1 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样态
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保障效率公平为前提。《意见》提出“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乡村教育实践也在不断演进涌现出多种办学模式,如城乡学校捆绑发展、骨干教师交流轮岗、学校委托管理、集团化办学等,促进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这些模式为城乡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提供有益借鉴,保证乡村学校以“量小质优”为基本格局。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乡村学校由数量扩张向内涵充实转变,质量水平大幅跃升。
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优质发展为理念。乡村学生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飞跃体现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乡村教育振兴进程。乡村教育振兴对应城乡教育一体化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乡村现代化教育以人为中心作为基本立场,将乡村教育的育人性与乡村文化发展融为一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提升乡村人口质量和培养高质量的乡村人才,进而将乡村人口资源转化为促进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1];差异性体现在乡村教育振兴在乡土资源优势上的不同,因之实现城乡教育的高位均衡。在推动教育的高位均衡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学校系统以及社会各方需共同努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如社会资源、农耕文化资源等,重构高质量乡村教育体系,从外在帮扶转向内生发展,促进城乡教育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努力实现乡村教育的均衡发展。
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共享为根本遵循。首先,借助数字智能共享使优质资源全民享有。一方面,缓解乡村学校信息资源不足,打破城乡信息壁垒;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改造,建设数字智慧校园。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教育吸收并再创造技术的价值,形成具有乡土特色的教育体系,进而实现乡村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其次,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跳出乡村的空间维度,在强调乡村振兴的同时,要确保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齐头并进。乡村的提质增效扭转城市教育对乡村教育的“虹吸”效应,逐步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实现城乡教育的融合发展,解决“乡空”的现实困境;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县级教育“扩容”,解决“城挤”的人口维度。
2 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现实困境
2.1 生源数量和质量面临挑战
义务教育阶段生源缩减。首先,我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给义务教育阶段生源带来挑战。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人3BuWeZf/t2EI40Hhl3B00w==口负增长,人口维度不均衡导致生源数量缩减。其次,乡村人口“晚婚晚育”现象与不断增长的离婚率,导致乡村生育率低。最后,乡村“少子化”结构缩减在校生数量规模。鼓励生育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作用逐渐衰弱,现代农村人口生育意愿发生变化,乡村人口进入“少子”状态。乡村中小学数量及在校生规模未来将持续萎缩。
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导致乡村学校学生数量进一步减少,村落学龄人口外流。首先,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根据国家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统计,2010—2020年
全国乡村人口年均减幅2.76百分点,城乡人口比例从1.01∶1增长至1.77∶1,增长近1倍。其次,乡村学校优质生源向城市流动。尽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推进、2012年对乡村学校“撤点并校”的政策刹车,2012—2020年年均减幅仍高达4.8百分点。最后,乡村学校陷入“空心化”的困境[2]。城市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和良好教育环境对乡村教育发展构成制约。虽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乡村教育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有所补充改善,但与城市教育相比仍存在客观差距,城市虹吸效应导致农村家庭将孩子带到县域上学,县域家庭将孩子带到城市上学的现象。
2.2 人才供给制度存在短板
优质教师供给不足。首先,乡村教育天然劣势是城乡师资差距。2019年以前,在我国每年60多万名毕业师范生与基础教育提供25万个需求岗位的供需倒挂现状下,仅有近30%的师范生到城乡学校任教。乡村振兴背景下,公费师范生政策、优师计划、特岗计划、城乡教师交流轮岗等强化乡村教师培养的政策出台,大批专业师范毕业生到乡村任教缓解教师不足问题。数据显示,2022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为81.02%,乡村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为76.01%,乡村师资队伍依然较城市落后。其次,教师“离土离农”的信念困境制约教师留岗。师范生培养环境的“去乡离土”导致其乡村教育情怀的欠缺,不愿意去乡村任教,到岗因个人发展原因申请调离比率较高。
教师职业价值受限。首先,教师传承乡土文化作用被削弱。宏观语境下乡村义务教育的向城化,使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乡村教育内容之间的裂痕逐渐显现,乡土文化自信受到冲击;中观语境下教学场域与当地区隔导致地方文化衰落;微观语境下教育者脱离乡村环境,导致服务乡村的意愿与能力代际区隔,乡村教育主体的身份“异化”,城市教育理念与本土文化缺乏有效融合。其次,教师的社会服务功能被削弱。教师的职能不仅是教育育人,作为乡土场域中文化资本的所有者,还承担着文化传播、参与公共服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服务功能。然而,随着乡村人口、产业和治理的空心化,乡村教师作为治理主体,融入性差,乡村教师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减弱。教师职业作用发挥受到限制,使教师资源供给与治理效果难以实现良性循环。
2.3 乡村特色教育起步较晚
学校教育的路径依赖。一是过度依赖城镇教育已有发展经验。现阶段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模式是将乡村与城镇教育对齐,甚至同化乡村教育。不同地区教育有不同的特征,忽视本土特色资源仅将城市现有模式照搬到乡村,不但建设过程中易造成乡民缺乏共情的“他期待”,建设结果也会导致学校同质化与乡村特色化的怠懒。二是过度依赖指标,“指标化”使执行出现偏差。指标化有利于政策执行效果的直接显示和监督考察,但由于教育执行环境差异和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以政府为主、自上而下推进乡村教育发展过程中,通过硬性指标衡量和评价政策,容易导致乡村教育考核出现唯指标与刻板化,着重以“他标准”衡量自身建设成果,必然导致乡村特色教育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特色文化教学发展迟缓。首先,教育资金投入总量提升但文化关怀不足。“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是乡村振兴对接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当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和衡量标准,加之乡村学校资金投入重点多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教学设施建设等硬件设施上,特色文化教学发展关注不足。乡村教育振兴也是以文兴教的文化历程,如果不能消除城乡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排斥与隔阂,单纯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只会形式上使城乡教育发展水平接近,而不能实现本质上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其次,教学策略脱离乡村课堂语境,影响教学成效。现代化教育是在对服务人群教育需求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提供的专业性教育服务,而不是简单迎合服务人群的短期功利主义教育需求或对教育服务的片面需求。乡村教育振兴通过传承优秀乡土文化,推动乡民精神富足、增强归属感。通过学校特色文化教学,焕发乡土文化的新活力,实现乡村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城镇化就是标准化”背景下,乡村文化话语权逐渐衰落;乡村学校为控制缓解近年来不断缩减的生源,更强调以分数为导向的教学,试图通过提高乡村教育“入学率”“升学率”留住学生而忽视学校的特色发展,乡村学生缺乏本土化教育,使年轻一代的乡土文化传播者和再生产者减少,导致乡土文化的衰弱和失传。
3 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应对策略
3.1 全面提升乡村义务教育供给效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加速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留住本地生源。乡村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通过乡村产业振兴创造更多乡村就业岗位吸引人口回流,留住家长从而留住学生;通过加大乡村创业补贴力度、宣传优秀返乡企业家事迹鼓励青壮年返乡创业就业;通过缩小城乡差距、改善乡民生活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教育惠民提供基础物质条件。
保障优质乡村生源需要注重提升乡村教育供给的有效性和创造性。首先是积极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基层乡村学校拓展。学校教育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在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的背景下通过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完善现有硬件设施、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城乡学校合作办学等措施,提升乡村学校教育水平。同时,积极传播乡土文化,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创新乡土教育课程,使乡村教育回归“乡土本质”,引导学生培养文化、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学习储备,培养乡村生源的乡土情怀,使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成为乡村振兴的后备力量。
3.2 完善乡村教师成长体系
完善乡村教师成长体系,对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激发教师的工作动力、促进城乡资源均衡分配具有重要意义[3]。首先,完善待遇体系。通过优化工资收入结构,在级别和工作年限决定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引入价格调节,使教师的基本工资水平和当地消费水平相适应;完善津补贴的项目类型,将教师生活成本列为重要的补贴标准依据,对乡村教师的奉献采取持续性激励。其次,提高教师的现代化从教能力。一是利用信息化资源赋能乡村教师教育能力。通过新时代乡村“数字教育”行动计划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满足乡村中小学在现代化课程服务中的需求,促进行政、乡土、党建、法治及信息技术等专项课程的深度融合,确保教育资源的均等可达。二是强化教师乡土情怀。肩负着守护、传播和引领乡土文化的使命,乡村教师扎根于乡土,缓解传统文化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逐渐消解。最后,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契合乡村特色教育的要求。作为乡村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乡村教师需具备深厚的情感根基、坚定的服务意识,提高乡村教师自身的数字素养的同时,要鼓励乡村教师将本土文化融入教学中,促成“智能+特色文化教育”的深度结合,打造出彰显乡村特色的优秀文化标识。
3.3 打造乡村教育振兴共同体
公平均衡是义务教育供给的最根本特征,在乡村教育均衡发展阶段,其成功不仅依赖于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推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乡村内生力量的积极参与,形成“坚持政府推动引导、社会市场协同发力”的协同机制。首先,加强引导推动。构建上下贯通的乡村教育政策体系,对乡村教育进行全方位支持,引领乡村教育步入稳定长效的发展态势[4]。同时建设信息反馈机制,及时了解乡村教育的需求和问题,为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此外,政府协调社会资源,强化优质带动、资源共享、互补合作,引导全国优质教育资源参与乡村教育振兴。
高质量乡村教育振兴需要积极发掘乡村内生力量,实现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要注重角色转变和职能转型,给予乡村主体的自主发挥空间;乡村基层政府需要提升自身的工作能力,主动挖掘本土教育资源,引导乡村教育融入乡村文化元素,推动乡村教育“自我造血”功能的实现。不仅包括培育自身本土化、专业化人才,课程本土化综合化等“软件”建设,还包括促进乡村学校的各方能动主体建设、加强社会和市场在乡村教育工作中的参与,形成多元主体的乡村教育振兴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杜尚荣,张娜.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乡村教育振兴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向度[J].教育科学,2023,39(5):82-89.
[2] 周均旭,常亚军.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育转型衔接的三重向度与现实进路[J/OL].现代教育管理,2024(5):39-49.
[3] 罗茜.资源投入“内卷化”与乡村义务教育功能偏移——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J].教育与经济,2024,40(2):89-96.
[4] 柳海民,杨宇轩,张晓梅.优质均衡:义务教育发展的时代转换、学理阐释与现实指向[J].现代教育管理,2023(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