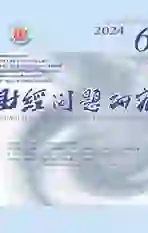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2024-08-02张方波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成为后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根本遵循。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即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在货币开放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借助于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载体实现跨境自由流动并完成积累和增殖,同时规避货币、货币索取权或证券形式的权利证书的快速积累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的经济过程。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进程丰富了这一逻辑,即金融开放为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夯实了基础,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载体种类不断扩围,以及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型开放。然而,当前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全球美元依赖型金融环境的外部约束、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存在结构性错配、金融机构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释放和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等。因此,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策略选择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形成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以发挥货币在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中的基础作用、疏通金融机构载体职能发挥中的堵点以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大便利、提升金融市场“管道式”开放能级以促进金融资本在更大合理范围内流动、优化境内外金融资本环境提高收益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积极培育促进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防范快速积累风险的规训环境。
关键词:金融开放;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跨境流动
中图分类号:F125;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4)06-0031-12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成为后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根本遵循。这一论断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金融开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国际资本对国内市场配置诉求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综合因素。
整体而言,学术界就金融开放的内涵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它包括金融服务业开放、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四类子项目[1]。中国四十多年的金融开放历程、发达国家实现或基本实现金融开放的历史经验均证实了这一内涵的合理性。金融开放的四类子项目之间互相影响,如资本账户开放要求货币国际化先行,资本账户开放与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之间互为因果关系[2-3]。金融开放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4],牵一发而动身,在推进过程中势必考虑各个项目的开放次序,除了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应该先于货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得到认可外[5],其他开放次序仍存在争议。此外,国际金融理论中存在的“三元悖论”“二元悖论”,反映出汇率与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之间的权衡取舍。“三元悖论”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得到满足,须放弃其中一个目标;“二元悖论”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与对冲外部风险存在两难困境[6-7]。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必要对金融开放进行整体性反思。
金融开放意味着境内外市场主体可以自由地以本外币持有金融产品、配置金融资产和享受金融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业开放还是资本账户开放,二者均是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8],其本质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的阐述是一致的。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包括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两大类,同时这两类金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并自由流动[9]。因此,有必要对金融开放进行系统性考察,从而揭示金融开放的本质,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这将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也可以降低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依附[10]。
二、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
(一)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的阐述及时代内涵
⒈货币是金融资本的逻辑出发点
马克思[11] 171认为,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它与劳动力商品相结合的时候才能羽化为资本。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一个亚种,自然而然地也应该以货币作为逻辑出发点。此外,货币的两种存在形态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一,作为货币的货币,其在商品交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其中,世界货币职能是前四类职能在全球范围和地理空间的延伸。正像商品资本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执行货币职能,因而货币具有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12]。金融交易作为商品交易的重要部分,货币职能的发挥也有助于本外币的货币兑换。其二,作为借贷货币资本的货币,它由从生产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转化而成,进而借助信用体系和信用机制转化为虚拟资本,并向其国际形式转变,从而丰富自身的内涵。由此,借贷货币资本以存款、贷款、信贷(如贸易信贷、商业信贷和金融信贷等)、货币市场工具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以本外币计价且以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虚拟资本以股票(股权)、债券、集合证券工具、金融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表现形式,①本质上是以本外币计价且以证券形式表示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货币作为金融资本的逻辑出发点,为货币开放成为金融开放的前提条件和重要部分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促进金融开放需要以货币开放为提前,而货币开放不仅意味着货币“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目标,也意味着作为货币对外价值的数量信号——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②这契合了学术界关于金融开放内涵的一些论断。
⒉金融资本具有国际扩张的本质属性
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在于它具有向外扩张的本能,因而金融资本的内涵也包括了世界市场这一元素。金融资本在流动性和增殖性方面优于产业资本和流通资本,因而更具有向国际扩张的能动性。从历史演进视角来看,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时代,过剩的借贷货币资本通过跨境流动获得相应的收益。“正如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11] 866对于虚拟资本的跨境流动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13]认为,在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其他一切国家,他们的国家证券是在世界市场上流动的,由此国家信用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列宁和希法亭所处的时代,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和食利性变得十分明显,其通过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加强对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控制[14]。20世纪80年代,在产业资本利润和增殖程度出现下滑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更大限度的增殖,金融资本以不同的输出方式扩张到全球范围,这不断驱动着世界市场的发展。按照哈维关于资本空间化的理论来看,全球范围为金融资本提供了更大的修复空间[15] 46。由此可知,金融资本国际扩张在当代仍然具有它的一般意义,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对于中国而言,金融资本国际扩张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完全国际化的背景下具有自身的含义。
⒊开放的金融体系是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重要载体
Lapavitsas[16]认为,金融体系的实质是将暂时闲置的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的一系列社会机制,是维持资本积累的内在组成部分。随着产业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逐步过渡到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逐步让位于经营证券经纪、交易业务的投资银行[17]。这种转变离不开大型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证券化带来的革命性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可以在商业银行所处的规范框架之外为金融资本的积累和增殖提供更加便利的场所,这种去中介化的过程也导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与莱茵模式的比较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普及,金融机构可以在更大的法律空间与技术空间中,以较低资本灵活地在本国政府债券、外国证券、消费者信用贷款和公司贷款之间融通资金;还可以在外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从事投机业务[18]。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全球性的金融机构组织网络渐成体系,原先持有借贷货币资本或虚拟资本的资本家逐渐被一些金融机构代替,金融资本持有者的范围不断扩大,由具有QDII、QDLP、QDIE资格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境内市场主体拓展到境外非居民市场主体,如具有QFII、RQFII和QFLP资格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其他资产管理机构,以及国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和主权财富基金等。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的不断推进,金融资本的境内外持有者范围也会随之进一步扩大。金融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证券化、衍生化使得资本的二次方、三次方不断出现,国际金融机构和开放式金融市场则成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积累和增殖的新载体。因此,金融开放意味着金融资本在自由流动的同时,它的载体也处于不断开放之中。
⒋从资本主义社会争夺金融霸权而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到新语境下的中国金融开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导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全球化进程,将资本的原罪逻辑演绎到全球范围内,并确立自身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主义,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放松了对外资和跨境金融交易的限制[19-20]。金融资本全球化是指金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扩张,它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为基础,但同时也需要各国保护本国金融主权以维护经济安全[21-22]。随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霸权在各国金融政策趋同、汇率重构、追求国际铸币税、金融利益集团的合力得以形成,从而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圈层不断稳定、外围圈层不断蚀空,导致全球金融难以可持续发展[23]。正如布哈林[24]所言,金融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特别流动灵活,特别错综复杂;它特别不固定,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于是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时至今日,中国金融开放的语境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争夺金融霸权而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金融开放的目标是要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金融资产和资源的多元持有和有效配置,为本国和他国的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实现金融资本的应得收益。金融资本的收益既可以从全球范围内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分割ΔG,也可以根据它自身运动和积累的特殊性而获得超越生产过程的增殖程度。金融高水平开放意味着金融资本在追求跨境自由流动的同时,会规避货币、货币索取权或证券形式的权利证书在一国快速流动和过度积累形成的金融风险。因此,“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成为党的二十大以来重要的政策语境。此外,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型开放为金融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了有力的规训环境,而这也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要旨。
(二) 实践逻辑:金融开放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
众所周知,基于改革开放的特定要求和整体步伐不断推进,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进程经历了1978—1991年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基础奠定阶段、1992—2000年的深入探索阶段、2001—2017年加入WTO后的承诺开放阶段和2018年至今的制度型开放阶段[25],正朝着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目标迈进。整体而言,金融开放是内嵌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秉持了渐进式、增量式改革的逻辑,考虑到金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已有的金融开放实践主要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制度型开放等稳步有序地推进。
⒈货币开放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夯实基础
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的世界货币职能不断强化的过程,同时世界货币职能形成和发挥的前提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运行[26]。从价值尺度来看,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和金融资产种类不断增多,如原油、铁矿石等期货或期权、B股、熊猫债、莲花债等金融产品。从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来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金额从2009年的25. 60亿元快速增至2022年的42. 10万亿元,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31. 70万亿元,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贮藏手段来看,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规模从2016年的907亿美元曲折上升到2022年的2 878. 12亿美元,占比也从1. 08%上升到2. 61%,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 92%上升至12. 28%,维持全球第三位,人民币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纸黄金”。同时,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规模再上新台阶,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职能,截至2022年底,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规模已超过4万亿元,涉及到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推动与其他国家开展本币结算合作(LCS)。此外,离岸市场不断发展也为人民币的境外积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银行统计的离岸人民币指数(ORI) 从2014年的1. 20%上升至2022年的1. 78%。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部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提供了适宜环境和便利条件,汇率从1994年的0. 30%逐步扩大到2014年的2%,甚至在2018年达到3%—4%,实现了人民币汇率从窄幅波动向宽幅波动的转变。另外,2017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具有成熟货币所拥有的弹性和资产价格属性,达成了实现多重均衡汇率的“内点解”。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和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共同推进中国货币开放进程,为金融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⒉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载体种类不断扩围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集中出台50多条金融业开放政策,尤其是2021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标志着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正式清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不断放松准入准营限制,批准设立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公司、支付清算机构等在内的外资机构100多家,促进内外资金融机构处于公平合理的市场地位,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根据OECD最新数据,2001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开放金融业以来,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业FDI限制指数不断下降,从2003年的0. 76降至2020年的0. 05,并在2016—2020年的五年中降幅高达0. 35,高于同期其他国家。此外,金融账户作为金融机构处理货币汇兑和金融资产交易的基本单元,是实现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积累和增殖载体功能的微观基础,金融账户的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中国银行已经形成包括境内账户(境内人民币账户和境内外汇账户)、离岸账户(OSA)、非居民账户(NRA) 和自由贸易账户(FT) 在内的多元化账户体系,其范围已覆盖在岸业务、离岸业务和跨境业务。金融市场“管道式”的双向开放为境内外市场主体持有金融资本类产品提供了多样化选择。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不断开拓多个链接全球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渠道,如债券通、互换通、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跨境资产投资渠道,公募REITs、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对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显著提升;同时全球三大指数MSCI、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将A股纳入其中,富时世界国债指数将国债纳入其中,这为境内外市场主体持有金融资本类产品提供了多元渠道。根据IMF 发布的2022 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目前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RQFII渠道购买境内的股票(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的股份)、存托凭证、债券(包括债券回购、附有认股权证的债券)、投资基金等集合投资类证券、其他证券、利率衍生品、外汇衍生品和股指期货等金融产品。此外,境内银行、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购买境外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其他金融工具等金融产品,还可以通过QDIE、QDLP等渠道购买境外股权或股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载体的不断开放,为境内外市场主体持有和交易金融资本类产品提供了多样化的平台,金融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也不断扩大。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1年底,境外投资者和个人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总规模不断扩大。其中,持有股票和债券规模扩大到39 419. 90亿元和40 904. 54亿元。无论是以贷款为表现形式的借贷货币资本,还是以股票、债券为表现形式的虚拟资本,持有量都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这表明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积累,并成为金融开放的特征事实。
⒊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型开放
金融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个层面的开放培育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市场秩序,从而形成规训意义上的制度环境。目前中国制度型开放已经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转向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转向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正逐步显现,为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自主开放和协定开放齐头并进。从2013年探索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到目前成立7个批次的自贸区(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自主开放的金融举措,如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建立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和建立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提高货币开放和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尤其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1年版》《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的出台标志着四种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此外,中国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协定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开放。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数据,中国已与2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0个双边自贸协定,部分协定为修订版或完善版。其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载体,受到了一些规范框架的约束,包括与国际监管协调一致的会计实务或披露的相关准则。为了对接国际上规制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巴塞尔协议Ⅲ,中国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等一系列监管措施,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R)、流动性覆盖率(LCR) 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其三,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管理(MPMs) 和资本流动管理(CFMs) 相结合的双支柱模式,推动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以应对顺周期资本流动带来汇率、资产价格的超调问题,通过宏观审慎调节系数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为境内机构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得境外资金提供更大便利。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不断深入为金融资本的跨境双向流动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由此梳理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即在货币开放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借助国际化金融机构和开放式金融市场等载体实现跨境自由流动并完成积累和增殖,同时规避货币、货币索取权或证券形式的权利证书的快速积累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的经济过程。总体而言,它是金融资本在地理维度上不断地从区域空间向全球空间的拓展,是金融资本空间化的重要体现[27],具体包括:货币开放是金融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本及其载体(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账户) 不断扩围;金融资本跨境积累和增殖是实现金融资源全球配置的重要体现,并非为了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和实现金融霸权;统筹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防范金融资本快速积累和增殖的风险是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相比而言,这一新的生成逻辑自然而然地将学术界关于金融开放的四类子项目纳入其中,并以金融资本及其载体为纽带,不仅解决了它们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的碎片化问题,而且揭示出它们在改革实践中存在的内在有机统一联系,从而为系统性政策制定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面临的现实困境
综上所述,金融开放实践进程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有益的铺垫,但同时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其中,有些属于外部环境因素,如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环境;也有些属于改革开放中的阶段性问题,如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及由此带来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同时也有自身开放存在的问题,如金融机构的载体功能尚无法完全释放、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一) 全球美元依赖型金融环境是重要外部约束
美国金融开放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这得益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国金融开放在本国货币开放助力下得以快速推进,但同时面临着美元霸权所形成的外部约束。诚然,国际货币权力的运用包括进行货币操纵、利用货币依赖和实施体系破坏三种方式,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美元依赖型金融环境[28]。第一,从世界货币职能来看,无论是在价值尺度、支付结算方面,还是储备货币方面,美元在全球金融资本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占据主导性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美元的规模和占比依然远超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其他国际货币,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头羊。根据IMF数据,2022年底,全球外汇储备中持有美元规模达到64 602. 61亿美元,远高于同期持有欧元规模的22 520. 63亿美元以及持有人民币规模的2 878. 12亿美元。第二,美联储作为美国的央行,却充当了全球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掌控全世界的美元流动性,不仅通过发行美元获得大量铸币税进行国际剥削,而且通过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和退出政策为金融资本的扩张和收缩提供了机会[29],即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快速流动和过度积累导致国际金融资本在东道国大进大出,破坏了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对东道国的经济金融造成重大冲击,并造成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本急剧扩张和收缩。一些国家因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退出而陷入货币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21世纪的欧债危机。由此,美国金融资本的输出是一种“掠夺式”输出,旨在全球范围实现以获取金融利润为主要目标的金融霸权。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输入国的发展并不是从国家战略诉求出发,而是为了满足美国金融资本在该国国内实现积累和增殖的需要。换言之,按照哈维关于资本空间化的理论,境外他国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进行时空修复的场所,在修复完成之后面临着资本快速流出而引发的国内动荡[15] 112。第三,SWIFT作为全球支付结算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度受到美国操控,成为美国实施“长臂管辖”和金融制裁的重要工具。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先后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发动制裁,致使这些国家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严重受阻。综上所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事实上的金融依附国,形成金融开放领域的中心—外围圈层。
(二) 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中存在结构性错配
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完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开放的推进意味着中国金融资本逐渐被境内外市场主体持有,同时国内投资者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持有金融资本。按照马克思[30]所言,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因此,积累和增殖是资本运动的动机,金融资本也不例外,它通过货币、货币形式的所有权、证券形式的所有权和权利证书获取利息、股息、红利、汇差等金融利润。对于中国投资主体而言,却存在积累和增殖上的结构性错配,如境内市场主体持有境外金融资本所获得的收益率低于境外市场主体持有境内金融资本所获得的收益率,这种收益率上的错配也被认为是“斯蒂格利茨怪圈”,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增殖场景。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美国国际投资净头寸为负数并且不断扩大,在次贷危机后达到2. 86万亿美元的峰值,并且2003—2021年美国对外总资产年均收益率为6. 98%,对外负债利率为2. 66%,由此获得了4. 32%的额外收益。中国与此相反,即国际投资头寸为正、收益为负。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22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为92 580亿美元,对外负债为67 267亿美元,净头寸为25 313亿美元,2022 年中国对外负债利率为5. 95%,对外金融资产收益率为2. 26%,净收益率为3. 69%,是2014年以来的最大差值。中国成为头寸顺差国和收益逆差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类型和持有者双重错配。具体而言,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以外汇储备类资产为主,持有者为官方机构,储备资产的收益率较低,而对外金融负债以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类为主,持有者主要为非官方机构,从而带来较大的融资成本。同时,中国积累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资产,却被禁止投资于高科技企业或企业收购等有前景的实体经济领域,而只能将其用于购买投资收益率较低的美债或其他金融产品,这些回流美国境内的美元又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进一步控制全球范围内产业资本以便获取更高利润的筹码,从而使净收益率得以继续维持[31]。以虚拟资本中的债券为例,美国通过低成本发债获得融资,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根据Wind数据,近年来美国、法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均低于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其中,2015—2022年,美国国债收益率为1. 44%—2. 95%,法国国债收益率在1%上下浮动,甚至在2020年出现负值,中国国债收益率为2. 83%—3. 89%,巴西国债收益率为7. 15%—13. 75%,印尼国债收益率为6. 38%—8. 22%,俄罗斯国债收益率为6. 12%—11. 36%。剔除与汇率、资产价格变动相关的估值效应后,上述国家的收益率依然高于其他国家。收益率差距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金融资本工具获得低成本资源的调配权,并从中反向获得相应补贴。
(三) 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释放
根据Wind数据,尽管外资持有国内金融机构股本的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持股数量和持股市值分别达到10 932 463. 75万股和30 197. 26亿元,但在准入准营的国民待遇管理上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外资在华展业仍然碰到一些玻璃门,导致外资在境内金融机构中的占比仍然较低。其中,外资占流通A股市值仅为4. 02%,外资持股占总股本市值仅为3. 06%,与新兴市场国家外资占比的平均水平(20%—30%) 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从具体指标来看,根据OECD数据,中国金融业FDI 限制指数在2020 年为0. 21,高于同期的美国和所有OECD 国家,甚至高于巴西(0. 08)、文莱(0. 15)、柬埔寨(0. 05)、老挝(0. 19)、越南(0. 13) 和南非(0. 06) 等国家。此外,2020年,中国的股权限制指数为0. 14,高于所有OECD国家,同时也高于文莱的0. 13;中国聘用外国人作为关键雇员这一指标在2020年为0. 05,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高于印度(0. 01)、菲律宾(0. 02)、泰国(0. 01) 和越南(0. 02) 等国家。由此可见,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运动和积累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释放,会阻碍金融开放的进程。因此,金融开放需要在外资金融机构符合国内政策和规定的前提下减少对外资进入的控制[32]。
(四) 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是金融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出金融资本进出一国的便利程度,是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构成要件。尽管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通过国际通用标准的Chinn⁃Ito指数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33],甚至在金砖国家中,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低于巴西和俄罗斯,与南非、印度水平大体相当。中国自1996年以来长期维持在-1. 24的水平,同期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维持在2. 30的水平,韩国经历了从-1. 24到-0. 17、1. 10的阶段,现在保持在2. 30的水平,而俄罗斯维持在0. 09、1. 10的水平,近年来因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影响又返回到-1. 24的水平。此外,从对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性三个层面进行综合度量而成的“三元悖论”指数来看,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仍然整体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这与Chinn⁃Ito指数衡量得出的结论大体是一致的。
具体来看,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意味着境内市场主体无法持有境外金融资本或境外市场主体无法持有境内金融资本。由IMF发布的2022年《汇率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可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完全开放的账户有4个,部分开放的账户有33个,完全不开放的账户有3个。反观美国,完全开放的账户有29个,部分开放的账户有11个,不存在完全不开放的账户。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完全开放的账户数量也少于巴西和俄罗斯,部分开放的账户数量多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便在部分开放的账户中,仍存在一些细项需要报批或属于额度管理,从而影响整体的金融开放水平,如QFII、RQFII等渠道虽然已经放开额度,但资质的获得依然是需要审批的。此外,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主要是关于交易行为本身的限制,属于实质性不开放的细项,如境内外居民与非居民之间不可相互提供贷款;境内居民不能自由地进行跨境直接投资和跨境证券投资,须通过QDII和RQDII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境外非居民不能从事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不能自由地在境内购买、出售或发行货币市场工具、股票类有价证券和衍生品工具。
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策略选择
在金融开放的逻辑框架下,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需要继续发挥货币开放在金融开放中的基础性作用,扩大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范围,提升金融机构的载体功能,拓宽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渠道,适度提高金融资本的增殖程度,同时防范化解金融资本快速积累带来的风险,而这也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的重要内容。
(一) 形成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以发挥货币在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中的基础作用
如前所述,过剩的货币流动性有助于向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等转换。金融开放意味着货币和金融资本的双向开放,因而形成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促进境外人民币世界货币职能的发挥,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跨境金融资产交易和投融资领域结算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另外,境外人民币可以更多地向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转化,从而为境内外市场主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选择。除了已有的供给渠道外,形成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在官方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外,通过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补充人民币流动性。第二,完善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外汇掉期、离岸银行间拆借、清算行回购等工具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补充作用,同时协调推动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即上海浦东新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和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加强境内外离岸人民币市场之间协同发展,以及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业务参加行的互动性。第三,人民币境外货币职能的发挥需要有效的外汇市场作为支撑,因而大力发展人民币远期、掉期和期权等外汇衍生品业务,扩大人民币对外衍生品业务资格银行白名单,吸纳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外汇市场以形成共同持汇的局面,提高外汇市场一体化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能反映境内外汇市场的整体状况,进而实现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 疏通金融机构载体职能发挥中的堵点以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大便利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本发挥职能的重要载体。因此,疏通金融机构载体职能发挥中的堵点能有效促进金融资本的高水平双向跨境流动。第一,不断完善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境外金融机构来华准入准营提供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全面落实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政策,在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引入金融业“竞争中性”相关具体条款,为境外金融机构在华发展提供公平环境,建立内外资金融机构统一适用的审慎监管体系,提高金融机构双向开放的软实力。第二,完善对符合在境内经营和上市条件的金融机构的牌照申请审核和服务体系,规范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持牌经营,引进国际视野更高、全球竞争力更强、管理体系更成熟、对金融资本具有更重要配置能力和金融产品设计能力更强的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和外资法人机构,引导外资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客户服务、风险管理和产品定价等方面积极展业,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发挥“鲶鱼效应”。第三,利用QFLP试点企业投资一级市场或定向增发市场的政策优势,率先开放外资发起设立管理人的门槛,让外资在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中拥有相应的投票权,发挥境外投资者在优化金融机构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外资在金融机构中的占比,让外资持有更多的A股市值,进而发挥其资产资质提升的作用。第四,可以通过吸纳熟悉全球业务和国际经贸规则、商务谈判能力强的外国优质人才担任金融机构高管等关键岗位。第五,从金融基础设施来看,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和离岸市场人民币实时支付结算系统(RTGS) 的功能,为人民币及以其计价的金融资本流动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加强CIPS与SWIFT的深度合作,通过接口SWIFT系统的GPI来提高人民币全球支付结算的辐射力,为后期跨境人民币独立支付结算奠定基础,用以规避美国可能实施的“长臂管辖”风险。第六,加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信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为内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做好辅助服务。
(三) 提升金融市场“管道式”开放能级以促进金融资本在更大合理范围内流动
金融市场“管道式”开放是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之前的过渡安排,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是联通全球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必要从扩大“管道”半径入手以吸引更多境内外市场主体。第一,在QFII和RQFII取消额度限制,以及取消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的基础上,完善QFII和RQFII的资格制度规则,为经营稳健性良好的境外金融机构提供境内展业资质,从而使得更多的境外主体通过该渠道持有境内金融资本,如持有和发售股票、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以及投资国内股指期货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等。第二,完善QFLP试点审批和外汇资金汇兑、登记监管环节,提供更多的便利性和灵活性,让符合条件的国际知名机构加快投资境内私募股权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推动更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参与天使投资、人民币基金产品管理等。第三,以“债券通”互联互通机制采取“多级托管、名义持有、集中交易、穿透式监管”的制度安排为样板,推动各类联通机制采取国际投资者接受的通行安排,降低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金融资本的成本,从而提高跨境金融交易效率,解决境外投资者在不同账户之间头寸转换受阻的问题。第四,在汇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让境内企业获得更高的境外融资额度,大幅降低融资限制,使得境外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境内银行机构为境外提供更多商业信贷和金融信贷等借贷货币资本类产品,提高对外贷款规模,为境外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大的自由度。第五,适度增加QDII、QDII2、QDIE、QDLP的额度上限,持续完善额度发放机制,让境内市场主体获得更高的外汇额度用于境外的证券投资,包括购买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集合投资类证券工具等虚拟资本类产品。
(四) 优化境内外金融资本环境提高收益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金融开放意味着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在全球美元依赖型宏观金融环境下,中国需要积极优化金融资本积累布局以避免过多持有美元金融资产而形成脆弱性,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鉴于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如美债、美股) 占比较高,可以有计划地减持美元资产头寸,减持的部分既可以转为持有SDR计价的金融资产,也可以转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资产,这有助于分散外汇储备资产风险。第二,以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依托,将部分对外金融资产转化为实体投资和股权投资,不仅有利于东道国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促进东道国的扩大再生产,而且还能改变头寸顺差但收益逆差的国际形象。第三,目前外汇储备资产中持有主体主要为官方机构,非金融企业、个人等微观持有主体较少,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各类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渠道提供的对外开放平台,增加市场主体外汇持有额度、提高对外投资灵活度,如非金融企业可以从事多样化跨境投资,积极优化对外资产负债表,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提供可供参考的积累和增殖方式;个人可以通过跨境理财通、跨境资产投资等试点渠道增加海外金融资产配置,实现“藏汇于民”。第四,优化金融资本积累的地理布局,尽量减少对美国金融资产的积累,扩大对欧洲(如法国、德国、卢森堡)、亚洲(日本、新加坡) 等国家的金融资产配置,提高对外金融资产的综合收益率。
(五) 积极培育促进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防范快速积累风险的规训环境
金融高水平开放在扩大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会导致跨境金融资本快速积累,从而冲击国内市场的风险,这在各国金融开放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因此,需要积极培育良好的制度与技术两位一体的规训环境,寻找两者之间平衡的“最大公约数”,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从制度层面来看,鉴于单纯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尚未成型,因而需要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个方面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为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防范境内外金融资本快进快出和过度积累。以目前正在进行的CPTPP和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为契机,加强对金融服务相关条款和规则的系统性研究,借鉴已有的RCE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和WTO传统规则的文本特征,如协定中存在的冻结条款、棘轮条款,以及从WTO沿袭来的对等原则,同时保留未来采取限制措施权利的兜底条款,这些条款内容的设计可以从维护金融稳定、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和以“三反”为目的的不符措施等方面入手,发挥金融条款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保护性功能。此外,积极参与国内金融领域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形成具有操作性的金融规制条款,以便在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中寻求平衡。第二,从技术层面来看,在基本实现巴塞尔协议Ⅲ国内落地的基础上,持续做好压力测试和常态化评级分析,利用金融科技加大对金融机构潜在风险的识别、监督、预警和处置,探索国际通行的“沙盒监管”模式;同时加强对金融资本双向跨境流动的监测和分析,发挥汇率在降低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风险中的第一道防线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统一,防范短期内跨境资金的异常流动,加强与金融开放水平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以提高监管质量。
参考文献:
[1] 周宇.中国金融开放的三个阶段:从局部开放走向全面开放[J].世界经济研究,2021(2):90-101.
[2] 徐建炜,黄懿杰.汇率自由与资本账户开放:孰先孰后?——对外金融开放次序的探索[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40-47.
[3] 江春,司登奎.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与资本账户的开放:现实选择与经济效应[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55-170.
[4] 陈雨露.推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行稳致远[J].中国金融,2021(24):9-10.
[5] 张明,孔大鹏,潘松李江.中国金融开放的维度、次序与风险防范[J].新金融,2021(4):4-10.
[6] REY H. Dilemma not trilemma: 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No.10591, 2015.
[7] 陈雷,张哲,陈平.三元悖论还是二元悖论——基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视角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21(6):34-44.
[8] 曹远征.大国模型下的金融开放及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思考[J].国际经济评论,2021(1):76-86.
[9] KALDOR Y. Financialization and fictitious capit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securities as a form of private property[J].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22,54(2):239-254.
[10] 贾根良,何增平.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困局[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5):66-77.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7.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48.
[14] 武海宝.金融资本全球积累视角下的当代国际关系——兼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根基[J].教学与研究,2019(4):59-69.
[15] 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M].付克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16] LAPAVITSAS C.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M]. London:Verso, 2013:11.
[17] SECCARECCIA M. Financi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ing: understanding the recent canadian experience before an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12,35(2):277-300.
[18] 伊藤·诚,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M]. 孙刚,戴淑艳,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49.
[19] MOTELLE S, BIEKPE N.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15,79(3):100-117.
[20] BRONER F, VENTURA J. Rethinking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131(3):1497-1542.
[21] LAVOIE M. Financialization, neo⁃liberalism, and securitization[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12,35(2):215-233.
[22] LI G, ZHOU H.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its impact on financial sovereignty[J].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5,6(2):176-191.
[23] 胡松明.金融资本全球化与新金融霸权主义[J].世界经济,2001(7):27-31.
[24] 尼·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M].蒯兆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Ⅲ.
[25] 郭威,司孟慧.新中国70年金融开放的逻辑机理与经验启示:兼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开放取向[J].世界经济研究,2019(10):15-28.
[26] 王国刚.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经济学动态,2020(11): 3-16.
[27] 张方波.金融资本空间化:叙述逻辑、历史考察与理性回归[J].财贸经济,2022(7):103-117.
[28] 乔纳森·科什纳. 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局经济学[M]. 李巍,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
[29] 乔榛,张志欣.金融资本扩张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历史变迁、现实状况与未来趋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48-57.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85.
[31] 宋朝龙,吴迪曼.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21世纪新版大萧条[J].当代经济研究,2021(10):46-57.
[32] CHANDRASEKHAR C P.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fragility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risk: can capital controls work?[J]. Social scientist,2005,33(3):3-39.
[33] CHINN M, ITO H. The Chinn⁃Ito index: a de jure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EB/OL].( 2023-11-14)[2023-12-19]. https://web.pdx.edu/~ito/Chinn⁃Ito_website.htm.
(责任编辑:尚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