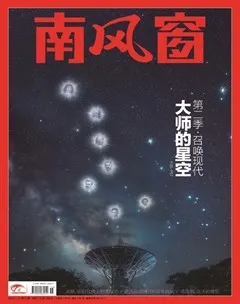如彗星划破夜空
2024-07-23向治霖


创世纪说,这世界的出现,是因为造物主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昼夜。
18世纪,创世一般的意义,被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赋予牛顿。诗句就刻在牛顿墓旁的纪念碑上,道是:“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一片光明。”
牛顿带来光,照亮了“自然的规律”,也就是真理。
光与真理,同等重要。光让人们看见世界,真理让人们看清楚世界,从而脱离蒙昧。
然而人们依然在追问,“蒙昧”之前是什么呢?
比如创世的光,在它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连牛顿也是追问者之一,他在后半生试图证明上帝存在,在“创世之前、时空之外”。
经过科学几个世纪的洗礼,疑问依然存在,只是换了版本:宇宙大爆炸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有空间吗、有时间吗?
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比较而言,在真理出现之前的“蒙昧”状态,容易探寻得多。几个世纪的英杰们,拿着各式“文明的尺规”丈量远古的人类。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探知世界的过程,决定了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人。
科学是最大的一盏光。从牛顿的时代再往前,在他的“真理”之光照亮的边界,与“黑暗中世纪”的接壤处,隐隐地出现两个身影:培根、笛卡尔。
两种传统
培根,生于1561年,卒于1626年。笛卡尔,生于1596年,卒于1650年。
两人生命接续的89年,前承文艺复兴时期,后启牛顿的时代。他们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同时代人,一起撑起科学革命的天空。
不免要问,追寻在16、17世纪人们的思想旅程,于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的世界,科技的强盛与人们内心的贫乏感,成为现代生活一个显性的悖论。人类制造的武器,强大到能够毁灭人类自己;人与人的交流无视距离,越来越迅速、沉浸式,内心的距离却在拉远;最新的AI浪潮,机器也精通琴棋书画,能开车、能进厂,人们却担心自己的生计……当然,科技不是造就了这个奇怪世界的唯一推手,但科技与人的紧张关系,确是事实。
对未来感到紧张的年轻人,也在社交媒体上造梗:原以为,科技的发展是为人类当牛做马,到头来,“牛马”竟是我们自己。
科技与人的关系,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早在20世纪,科学史家们便开始探寻这种紧张感的起源,于是,培根与笛卡尔被再次发现,他们被认为是“将人从自然中分割出去”的肇始。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隐含的意思,即知识是工具性的,它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人与自然因此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培根对自然充满征服的欲望,他在书中对青年说:“我是真正来把你引向自然和它的一切产物,支配它,使它成为你的奴隶,并为你服务。”
培根有别于传统的另一方面是,他极为重视实验,“自然的知识只有通过对事物有效地观察才能发现”。
他批判柏拉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这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偏见,因人类总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探知世界。培根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尽量不带偏见地搜集事实,越多越好”;在充足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必须分类和鉴别;然后是归纳,以此获取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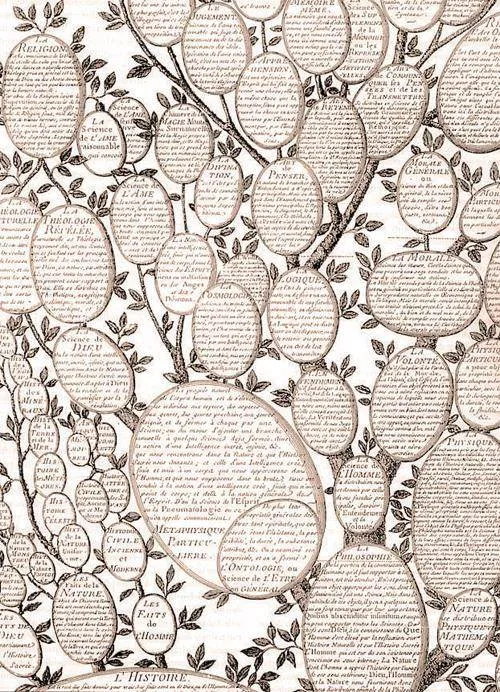
这是一次观念上的革新,从培根开始,知识成为一个外部对象,人可以认识它,它也可以脱离人而存在。
这在现代人听来,不觉奇怪,但在培根之前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欧洲中世纪后期,在神学基础上高度思辨化的经院哲学是主流观念,经院哲学大量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目的因”,其核心思想是,自然与人都是神所造的,各在其位,已是完美。
培根痛恨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发出了“堪称恶毒”的批判,称亚氏为“可怜的诡辩家”“眷养和指使一批讹诈和轻浮的人”,柏拉图则是“狡猾的诽谤者、浮夸的诗人、见鬼的神学家”。
也就是说,培根将西方古典科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及他们代表的两个传统,都否定了。
在16世纪,这就是向整个的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开炮。
人的位置
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这在今天无需说明。但科学史这一学科,研究的不是具体科学问题的真假,而是更为幽微的观念演变。
培根否定了柏拉图与亚氏的两种传统,不代表他的观念是凭空出现的。科学史学家们认为,培根强调的“观察—归纳”的科学实验范式,实际延续了亚氏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希腊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师从柏拉图,但是创立了非常不同的哲学体系。他也有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亚氏的真理是,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寓于事物本身,是内在的,不是超越的,“为了把握世界的真理,必须重视感性经验”。亚氏也会格物致知,注意收集第一手材料,亲手解剖动物,观察它们的习性。
要说他与培根的区别,就是亚氏主张以感性经验来处理材料,而培根主张实验。
亚氏的感性经验论,在被神学吸收后,构成了中世纪“整体宇宙观”的权威观念。人与自然乃一整体,密不可分。因为要用感性经验获取知识,所以中世纪没有独立的“知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的心灵可以理解整个世界。
于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里,人与自然安然相处,但这是一种蒙昧的和谐。
培根无法忍受亚氏主义的漏洞,收集的材料太少、推理的逻辑太“水”。他形容经院哲学,其思辨方法充满“难懂的术语”“故弄玄虚”和“空洞的结论”。
培根曾用一则寓言式的故事对此讽刺。他说,去问牛有几颗牙齿,经院哲学家宁愿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争论数天,也不愿意牵一头牛来数数—因为理解“内在的”本质,只需要研究造物者的意图。
培根的一生强调实验科学,自己也做实验,但他的“收集—分类—归纳”方法落实处,与亚氏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在科学成果上建树稀少。
培根的意义,是在近代开始时,对精致而空洞的蛛网般的经院哲学的批判,是对从他开始的几个世纪里的科学实验从事者的鼓舞。他的思想有深远的意义。

16、17世纪,确实也无法成为培根的时代。培根强调观察,反感假设与推理,这导致他对同时期的伽利略的实验无动于衷,也就错过了从哥白尼到牛顿的这一支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脉络。
导致亚氏主义衰退的真正敌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徒们。两者针尖对麦芒,概言之,对于事物的本质,亚氏认为是“内在的”,需要通过观察和经验获得;柏拉图认为是“超越的”,因此更需要的是推理演绎。
笛卡尔是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延续者。他重视实验,但更重视从实验中推理出的由数学语言描述的一般规律。他相信,从一般规律起,可以推导出越来越复杂的规律。因为一般规律是确定的,推理与演绎也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得到的规律也都是确定无疑的,它们构成真理。
笛卡尔的哲学观念无法详述,但回到最初的问题,“人与自然是如何分离的?”可以发现,笛卡尔比培根更进一步。
培根从真理中摘除了人的感性经验,笛卡尔相信真理是从“绝对的、简单的第一哲学”出发、经正确的推理获得,也就是说,不能用数学语言描述的,都被排除在真理之外了。
独立的“弃子”
同培根一样,笛卡尔也反对经院哲学的圈套,不认为心灵能够天然地获取知识。他采取“普遍的怀疑”态度表达叛逆。
《哲学原理》中,笛卡尔写到对现有知识的不信任:“我们从小到大,在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之前,就已经先行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意见、看法、传统与习俗;那么当我们有一天想到应该从自己的思维出发时,是不是应该对以前所接受的一切统统加以怀疑呢?”
笛卡尔怀疑的范围,比培根、甚至比同时代人都要广泛。正是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评价,笛卡尔是第一个以非学院的独立思想者的身份开始哲学讨论的。
笛卡尔是一位擅长数学的哲学家,关注同时代的物理实验和推导,但他不十分赞同伽利略,认为其不够严谨,“他(伽利略)还没打地基就开始盖楼了”。
在1638年10月的一封信中,笛卡尔如此评价伽利略:“他没有考虑自然的第一因,只试图解释一些个别现象。”
这个“地基”,或者“第一因”,在笛卡尔生命中漫长的颠沛流离和离群索居之后,被他总结为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我思”的释义繁多。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表示,“我思”中的“我”字于理不通,因为这里的“我”指的就是“思”,“我在”即“我思”,它并不是指笛卡尔(自己)的存在或任何一个思维者(作为肉身)的存在,它确定的只是“思维自身”的“存在”。
也就是说,笛卡尔认为,伽利略的物理学空有细节,缺少统一性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力是什么的解答,经典力学大厦的建成,还要等到牛顿的时代。
笛卡尔坚信,真理不应是伽利略的实验揭示的那样分散,而应该是统一的、简明的,可以推导的—因为“思维存在”是第一因(笛卡尔称为第一哲学),是先验的存在。必须找到这先验的第一因,其后的实验和推导才有意义。
笛卡尔的一生试图建立这个科学体系,此处无需再叙,因为在科学成果上,牛顿的光辉很快掩盖了他。
18世纪下半叶,笛卡尔所建立的高度思辨的涡旋宇宙理论,被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替代。而涡旋理论中的以太,也被后世证实了并不存在。
就狭义的科学成果而言,培根、笛卡尔两人,均是尝试之后失败的失意者。或许因为如此,他们更常出现在文科教材上,以“格言”和对旧时代的反叛为人所知。
但在科学哲学史上,培根和笛卡尔,接续了亚氏与柏拉图,他们是科学发展“从古典到近代”的标记点。
回到本文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分离已然完成:对真理的认识上,培根驱逐了人的感情经验,将人与自然对立;在笛卡尔这,真理剥离由更抽象的数学语言描述,并且是先验的—人类在或不在,无碍真理。
走出中世纪后,人们不再蒙昧,但也不再“安然”。因为人不再是被安排在自然里,从那时起,他/她成为旷野上个个独立的“弃子”,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
人与自然分离后,科学加快了对自然的改造,培根的“新工具”到18世纪发展为改天换地的“工业革命1.0”,也就是蒸汽机时代。就在那个时代,英国民间出现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机的一群人,他们被称为“卢德分子”。
这一“工业革命1.0”时期的名称被沿用下来,代指“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人类与科技的紧张关系,已经以冲突的方式呈现。
今天的我们已处在“工业革命4.0”时代。
人与科技能够友好相处吗?至少我们知道,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每在开始阶段都会迎来阵痛,但最终,技术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今天的我们,能探测更远的天体,研究更细的粒子。人类能及的地图无限扩大,也一直没有找到上帝。
最终能做决定的,从来就只有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