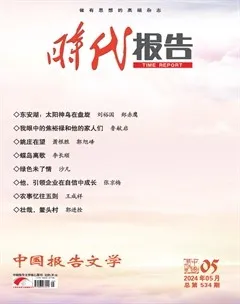当代中国报告文学作家集锦
2024-07-19李春雷杨桂林白雪
导师 李春雷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省成安县人,文学创作一级。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系中宣部确定的“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誉为“中国短篇报告文学之王”。
主要作品: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40余部,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200余篇。
曾获第三届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是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和唯一以短篇作品获奖的作家,也是新世纪以来唯一两次获得该奖的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是该奖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大奖的作家、全国优秀短篇报告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孙犁文学奖、郭沫若散文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蝉联四届)、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用文学报告生活
的确,在经济高度发展、信息无限灵通的今天,我们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正在丢失优良传统,正在越来越走向自我,从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历史责任。
虚的多,实的少;大的多,小的少;长的多,短的少;报告多,文学少。我认为,这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报告文学这个题材源于新闻纪实,直接脱胎于火热的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经典作家们的经典作品无不如此。但近年来,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却正在逐渐丧失这个传统。浮光掠影,图解生活,表面反映,缺少来自生活底层的呼喊和期盼,感受不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火的灼热、泪的酸苦、血的腥咸,感受不到那种实实在在的来自生活和生命深处的震撼。
这是报告文学作家集体浮躁的结果。
我们的窗外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片沸腾的海洋。每一个作家,只有真正深入下去,才能拨开表层虚假的泡沫,获取深处实实在在的鲜虾活鱼。
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热于抓重大题材,过分相信重大题材决定论,对生活中的小人物缺乏关注。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从小人物身上折射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更能彰显出报告文学的特殊价值。
生活中最多的是“无名氏”,大人物出名之前都是小人物。陈景润不是这样吗?焦裕禄不是这样吗?不要看他们官职多大、名气多大、地位多高,而要看他们身上蕴含的意义有多大,要善于从他们的“微小”中发现宏大,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慧眼。陈景润原本是科技界的“无名氏”,如果不是作家的发现,决不会成为名人;焦裕禄成名的时候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如果不是作家的发现,他或许就永远默默无闻地长眠了。正是由于他们身上蕴含着巨大的时代精神并被作家挖掘了出来,就变成了文学世界里的大人物。
现在不少报告文学动辄数十万字,名曰追求宏大叙事,实则搀沙搀水,是豆腐渣工程。
真正的报告文学精品应该像量体裁衣那样,可长可短,随身赋形。
其实,中短篇报告文学反映生活更快捷,阅读感觉更酣畅。所以,我们实在有必要提倡和鼓励报告文学作家多写短篇,这样不仅为读者节省时间,为出版社节省纸张,也为我们的国家节省木材,从而保护生态,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报告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报告文学要具有人文关怀、主持社会正义、心怀人类良知、善作文明批判,但更要有其独特的艺术性,就像鸟之羽翼,车之双轮,歌之旋律。没有这些,就不是文学,就不是艺术品。
而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且不说大量的枯燥无味的以企业宣传为主的“广告文学”,即使一些名刊大报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艺术品位也明显偏低,堆砌材料,罗列事实,表面分析,别说让人感悟、感动,就是让人心灵感染的艺术情节也稀少。
当然,真正的报告文学,不仅仅是关注生活本身,更主要的是要站在人类的高度,冷静地审视生活的背后,侧重于描摹和捕捉生活、生存、生命的坎坷或打斗过程折射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一片片深深浅浅的投影,那一处处隐隐显显的伤痕、那一双双明明暗暗的泪眼,并将这种悲悯和悲壮的氛围和思索融通于文字里和书页间。
这才是报告文学永远的魅力,这才是报告文学永远的方向。总之,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透视最深刻,反映最敏捷的艺术形式,正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喜爱。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经济社会都正在细细碎碎却又轰轰烈烈地变化着,各种社会焦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如何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冷峻地反映现实生活,写出对时代具有震撼和药补作用的文学报告,这不仅需要作家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健全的知识结构,更需要作家具有高超的文明思想、高远的历史思维。
在此基础上,再真正走进火热的生活,真正体验血的腥热、火的灼烈、泪的酸苦,并把这一切都化为沉甸甸的文明思考、鲜凌凌的文学感觉,渗透到文字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记录时代、记录历史,才能写出更纯正、更真诚、更深刻、更震撼的文学作品,从而走进读者心里,走向历史长远。
作家 白雪
白雪(吴红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广东侨界作家联合会常务理事。
出版个人文集六部(其中一部合集)。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报告文学》《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长江丛刊》《人物传记》《散文选刊》《散文选刊·下半月》《中国地理》《青海湖视野》《作品》《华夏》《侨星》《嘉应文学》《南方日报》《青海日报》《贵州日报》《羊城晚报》《中文周刊》《千岛日报》等报刊。长篇小说《恨别鸟惊心》载于《长篇小说》选刊夏季卷。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多篇报告文学、散文作品多次获省级以上奖项并入选多种文选。
创作感悟:
我与文学结缘应该感谢在遥远天堂里的母亲。母亲喜欢看书,收藏了不经典小说,20世纪70年代初期,它们统统被锁在一个大木箱子里。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假期,在州上住校读初中的哥哥放假回来。一天晚上家属院熄灯后,他拿着手电筒蹑手蹑脚地推开了我和妹妹房间的门,把我叫出来,做了一个不许出声的手势。神秘地对我说:“我们到后屋去。”我俩踮着脚尖悄悄打开那扇门,哥哥打开手电筒说:“你在门口站岗,别让妈发现了,我到箱子里给你拿好看的书,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我两岁的哥哥顺手奖励了我一本书——《苦斗》。
那时母亲经常查夜,一听到她到走廊的声音,我马上吹灭蜡烛,藏起书装睡。就这样,我在懵懵懂懂之中读完了《苦菜花》《上海的早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看完一本后就跟哥哥去木箱里换。
在之后的时间里,只有哥哥放假回来我才有如饥似渴读小说的机会。记得上初二那年,我开始看《红楼梦》,许多内容都看不懂,但很喜欢里面的诗,就拿出小本子抄写。一天被哥哥发现,他张口问我:“你在抄药方吧?”慌乱中的我竟连连点头。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哥哥,或许还不知道《红楼梦》里有许多情诗艳词呢。
文学作品让从小就喜欢语文课的我爱上了写作。高一那年,我写了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说,是写在那种格子作文本上的,整整一本。跟同学去邮局寄走的那天,像做贼一样,信封上根本不敢写地址,生怕被退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总到书店翻阅每一期《青海湖》杂志的目录,从一天天渴望见到自己的名字开始,一直失望到参加工作为止。
喜欢文学是从阅读小说开始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庆幸自己有一位爱看书、重教育的母亲,庆幸自己从少年时代就有经典作品可读。
1988年,在中学教书的我参加了系统组织的一次征文活动,一篇散文获得二等奖并变成了铅字。从此,开启了我的创作之路。
1998年1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红霞·白雪·蓝天》,作品也开始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并多次获奖:《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获 2003年“古风杯”全国散文大赛优秀奖,收录于《华夏散文精选》;散文《芨芨草的情怀》入《散文选刊》2008第8期;《难说再见》《思念》《芨芨草的情怀》收录于《中华散文百年精华》;《半个月亮爬上来》获2010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载于《散文选刊·下半月》2011年1月第1期;《自行车情缘》载于《散文选刊·下半月》2011年12月第12期,获2011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2016年《父亲的故事》获2016年中国散文年度二等奖;2009年出版散文集《深谷幽兰》。
其间开始尝试写小说。2002年在《伯乐》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雪雨飞花》,获中国作家第二届笔会优秀奖。2005年出版小说集《飞越红尘》。长篇小说《恨别鸟惊心》获首届“先觉杯”全国文学大赛优秀作品奖,年并入选《长篇小说选刊》夏季卷。
2000年开始钟情报告文学写作。至今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报告文学作品80余万字,出版报告文学书籍三本(一本合著),2014年8月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两代人的文化情缘》《羊城晚报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报告文学集《南粤惠风》《团结出版社》;2019年8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合著)。
报告文学获奖及比较有影响的作品:2006年报告文学《惠东强人叶东强》获第一届“先锋杯”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载于《报告文学》2006年第1期;报告文学《一个播洒阳光的志愿者》获《中国作家》第三届金秋笔会三等奖(载于《江门文艺》2007年12期);中篇报告文学《走过去,前面是个天》载于《中国作家》2008年第6期;报告文学《惠民之州》载于《中国作家》2009年第6期,并于2010年获惠州市首届六如轩杯文学奖;《陈密院长的传奇》载于《文学界·中国报告》2011年第6期,同年6月获陕西省作协、《陕西日报》建党90年征文优秀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合著)获“2020惠州文脉·花地西湖文学榜”金奖;并获惠州市“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当你老了》载于《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获第四届石膏山杯优秀作品奖,并获“2020惠州文脉·花地西湖文学榜”银奖;短篇报告文学《黄埔司法的黄玫瑰》载于《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3年第12期,2015年获河南省首届“圣光杯”全国报告文学大赛三等奖;报告文学《把爱写在祖国的土地上》获2019年“华夏杯”世界华人、华侨与新中国征文赛二等奖,并载于2020年《华夏》杂志第1期;《为我们的时代而歌》获“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惠州市直机关纪念建党98周年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一等奖;《化茧成蝶》获“生命如花 绿色无毒”全国禁毒征文二等奖;2021年2月,《抗阻疫情 和衷共济》入选《千里驰援——广东作家“抗疫”主题作品选》。
代表作《当你老了》发表后,被中国报告文学网、文学创新网、惠州民间文化网等多家文学网站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反响,多名评论家为之撰文。该作品颁奖辞:“以报告文学的视野,全方位、多视角、真实、全面地对中国式养老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一次文学性扫描和探索。秉笔直书居家养老力不从心的无奈,机构养老监督缺失引发的灾难,因病致贫和孝道消弭造成的人间悲凉,高成本低收入养老和管理水平落后带来的尴尬等等,无不引人深思。当传统的养老模式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养老刚需,一个个多元化养老模式应运而出,显露出一片耀眼的曙光。文中那俘获人心的场景,那写满人间大爱的故事,那颐养天年的画面,入心入眼。夕阳红映照的人间晚景,寄予了作者和读者对未来中国式养老趋势的共同期盼。”
2009年12月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2017年8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近20年,我把创作的主要精力投放在报告文学领域。报告文学写作已融入我的生命之中,尽管至今尚未写出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但我享受创作的快乐和过程。截至今年,断断续续写了十余年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式养老》,计划于年底出版。
我喜欢报告文学,近年读过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经典报告文学作品的忠实读者,并不断从中获取营养和鼓励。
作家 杨桂林
杨桂林,作家、学者。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师大在职大专毕业。先后出版报告文学、散文、历史等体裁的著作10余部,计300余万字。同时,在《中国报告文学》等国内文学刊物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两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生态散文11篇,被央视网、人民网、中国网、海外网等几十家海内外重点网站和媒体转发。其中,与他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动脉——河套治水回望》荣获内蒙古自治区2022年五个一工程奖。作者通过几十年系统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即:文学是一门关于美的语言艺术,文学要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理性、美善、正义与良知,这种创作个性美包括人性的美和自然的美,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美,以及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美。
文字里的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片飘荡在河滩的苇叶,
飘到那头,落在这头。
长大后,
乡愁是四处奔波的脚步,
客居在这头,
思念那头。
再后来啊,
乡愁是父亲的一壶地纯老酒,
咽到肚里,
望着外头。
如今,父母是牵魂萦梦的乡愁,
那是两座永远守望在家乡的坟头。
这是我的历史文化散文《激情大河套》中开篇中的一段话。几十年,我以故土心路、故土情怀、故土追寻,深耕在故土的这片土地上,并以此完成了300多万的文字。其中,我与牛丽萍合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脉动——河套治水回望》,荣获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发行《激情大河套》《咱们的全二平》《千年不衰的佘太酒魂》等著作,《激情大河套》是我用十年的时间精心打磨的一部集历史、文学60余万字的著作。我时常提醒自己:在世事难料的浮华与喧嚣中时刻要保持心灵中的宁静。同时在审视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审视自己。家乡浓浓的乡愁是我永远写不完的母题,在我脚下的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予以我的是吸吮不完的创作源泉的乳汁,所以所见所想甚至是触摸到的喜、怒、哀、乐常常用文字来表达。年轻时读到徐迟先生《哥德巴赫猜想》就梦想在《中国报告文学》发表作品。我的梦想实现了!在《中国报告文学》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一诺千金黄河作证》《致敬!战斗在第二战线上的人们》(发表在《中国报告文学》2022年9期) 。
2016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我与田玥飞应邀合作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鄂尔多斯——大漠丝路上的绿色长歌》,分两期在《鄂尔多斯文学》杂志上发表。同年被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吸收为会员,并被《中国报告文学》聘用为特约作家。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每段文字都离不开浓浓的乡愁和故乡情。2021年6月26日我与“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庆邦、纪红建等著名作家同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华人作品”中发表了散文《故乡的六月兰》。这是我继《乌梁素海边看赛马》《高粱田里的仰望》《回家过年》《黄河流凌踏春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河套系列第11篇散文。
在《回家过年》中,我把中国人“年文化”与游子的乡愁情结紧密结合在一起。过年回家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而言,不仅是乡愁,更多的是一种难眠的牵挂和望眼欲穿的期待。以回老家与94岁的岳父一起过年为主线,寄情于思乡之中。《高粱田里的仰望》以家乡河套地区佘太红高粱成熟的背景为底色。进而对黄河故道、水质、土壤结构、高粱酒进行书写,记忆是永远绕不开的乡愁。譬如:万亩红高粱瞬间动荡起来,叶子与叶子相互沙沙而细碎地撞击声。《黄河流凌踏春来》,以不可阻挡的雄浑气势顺流直下。《乌梁素海边看赛马》是对蒙古马精神的赞美。《故乡的六月兰》不仅仅开在眼前,而且开在人的心中。花,一茬接着一茬地开,生生不息地开。接着又将目光盯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先后写出《绿染大桦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03月23日第12版)、《到新华林场看绿色传奇》(《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06月26日第08版)、《品读二黄河之美》(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09月14日)、《绿满百里煤海》(《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06月29日第 12 版)。
我心归处还是故乡,心灵的归属还是故乡。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黄河最大的湿地,也是我的故乡——乌梁素海。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采写生态散文《近乌梁素海》发表在2023年6年15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这篇散文发表后并获奖。其中有段文字这样写道:“近年来,湖区通过土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发展现代农业,推动科学灌溉,改善农田小气候,提高土壤肥力,取得显著效果。大佘太酒厂负责人吴海计划在湿地周边种植万亩红高粱,促进现代农业、酿酒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又如在《高粱田里的仰望》中写道:“白露过后,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是我的家乡河套地区佘太川上红高粱成熟的季节。这些天一场又一场淅淅沥沥的雨丝,不经意地勾勒出漫川遍洼湿漉漉的红高粱。据说这里种植红高粱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因为这里处于黄河故道微生物密集丰富的神秘地带,水质甘甜,土壤结构疏松,是酿造清香型高粱酒的核心区域之一。所以,这里有十里高粱红、十里酒飘香的古老传说。这些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绕不开的乡愁!
“这个美丽的传说是我童年时,听村里一个老酒匠爷爷说的。老酒匠爷爷祖辈都是开缸房的。他那间土屋里堆满坛坛罐罐,冒出缕缕酒香,老瓷碗里盛满红红的高粱面条、面鱼、面卷、大煎饼,这些把我幼小的心灵占据了。老爷爷在大山深处一个叫野马沟的山坳里,曾种过一片高粱。在他精心呵护下,惊蛰过后又几经春雨滋润,在这块处女地上长出油绿绿的高粱苗。又过了一些日子,这些细细的高粱苗在拔节声中一夜间竟然蹿得老高。高粱穗子垂下如礼花绽放,这时花粉也开始飘飘洒洒。即将成熟的穗上缀满了剔透晶莹的浅绿珍珠,并开始由淡粉变浅红。过些日子在金风的轻抚下一夜间腾起灿烂的醉红。后来老酒匠爷爷去世了,家乡的红高粱也远去了……”
在我看来,写好故乡、写好农民、写好生态、写好乡村振兴,作者必须将自己的心鹰爪似的结紧贴故乡的大地,以仰民之情为己任,同时还要抓住“本土”这条根脉,凸显家乡这一片黄色的土地,尽可能地将以往生动的画面展开来叙述;力求作品中不拿捏,不掩饰。2023年秋天,在热衷于黄河几子弯生态事业的吴海先生的资助下,我用一个多月时间晓行夜宿徒步考查了黄河沿岸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在山川间行走,在与历史与大自然的对话中顿悟出,黄河这条中华民族血脉之河的哲学蕴含,在波涛汹涌的黄河激流中打捞出来的文明碎片,创作出黄河生态散文系列《问道黄河几子弯》,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我看来,故乡永远是我的出发地,是我心灵的回响。故乡的世俗人生、柔肠百结的人性、人与自然在乡恋乡愁的多重情愫中,必然蕴藏着生命个体冲决挫折与困惑的苦涩反省、沉思乡愁一起寄寓心灵,面对消失和存在或者颤栗,或者歌唱,或者哭泣!
故乡的红高粱是我面对人与自然、人与大地、人与世界的精神建构,是我对生命深刻的眷恋。我无论在外走多久,故乡个个鲜活的匍匐在大地上创造生命的人们,总使我回头望望——高粱田里上空飘荡着袅袅炊烟,闻滴滴地纯酒的清香,回望这些人们的喜怒哀乐。这种情结如同我被乡亲们种红高粱一样播撒在这片生命勃发的黄土地上。
责任编辑/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