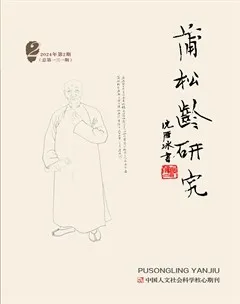论新编梨园戏《促织记》的互文性书写策略
2024-07-07任奕洁
收稿日期:2023-08-18
作者简介:任奕洁(2000- ),女,河南濮阳人。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戏曲史论研究。
摘要:新编梨园戏《促织记》是蒲松龄小说《促织》在当代的重演与再生产,该剧采纳了对《促织》进行互文性改写的策略,在衍续原作整体架构和怪诞色彩的同时,更将文本上升到人性悲剧的高度,呈现出新编戏曲独特的风神韵致。通过比对两个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既有认同和关涉,又存在颠覆与重构。借助互文性的视角,无疑能够从《促织记》的情节营构、艺术情境、立意主旨等层面窥见一次现代对经典的重释与升华。
关键词:《促织记》;《促织》;互文性;改写;梨园戏
中图分类号:I236 文献标志码:A
由林清华教授编剧、曾静萍女士执导的新编梨园戏《促织记》自《聊斋志异·促织》改编而成,演绎了成名父子的人生遭际,借此折射出统治者因喜好“促织之戏”而无限压榨、摧残底层百姓,最终致使“人形”与“人性”共同遭遇极端异变的奇诡故事。该剧于2022年荣获第二十八届福建省戏剧会演剧本一等奖,在2023年2月25日于泉州首演后,亦获得了戏迷与学界的共同关注,究其缘由,与其在创作中采纳的“改写”这一互文性叙事策略不无干系。“互文性”概念最早由法国文论家茱莉亚·克莉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在当今,其义可被释作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转换,即任何一个可见的文学文本都并非独立的创造,而是存有对过去文本进行“改写”的痕迹——而基于互文性的理论之上,“改写”又可被定义为新的文本对原文本的复述、仿拟,抑或改编等再创作。依照上述理论,《促织记》无疑施用了“改写”这一典型的互文性创作策略,与《促织》构设了某种自由开阔的对话关系:该剧在与原文本存在文本相似、交互的同时,亦以出色的艺术创造,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质感风貌、艺术品格。通过互文性视阈下对文本的比照,可见《促织记》的关目结构、艺术情境的设计,抑或主题的开掘与升华,皆存在与原作的密切指涉,甚而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即实现了“改写”这一较为成功的艺术实践。
一、戏剧张力的共通与强化——关目冲突的互文性
从案头小说改写为戏曲作品,最直观的比对即为不同文本整体结构与关目的裁织,这恰与互文性构成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对应,即文本A、文本B和它们之间的互文性联系。[1]5就此一点而言,《促织记》与作为原文本的《促织》之间首先构成了高度的互文性关联,在改写过程中沿用了原作中大量环环相扣的桥段。徐进在改编越剧《红楼梦》时曾提及:“应先从大处着眼,即先注意小说章回中的重要回目,把这些最能接触本质和最富于矛盾冲突的事件挑选出来……我决定笨拙地然而苦心地做一种摘记,即把书中一些重要事件和动人细节,罗列成行,予以推敲和评比,从这里作出抉择。” [2]5《促织记》的改写与此即存异曲同工之妙,首先择选原文本中的重要关目,与其构成回响与对应,后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为新的文本添加了戏剧气质。
“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 [3]169《促织》之所以能够成为被改写的蓝本,与其百转千回、引人入胜的情节构织密不可分。原文本中,仅围绕成名“得”“失”促织的过程,即有三重大起大落:成名遭遇摊派,无奈求助神鬼,奇迹般觅得佳虫;成子顽皮,放出促织,致使成名失虫;成子受惊投井,其魂化促织而归,成名再度得虫。其情节之起伏、曲折、诡谲,颇具戏剧性与艺术张力。《促织记》即以其曲折奇幻的剧情设计作为与《促织》之间共通的桥梁,存留并进一步发扬了故事脉络的起落回环,与《促织》在情节冲突设置的层面构成交互。
正如李渔“填词当首重结构”所言,《促织记》于大体上依照原文本的创作思路排布剧情,在高度还原原文本“文章之波澜”之余,又衍生出了独立的戏剧性。全剧框架共由《遭陷》《问巫》《得失》《虫变》《斗虫》《虫笑》《促织》七出构成,其中前五出皆为在取材原作的基础上加以深化、渲染,《虫笑》《促织》两出,既脱离了原著的艺术创造,又不失原文本灵魂的烙印。如第四出《虫变》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原文本中该情节的曲折性,还着意突出了“魂化促织”这一全剧之高光,阐发出改写手法的魅力。原作中,成子落井气绝,其魂魄却变作促织返回家中,为父母排忧解难,这一设计无疑是饱含魔幻色彩的,也是最具突转之“奇”、动人之义的。《促织记》以林清华教授之笔墨同原作相融,于舞台之上生动重现了这一情节:成名夫妇抚子之尸,悲怆不已,几欲随之而去,“我儿衣裳薄影孤单,咱同去冥府且陪伴” ① ;成子骤然醒转,二人喜出望外,然“心稍慰”不过片刻,念及无法拿出蟋蟀交差的成名,再度陷入恐慌与愁绪之中。《促织记》将其心声娓娓道来:“竹笼虚闲,凄风为伴,梧桐叶雨冷薄衫。独子新生欢,难抵人间旧愁依然。唯愿长夜无尽,东君永不起,避一时死生摧肝胆。”将《促织》中成名举目望见“蟋蟀笼虚” ② 后“气断声吞”“僵卧长愁”的心理转折诠释得淋漓尽致。在成子之魂变作促织后,成名先是“喜而捕之”,见其“顿非前物”,又不由以“小”劣之,《促织记》借成妻之言道尽成名“惴惴恐不当意”:“促织啊!你头小腿细牙爪无力,怎能上阵去拼戮?官人,放他去吧!这小小促织甚是可怜,何必捉他送了小命?”此处,原作仅以寥寥数笔带过,而《促织记》以其文采与声色兼备的曲词宾白,生动演绎了其间成名心境的数度起落、情节的几重波澜迭伏。《虫变》一出,既是《促织记》擅造转折之笔法的力证,亦是对《促织》原著高潮部分的戏剧化呼应。
《促织记》的最后两出《虫笑》《促织》,与前文对原作近乎仿写的援引不同,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与变更,发扬艺术想象、实现合理虚构的成果。《虫笑》所述成子化作促织入宫后,与拟人化的群虫交流时的所见所闻,并凭借“虫”之视角观测人类世界的虚假可怖,为全剧之收梢埋下了伏笔:《促织》一出,可谓对原文本颠覆性的扭转。蒲松龄为原作铺设了一个高度理想的结局,即成子以人身的形态顺利苏醒,成名也因虫发迹;但《促织记》却将剧作的末场处理为觉悟后的成子化鸟归去,徒留成名夫妇凄迷悲伤,如此浓烈激荡的悲剧性冲突无疑同蒲氏笔下的“大团圆”高度相悖,但若结合上文,这样的设计则是更顺理成章的。成子的“变形”原本即出于极端困境下的无奈,而当他目睹人性是如何在现实的诱导下被魔化和摧毁之后,所谓的“大团圆”便愈加缺乏说服力了。汪曾祺的《聊斋新义》,亦曾指出原作此处的不合理性,“这与前面一家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绪是矛盾的,孩子的变形也失去了力量” [4]238;“本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的悲剧” [4]238。可见,原文本收场的喜剧性质是“蒲松龄趋于传统的‘善恶有报价值观的一种愿望诉求” [5]169。而《促织记》改写的结果,则与前文成子“变形”的初衷、经历等衔接更为顺畅,其悲剧的性质也更加具有警示现世、震撼人心的力量,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实现了剧情的统一性。
概而言之,《促织记》在关目结撰的层面既存在对《促织》的充分回溯,又于其中融入崭新的匠心与思索,以“改写”手法发扬了重释旧文本的效用,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联可谓一览无遗。
二、人境、虫境、神鬼之境——艺术情境的互文性
蒲松龄创作的独特处在于并非直接展示真人实事,而是以阴间神界作为对现世的影射,于看似荒诞不经中抨击世事、暗讽人性,他在《促织》中精心织造了现实、虫界、神鬼三个世界 [6]81,既具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又饱蕴浪漫主义的想象与寄托。《促织记》在改写中沿袭了与《促织》相近的故事演绎模式,在舞台之上建构了“人间、虫间、神鬼”三重现实共梦幻交织的艺术情境,实现了以“互文”手法丰富剧情文化空间的妙用 [7]97,具有戏仿的色彩;同时又对三重情境加以戏剧化的渲染,充分发扬了“互文性”改写策略的优长。
(一)人境——人物的立体化重塑
《聊斋志异》本质是针对昏戾现实的批判,《促织》与《促织记》建构的首重境界皆为“人境”,同样绘制了真实时代背景下被无限压榨的现实空间。《促织》起笔之初,即有时代的阴影悄缓而落:“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被强行“摊派”是成名悲剧的序幕,而在《促织记》中,成名的遭际亦是自一句悠长的“摊派”起始。在两重文本各自构筑的“人境”中,统治阶级的昏聩无度、荒淫挥霍,官员的媚上欺下、借机盘剥皆如出一辙,这无疑皆为《促织记》同原文本间形成的指涉;但是,献上奇品促织后的成名又摇身一变,在两个文本中分别迎来了“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君心悦,钦点为官,青云忽直上”的命运转折,令人唏嘘。然而,两个成名的生命轨迹虽基本一致,但《促织记》所构筑的“人境”似乎更为震撼心魄、深切动人。究其缘由,《促织》作为短篇小说,对具体人物的形象、心理变幻等刻画难免有失细腻、鲜活;而《促织记》作为新编戏曲,则充分弥其不足,在展现广阔社会图景的同时,亦深入人物内心,勾勒出多面立体,实现了以成名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解构。
《促织》中的成名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而更似蒲松龄用以影射庶民集体遭际的艺术符号。成名因“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对上层欺压只能逆来顺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无疑是不得志文人与底层劳苦百姓两类群体特质的糅合。而最终成名的圆满结局,又折射了畸形制度下普通知识分子对利禄功名的共同渴望,即“裘马过世家”。成名从多年受压迫者一朝跻身上层,其间经历定然难以言表,然而囿于历史和视角的局限,成名的心路历程在小说中并未得以展现。《促织记》正是对此一点进行改写,在保留以上人物特质的同时,构设了一个更加具备独立精神人格、逐步向扭曲和异化下堕的成名形象。
《促织记》中的成名,其底层人民的身份更为纯粹,并未如原文本尚可坐拥里正之职,这便致使他前期的命运更加无奈、无助且无从选择了。除此之外,成名落魄知识分子的气质较《促织》亦为尤甚。在成妻劝导他向里正求情时,他先是坚持书生傲骨,自称“夏虫不可语冰”,在受到里正恫吓后,他所思亦非贿赂钱款,而是培养里正之子成才,以赚生机,此时的成名尚且维持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思维。然而,饱受折磨的成名其心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历经着无声的变幻,这亦是《促织》所不具备的。在第三出《得失》中,成名初始尚谨记“事鬼敬神而远之”的圣人之言,自愧听信野巫,“羞煞人也”,然而忆及无法交差的后果,竟又开始焚香跪拜促织之神,印证其性格中亦有软弱和妥协的成分:在自保面前,他并不是始终坚守气节、宁折不弯的。当成名典当笔墨纸砚以换促织之食时,此刻的他已在无意识中经历了第一重人性的异变,“虫”在其心中的地位高于了圣贤之“书”,这一点亦为其后成名抛却初心、成为霸凌民众的新“恶”之源铺下了伏笔。而在成子奄奄一息之际,成名又呈现出原文本着笔甚少的慈父形象,抚子泪垂:“恨不能,一夕青云得攀,大翅得伸展,却看戏辱驱撵谁敢?到那时,佑妻儿,饱食无忧绫罗穿。”由此视之,成名重视利禄富贵,亦是出于爱子、爱妻之心,而不仅限于原作中求名索财的赤裸欲望,即便其后逐步迷失堕落,也还尚存使人理解、同情之处。如此改写后的人物同原文本相较,无疑是更为完整、鲜活,且有声有色的——以青松自比的成名,最终却被高度魔化,堕入利欲的尘网之中,这不可不称之为《促织记》对“人境”现实的浓郁嘲讽。《促织记》对以成名为典例的人性、人境之解构,无疑更能引发观众对时代、对社会、对“人”之个体的广泛思考。
(二)虫境——全新视角的投射
未负“促织”之名,《促织》与《促织记》共同构筑的第二重境界即为“虫境”,两个文本塑刻“虫境”的手法具备颇多要素的对应性,即在描绘“促织”时对此倾注一定的笔墨篇幅。在原文本中,蒲松龄如数家珍,罗列出蟹壳青、油利挞、青丝额、蝴蝶、螳螂等促织品种,更运笔详细,将“促织”样态勾画栩栩如生:“始出,状极俊健。……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无独有偶,《促织记》中,绝望的成名在乱石丛中偶得促织,欢欣之余亦盛赞此虫外形:“项宽象牙如钢锯,额鼓棱角黄金瞳。翅生梅花爪似龙,天生异象将军勇。”可见,“促织”在原文本与《促织记》中皆拥举足轻重之位,甚而需如塑造人物角色一般,勾勒其状貌细节。而在《促织记》的改写之中,不仅以客观笔触刻画“虫”形,更借“虫”之目光,携其主观意识洞察世界,这样的手法较原文本而言,毋庸置疑是新颖、大胆且超脱的。
《促织记》中“虫境”存在的要义不仅止于揭示“人”化为“虫”的诡谲荒诞,而是对人性的异化倾入了更深层次的回味与思考。在两个文本之中,成名获得促织后,皆不顾家中早已无米为炊,换取蟹白粟黄与虫饲食,《促织记》中的成名更不惜为此典当赖以谋生的文房四宝,此刻“虫”之位竟远高于“人”之位,其间荒谬难以言表,此乃《促织》与《促织记》构建“虫境”的第一重意义,二者的动物寓言是共通的。但视《促织记》第六出《虫笑》,其较《促织》所构“虫境”则可予人以“更上一层楼”之感。
《虫笑》一出,编织出的是一个如梦似幻、高度拟人化的“促织之界”,更是对蒲氏未尽之言高度具象化、真正视觉意义上的“虫境”——成子化作的促织初入宫廷,目视众虫模拟人类宴饮风月、谈情说爱,但模仿之余,又难掩对人类的无限蔑视:“我生在屋檐,见人脸上千,唯人心难见。如梦又如幻,谁有如炬慧眼?谁好谁奸,且留待亿万斯年。”《虫笑》道尽“人心难见”之实,借“虫”之口指出人之引以为傲的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终将沦作虚幻泡影,反倒是看似微末、为人玩物的小小昆虫,方能坚守自然本心:“虽生也短暂,但哭即是哭,笑即是笑,何等天然。”以“虫”之视角对人类虚伪本性的洞察,阐发成子与观众的恍然彻悟,此为《促织记》中“虫境”构造的第二重意义。《促织》与《促织记》皆营造出了物种颠覆的荒唐与魔幻,然而《促织记》却通过互文性的改写,以动物性的视角对世界进行观照与窥视,进一步映射出了人性的极致迷惘和破碎。
(三)神鬼之境——以现实为底色的浪漫主义色彩
《聊斋》擅书花妖狐魅、幽冥通灵等奇闻异事,“神鬼”乃《促织》同《促织记》构造的第三重境界,在此情境之内,人与鬼神的灵识可谓是相互联通的。原作中,成名因无法上交促织而忧闷欲死,“转侧床头,唯思自尽”,然而驼巫的指引却于千钧一发处助其一臂,成名依其所赐画像,果然再得佳虫。可见,《促织》作为孕育于清代的文本,无论是其作者抑或受众,对神仙狐鬼等所谓的超自然力量都仍持有敬畏与信任,成名走投无路,所思唯有向神明祝祷,而驼巫作为“人”与“神鬼”之间的摆渡者,亦以诚心相助,助其渡过难关。这既可称之为蒲氏创作的恻隐之心,亦为时代的局限之处。《促织记》对此的改写,仍保留了原文本中浪漫主义的特质,但同时也倾注了直面现实时更为客观、冷峻的目光。
《促织记》第二出《问巫》亦叙述了成妻求神问卜之故事,看似是对原文本的仿写,然其内核却大有不同。原作中的驼巫当真有通神之能,对前来求告的信徒亦为诚心赐教,而在《促织记》中,驼巫却被改写作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明知成妻“搜尽家产,只有十文余资”,仍要“且以方才梦中之境戏之”,胡乱赐齑之后,便与其徒卷款而逃,去他乡继续行骗。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原作满溢浪漫色彩的心理寄托,然而《促织记》另行建构其“神鬼”情境的特殊方式,第三出《得失》,才是《促织记》中“人”同“神鬼”真正建立精神链接的起始。在《得失》中,原本不信鬼神之说的成名为求虫而频频祝祷:“促织,我的神,祝之祷之,盼兮切兮。”如此三拜三祝过后,原本绝望的成名终于捉得促织,而其得虫的过程恰与驼巫所赐之齑一般无二,歪打正着的戏谑色彩之余,更似冥冥中真有天意襄助,成名作为“人”直接同“神”产生了心灵的对接,这正为《促织记》所改写的“神鬼之境”注入了一种相对更为纯净的奇幻力量。而在第四出《虫变》中,成子身死而魂魄犹在,幻化作虫,重返人间:“爹啊娘,莫恼儿,三分气息犹在,魂变促织还恩情。”在《促织》中,虫形与人性相互剥离,各自独立,而《促织记》中,死后化虫的成子仍然维持着为人时的意识和性情,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得以融合,此乃《促织记》在《促织》“变形”设想的基础之上,倾注了浓郁情感所建构出“人”“鬼”共存的平行空间,以瑰奇想象作为人文情怀的寄托,可见《促织记》的浪漫主义精神既是与原文本互通的,又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促织》的。二者同以“神鬼”之境作为对人界缺憾的延伸与弥合,实现了在“虫高于人”的荒诞世界中的逻辑自洽。
综上而述,《促织记》以互文手法将《促织》所编织的三重意境牵涉入文本之中,并通过“改写”策略将经典与戏剧性、现代性相融,实现了超脱时空的表达效果,其阐发出的艺术吸引力、感染力是无可比拟的。
三、批判现实与人性讽喻——主旨立意的互文性
《促织》原为蒲松龄借“人”与“虫”影射社会状况、抨击晦暗时代之作,然而,比之注入了现代意识的《促织记》,《促织》的主旨意涵相对单一,其矛头仍停驻于对封建时代中丑恶行径的针对和控诉;同时,由于宏观视角的限制,《促织》只注重营造统治阶级和庶民阶层之间的对立,并未能够深入触及微观、具体的人性内部矛盾。可见,《促织》同《促织记》的主题立意虽相互交织,然而《促织记》却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对人性异变过程的刻画和揭示,这是对原文本而言的另一重升华。
首先,《促织记》与原文本批判现实、揭示社会的主旨仍是交互重叠的。两重文本同样借助“变形”手法,针砭畸形制度下的种种压迫、剥削等时事危机,对“非人”的现实社会流露出高度否定的态度。仅视此点而言,《促织》似乎也关注到了“人”的异变,但整体只倾向于针对社会弊端的嬉笑怒骂,对于变形的概念也仅仅停驻于人“形”,却未能深入至人“性”的高度。换言之,蒲松龄只是在无意识中粗疏地描绘了“变形”这一结果,而并未触及人在异化过程中对自我的剥离及心路变迁的复杂性。对此,有学者指出:“蒲氏的异化变形观是朦胧的,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由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和建立在人身依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关系特征,以及封建文人的文化视野局限,蒲松龄还未能深刻认识与理解异化现象。” [8]14在《促织》中,关于人性“异化”的概念尚未成熟,这一点依托《促织记》的改写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自存在主义的视角深入探微,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主旨升华。《促织记》对于人性被异化的普遍性、深入性的揭示与嘲弄,具有非凡的启迪。
《促织记》于现代主义的视阈下对原文本的主旨内涵作了较大程度的解构,揭露出人性在极端迫害下扭曲和异化的过程。《促织》全文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事,然而在《促织记》当中,叙述者的目光却是不断变幻的,促织与成子视角的先后出现,为《促织记》深化揭示现实以外的主旨提供了崭新的维度。人可因“杖责处、皮肉炭滚,更有那,小鬼凭势,官吏心机狠”的威逼而异变化“虫”,已是极致的荒谬,而“虫”目光中对人界的所见所闻,则更是骇人听闻、极尽嘲讽。《促织记》第六出《虫笑》,依凭戏曲艺术中的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呈现了促织目中的人类世界,亦为观众揭示了批判现实以外的崭新主旨。在这一世界中,群虫倾情演绎人界中的风光无缺、男欢女爱,然至欢愉尽时,却只余“嫌恶如破履,攀扯又撕咬,尤甚促织搏斗在瓦槽”,借此发出“谁是促织,谁是人者,万物混沌怎分辨”的质问,可谓振聋发聩,同时启发观众深思:何为动物?何为人类?在晦暗现实下不可避免地堕入矛盾和异化的人性,究竟是否比淳朴天然、哭即是哭、笑即是笑的“动物性”更为深刻和高贵?成子身处现实人界时,尚因弱小卑微而饱受里正之子霸凌,而入促织之界后,却在群虫的合力促成下“独占鳌头”,感受到了春风沐雨般的人道主义关怀,如此鲜明的对比映照更加强化了文本主题的讽喻意涵,《促织记》中浓郁的荒诞色彩在此处展露无遗,这一点是原文本所无可比拟的。
萨特曾指出“人”的生存处境与自由选择的关联:“人所处的位置是自由选择的起点;人的过去是人存在的历史及自由选择的基础;周围的物体是赞成或反对自由选择的条件;他人是自由选择的外因;死亡是对自由选择的否定。” [9]400《促织》对成子着墨相对不多,即使成子以魂化虫、为父分忧,蒲松龄也只将笔触停留于成子放虫、化虫后的一系列客观概况,而未抒写以其主观视角出发的情感与思考。《促织记》则对此进行拓展,从孩童纯净的目光出发,一改成子于原文本中近似工具的位置,并借其每一次的自由选择,透视出人性异变的震撼与可怖。成子初时纯真犹存,所念唯为父母分忧,故而选择化虫;《虫笑》一出,成子初入宫廷,面对群虫对人类“自视万物灵长,却蒙昧不分,是非不明”的指责,成子坚信父亲深谙礼仪教化,因此选择接受群虫“送其父一场功名”的“馈赠”;最终,亲眼目睹成名小人得志、趾高气昂之状的成子舍弃重生、化身飞鸟,前去追寻真正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仍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以上几种选择皆是在剧中的存在主义对人之境遇推向极致的前提下完成的。
《促织记》中,尚未涉世的成子徘徊于“虫形”与“人魂”的中间地带,其终极目的不过为助父母避祸;然而,在促成了成名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亲睹父亲人性坍塌的成子油然而生绝望、迷惘之情,不由自主地坠入回归人身或脱离人界的荒诞抉择之中,并被迫开始思考“人”之生存的意义。在成子的最终选择背后,无疑暗涌的是编剧对于人性的无限嘲弄,以及对人类存在危机的影射。于荒谬不经的境遇中探寻和剖析人性本质,正是《促织记》现实批判之上的讽刺性议题,实现了对原文本立意的升华。
结语
《促织》,一部诞生于封建时代落拓文人之笔的短篇小说,其关目设置、情境构设、主题深度等皆不免受制于时代思潮、形式篇幅和作者目光的囿限。新编梨园戏《促织记》作为后世对此的互文性改写,则挣离了重重束缚,既保存了原文本的传奇本质、讽喻旨趣与批判意涵,又在此基础上开拓视野,完成了对其情节、境界、主旨等层面的再创造,深入探寻人性的晦暗和幽微,不可不谓之当代以新编戏曲重释文学经典的优秀范例。观照互文性视阈下《促织记》对《促织》的改写,不仅是一次调动自我生命经验与情感体验的精神旅程,更能阐发对“人”之存在意义的思索。
参考文献:
[1]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徐进.从小说到戏——谈越剧《红楼梦》的改编[N].人民日报,1962-7-15(5).
[3][清]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总评[M]//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代编)·第1集.合肥:黄山书社,2008.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邓九平,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李明彦,孙琪祺.经典改写背后的“现代主义”焦虑——论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
的主题重构[J].文艺争鸣,2019,(6).
[6]钟子薇.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物种世界与人鬼世界——读蒲松龄《促织》[J].荆楚学术,
2019,(2).
[7]叶子.清代曲牌体红楼戏与经典戏曲之“互文性”研究[J].戏曲研究,2022,(3).
[8]陈卫华.《促织》和《变形记》比较分析[J].株洲教育学院学报,1998,(4).
[9]冉常建.东西方戏剧流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On the Intertextuality Writing Strategy of
Cuzhiji in the Newly Edited Liyuan Opera
Ren Yijie
(School of Film,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0,China)
Abstract: The newly edited Liyuan Opera Cuzhiji is the contemporary replay and reproduction of Pu Songling's novel Cuzhi,while continuing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grotesque color of the original work,the text rises to the height of human tragedy,showing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newly edited Opera. By comparing the dia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exts,we can find that the former not only identifies and relates to the latter,but also subverts and reconstruct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we can undoubtedly see a modern reinterpret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classics from the aspects of plot construction,artistic context and purposive.
Key words: Cuzhiji;Cuzhi;intertextuality;rewriting;Liyuan Opera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