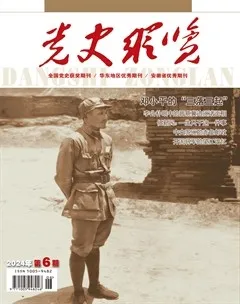诞生于烽火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
2024-07-03周文洋
周文洋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于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地区,生活困苦、文化落后,90%以上的民众都是文盲,大多数红军战士因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所以对党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对国家前途命运更是所知甚少。如何尽快改变这种知识匮缺、觉悟低下的状况,提高军民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适应斗争和发展需要,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收缴战利物资时,在漳州高中发现3000多册图书。毛泽东命令将书全部运回瑞金,并请来时任中央苏区教育部代理部长的徐特立,商讨创办一座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图书馆。
徐特立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老师,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教育家,他曾主持创建长沙女子师范、稻田师范等学校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运作和管理经验。
徐特立见到缴获的图书后,对毛泽东说:“如是阅读和收藏,这些书已很可观,但要建一座图书馆还远远不够,要继续收缴,多多益善。”
依照徐特立的建议,毛泽东在签发《关于扩大红军的通告》中加入了如“在攻打城市时,发现所有书籍一律上交,不可以就地销毁,因为大部分书籍可以拿来为我党所用”的内容。遵照该要求,红军各部队每占领一座县城都特别注意搜查学校、书店等,见到书刊立即封存,并派专人整理、保护。红军攻克兴国、于都、广昌等县城时,共收缴书刊近万册,这些书刊被集中送到瑞金。书的数量已经满足了成立图书馆的需求,但徐特立觉得还必须整理分类。毛泽东听了徐特立的意见,说:“干部群众学文化是当务之急,图书馆应该先办起来,分类可以边干边分,没有的再想办法收集嘛。”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32年6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央图书馆”)在瑞金叶坪村挂牌,并从部队、机关选拔出20多名文化水平高、政治素质强的干部战士,组成图书馆工作团队,徐特立任馆长。
中央图书馆设在一个被称为“熬厅子”的大院里,有20多个房间。大家在整理书籍时,发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书刊中,极少有马列著作和关于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红色图书,难以满足苏区读者的需要。于是,徐特立又向毛泽东建议:“可以动员苏区机关、学校、部队和个人捐赠红色图书。”毛泽东觉得这个建议十分可行,就亲自审定中央图书馆征书启事,刊登在1932年9月6日的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该启示提出:“为着充分给革命工作的参考需要,给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起见,极力扩充内容材料,增加革命图书,向诸位同志及革命团体征求赠书,倘有特别优良图书将出售者,可函知本馆,在可能条件下采购,亦所欢迎的。”
征书启事得到广泛响应,当时,少共(共青团)中央局正准备建立少共图书馆,看到启事后,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以大局为重,决定缓办少共图书馆,将现存的3000多册图书全部捐献;红军子弟小学号召全体师生踊跃捐书,不到10天就收集红色图书900多册……
1932年9月至11月,中央图书馆先后收到社会各界和个人捐书两万多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拨给中央图书馆3000块银元购书专款,徐特立还利用“中华苏维埃钨矿总公司”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钨矿石交易的机会,派人搭乘矿石运输船前往广州、珠海等地采购人文历史、医疗保健、农业技艺等方面的图书5000多册,极大地丰富了图书内容。
二
在对中央图书馆的管理上,徐特立不照搬老经验、旧模式,而是根据中央苏区的社会现状、发展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设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首先,他带领工作团队夜以继日地对全部图书进行整理,分成革命理论、社会经济、农业科普、文化知识等20多个类别,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产党宣言》《劳动经济论》《新经济学方法论》《种子学新编》《农艺学》《成人读本》《识字课本》等数万本图书一册册填写类别索引、书目卡片,供读者查询。同时制定出《管理条例》《阅览须知》《借阅规则》等一系列便于执行、易于操作的规章条例。如《借阅规则》详细规定:“馆存书籍一律外借,有教学、办班、会议等特殊需要可以批量借阅;借阅的个人或团体,须持隶属单位或苏维埃政府介绍信;借阅期限为2周,有特殊原因逾期最多不得超4周;超越规定2周不还者,通知其单位协助追收。”这些硬性条规既照顾到了红军频繁转移还书不便的困难,也考虑到了机关干部经常集体学习,学习资料需要人手一册等特点,深得读者赞誉。
富于苏区特色的图书管理条例、阅览须知、借阅规则都是在没有参照、借鉴的前提下制定完成的,不但饱含徐特立与工作团队的心血和智慧,也为红色政权图书馆建设积累下宝贵经验。5年后的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中山图书馆”,沿用的就是这套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
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图书馆管理团队对图书的收藏和保护也提出严格要求,如“破损的封面、书脊要加包封皮或粘好;不许在书页上圈点批注、折叠;不许散乱存放,要防雨、防潮、防霉、防蛀;每册封面须加盖‘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藏书章”等。
有一次,徐特立去一个村办事,走到一座青砖门楼前,忽然看到院里一群农民正在焚烧一堆书报,他即刻进院喝止。原来,村里正在“打土豪”,农会干部从这家劣绅的库房中搜出许多书报,他们认为书报也没用,便下令烧掉。徐特立急忙找来村农会干部,表明自己的身份,耐心地对他宣讲书报在提高苏区群众文化素质、政治觉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要求把书刊暂存在农会,过几天会派人运走。中央图书馆得到这批书报后,立即进行清理,对破损的旧报纸也不丢弃,把有价值的、完整的文章裁剪下来,分门别类粘贴成册,存放到资料室。
还有一次,从民间征集来一套4册线装古籍《四书句解》,由于年岁久远,古书的订线朽断,许多页码散乱、纸张破损,徐特立带领工作团队用了两天时间,才将书页一张张整理、粘贴完好,重新装订,上架借阅。
三
当时的瑞金没有电影院、俱乐部等文化设施,中央图书馆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天前来叶坪村借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大家三五成群地在图书馆门外围坐阅读。
为方便白天工作繁忙的士兵和百姓利用晚上空闲时间阅读,中央图书馆将闭馆时间延至23时,没有电灯,工作人员就用汽灯、马灯、油灯照明。当年居住在中央图书馆隔壁的谢成福老人回忆说:“‘熬厅子的凳子经常不够坐,读书的人屋里挤不下了,许多人就在厅子外看书。”
1957年,毛泽东回忆自己当年在瑞金的读书生活时,说:“1932年,将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列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就向图书馆和一些同志借。我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矛盾论》《实践论》,其中的思想和观点,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目前我们的宣传鼓动形式,只是限制于传单与标语这些死的文字,而没有考虑到苏区大部分群众都是文盲的现实。应该充分发展‘俱乐部和‘列宁室的读书、讲演工作,吸收群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为落实中宣部的指示精神,中央图书馆组成5个助读小分队,深入苏区各乡、村,协助成立“俱乐部”“列宁室”,组织“读报团”,培养读报团成员既做图书管理员、讲解员,又当识字教员、政策咨询员。毛泽东在一篇调查报告中记述:“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为一圩)读《斗争》《红色中华》《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苏区各乡、村共建起“俱乐部”“列宁室”1656个,有“读报团”1000多个,崇学尚读蔚然成风。
中央图书馆除致力于阅读、讲解服务外,还将“学以致用”作为工作重点。每当中央机关、红军部队、各学校开展政治理论学习、革命教育、知识竞赛等活动之际,中央图书馆都要备齐相应的书籍,供大家借阅、查询。
1932年5月,红一方面军红四军得到情报:国民党一个团兵力准备向苏区发动进攻,必须途经一条长约千米的峡谷。红四军参谋长粟裕仔细观察地形后,命令红一师第二团伏击敌人,并在战前召开二团排、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粟裕手持《战术学讲义》,根据书中对伏击战的要求,一边在黑板上画地形示意图,一边布置迫击炮摆在哪里、地雷埋在何处、架设机枪的位置……有人说这是“纸上谈兵”,但在实际战斗中,每个指战员都清楚自己的位置,知道仗该怎么打,结果大获全胜,歼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械和物资,这便是提升指战员文化水平而带来的好处。
红军总司令朱德曾要求指挥员:“战斗前要多看看书里的战法、战例,虽不能照着书本打仗,但一定能得到启发。”粟裕也说:“管什么‘纸上谈兵‘书上谈兵,只要打得胜,就是好打法!”
四
1933年,经常来中央图书馆借书的毛泽东听到反映:目前国民党对苏区严厉封锁,许多农村干部不知在艰苦环境中如何建设、巩固红色政权,一些地方的农会出现人心涣散、工作停滞状态。
为此,毛泽东深入上杭县才溪乡走访调查,总结出这个乡在土地革命、民主建政、执政为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写出《才溪乡调查》交给中央出版局印刷出版。这份报告极具启发性、指导性、实用性,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央图书馆上架不到3天就被借阅一空。
1933年至1934年,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都是中央图书馆阅览次数最多、借阅量最高的书籍。
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经常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中央图书馆调研,安排部署房舍维修、书架增设、书籍保护等工作,同时鼓励大家要“充分利用图书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斗争策略,增强党在斗争中的领导力和凝聚力,为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提供有力帮助”。
中央图书馆的运作状况、物质条件不但被中央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也得到诸多党政军干部的大力支持。中央出版局局长张人亚经常通过深入走访调查,去了解干部战士与群众都想读什么书、最受欢迎的是哪些书。张人亚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编辑、出版了《三个国际》《“左派”幼稚病》《战术学讲义》《兵器学教程》等政治、军事著作20多种。
《红色中华》主编沙可夫在借书时发现,阅览室里少儿读物极少,于是他深入苏区各学校以及乡村私塾,在孩子们中间走访、问询,用了3个多月时间收集到100多首红色儿歌、童谣,他将这些儿歌、童谣连同自己那些年创作的《帮助红军》《当红军》《爱我中华》等20多首少儿歌曲编辑成《共产儿童读本》和《革命歌谣集》,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平日很少在“熬厅子”中见到的中小学生,也成了阅览室的常客。
1934年2月,刚从上海到苏区出任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得知许多苏区文艺团体计划排演革命题材的戏剧,但苦于找不到剧本,而中央图书馆又没有这类书籍。瞿秋白便到红军部队、政府机关的文艺团体中走访,收集他们曾演出过的剧本。有的剧目已找不到文字记载,他就去找剧作的原作者,如从红军总政俱乐部主任胡底手中,借来他创作的话剧《为谁牺牲》原稿;有的连作者也找不到,瞿秋白就请曾演出过该剧的演员凭记忆一段一段背诵台词,如话剧《亡国恨》的剧本,就是通过演员背台词,逐字逐句记录出来的。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瞿秋白整理并编辑出版《一起抗日去》《杀上庐山》《广州暴动》等40多部(场)的《苏区剧本集》,出版后为各文艺团体提供了排演蓝本,也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图书储备。
1932年至1934年,中央出版局先后出版政治类书籍84种、教育类45种、军事类46种、文艺类36种,为中央图书馆书源和藏存提供了可靠保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前,中央图书馆将藏书全部装箱,送到瑞金高陂村等地隐蔽起来,但后来还是有一部分被国民党发现掠走。1949年瑞金解放后,党和政府开始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中央图书馆藏书,经过2年多的努力,陆续收回图书1429册、报刊300余份以及各种布告、传单、文件、信函等,并编印出《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馆藏总目录》,这些宝贵的史料目前被珍藏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国家图书馆,虽藏书并不丰富,并且仅开办2年多时间,却是苏区宣传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提高军民自身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铺筑出红色政权稳固的政治、文化根基。
(责任编辑:孔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