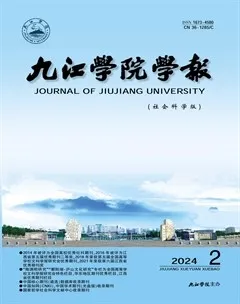抗战时期农民的生存困境与抗争
2024-06-28龚喜林
摘要: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湘黔边区实施征兵、征粮、禁烟、统制汞业等政策以动员更多的资源支持抗战。然而,因各级官吏的徇私舞弊,欺凌横生,国民政府的战时施政严重侵蚀了农民的生计利益。为了争取生存资源,湘黔边区的农民以“不抽兵”“不纳粮”“公开种烟”相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黔东事变”。“黔东事变”中,农民围攻县城,摧毁乡镇保甲地方行政机构,沉重打击了贪赃枉法的官吏势力,并迫使政府修正相关政策以利抗战。但是,“黔东事变”也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动荡。“黔东事变”表明国难背景下战争动员与民力供应之间的紧张关系,诠释了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复杂。
关键词:黔东;湘西;抗争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2-0057-(08)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2.011
1942年8月至1943年6月,湘黔边区的汉、苗、侗各族民众以“不抽兵”“不纳粮”“公开种烟”相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黔东事变”。“黔东事变”以贵州镇远、施秉、松桃和湖南晃县(现为新晃县)为中心,涉及贵州的三穗、台江、石阡、江口、剑河、玉屏、雷山、岑巩、天柱、锦屏、凯里、铜仁、黄平、思南、沿河,湖南的凤凰、芷江、辰溪、洪江等县。事变中,民众围攻县城,摧毁乡镇保甲地方行政机构,震动西南大后方,国民政府调动逾万兵力,“剿”“抚”兼施,最终平息了“黔东事变”。
对于“黔东事变”爆发的原因、过程及善后情况,事变主要处理者、时任第一行政督察专员的刘时范在事变结束后所写的《黔东事变纪要》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1943年6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了1942年大后方民变情况,其中,有六项涉及到“黔东事变”。改革开放后,经过广泛调研并遍访“黔东事变”亲历者,1986年12月,施秉、镇远党史办编辑出版“黔东事变”首辑;1987年12月,黔东南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黔东事变”专辑;1990年12月,铜仁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也编辑出版了“黔东事变在铜仁”专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贵州通史》(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1卷)等著作也都陈述了“黔东事变”的相关情况。在学术研究方面,何长风、欧大荣、石中光等学者叙述了“黔东事变”的全过程,梁家贵、任牧、桑文轩等学者则阐述了同善社与“黔东事变”的关系。在民族赓续存亡的抗战时期,湘黔边区的农民为何发动“黔东事变”?国民政府的战时施政是如何影响农民生计的?如何客观认识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黔东事变”?本文拟利用第一手史料,以战时农民的生存困境为切入点,在湘黔边区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探讨“黔东事变”爆发的原因及其性质,以期对上述问题有一客观认识。
一、战时征兵舞弊及苛虐壮丁造成社会对兵役的恐慌
抗战时期,为了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抗战所需要的兵员,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普遍推行征兵制度,凡是符合兵役条件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如果逃避或者反抗兵役,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为了征兵的顺利推进,贵州实行军师团管区制度,设省军管区主管全省兵役业务,其下辖贵节、安兴、镇独、遵乌四个师管区及贵阳、毕节、安顺、兴仁、独山、镇远、遵义、思南等团管区,由团管区所辖的各县市遵办具体的征兵事务。虽然国民政府构建了一整套兵役法规体系,确立了“平均”“平允”“平等”三平原则,贵州省也颁布了地方性兵役法规,但征兵过程中各级兵役人员的徇私舞弊,以及对被征服兵役者的虐待,造成了社会对征兵的恐慌,减损了农民服兵役的热情。
抗战初期,贵州省征兵实行摊派法,各县将应征兵额摊派到各乡镇,各乡镇摊派到各保甲。各保甲长或由出丁户出钱买人顶替,或者上下其手,贿赂公行,层层剥削,民多苛扰。后来,贵州省实行“三步抽签法”,通过抽签来决定壮丁服兵役的顺序。但是,各县办理征兵抽签极欠公允。在剑河县,凡是与乡镇保甲长有关系者或有钱有势者,或者抽签前贿赂兵役人员者都可以逃避抽签,而被抽中者多是无依无靠的贫苦农民;甚至有的乡镇保甲长专门抽征独子及维持一家生计者以勒索钱财。“现今乡政府办理兵役之方法,即捉拿、监禁、捆缚、押解等。县令一到,即由保长率领乡丁捉拿壮丁、而捉拿又多在夜间,如捕匪然,鸣枪是为,闾里惊骇。”[1]乡镇保甲长为了完成征兵任务甚至使用武力到处拉人顶替,以致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骚然,人民痛苦不堪。
“办理之保甲人员,则以弱者可欺,有利可图,以致有势有力者,纵有应征之子弟,亦公然逍遥法外。而无势无力者,纵系单丁独子,亦难遂其幸免。”“强拉硬派,假公济私,甚至交相报复,或辗转放卖,流弊所及,以致一般农村中之平民,因此酿成空前之恐怖。且有视役政为苛政而猛于虎者,其结怨人民之深,实匪言可喻。”[2]1940年铜仁县征兵,各级兵役人员罔顾兵役法令,以致估拉壮丁、买卖壮丁之事层出不穷。
壮丁被征后所受的苛虐使社会闻兵役而色变。为了防止壮丁逃跑,兵役机关将被征送的壮丁用绳子捆绑在一起,由持枪军警押解,如同押解犯人。壮丁被送入“新兵招待所”后,也被禁闭于一室之内,如同监犯失去人身自由。而从“新兵招待所”转送各师团补充团训练的壮丁,食不饱,衣不暖,生病得不到医治,因饥饿、疾病、虐待致死者众多。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蒋梦麟视察贵州、广西、湖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途经独山、镇远、贵阳,“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踟蹰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3]冯玉祥将军在贵州视察部队情况,“从贵阳到遵义看队伍,新兵穿的衣服破烂极了,都跟叫花子一样。我讲话的时候就栽倒了几个人。我下了台,到新兵跟前一个一个地仔细看,有的把肉皮子冻得发青,有的在那里打抖。”他询问当地士绅对兵役的印象,“这些老先生说,就是征兵的办法太坏,乱捉兵,待遇又不好,他们都痛恨这个办法。”[4]在社会对兵役普遍恐慌的氛围下,应征壮丁逃匿以规避兵役,视兵役为畏途;而狡黠强悍之徒,铤而走险,以武力抗拒兵役。“榕江、下江、毕节各地先后发生之民变,殆有由来也。”[5]1938年春,湖南会同县杨国雄聚集千余人,自称“湘黔边区抗日后援军自卫游击司令”,发动湘黔边区的农民抗兵、抗租、抗粮。1944年3月,都匀县春季征兵,“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壮丁未发出征费,内有独子负家庭生计者,有以公报私者。更有多子不抽,得钱卖放,张冠李戴,搜夺金钱,武力强迫,乱抓壮丁等情况。”[6]都匀民众因憎恨兵役不公而发动了反对兵役的“都匀事变”。
二、战时沉重的粮额负担加剧农民的生计危机
抗战期间,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国民政府加强了在大后方各地征粮的力度。为了稳定粮食来源,减少因物价上涨而对粮食供应造成的冲击,增加财政收入,从1941年6月起,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制度,将田赋由原来征收货币改征实物,农民负担不断加重。黔东和湘西因地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在此驻有大量军队,这些军队的粮食很大一部分仰仗于贵州和湖南供给。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后,贵州省应缴军粮尚差138万市石,贵州省乃实行“以盐易谷”办法,来完成军粮任务。位于黔东的第一行政督察区1941年征购军粮为228900市石,1942年征购军粮则增加到254500市石,比上年增加25600市石。为了田赋征实制度的顺利进行,第一行政督察区规定田赋征实税率为每元折合稻谷两斗,交通不便的县份按每斗折合法币六元的标准征缴法币。其中,镇远等十四县征收稻谷,总计征收137589市石6斗1升;松桃、沿河、石阡、锦屏等县因交通不便而征收法币计3852230.64元。如果将1941年征收的稻谷折合成法币计算,其总额为1940年的35倍。而该区各县农民赖以应急的积谷却微乎其微。据统计,自1936年至1941年止,该区各县积谷仅81720市石,若以该区总人口2066078人计算,平均每人仅有积谷3市升,只够一日的口粮,这与政府征购粮食过多有关[7]。铜仁产粮甚少,只能以特产桐油来缴纳田赋,但因桐油价格低落,农民入不敷出,无力完纳田赋。所以,有的农民因缴纳不出田赋而遭受政府没收桐树的处罚。
“征实完纳手续,农民受苦最深。距离征收机关较远之地之农民,往往因路途遥远,负担所纳粮食至所交纳之地,费时甚多。而又不能随到随征,以至其旅费之消耗,常超过其所纳粮食价值数倍以上。”[8]田赋征实前,农民完纳田赋,只需缴纳粮款即可,而在改征实物之后,农民则需要将粮食挑运到指定地点缴纳。而战时人力昂贵,一担稻谷,动辄需要十余元,路远者三四十元不等,以致运送粮食的人工费用超过应缴纳田赋者有之,稻谷送到交粮地点多天还不能按时收纳者有之。农民所缴纳粮食的价格也远低于市场价,农民因此承受相当大的损失,田赋征实无疑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粮食问题为“黔东事变”之主因[9]。国民政府大规模征粮使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加剧了农民的生存危机。在1941年的田粮征购过程中,剑河县民代表上书贵州省动员委员会请求减免军粮配额,其文如下:
为陈明购办军米困难情形仰祈核准豁免示遵由。
窃于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本县动委会通知,召开讨论军粮会议。关于军粮之筹集,在平时已属重要。值此抗战时期,其需要之迫切,当千倍于往昔。自应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之原则,努力以赴。抑况依照行情给价,又何乐而不为?无如剑河曾于去岁奉令征调民工五千,前往天柱修筑穗靖公路。彼时正值春耕时关,只以公路关系国防交通至巨,不能不忍痛抛弃农事,计征调各级壮丁到段工作者,为时数月。查本县壮丁,计仅八千余名,而征调者过半,以致田多荒芜,收成歉薄。加以黄河水利委员会清水江流域工程处员工数百人,所需食粮均仰给于剑河。又机械化部队暨企业木业公司等先后采购,约在六千大石以上。因之,入夏以还,食粮即告匮乏,环顾剑民,大多挖蕨延命,熬粥过活。近益以旱魃为虐,抗旱作物无望。重重演变,形成米价激增。每米一斗由十元售至二三十元不等,所有一般贫民,食米之未下咽者,一月或两月有余。即向称中产之家,亦多半蕨半米,掺食度日,哀鸿遍野,良用抚然。逖闻采购军粮,莫不咋舌相向。在会人等深知军粮之重要,惟此次摊购军粮四千大包,扫剑河现有之谷米,犹恐不及半额。以故当会议场合,均各噤若寒蝉,呆若木鸡。良以四千大包军粮,为数过巨,辗转筹划,委实无法办到。剑民等对于应征应调,罔敢后人,无如报国有心,筹粮无法。拟恳格外体恤,府准豁免,抑或准俟新谷登场后,再行认购。
谨呈贵州省动员委员会
剑河县公民代表何德、杨傧卿、洪余哉、龚曰三、何宪纲、丁叔仁、丁伯华、吴昌锐、王伯荣、潘定光[10]
全面抗战爆发后沉重的兵粮负担使湘黔边区的民众苦不堪言。“黔东事变”主导者吴宗尧发布的《为除暴安良告民众书》指出“人民负担日重”“民生凋敝已达极点”“天人共怒,有口皆碑。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11]。1939年7月,剑河县保警队队长韦善长在该县南洞司联保催收兵工粮款及区保经费,用残酷手段摧残农民引发众怒而发生农民武力抗征的“南洞司事件”。
三、战时的禁烟侵蚀农民的生存利益
湘黔边区的鸦片种植已有近百年历史,鸦片已成为农民生计的重要来源。民国以后,西南各军阀因争战频繁而大开烟禁,抽收关税以筹军政费用,以致种烟者多,吸食者也多。在贵州,“无论老少妇孺,咸多喜吸食鸦片,即婚丧燕尔,买卖交易,鸦片为招待媒介。甚至男婚女嫁,家长烟枪灯较多之家为中选,吸食者之多,可以想见。”[12]为了消减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戕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开始实施为期六年的禁烟计划。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继续战前的禁烟政策,且抗战时期的禁烟实属必要,具有特殊意义:第一,由于长期吸食鸦片,民众身体孱弱,征选合格兵员困难。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共有32万壮丁,其食鸦片者竟达1/3。出于兵源上的考虑,禁烟也就成为了战时国民政府的一项要政。第二,由于种植鸦片一本万利,“常常种稻田土,仅供一人;改种烟苗,足资十人。烟价昂者,获利尤厚。”[13]而政府的禁烟措施愈严,烟价愈贵,偷种者也愈多。农民因此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而偷种鸦片。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可耕地面积约750万市亩,其中,7/10以上被种植鸦片。为保障战时粮食生产,国民政府需要严厉禁烟。第三,“土匪与种烟是相依而存的。土匪靠包庇种烟的收入而生存,而扩充,而又以其力量包庇或压迫人民去种烟,以是匪烟的关系不可分。”[14]为了稳定湘黔边区的社会秩序,必须肃清湘黔边区的土匪;要肃清土匪,必须禁止种植鸦片以断绝土匪的经济来源。
根据国民政府的禁烟部署,贵州省政府施行四年禁烟计划,从1935年10月开始至1939年10月止为完全查禁烟毒时期。禁烟期间,在城镇,禁止偷运、偷售与偷吸鸦片;在农村禁止种植鸦片。但在禁运、禁售、禁吸过程中,官吏与警察徇私舞弊,营私发财。鸦片一经查获,就以假换真,或者据为己有,或者倒卖;烟贩被捕,出重金即开释,如敲诈不成,即予处死。
战时禁烟措施中禁止种植鸦片对农民生计影响最大。湘黔边区历来为种植鸦片的重要区域,湘黔边区因此成为贵州和湖南禁烟的重点区域之一。“无论任何地方断断不容有一苗一叶一花一苞发现,否则一经查出,不问种者包庇者均一律按法枪决,断不姑息!”[15]为了彻底禁止农民种植鸦片,各县市组织铲烟队查铲烟苗。但是,在查铲烟苗过程中,地方官员巧取豪夺,狼狈为奸,假禁烟之名,行一己之私,致使“禁烟者庇烟,铲烟者分烟。年年禁烟,年年种烟,年年收烟”[16]。面对上级严厉的禁烟政策,湘黔边区的农民大多采取观望的态度,因观望而违农时。“既种而查铲,既铲而再种者有之。查则壅土以掩蔽,查后则揭土以培植者亦有之。”“坐是之故,地多闲旷,民鲜生产,食粮不足,荒象立现。其种而幸得者虽立致巨富,仍难于得食。种而不得,则难免饥寒,铤而走险。”[17]战时严厉禁烟断绝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而政府又无适当的措施来弥补农民因禁烟所受的经济损失,使农民本就十分穷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特别是各地在铲烟过程中各级官吏对农民的苛虐行为激起了农民的愤怒,农民不得不以武力抗拒铲烟。1940年2月,贵州台拱县(1941年并丹江县,改为台江县)保警队在该县第五区黄泡、岑斗寨、小木等地暴力铲烟,烧毁农民房屋,农民因此与铲烟部队发生武力冲突,死伤甚多。1942年3月,由铜仁、松桃、江口三县联合组成铲烟队在三县边区联合铲烟。但铲烟过程中,铲烟队敲诈勒索,纵火烧屋,滥杀无辜,激起了松桃县农民的公愤,松桃农民联合起来武力抗铲。“镇、施十一县之种烟地区,几悉为黔东事变之酵母。”[18]“黔东事变”倡导者提出的“公开种烟”就是利用农民反对禁烟的心理煽动事变。1943年3月开始,发生于贞丰、望谟、镇宁、关岭、紫云、普定等县的“黔西事变”与“黔东事变”一样,也与禁烟官吏的贪赃枉法有关。1944年4月,黎平县铜关、双江等地农民,为反对保安团队烧杀掳掠的高压禁烟手段而酿成了农民攻陷县城、劫持黎平县长和行政督察专员的“黎平禁烟事件”。
四、战时汞业统制下农民生计步履维艰
贵州、云南、湖南、四川是我国汞矿主产地,而湘黔两省汞矿产量最大。湘黔边区汞矿分布于南起湖南新晃县,北至湖南乾城及贵州松桃,绵延几百公里的区域内,主要涉及婺川、三都、丹寨、玉屏、铜仁、松桃、思南、印江、江口、黄平、镇远、省溪、晃县、凤凰、乾城等县。矿厂主要有晃县所属酒店塘、三牛湾、向家地、砂坪,玉屏县属田坝坪,省溪县(1941年撤销,并入玉屏、石阡两县)属万山场,铜仁县属岩屋坪、茉莉坪、大硐喇,凤凰县属茶田、猴子坪,乾城县属雾神寨、麻潘坡,松桃县属鸦砂塘、落塘坳等。
湘黔边区的汞矿开采与冶炼始于明初的洪武年间,原来主要由各省设局或由民间自行开采。近代以后,曾由英法合办的英华公司开采,一战期间,年产量最多时达三四百吨。后来因时局不靖,产量日益衰微。抗战军兴,鉴于汞矿为战时军事工业急需原料,1938年6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管万山场、岩屋坪、大硐喇等地汞矿厂。1939年1月,资源委员会与贵州省政府成立贵州省矿务局和贵阳水银炼厂,统制贵州省内汞矿开采。5月,湖南省成立湖南汞业管理处,负责湘西汞矿开采。
战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汞矿的统制是维持抗战持久进行的必要措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一,为抗战军工生产提供原料;其二,汞矿产品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出口盟国以换取抗战急需的外汇;其三,避免汞矿产品走私落入日本人之手以制造武器。然而,分布在湘黔边区崇山峻岭之间的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汞矿厂,历经几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开采,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成千上万的农民以开采汞矿为生。政府对汞业的统制,无疑剥夺了民间汞矿开采权,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靠拾捡荒砂度日。“汞苗微薄者为之‘荒,一般人民,即将荒石检出提炼,每日收入可四五角或一元不等,故所有田园不愿耕种,而转营此业。”“人民乐此业者当在三分之二以上。”“所谓全人口三分之二以上营汞业者,全系帮工或检荒,每日所入,只勉强维持生活费用。”[19]同时,为了防止汞矿产品走私,国民政府规定民间的汞矿产品只能按照官价统一售卖给政府,否则,以汉奸罪论处;而政府的收购价格却远低于市场价。国民政府对汞矿的统制侵蚀了农民的利益,这自然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湖南省档案馆保存有一张省溪县农民要求开采汞矿以维生计的漫画,其所配文字如下:
省溪县朱砂水银各地都出现,因此数年都是民商办。民商办起都可炼,贫人专靠炼砂来吃饭。不料,矿局来到打破碗,一般民商喊皇天。朱砂水银不可卖,要归矿局卖。如果卖送别人,他说是汉奸。民商喊一天骂一天,有的气心肠断。骂不完,不觉来到一年满,民商游行示威才脱难,仍就把厂办。[20]
另外,丹寨县李双发因汞业统制而致生计断绝,不得不向上级请求救济,其困苦情状由此可见一斑。
贵州丹寨水银矿厂荒民李双发呈请救济案由。
贵州省丹寨县水银矿厂荒民李双发等为生计断绝,呺天作主,救济民命事。窃荒民等既无职业,后无家产,向来生活全靠在水银厂翻检荒砂,日获数钱数两不等。此乃厂主所弃余砂,并请备荒灶自行烧炼,照章上课,稍搏升斗,养活生家。自从水银统制以来,规定翻检荒砂,不准自行烧灶,若检获稍些,必须待上统制公灶方准烧炼。既成水银,又只给每公斤价值法币二十五元,除日食外,得不偿失,窘迫日至。窃思民等,贫苦已极,为生计所驱,乃不惜泥中出,风夕月夕,百耐劳苦,作此下乘活计,养活生家,苟且度日。今一旦受此奇窘,不只驱老弱于陷阱,罹穷民于荼毒。欲改业则苦无资本,欲移徙则无处可归。辗转思维,徒坐待毙。洋洋千言,类若游鱼。处此生路危已之时,救命心急,乃不避斧钺之诛首,呺天乞救之请。请求钧长一视同仁,援救贫苦,准民等仍旧翻检荒砂,给与相当价值,藉此度活。真生死人而肉白骨,生当衔环,死当结草,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呈荒民代表 李双发三十一年二月七日 [21]湘黔边区地瘠民贫,田地稀少,很多农民依赖开采汞矿为生,国民政府施行汞业统制政策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补贴以汞矿为生的农民的生计,这加剧了农民的生存危机并引发农民的反对。
五、动荡不安的环境与崇尚武力的传统催生农民的抗争行为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研究近代华北地区农民的抗争行为时指出,农民的抗争在地理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只有在一些特定地区,才不断地反复爆发。对于这种反复发生的现象,人们必须要仔细研究这种现象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地方环境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黔东事变”的发生还与湘黔边区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及崇尚武力的传统相关联。
湘黔边区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各县县城距离各省省会,近者在八九百里,远者在千里以上,各省政府对边区各县鞭长莫及,政府控制力薄弱,经济文化教育也相当落后。芷江县,“民心顽固,风气未开。妇女缠足蓄发,缠足者约有十分之四,蓄发者约在十分之七,男子蓄发结辫者亦尚有十分之一。”[22]会同县,“民性强悍,好械斗,健讼,但勤朴耐劳,豪侠好义,亦有足多者。”[23]在台江、剑河等县,“不识字的民众实在太多。例如国币到各县使用时,有许多人对上面的数目字也不认识,布告更无法认识,其他一切政令那能说得上有顺利的推行。”[24]
湘黔边区长期游离于政府治理体系之外,边区民众形成了争强好斗、崇尚武力的传统;自清末形成的匪患,根深蒂固,有“兵民匪三位一体”之说。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兵匪相寻,民间之枪支流转既多,恣睢暴戾之风长,往往拥枪自豪,寻仇报复,流为匪类而不自知。因之,社会意识逐渐轻法而重武。”[25]如以县城被土匪攻陷次数而论,镇远县城自1911年至1942年“黔东事变”发生时,先后被攻陷十二次。施秉县城于1921年、1922年、1929年被土匪攻陷。三穗县城于1918年、1923年、1926年被土匪攻陷。1912年,台江县城被土匪攻陷,民间损失甚巨;1924年,土匪再次攻陷县城;1925年和1929年,土匪又先后两次攻陷县城并将县城洗劫一空。“匪患实在是慢性的沉珂,这个慢性的沉珂,那时正以急性发作的姿态表现在湘西。”“在我到任前不久,有龙云飞部发动的‘乾城事变,有吴恒良部的‘革屯军在永绥一带的骚动。”[26]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湘西土匪,“群然蠢动,一时盗贼蜂起,行旅戒途,甚至军用车船亦遭抢劫。”[27]
军阀不断争战、政府控制与治理能力的衰弱使湘黔边区成为化外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湘鄂川黔边区既是抗战的后方基地,又是拱卫陪都重庆、捍卫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湘鄂川黔边区政治社会状况复杂、经济贫弱、交通闭塞。为了稳定湘鄂川黔边区,构筑捍卫大西南和重庆的战略屏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7月,成立鄂湘川黔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加强对边区的控制与治理。绥靖主任公署除清剿边区土匪,维护边区治安外,还配合贵州和湖南省政府在边区修筑公路,开发矿产,整顿保甲,组训民众,改良基层政治等等。同时,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军政部还在湘鄂川黔边区的重庆、綦江、芷江等地设置有第一、第二、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五、第三十二等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兵训练处除接收与训练新兵外,还有监视边区社会治安,维护边区社会稳定的目的。但是,因交通不便,政治力量难以延伸至乡村,县以下行政机构不健全,官员贪腐并欺压农民,国民政府加强湘鄂川黔边区开发、治理与控制的效果甚微。由于湘黔边区长期动荡,一般民众受“草莽英雄思想遗毒,不安分者大有人在”[28]。湘黔边区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上所形成的崇尚武力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黔东事变”发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六、结语
抗战时期,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兵粮税费,由于财政困窘,国民政府却又无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生计保障;加之官吏的腐败、欺凌、压榨与残暴,农民痛苦不堪,湘黔边区农民为了生存群起抗争。“取消苛捐杂税”“派兵拉夫豁免”“军食公买公卖”等口号表达了农民争取生存权益的诉求。董必武1945年3月在延安所作报告《大后方的一般概况》中指出,大后方民变大都是反对官吏贪污舞弊,反对兵役、粮政等办理不善,全是自保性质[29]。但是,“黔东事变”发生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震荡。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1943年5月2日和5日发表《巩固后方》《巩固国内团结》两篇社论,社论指出:“巩固的前线,更有赖于巩固的后方,没有巩固的后方,就难有坚强的前线。”“谁破环后方的秩序和安宁,谁就破坏了抗战,违背了民族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30]1943年6月,周恩来在《关于大后方民变问题致中央情报部的电报》中,分析了民变发生的原因、民变的性质,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民变扩大实乃抗战中不幸,亦由于抗战情绪低落,特务横行,经济困难,政治腐败等等所致。”“而且这多半是自发性的。”“我们对此事来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决不幸灾乐祸。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落后危险性。”[31]
虽然,农民通过武力抗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苦的农民也深明民族大义,他们深深懂得他们的苦难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战时的征兵、征粮、征税、禁烟与汞矿统制等政策是抗战必需的,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农民对所遭受的痛苦与付出的牺牲是可以理解和忍受的。这也正如《巩固后方》社论指出的那样:战时的征兵、征粮,“这些办法都是必要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全国人民应该热烈的拥护,而且也是在热烈的拥护着的。”[32]抗战期间,湘黔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极其困苦条件下,贡献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如修建黄平机场,服务于国防军事工程,保障军粮供应,三穗、天柱、凤岗等县编组志愿兵团开赴前线杀敌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黔东事变”表明了国难背景下战争动员与民力供应之间的紧张关系,诠释了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复杂。
参考文献:
[1]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和军委会政治部派员视察西南各省及协助兵役宣传事宜附视察报告[B].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七七二,目录2,卷宗957).
[2]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四次大会纪录[M].成都:《新新新闻》报馆印刷部,1941:65.
[3]蒋梦麟.西潮与新潮[M].北京:中华书局,2017:391-395.
[4]冯玉祥.我的抗日生活:冯玉祥自传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58.
[5]贵州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M].[出版者不详],1939:78.
[6]陆军炮兵学校政治部呈报贵州都匀因役政办理不良激起民变情形[B].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七七二,目录2,卷宗604).
[7]贵州省第一行政区县政参考资料:第二辑[M].贵阳:贵州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出版年份不详]:72.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22.
[9]财政部贵州省田赋管理处关于抄送松桃县粮政事变问题主因供参考的公函[B].贵阳:贵州省档案馆(全宗M008,目录1,卷宗02883).
[10]贵州省动员委员会关于对剑河县民众代表何德、洪余哉等呈报购军米困难情形以求豁免示遵由[B].贵阳:贵州省档案馆(全宗M005,目录1,卷宗0020).
[11][17][18]刘时范.黔东事变纪要[M].贵阳:[出版社不详],1943:16-55.
[12][13]水深火热之贵州烟祸[J].拒毒月刊,1929(33).63-64.
[14]湖南省政府公报室.湘政一年[B].长沙:湖南省档案馆(全宗22,目录3,卷宗1145).
[15]禁绝烟毒与民族复兴[N].大公报(重庆版),1940-06-02,(03).
[16][31]陈俊杰,傅顺章.抗战时期镇远专署关于铜、松、江三县铲烟部署,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民变问题致中央情报部的电报[J].铜仁地区文史资料,1999(1):49-135.
[19]贵州省省溪县概况一瞥:省溪县社会概况[B].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十一,目录2,卷宗1623).
[20]何玉衡关于汇报调查统制万山各商矿银砂收买情形给贵州矿务局的报告[B].长沙:湖南省档案馆(全宗M121,目录1,卷宗00099).
[21]贵州丹寨水银矿产荒民救济案[B].台北:台湾省史馆(全宗M003,目录010303,卷宗0625).
[22][23]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九服务团.湘西乡土调查汇编[M].沅陵:合利益群印刷所,1940:8-19.
[24]贵州省政府、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联合视察室徐实圃报告“黔东事变”情形座谈会记录[B].贵阳:贵州省档案馆(全宗M001,目录2,卷宗00742).
[25]刘时范.行政督察经验录[J].服务月刊,1940(5):6.
[26]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94.
[27]湖南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湘政二年[M].长沙:[出版社不详],1941:60.
[28]雷山县地方概况调查报告[B].贵阳:贵州省档案馆(全宗M008,目录1,卷宗00282).
[29]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1.
[30][32]巩固后方[N].新华日报.1943-05-02,(02).
(责任编辑 胡安娜)
*基金项目: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农民的生存困境与大后方民变研究”(编号22YJA770007)。
收稿日期:2024-03-13
作者简介:龚喜林(1967—),男,博士,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