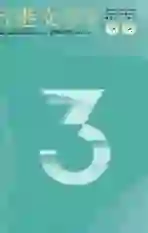花心的代价
2024-06-28杰弗里·阿切尔著陆地
杰弗里·阿切尔(英国)著 陆地 译
世上竟有这么漂亮的人?
那天,我开车去餐馆上班,路过艾得威剧院时,她那靓丽的身影一下就吸引了我。当时她正登上台阶往剧院走去,以至如果我多看一眼,我的车就要吻上前面那部车的屁股了。可是,还没等我来得及再看她,她已消失在熙熙攘攘准备看剧的人群中。
我看准了路边的一个停车位,快速地将车倒了进去。由于与后面一部车靠得太近,那部车的报警器都响了起来。我急急地往剧院门口走去,想立即找到她。但人太多了,要找到心中的她太难了。我在想,即便找到了她,她的身边会不会站着一个身高六英尺像哈里森一样的壮汉呢?
当我走到剧院前厅时,我用目光360度地扫瞄着正在聊天的人群,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我要不要去买一张票?我寻思着。但她有可能坐在任何地方啊,大厅,小包厢,甚至楼上的包厢。或许我该沿着过道去找她。但我知道,除非我有演出票,否则我根本进不了剧场。
不期然间,我看见了她。她正排队站在挂着“今晚演出”的窗口前,而且距离窗口只有一步之遥。排在她后面只有两个人,一个年轻妇女,一个中年男人。我急忙冲过去,排在了他们后面。这时,她已经排到了第一个,我倾身向前竖起耳朵,试图听到她在说些什么。但我只听到售票员回答:“距离开演只有几分钟了,退票真的不好办,夫人。”他说:“但你如果把票留给我,我会看看能否帮到你。”
她谢了,而后向剧场大厅走去。我最初的印象得到了确认,不管你是从头上往下看,抑或从脚后跟往上看,她都是完美的。我深深被她吸引住了。我也发现,前厅很多男人同样被她的美貌打动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真想告诉他们,她是我的,你们别那么色好吗?今晚她属于我!
当她从我视野中消失后,我伸长脖子看了看票房,她的那张票静静地躺在桌子一边。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年轻女郎用信用卡取了四张包厢票。然后,我也终于松了口气。我心中默默祈祷,排在我前面的男人别买单人票,千万别买单人票……
“今晚还有票吗?我想买一张。”那个男人满怀希望地问。这时,演出即将在三分钟后开始的铃声响了。我是该拿小刀刺他的背,还是该踢他的卵蛋,或者干脆臭骂他一顿?我想。
“先生,你想坐哪儿,大厅还是包厢?”售票员问他。
“千万别说大厅!”我心中默念,“快说包厢……包厢……包厢。”
“大厅……”他说。
“我们有一张H排靠走道的票。”售票员边说边在电脑上查寻。我心里暗暗高兴,我知道剧院是想先卖掉余票,再处理退票。可我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前面的男子买到H排靠头的那张票时,刚好我心里的剧本也已经编好了,只要演出时不至于胆怯就行。
“感谢上帝,我想我该不会太晚了吧。都是因为交通,我甚至担心找不到停车位。”我开始背台词,听起来像在自言自语。
售票员抬头看了看我,但对我的开场白似乎并无兴趣。
“我女友可能等不及了,她有没有交给你一张票,希望你把它转卖掉?”
售票员再一次看了我一眼,我的话显然没有打动他。“你能描述一下她的长相吗?”他狐疑地问。
“棕黑色短发,淡绿色眼睛,穿一件红色丝绸上衣……”
“哦,是的,我记起来了。”他拿起边上那张票递给我。
“谢谢您!”我说,但我并没有马上表现出松口气的样子,这只是我今晚整个演出台词中的开场白,演出成功与否,关键还在后头呢。我匆忙奔向大厅,并顺手从票房边上拿了一个信封。
我瞄了一眼票价:20英镑。我从钱包里抽出2张10镑的钞票,放入信封,沾了点口水封了起来。
大厅门口检票员看了我的票,说:“第6排F11号,右手边。”
沿着过道,我慢慢地走过去。她坐在6排的中间,旁边空了一个位子。当我穿过满地的脚丫子走向她时,她转过头向我笑了笑,显然很高兴有人买了她的那张票。
我报以微笑,递给她那个装了20英镑的信封,在她边上坐下。“售票员让我把这个信封给你。”
“谢谢。”她把信封放入黑色的小坤包。当灯光转暗,第一场演出揭幕时,我也开始酝酿我心中剧本的第二节的开场白。我突然意识到,我连今晚要看的剧名叫什么都还没搞明白。我瞄了一眼她放在大腿上的节目单,上面写着《侦探的电话》,剧作者是布里特利。
我记起来了,该剧在国家剧院首演时,媒体上好评如潮。特别是主角格林翰,评论更是一边倒。
我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舞台上。那个侦探正盯着一幢房子,爱德华一家人在准备用晚餐,以庆贺女儿订婚。“我想买一辆新车。”“父亲”弹着香烟灰,对着准女婿说。
当“父亲”说到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停在剧场外的车。是否它会刚好停在双黄线上,或者更糟?我正想着,观众爆出了笑声,我也只好跟着笑了,好让她感觉我也在专心看剧。但我今晚毕竟原定不是来看剧的!到现在,餐馆的人一定都还在奇怪我为什么没到。我知道不到中场休息,我根本不可能离座去看车,或者给老板解释一下我翘班的原因。我可得抓紧考虑我今晚的剧情该如何展开。
精彩的演出深深吸引住了观众,而我一直在斟酌自己的台词,准备在中间休息时开演。我伤感地意识到,我的演出只有15分钟,而且不可能再有第二晚。
第一场结束,幕布降了下来。我对自己的剧本也终于有了信心。观众掌声稍停下来,我即转向了她。
“这是一个原创作品,真的太棒了。”我依稀记得有一篇评论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很幸运,在最后时刻能得到一张票。”
“我也很幸运。”她回答,“我的意思是,这么凑巧,刚好有人要买一张单人票。”
我点点头,随即说:“我的名字叫迈克。”
“我叫安娜。”她说,并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
“想喝点什么吗?”我问。
“谢谢,太好了。”她回答。我起身引导她走往大厅的吧台,并不时地回头,看看她是否跟上,而她每次都回我迷人的微笑。
“喜欢喝什么?”穿过人群时,我再一次问她。
“请给我来一杯干马蒂尼吧。”
“您稍等,我马上回来。”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啊,我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吧台前等候。我掏出五英镑纸币攥在手里,但我前面还排着四个顾客。吧台服务生看到了我的钱,当我拿到一杯干马蒂尼和一杯冰酒时,虽然不想给他小费,但我很着急,不想浪费这难得的机会,还是装着十分大方的样子给了他。我急匆匆地端着饮料回到前厅的角落,安娜正在那安静地翻看节目单。她面向窗户,一袭红色的丝绸衣裳,柔和的灯光照着,她真的太优雅了。我抓紧机会,递给她干马蒂尼。
“谢谢您。”她再一次露出迷人的微笑。
“您怎么刚好买到我的退票?”她饮了一口饮料,问道。
“您怎么又退了一张呢?”我却故意反过去问她。
“我的同伴临时有一台急诊手术,”她说,“医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
“真遗憾,他(她)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我无法肯定她讲的伴侣究竟是女性还是男性。
“是的,”安娜说,“话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我就想去看了,可惜票都卖完了。票太紧张了。后来还是一个好友在最后时刻为我抢到了两张这里的票。”她又喝了一口干马蒂尼,问:“你怎么样?”这时距离第二场开演只剩三分钟响铃了。
“我?”我的剧本上可没有这样的情节呀。
“是的,迈克。”她说,半带开玩笑的口吻,“你在最后时刻是怎么找到这张票的?”
“莎朗·斯通晚上有事被困住了,最后一刻戴安娜王妃告诉我,她愿意来,但她要保持低调。”我回答,“实际上,我读过一些评论,而刚好路过捡了个漏。”安娜笑了。
“你同时也捡了另一个漏—一个女人。”安娜说。这时距离演出只剩两分钟响铃了。在我的台词中,我还不敢如此大胆地写上这样的话,或许,在她那淡绿色的眼睛里,还暗藏着更多的含义。
“是的,当然。”我轻声回答,“那么,你也是医生?”
“也是什么?”安娜问。
“和你伴侣一样。”我说,不知道她是否又在开我玩笑。
“是的,我是福翰的全科医生。我们本来今晚有三个人值班,但只有我能够离得开。你刚才说莎朗·斯通今晚没空与你聊天,只好陪同戴安娜王妃来看演出。这又是什么情况?”
“我在餐馆上班。”我如实告诉她。
“与我相比,那是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更糟的少有的几个行业之一。”安娜说,这时距开演只有一分钟响铃了。
我看着她浅绿色的眼睛,真想对她说,安娜,让我们忘了下半场的演出吧,我知道下半场的戏很棒,但我最想做的是把今晚余下的时间都给你,我不想把这么美好的时光与其他800个观众混在一起。
“你同意我的看法吗?”她问我。
我试图去回忆她刚才的问话。“我期待有更多的人提出意见。”我只能这样回答她。
“我很怀疑。”安娜果断地说,“在医疗行业,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在几天内治愈病人,他们就会怀疑你的医术水平。”
我笑了起来。当我喝完饮料,一个浑厚的男声响了起来:“请各位观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下半场演出马上开始。”
“我们回去吧。”安娜说着,把空杯子放在窗户的边上。
“嗯。”我故意让她走错方向,而后又借机拉她一把。
“谢谢你的饮料。”她说着,朝着我们的座位走去。
“小小的心意而已。”我回答。
但是,她忽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为了这么好的一张票。”我解释道。
她微笑着,我们穿过满是脚丫子的通道。我还想对她再说点什么,可剧场的灯光暗了下来。
在下半场,不管观众是不是有笑声,我都时不时地转过头看看安娜,她偶尔也给我以热情的回应。最大的收获是,在话剧即将结束,侦探向女儿展示一张已经死亡的妇女照片时,女儿尖叫了一声,舞台的灯光突然灭了。
安娜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又迅速地抽回,并向我致歉。
“没关系。”我轻声说,“我刚才也正想做同样的事。”在黑暗中,我不知道她的反应如何。
一会儿,舞台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每个观众都知道肯定是侦探的来电,虽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最后的剧情把全体观众的心纠了起来。
当幕布最终降下时,安娜转向我说,“演出太精彩了,我很高兴我没有错过。更高兴的是,有人陪着我看。”
“我也一样。”我告诉她。我隐瞒了真相,今晚我本意并不是来看演出的。
散场了,夹在人流之中,她和我并肩走着,趁着这难得的时间,交流着观剧的感受,从演员的精彩动作到服装的设计、灯光的运用等等。直到走到剧院门口,我们才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再见,迈克。”安娜说,“谢谢陪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她向我握了下手。
“再见。”我说,再一次看了看她浅绿色的眼睛。
她转身要走,我还有可能见到她吗?
“安娜。”我叫了一声。
她转过身看我。
“如果你没有别的安排,愿意与我共进晚餐吗?”
“谢谢,迈克,我愿意。”
我笑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嗨,安娜,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了。”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高个子、英俊的男人,正在向安娜招手,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是那么显眼。
安娜给了他一个我此前从未见过的开心的笑容。
“嗨,亲爱的。”她说,“这是迈克。你很幸运,他买了你的票,你如果再不来,我就要接受他的邀请,跟他共进晚餐了。”她又转向我,“迈克,这是我先生卓翰,他刚才被医院的事耽搁了,到现在才忙完。”
我不知道此刻如何形容我的心情了。
卓翰握了握我的手:“谢谢您陪我的妻子,愿意跟我们共进晚餐吗?”
“感谢你们的善意,”我回答,“我刚记起来,我还要去一个地方,我得马上走了。”
“那很遗憾,”安娜说,“我很期待听你聊有关餐馆方面的事。也许我们下次还会在哪里再见,当我丈夫不管我的时候。再见,迈克。”
“再见,安娜。”
看着他们坐进出租车,我恨不得卓翰就在我面前摔死,但他没有。我只好往回走,去寻找我停车的地方。“卓翰,你是个幸运的人。”我无奈地自言自语,但没有人注意。接下来蹦出在唇边的一句话是“该死的!”我重复了好几遍。在我刚才停车的地方,现在空空荡荡。
我沿着那条街道来来回回地找。会不会是我记错了停车的地方?我又不确定我的车是被偷还是拖走。然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话亭,我拿起话机拨了999。
“你需要什么服务呢?火警、治安还是急救?”
“治安。”我说。对方立即把电话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
“这里是查林街警察局,请问你是什么情况?”
“我想我的车被偷了。”
“请告诉我车的款式、颜色和牌号。”
“红色福特飞斯达,车牌号H107SHV。”那边电话无声了一阵子,但我可以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在谈话。
“先生,你车没有被偷。”对方警员重新拿起电话对我说,“你的车违规停在双黄线,已经被拖到沃桥车管所去了。”
“那我现在可以取回来吗?”我问。
“当然可以,那你怎么过去?”
“我可以打的过去。”
“那你只要告诉司机去沃桥车管所就行了。到那里后,你必须填一些表格,开一张105英镑的支票—如果你没带够现金的话。”
“105英镑?”我简直不敢相信。
“是的,没错,是105英镑。”
我放下电话,天上下起了雨。我快步回到艾得威剧场门口,希望在那儿拦上一辆出租车。我发现那儿人还不少,无疑他们也是在等车。我竖起衣领,穿过满是缓慢移动车辆的街道,当我到达街的对面,又走了一段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躲雨的屋檐。
我浑身发抖,打了好几个喷嚏,才等到一辆空车。
“沃桥车管所。”我跳进出租车,对司机说。
“运气不好啊。”司机说,“你是我今晚载的第二个,是车被拖走了吧。”
我沉默。
当车在雨中缓慢地往前挪,开到滑特卢桥时,司机开始聊开了。他聊到了天气、市长、英国橄榄球和外国游客等等。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只简单地回应他几句。谈到一些新的话题,他对前景充满了悲观。
到沃桥时,我付给了他10英镑纸币,在雨中等他找零。而后我冲过雨帘,到了一个临时移动房,那儿我遇到了今晚的第二次排队,排队的人比前一次还多。我知道,即使我排到最前面,付了我的罚款后,回报给我的,也不会是什么好的结局。终于到我了,一个警察指了指柜台的表格,我看了说明,第一步要出示我的驾驶证,然后要开一张105英镑的支票给交通警局。我将驾驶证和支票递给他们。那个大个子警员一脸严肃,好像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抓毒品走私犯和偷车者之类。
“你的车在最边上那个角落。”他向我指了指远方,中间停了无数的车。
“我知道了。”我回答,走出移动房,再一次回到雨中。穿过一排又一排的车辆,我不顾脚下溅起的水花,快速地跑到最远的角落,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我的红色福特飞斯达。我觉得这是这款在英国最流行的车辆的一个缺点。我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又打了一个喷嚏。我转动点火开关,但发动机怎么也发动不了,只是不时地发出噗噗的声音,最后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记起来了,当时为一个计划外的安排,太过着急下车了,连车灯都忘记了关,结果就将电池耗尽了。该死的,我连骂了几句,也无法表达我真实的感受。
我看到有一个人走过来,就停在我车的前排,我摇下车窗,可是还没等我喊出“哥们,跨接电线……”,他却开车溜走了。我从车里走出来,从后备厢里抽出我的跨接电线,走到车的前面,打开引擎盖,还是把线接到电池上。在等待下一个人来的过程中,我身上又开始发抖了。
我满脑子都是安娜,但我承认,今晚我唯一成功得到的东西,却是“感冒”。
雨一直在下,我等了几十分钟,有三个人在我面前走过,只有第四个年轻人问我:“遇到麻烦了吗?”我对他作了解释,他把他那辆破车挪到我的车边,打开车盖,把线连接到了他的电池上,然后我发动车辆,发动机终于启动了。
“谢谢!”我大声说道,试了几次发动机,确定它确实可以工作了。
“不用谢,先生。”他说着,迅速地在雨中消失了。
从停车场出来,我打开收音机,听到大笨钟的报时声:午夜十二点。我猛然想起,我今晚没去上班,如果要保住饭碗,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鼻水又流了下来,我决定就以“感冒”为由。虽然这可能是至今为止想到的最差劲的一个借口,杰拉德应该还没有关上厨房吧。
我穿过雨幕,希望在路边找到一个付费电话亭,终于在邮局门口看见了一排三个电话,我停下车跳了出来,但上面贴着一个提示,三个电话已经坏了。我爬进车继续寻找,最后在一个街角找到了一个电话亭,看起来应该没有坏。
我拨了餐馆电话,等了很久才有人来接,是一个带有印度口音的女孩。
“珍妮,是你吧?我是迈克。”
“是,是我,迈克。”珍妮低声说。
“我必须告诉你,今晚你的名字被反复提到,杰拉德手里拿了一把砍牛的斧头。”
“为什么?”我问,“不是还有尼克在厨房帮忙吗?”
“尼克今晚早些时候不小心切了一个指头,杰拉德不得不送他去医院。我只好留下值班。他很不高兴呢!”
“哦,见鬼。”我说,“但我得了……”
“你被开除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另外一个声音,这回可不是小声了。
“杰拉德,你听我解释……”
“你为什么不来上班?”
鼻水又流了下来。我捻了一下鼻子,“我感冒了,如果我今晚来上班,有可能会传染给一半的顾客。”
“会吗?”杰拉德说,“好吧,那总比你在剧院里坐在一个美女旁边会更好些。”
“你什么意思?”我问,任鼻水随意地流淌。
“我说的一点没错,迈克,你知道吗?你真的很不幸,我们有一对常客正好坐在你的后两排,他们和你一样很欣赏那个剧,他们说,和你约会的那个女孩非常迷人。”
“他们肯定认错人了。”我说,尽量不让他听出我的沮丧。
“也可能吧,迈克,但我不,你被开除了。你别想再进来领你的薪水。因为没有一个领班宁愿带着一个蠢女人去看剧而不来上班的。”他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开始臭骂自己,慢慢地向我的车走去。剩下不到几步时,一个男孩子突然跳进我驾驶座,发动了车辆。车摇摇晃晃地开到路中间,发出可怕的擦地声。我追上正在倒退的车,他却立即加速,我知道我追不上他了。
我立即返回到电话亭,再一次报了999。
“火警、治安还是急救?”今晚我被问了第二次。
“治安。”我说,过了一会儿,电话被转接到了其他人。
“这里是巴尔克警察所,你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我的车被偷了!”我喊叫。
“款式、颜色、车牌号?”
“红色福特飞斯达,车牌号H107SHV。”
我不耐烦地等待。
“你的车没有被偷,是你自己违规停放在双……”。
“不,不是的!”我更大声地喊叫。
“我付出105英镑,半小时前才把车取了出来。我刚才在路边打电话时,一个坏小子把车开走了。”
“先生,你现在哪?”
“我在沃瑞克街的拐角这里”。
“车开往哪个方向?”
“往北。”
“你电话号码多少?先生。”
“0812904820。”
“你在工作吗?”
“就像那辆车,我刚刚解雇了。”
“好吧,我们会尽量采取办法,如果有消息,我会尽快联系你。”
我放下电话,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实际上我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维多利亚车站。和前面一个出租车司机不同的是,他似乎对什么话题都不感兴趣。车停下来后,我递给他唯一的一张纸币,他找我一点点的零钱。我嘟嘟囔囔地骂了一两句。用仅剩的几元钱买了张去布鲁利的车票,进站找到了站台。
“你刚好赶上了,哥们。”检票员告诉我,“随时都会没车了。”但我还要在冷雨中等20分钟,在这空荡的阳台上,直到最后一班火车进了站。我的鼻水有规律地一阵一阵地流着。
火车停稳后,我登上车找了个靠前头的位子坐下,又等了10分钟火车才重新启动,又过了40分钟才到达布鲁利站。
又过了25分钟,快到凌晨一点,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到了我那破旧的小屋门前,我开始找钥匙,才记起来落在了我小车上。我已经无力再咒骂了,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我藏在某块石头底下的备用钥匙。到底在哪块石头底下呢?找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打开门,刚踏进客厅,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我抓起了话机。
“我是怀特先生。”
“你说……”
“我是警察,先生,你的车找到了,但……”
“感谢上帝。”我说,没等那个警察说完,“我的车现在哪?”
“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一辆拖车上。那个偷车的小子大约只开了一英里,就撞上了道牙,然后直直地撞到了边墙上。我很抱歉地通知你,你的车完全报废了。”
“完全报废?”我简直不敢相信。
“是的,先生,拖车公司把它拖走了,我们已经把你的电话给了他们,他们明早会联系你。”
我无话可说了。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抓到了那个坏小子。”那个警察继续说道,“坏消息是他只有15岁,没有驾驶证,当然也就没有投保。”
“这不成问题。”我说,“我投了全保。”
“这里有个情况,先生,你是不是把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
“是的,我只是想快快地打一个电话,只要几分钟即可。”
“那么,我认为你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不能得到赔偿?你在说什么?”
“现在的保险政策是,如果你把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你就无法得到赔偿。你当时应该好好地检查一下的,先生。”
我放下电话,寻思着到底还有哪里出了错。我脱下夹克,开始爬上楼梯,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家里的那只母老虎正叉着腰站在楼梯口上。
“莫琳,我……”我开口,无地自容。
“你等下再告诉我为什么车完全报废,”她说,“你先告诉我今晚为什么没有去上班。杰拉德告诉我,你与一个‘骚货一起去了剧院,那女人到底是谁?……”
本辑责任编辑:马洪滔 魏 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