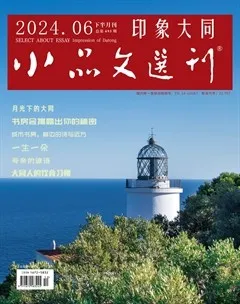唐诗三千人
2024-06-27任晓明
任晓明

最近上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让唐诗又火了一把。盛唐气象自是群星璀璨,万邦来朝。影片通过动画的形式将那个时代的一众巨星串联起来。该片最大的特点是以高适为视角,以李白天马行空的一生为主线,刻画了与之相关的几位诗人名士的华彩人生,也暗寓了诗人名士们的命运。李白与高适,一个是天纵奇才,一个草根逆袭,一个高蹈出尘,一个是循规蹈矩。如果没有那场安史之乱,诗人的队伍里出不了那个官位最高的渤海县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不知当由何人来书写?
作为岐王府里座上宾的王维,与四处干谒的李白都曾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玉真公主。只因她是唐玄宗的宠妹,通过她可以在科举考试中成功突围。历史给了王维优先表现的舞台,一曲《郁轮袍》,换来了第二年进士及第。历史给李白开了个玩笑,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才获得唐玄宗召见,不到两年就“仰天大笑出门去”。王维与李白,尽管很多人猜测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性格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一个独自吟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个聚众狂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真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杜甫曾经是李白的超级粉丝,就像当年李白曾经是孟浩然的粉丝一样。杜甫一生给李白写了十五首诗,而李白赠诗只有两首。李白为孟浩然写下肉麻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可孟浩然好像并没有答诗见诸史料。与王维更为相投的孟夫子是否清楚其中玄机呢,也许只有让我们继续猜测下去。电影中杜甫的人设一如他在诗中描写的那样:“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早年的他也曾四处干谒,却处处碰壁。势移时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悲天悯人让他终而成圣。《长安三万里》应该补录一个镜头,当颠沛流离的杜甫在那烟雨江南里偶遇曾经英姿飒爽、操琴若神,如今衣衫褴褛、卖艺为生的李龟年,四目相对之下,曾经“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长安城何止万里,曾经的“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早已成了他们心头的深深烙印。
中唐的天空依然繁星闪烁,韩愈当是另一个“高适”,不仅仅因为他同样出身草根,也不是二人品级相当,更在于他既是一个“文起八代之衰”师者,也是“道济天下之溺”的楷模,更是一个“勇夺三军之冠”的帅才。如果说中唐谁最有太白气质,答案应该是同样姓李的李贺。自诩有皇家血统的他,仅仅因为父亲的名字,被科举一次次拒之门外,这与商人出身不得参与科举的李白何其相似乃尔!韩愈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不惜冒犯天颜,惹得众怒,只为给李贺一个参与科举的机会,可谓是苦心孤诣,刻意护全。然而天妒英才,那个写下“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天才,那个让人感叹“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鬼”终是没有“报君黄金台上意”,最终“提携玉龙为君死”,时年27岁。他报答韩愈的知遇之恩也许就是用那篇辞藻华丽、想象奇崛的《李凭箜篌吟》,致敬老师的《听颖师弹琴》。韩愈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那些曾经价值千金的碑文,那些气势磅礴、掷地有声的杂说,那331个入脑入心的成语,或许只是他非凡人格的一端。也许只有默默诵读那篇《祭十二郎文》,那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你才会真正理解那个三岁失怙的孩子,那个在荒郊野岭草葬女儿的父亲深潜内心的慈悲与悯怀。“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
说到韩愈就不得不提柳宗元,在唐代那个门第至上的社会,河东柳氏曾经是那么地赫赫扬扬,二十六岁就高中进士的柳宗元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三十二岁进入改革核心圈层,本可以大展宏图,然而,历史的河流有时会为一个偶然事件转变流向,个人命运也会因为另一个人的命运而翻云覆雨。唐顺宗在位不及一年,“永贞革新”戛然而止,柳宗元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少年得志,什么叫盛极必衰。那个“独钓寒江雪”的渔翁,是诗人心境的写照,是他对挚友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呼应,是所有生不逢时的诗人们的宿命。
元白互梦有可能是假的,元白之间的感情一定是真的,就像元稹对亡妻韦丛,如果没有如许深情,绝对写不出穿透千年的三首《悲怀》。而他对薛涛,也只能算是始乱终弃罢了。倒是白居易,除了俗世的爱恋,他的生命底层应该暗流着一股佛家的余脉,否则,他不可能如此高寿。因为他是那么撕心裂肺地思念着他的初恋湘灵,因为他后期沉浸在“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去洛阳旅游,我弃龙门石窟而择香山游,只为那个香山居士。曾经,那是多么诗意的一个名字,多么令人神往的所在。观瞻完毕,我却只能感叹:那已经不是白居易的香山,那是佛家的香山寺,那是蒋中正与宋美龄的红楼。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乐天泉下有知,会在梦中与他的知己互诉衷肠么?
那年在滁州,去往醉翁亭的路上,不经意看到了那个路牌——“西涧路”,心头一惊,这里曾经就是韦应物的西涧么?这就是那句“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的温馨所在么?早年的韦应物有点类似曹阿瞒,斗鸡走狗,横行乡里。安史之乱让他的人生发生急转,失职流落后不到几年,诗名远播,更是写出了“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剖心之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心怀黎民的诗人,一代良臣,死后竟无钱安葬,这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唐朝的悲哀。吊诡的是,悲哀的唐朝事实上消亡在他玄孙的《秦妇吟》里。与祖爷爷的人生大相径庭,年轻时流落长安街头的韦庄,晚年却官至前蜀宰相。早年写出“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的愤青,后来竟是“花间派”最著名的词人。那首“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是他回不去的江南,是对那个前朝的一咏三叹,也是他对祖爷爷的另一种告别。
我以前一直没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的边塞诗人都出现在唐朝早期,那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洒脱,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到了一个朝代的晚期已然沉沦委顿,内向发力最终催生出“小李杜”。杜牧其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军事家存在的,他在二十岁以前写的那些策论,一度是李德裕平叛成功的理论基础,可惜他迟生了二百年,否则隋末乱战,几十位草头王中当多了一位教父级的军师,李唐的江山,“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幸好,他错过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否则,春风十里的扬州,卷上珠帘总差一个牧之,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村里,少了一个个欲断魂的行人。
就像李商隐芜杂的别号一样,他的无题诗纷繁难解。如同生前被裹挟在两党间进退维谷一样,在他死后,对他诗作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他只是一个最深情的人。生在那样一个波谲云诡的时代,连皇帝都是任人摆布的木偶,遑论善良柔弱如他。悲伤的灵魂只能用晦涩的文字,堆砌出一个个多义的典故,力图舒缓心中块垒,却也只能无限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与杜牧一样,他没能活过天命之年,因为他们心系天下,情发于中,一样慨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样苦吟“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倒是晚唐另一位诗人可谓高寿。那是罗隐,一个被毛主席多次提及的名字。一个终其一生科举不第的落魄文人呼唤出了那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个见证了江山兴亡的士子无奈而绝望地苦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那一句:“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是在诉说杜牧之的醉生,还是李义山的迷梦?也许,也是在点化你和我。
诗人已然离我们远去。可那些如椽彩笔刻画出的五岳山川,塑造出的英雄美人;那些低吟浅唱描写的人生百态、心绪万端,那些诗,早已融汇进一个民族的血液系统,化作无穷的精神养分,与日月同辉,与宇宙共存。
选自《剑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