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与重构:海外汉学视域下《诗经》风雨意象研究
2024-06-24胡星雨戴文静
胡星雨 戴文静
[摘 要] 自1887年《诗经》传播海外开始,百余年来海外汉学研究场域中的诗经学研究成果迭出,中西学术对话与相互影响的同时,也面临着两种文化的差异、误解、冲突、融合等问题。研究选取《诗经》中风雨这一类独特的文化意象,检视它的讽喻阐释在西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发现风雨的讽喻性意义在海外研究中逐渐受到削减,后来这类意象成为情感抒发的媒介,承担渲染烘托的功能。由此观之,《诗经》文本的开放视域显化出来,形成了多元诠释空间,这无疑在当时对《诗经》文化发展与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需要引起警觉的是,风雨意象的讽喻性意义依托《诗经》经典文本阅读方式而产生,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海外汉学家对于讽喻及《诗经》经典意义的评判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因此《诗经》海外传译的过程需要在全面认识《诗经》的基础上,建立起《诗经》文化的多元视角,由此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关 键 词] 《诗经》;风雨意象;英译;讽喻;比兴
基金项目:2023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海外汉学视域下《诗经》风雨意象研究”(202310299025Z)。
《诗经》在西方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887年,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从《诗经》中寻找文化宗教认同,将《诗经》带入欧洲人的视野。经过百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在海外逐渐形成诗经学这一门学问,涵盖了关于《诗经》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诗经》译介、文学、语言音韵、历史文化研究等。
在《诗经》的诸多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海外汉学家对意象的阐释与理解。意象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在中西方诗歌中均有较长时间的实践,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审美意蕴。但在《诗经》中,意象的功用并不仅仅在于塑造诗歌美学符号,古人“立象以尽意”,在意象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意义和内涵。动物、植物、器物和其他自然意象在中国经学阐释传统下,以赋比兴手法为寄托,产生了审美意蕴之外的讽喻意蕴。
风雨本是极其常见的自然意象,进入诗歌的叙事文本后,就带有了不同的感情色彩和思想表达,并且在注释文本下还与政治道德教化相联系,带上了讽喻色彩。而海外汉学视域下的意象研究往往忽视或削减它们的讽喻性意义,例如最早研究《诗经》意象的汉学家麦克诺顿(William McNaughton)提出了“混合意象”及其功能,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意象的讽喻性,而是聚焦于意象本身的形象鲜明及其他在诗文中的艺术效果,总结了意象的五种功能:time-shift,emotional complex,intellectual complex,transmutation,praxis and pathos。葛兰言将风雨作为天候,“为情感的表露提供了一个框架或契机”。之后海外汉学界对《诗经》意象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著发现了意象的讽喻诠释,但是聚焦于动植物,鲜有关于风雨意象的研究。并且在当时重象征轻讽喻的文艺理论影响下,研究者往往摒弃讽喻性意义,转而从文学角度解读意象。本文从风雨意象的讽喻性阐释在海外的传达出发,探究意象讽喻性嬗变与重构的具体表现。
一、《诗经》中风雨意象的讽喻阐释
“讽喻是创造文本深层意蕴的重要方式,但丁提出‘诗人的讽喻,强调诗歌在美丽的虚构背后潜藏着真理”。从诗人作诗的角度来看,讽喻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方式,深化了诗之意蕴。而《诗经》虽是诗,但由于生成的历史久远,在不断的流传过程中,诗人及其创作主旨无从考证。这就造成了一种《诗经》“诗无定指”的局面,使其阐释空间被打开。儒家话语体系进入《诗经》阐释空间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该话语体系下的注释家基于社会政治及自身诉求诠释《诗经》,他们“这种政治干预意识和淑世情怀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语境中以‘讽喻来论《诗》解《诗》的传统”。在此释诗传统下,《诗经》文本中的风雨意象就会产生讽喻性意义,具体有以下两条相辅相成的内在生成理路。
(一)建构风雨意象的历史背景
整理《诗经》中关于风雨意象的诗句可以发现,《毛诗序》基本上将每一首诗放置在对应的历史背景下,在阐释中出现大量的历史人物,无一诗无来历。例如在《何人斯》中,写的是关于苏公和暴公之间的矛盾;在《蓼莪》《谷风》中,写的是关于周幽王施行暴政、人民苦不堪言的历史。在朱熹的《诗集传》中,虽然在主旨上出现一些变化,例如《风雨》从原来的乱世思君子变为淫奔之诗,但大部分还是沿袭前人的注释,保留基本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诗经》的传统注释从历史的角度对诗经加以注释,将每首诗都赋予独特的历史意义,以此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而历史的附会作用便在于实施政治教化,在古代中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用史观念使得统治者把历史记录、历史教育当作国家大事来做,从历史中总结规律,用以劝诫教化臣民。
由于历史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以及政教功能,注释家为《诗经》每首诗附上的历史就具有合理性,它们往往带上注释家们对于历史的看法,也就是“美刺”,构成诗歌的主旨。例如《凯风》的主旨“美孝子也”,《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北风》“刺虐也”等,这也体现了郑玄的“美刺观”,他将“美刺”与礼法紧密联系起来,符合礼法的就进行歌颂,不符合礼法的就加以讽刺,其目的都是与王道联系起来,最终实现政治教化。
李玉良在《〈诗经〉英译研究》中总结出“以《诗》附史,喻政宣礼”的特点,同时点眀了《诗经》当时的功能是“美刺的政教功能”。宋儒理学发展对《诗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诗经》宋学发生了从言外‘求圣人之志到‘求诗之本义的转向,但终究没有摆脱道德说教的藩篱,它只是《诗经》经学传统的一种变体而已”。由此可见,在传统“诗经学”下,《诗经》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对其诠释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于意象不可避免会出现讽喻性的阐释。
(二)赋予风雨意象比兴之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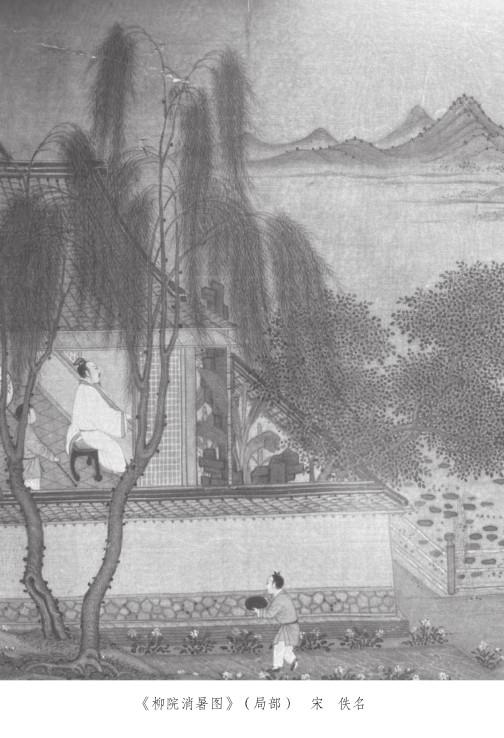
赋比兴是《诗经》中最重要的修辞手法,也是最基本的释诗方式,传统经学家将赋比兴手法广泛运用于《诗经》的解释中。而整理《诗经》中风雨意象有关的诗句,它们的注释大多表现为以风雨起兴,例如《邶风·终风》中以“终风且暴”兴“州吁之不为善,如终风之无休止”;《邶风·凯风》中以“凯风”兴“宽仁之母”;《郑风·风雨》中以“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兴“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其节”。注释家将风雨意象置于比兴传统下,不仅拓展了风雨意象的内涵,也增强了它们的政教意味。因为《诗经》的比兴传统是为政教功能服务的,前有郑玄把赋比兴解释为铺陈政教善恶,取譬言失、取事劝喻的方法,即美刺的手法,后有《文心雕龙·比兴》中的“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将比兴冠以阐发义理的功用。比兴与美刺说教密不可分,在《诗经》传统阐释系统中被广泛使用。这一特点在对风雨意象的解释中尤为突出,如《北风》讽刺卫国施行暴政,百姓苦不堪言携手出逃。这首诗的前两句“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毛诗序》在此处标兴,兼有比兴和譬喻之意。郑笺在此处点明“寒凉之风,病害万物。兴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比兴之意正好对应“刺虐”主旨,北风意象就被赋予一层政治隐喻。这也是风意象讽喻性意义的内在生发机制,就是将意象与美刺比兴紧密相连,达到了“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效果。
由上述可观,在《诗经》的传统注释下,风雨意象具有讽喻性特征。首先是从诗的背景阐释中发现了历史的痕迹,而历史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历史事件的发生伴随着风雨意象的出现,就会给人联想。其次从比兴美刺的手法来看,这些带有风雨意象的诗歌往往通过比兴手法褒扬或讽刺某一政治现象或是历史人物,从而赋予风雨意象在《诗经》注释中的讽喻性意义。风可长养万物,也会病害万物,政令也是如此。而以风或风雨起兴或是隐喻,大大拓宽了风雨意象的含义,但是也给《诗经》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带来挑战。
二、《诗经》风雨意象的英译诠释
上述提到,作为经典的《诗经》文本一直处于被阐释的过程中,所以《诗经》的海外传播不只是《诗经》本身的传播,更是《诗经》诠释系统的传播。
在《诗经》传统注释下,风雨意象以历史背景和美刺比兴为依托,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讽喻性解读。从风和风雨的特点出发,古代注释家通过三种路径为风雨意象进行解释:以大风的特性联想人的性格特征;以风或风雨的动态特点联想社会事件的发生;以风或风雨的自然特征联想社会中的某种规律和道理。依据这三种途径可以对《诗经》风雨意象的讽喻性意义进行分类,分为喻人、喻事和喻理。由于讽喻性意义十分隐晦,加之海外汉学家与中国传统的隔阂,在研究和阐释过程中,对于风雨意象的解读就产生了异变。
本文研究聚焦于海外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诗经》全译本:理雅各(James Legge)散体译本、韦利(Arthur Waley)译本和庞德(Ezra Pound)译本,根据上述风雨意象讽喻性意义的分类,分别为以风喻人、风雨喻事、风雨喻理,汇总出《诗经》中讽喻性风雨意象及其英译诠释。接下来将从这三个分类出发,参酌原文,研究三个译本的译释,探究风雨意象的变异情况。
(一)以风喻人
《诗经》中通过大风的特征映射人物特点有三处,分别为“终风”(《邶风·终风》)、“凯风”(《邶风·凯风》)和“飘风”(《小雅·何人斯》)。“终风”用以讽刺庄公性格狂暴,“如终风之无休止”;“凯风”用以赞美母亲的宽爱仁厚;“飘风”出现在“彼何人斯,其为飘风”的句子中,“飘风”是暴风的意思,用以讥讽暴公性情无常、行如飘风、变幻莫测。三个译本中对这三种风的翻译如下表所示:
理雅各的翻译平实准确,可以看出他遵循了传统诗经学的解读,在翻译和注释中保留了这类风意象背后的深层意义。在“终风”的翻译上,虽说只用了一个简单的词条,不加以修饰,但在注解中指明“终风”为“a metaphorical description of the harassing conduct of duke Chwang”;“凯风”译为“the genial wind”,与下文母亲的性格特点直接呼应;对于“飘风”的翻译,理雅各与其他两位译者不同,他认为“飘风”意为“characteristic of a slanderer”,用“violent”喻指暴公更加明显贴切。
韦利和庞德的翻译并不遵从传统阐释,对意象直接感知并理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到了此类风意象的喻指,两译者将“凯风”分别译为“a gentle wind”和“soft wind”,词汇意义逐渐丰富,文学色彩增强,也可指向下文对母亲的描述。而“终风”在诗文中用于意境塑造和情感抒发。翻译“终风”时,韦利译文中“Wild and windy was the way”“There was a great sandstorm that day”“A great wind and darkness”以恶劣的天气塑造出压抑的气氛,与下文的悲伤情绪呼应起来。庞德将“终风”译为“the end wind”,取“终”为终结之意,也暗示着感情的终结,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下文感情的抒发。
(二)风雨喻事
《诗经》中通过风或风雨的动态特征来联想社会事件的发生十分普遍,在传统阐释中一般都具有褒扬或讽刺之意,例如以“北风其凉,雨雪其雱”(《邺风·北风》)讽刺社会政治纷乱,残害百姓;以“匪风发兮,匪车偈兮”(《桧风·匪风》)暗含当时“周道既灭,风为之变,俗为之改”的现实;以“南山烈烈,飘风发发”(《小雅·蓼莪》)讽刺当时王政的酷虐。接下来选取此类风雨意象的例子在译本中的诠释状况进行分析:
例1:北风其凉,雨雪其雱。(《邶风·北风》)
理雅各:Clod blows the north wind;
Thick falls the snow.
韦利:Cold blows the northern wind,
Thick falls the snow.
庞德:Cold wind,and rain;
North snows again.
风、雨、雪作为常见的自然景物,译者容易感知并翻译出来,并且作为环境描写,在译文中起着衬托背景的作用,但以历史联想而产生的讽喻解读在英译诠释的过程中无法传达,受到了削减和转变。理雅各在注释中点明这两句的隐喻意义:“The first two lines in all the stanzas are metaphorical description of the miserable condition of the state.”其次在译文中以“urgency”指出当时的紧急状况,为风雨意象的联想构建出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隐喻意义得到了保留。而韦利在译文中用“she”改变了原诗的主人公,对象变成一位女子,再与文中“love”“go home”相联系,这首诗的主题由政治讽喻诗变为一首婚恋歌。风雨意象在韦利的译文中,起到渲染环境的作用,达到衬托主人公焦急紧张心情的艺术效果。庞德译文在没有历史语境的情况下,在诗歌首两句构建出“North snows again”这样一个事件,同时丢失了“北风”意象。所以首两句用以描述北方雨雪交加的场景,其实也和韦利译文一样,成为渲染环境和抒发情感的媒介。
(三)风雨喻理
通过风或雨在自然界的变化来联想一些道理,由于社会现实不理想,道理的阐发就出于劝诫的目的,向上讽谏君王,向下教化社会。《诗经》中此类风雨意象有三种,分别为“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劝导夫妻或朋友之间应和谐相处;以“有卷阿者,飘风自南”(《大雅·卷阿》)劝诫君王“当屈体以待贤者,贤者则猥然就之,如飘风之入曲阿然”;以“大风有隧,有空大谷”(《大雅·桑柔》)喻指贤愚之所行各由其性。选取其中一例探究此类意象在译本中的诠释:
例2: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小雅·谷风》)
理雅各:Gently blows the east wind;
The wind followed by the rain.
韦利:Zip, zip the valley wind!
Nothing but wind and rain.
庞德:Soft wind of the vale that brings the turning rain,peril,foreboding.
理雅各的译文表达出“谷风”和雨意象之间相依相随的关系,在注释中遵循传统看法,认为这一句“set forth how friends depend on each other”,与下文朋友的转变形成反差。而韦利对“谷风”意象直接感知,翻译为“the valley wind”,“谷风”指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庞德的译文体现出相似的处理特征,两者皆把“谷风”和风雨意象视为不祥的征兆,天气的改变喻指下文关系的转变和破裂。风雨意象的讽喻性发生了内在转变,由喻理到喻事。并且所喻之事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从而引起译者与文本之间的情感共鸣,在意象的译释上抒情色彩更为强烈,例如韦利译文“Zip,zip the valley wind!”凸显风之强盛,庞德译文将“谷风”与“far in your pleasure,near in your pain”的情感转变直接联系起来。
三、风雨意象在海外传播中的嬗变与重构
在上述三个译本的对比研究中可见,海外风雨意象的译释在不同的译本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蕴含的意义发生了历时性的转变与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经学化到文学化的转变
从整个《诗经》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海外汉学家对于《诗经》的认识有从经学化走向文学化的趋势。李广伟在《诠释学视域下〈诗经〉英语译介研究》中,指出当时理雅各时代的译介风格为“经学化诠释”,置于传统经学下对《诗经》进行翻译和注释。基于这样的诠释理念,理雅各保留了风雨意象的讽喻性意义,译文以忠实性为主,并不重视《诗经》的文学价值,语言注重准确,缺乏美感。在对风雨意象的翻译中,多采用内涵比较简单的词条,句式多用客观冷静的陈述句,感情色彩较少。
随着《诗经》的传播,韦利、庞德时代《诗经》译介风格变为“多元化”诠释。虽说是多元化,却都基于一个出发点,将《诗经》看作是一部文学作品而非文化经典,《诗经》脱离政教系统进入文学视域。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诗歌意象,在海外汉学家眼里具有独特的美学魅力。在对风雨意象的译释中,他们注重对意象的直观感知,同时观照在行文中的表达效果,进行文学型翻译。
意象译释从经学化到文学化,是诠释视角与方式的转变,也是跨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为风雨意象在异文化中意义的嬗变与重构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从讽喻性到抒情性的转变
风雨意象的讽喻性意义是依托传统诗教下,通过比兴手法,引发与下文人、事、理的联想,用于政治教化和讽谏。对于来自西方理论背景下的海外汉学家,他们在无法完全了解诗教传统的情况下,会开拓出不同于传统诗经学的研究视角即文学文化视角,发掘《诗经》的文化价值。以这种视角看待《诗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特点更加凸显,诗歌意象作为内心志趣的主要载体,成为抒发情感的主要窗口。韦利和庞德的译本正是基于文学视角出发,而其中风雨意象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从讽喻性到抒情性的转变。在喻人、喻事、喻理三类讽喻性意义中都体现了这一变化,译者在翻译时倾向于将风雨视为恶劣的气候,与下文主人公的情感呼应起来,用于诗句开头的风雨意象就达到环境描写和情感渲染的艺术效果。
四、风雨意象嬗变重构背后的反思
《诗经》风雨意象嬗变与重构的背后,体现了19至20世纪海外汉学对《诗经》认识过程的深化,对《诗经》的解读走向多元化。《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文本之一,在古今和中外交流中一直处于阐释与再阐释的过程中。“《诗经》之所以在中国传统中保持其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具有阐释开放性的一部诗集”,而海外汉学家对风雨意象解构重构的过程,正拓宽了《诗经》的诠释视域,使文本开放性显化出来,这无疑对《诗经》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深入挖掘对讽喻意义的解构重构,其中体现出了一种倾向——对《诗经》经典意义评判的失衡,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理雅各时代,《诗经》的海外研究不关涉讽喻。因为当时《诗经》处于经典地位,它以“中国经典”的面貌传播到海外,《诗经》的讽喻阐释传统在海外汉学家的认知图式中是存在且合理的,“在东西方经典评注传统中,这种阐释方法经常出现”。理雅各的翻译大量参考《诗经》传统注释,体现出经学化色彩,“这种学术翻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是中西方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在经典诠释体系下生发的讽喻性意义,自然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研究对象。
但《诗经》不断传播的过程中,许多新兴思想进入《诗经》文本研究,《诗经》的面貌也在不断改变,但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诗经》的经典意义,体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趋势。20世纪后,海外汉学界关于“讽寓”研究开始出现,但“这个词绝不是褒义的术语”,因为“长期以来被当作经典的《诗序》在《诗经》新版本中消失与它开始被认为具有‘讽寓性同时发生应该不是个偶然现象。这两件事俱导源于对古典传统的价值重估,它的后继影响仍左右着我们”。自讽喻研究出现后,海外汉学家多用于批判《诗经》传统注释方法,例如葛兰言、韦利、王靖献等,认为这“既曲解了《诗经》的渊源特点,也从总体上曲解了‘诗的原始定义”。还有的汉学家认为《诗经》的解释传统“对于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具体诗歌的解释史,这类批评之作的力量不具普泛性;因此,西方读者很难接近它们”。基于这些认识,他们在《诗经》译介上就削减了意象的讽喻性意义,而从“诗”的角度去诠释诗歌意象,并且还找到了一种更“普泛”的释诗视角——从情感的角度重构意象意义,以此促进《诗经》的传播与接受。
由上述可观,讽喻性意义不断削弱背后体现着《诗经》面貌的革新,这是《诗经》文化的更新与进步。但是这一过程中却体现了汉学家厚此薄彼的态度,他们致力于寻找更符合《诗经》的原义,即它的文学文化意义,而斥责讽喻为“过度阐释”“胡乱对应文本与注释”,这对于《诗经》经典意义的评判是失衡的。将讽喻阐释放之当时中国历史语境下,它的产生与应用有其合理性与生命力。讽喻解诗的传统维护了《诗经》的经典地位,使《诗经》符合当时政治社会的诉求,对于规范社会上下等级以及等级内部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诗经》作为经典的意义。
五、结论
《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经典,在海外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研究。而以风雨意象为例,这一特殊的文化意象以及它所代表的讽喻性阐释,在海外汉学研究中从经学化走向文学化,从讽喻性走向抒情性。《诗经》文化和异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开始从政治走向文学,从庙堂走向世俗,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而是展示中国古时风俗面貌的美丽诗集。它以开放的姿态,邀请每一位读者阅读欣赏,做出不同的理解。不止是风雨意象,《诗经》中许多动物、名物、植物意象,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进行欣赏与品鉴,建构起《诗经》文化的新视角。
在《诗经》的对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诗经》历史悠久,在传播上拥有着广阔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这也促使《诗经》多元意义的生发,但每一种意义放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都有其合理性,包括讽喻意义、文学意义、文化意义,而对《诗经》跨历史语境的审视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意义评判上的失衡。所以这启示我们在建构《诗经》文化的新视角同时,更要对其进行整体关照,辩证地看待《诗经》古今演变历程,将它的古典价值和现代价值统一起来。彼此的割裂不足以全面认识《诗经》,更不能准确传达出《诗经》的多元意义。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的共融,才是《诗经》传播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诗经[M].王秀梅,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
[2]Waley. The Book of Song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6.
[3]Ezra, Pound. The Classic Anthology[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59.
[4]Legge, James. The She King[M]. Hongkong: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Willam, McNaughton. The Composite Image: Shy Jing Poetic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3,81(3):92-106.
[8]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9]姜智芹.一切评论都是讽喻的阐释:《欧美文学的讽喻传统》评介[J].山东社会科学,2023(8):2.
[10][美]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M].卞东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1][美]顾明栋.诠释学和开放诗学:中国阅读和书写理论[M].陈永国,(美)顾明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2]代婵.《诗经》阐释的“讽喻”与“讽寓”研究[D].南充:西华师范大学,2021.
[13]李广伟.诠释学视阈下《诗经》英语译介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1.
[14]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J].文艺理论研究,2021,41(1):1-14.
[15][美]吴伏生.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16]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M].谢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17][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