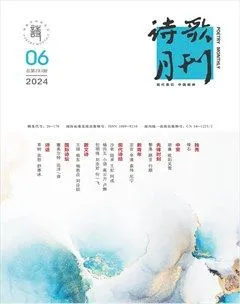语言学意义上异乎寻常的激光
2024-06-24草树
从山水诗到人工智能,实现诗的穿透,需要怎样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激光?这种激光当然不是物理学的,而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它的生成,首先需要对山水诗或山水诗蕴含的古典美学和人工智能的当代征候,具有深刻的理解。中国古代山水诗蕴含的诗歌美学是一元论的,物我交融,托物言志,更高级的哲学在道统一脉,齐物归一,物物而不物于物。经历了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洗礼,我们发现以突出自我意识表现的现代诗歌,有着强烈的“立法”倾向,以我为主,唯我主义,二元对立,是二元论的,没有古代诗歌美学那样一种谦逊和松弛:平等看待万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它表现在语言形式上,是一种情境,是独立自足又开放敞开的语言组织,具有开放性和多义性;它打破词与物的同一性,不是通过意象的晦暗实现诗性表达,而是将诗意蕴含在一个语言结构的空间形式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倡导诗歌回到个人,回到日常,回到语言本体,其本质也是要破除上帝本体论和本质主义,打破现代主义的唯我主义和将世界对象化的倾向,或者说去中心化,去浪漫化和形而上学,建构一种以日常和感官为本体的诗学。它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其实是与古典主义可以秘密接头的。但是环顾当下,现代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留下的各种古怪病症,已然进入无数诗人的思维和意识之中。
人工智能意味着人类从几千年以来生存的三维空间变成了四维。这多出来的一维是一个数字空间,无论我们称之为“云”“元宇宙”,还是别的什么,总之是一个虚拟空间,独立于三维空间以外又切实存在。它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处境,无疑会形成巨大的影响。美国有一部科幻片《西部世界》,描述了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人和AI(机器人)的相处场景,人的欲望可以在那个机器人世界尽情释放,无论杀戮还是色情,但是当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就对人类形成反噬。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伦理和精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诗人何为?这是我们这一代诗人面临的问题。诗人致力于自我的辨析和塑造,为人类的精神寻找原乡,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切不再是建立在一个三维空间,而是包含一个更为虚幻的数字空间,未来的未知或已经到来还不为人们认知,带着微微的恐惧。我们只要设想一下一架隐形六代机带着大批蜂群般的无人机扑向某个区域,未来战争的场景将颠覆人类的想象——远不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能参照,而是不可想象的。人工智能的最大危险在于恶性竞争导致技术和伦理标准的失范,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带来毁灭性的战争。特别令人忧虑的是霸权主义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思维,它在意识形态上和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如出一辙。人类对人工智能保持恐惧、忧思和谨慎是必要的,尤其对于诗人来说,不是作为先知,至少作为“战斗”在语言的前线的“战士”,理应更敏感,以灵敏的鼻子嗅出未来“敌人”的恐怖气息。
诗人当然不能改变什么。诚如谢默斯·希尼所说,诗歌不能阻止一辆坦克的前行,但是诗歌是一种更为远大的政治。对于诗人来说,山水诗给我们的启迪是敬畏自然,道法自然,平等看待万物,与万物构成一种心灵对话,从而让人类在大地生根、栖居。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始终不能化解非此即彼的困境,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但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以来,西方这一人文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人和作家的观念,但是文学对世界和人类现实生活的影响,有一个滞后的过程。从最近几年中美的地缘政治激烈冲突的现状看来,西方的唯我主义是很难在短时间改变的。但是我们由此反观自身,却发现几代诗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在诗歌写作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本质主义和唯我主义的倾向,而将山水诗蕴含的观看世界的方式乃至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弃如敝履,倒是墨西哥大诗人帕斯早就发现了中国古典传统世界观的高级,他在讨论现代主义非此即彼的困境时引用了庄子的《齐物论》。他很惊讶地在庄子那里发现,此和彼之间嵌入了一种相对论的观看世界的方式,“此”中还可以生出“此和彼”,“此和彼”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此和彼”最终是依循于“道”(帕斯《弓与琴》)。无独有偶,美国哲学家乔治·斯坦纳发现佛教和道教中,通常是以逃离言词的方式,比如崖洞里的苦修,通过悟道,“直抵愈加深邃的沉默,‘思的至高境界是‘廓尔忘言……在‘大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诗人翟永明在她的最新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有一组诗书写人工智能和当下关系,其中《德洛丽丝的梦》中的德洛丽丝是美国科幻电视剧《西部世界》的女主角,也是同名大型游戏中的机器人。与科幻和游戏人物对话,我们不妨理解为当下和未来的对话。机器人有一天获得意识,反过来奴役和屠杀人类,它除了表现出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担忧和世界末日的可能图景的想象,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省察当下的未来维度,就像历史意识对“此时”的穿透一样。当代诗理所当然要在写作中贯彻这样一种当代性的观念,同时也基于当代诗人普遍具有的共识——语言即存在,或写作即写语言,因此德洛丽丝作为一种语言(电影或游戏)存在,完全可以在某个特定维度上实现沟通和理解的可能,尽管是个人化的,但是这种个人化的对话为人类看待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维度。《雪豹的故乡》以一张长桌上的雪豹一家五十万张照片和菲力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起兴,展开了时间之思,现实和梦境,现在和未来,在此有了重叠的可能,即叠合在日历上。日历是时间的象征,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的地区的空间之别,在此获得了某种时间性,也许若干年以后像吕玲珑这样的摄影家已经拍摄不到雪域高原的雪豹,一切都被一个仿生世界取代,那么仿生人又能否梦见电子羊?而按照人类现有观念,仿生人当然是没有情感和意识的,当然也就没有梦,而对于有梦的人类,在梦之外又是否依照《西尼目录》的价格确认存在?总之诗人在这里比起藏地摄影家对环境保护和动物生存的关注,有更深一层的时间之忧。未来每一天都在变成当下,也许由于某种加速度,或许会发生未来和现在的叠合,就像雪豹(过去或记忆)和电子羊(未来)叠合在一张日历上(现在),它体现的当代性不足为奇,但是让不同时间维度的叠合在空间实现,则不啻是一种敏慧的诗意发现,也不妨说是一次诗的穿透:极地雪域的雪豹和电子羊有了一次会面,一次在日历上的叠合。《雪豹的故乡》(节选):
长桌的一边摆放着日历
吕玲珑拍摄的雪豹一家:
雪豹爸爸、雪豹妈妈、雪豹崽崽
近50万张高清晰度的珍贵胶片
构成庞大的藏地密码
山、水、冰峰、峡谷、
花卉及原住民
还有花丛中的雪豹一家
长桌的另一边
是菲利浦·迪克的书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昨晚 我梦见高原上跑的雪豹
我是仿生人吗?或它是电子雪豹
在梦中没有分别
但是《西尼目录》中动物都有标价
在未来式中价格才能判断原住民
电子动物以及仿生人的真假
人工智能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没有人能够阻挡它的到来,也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机器人时代人类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无论机器人以更高级的形态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威胁人类的基本伦理;或机器人进入军事领域,成几何倍数增加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的可能,对于诗人来说,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是在语言上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人类对待矛盾、竞争和利益的态度,因为语言会渗透到人的思维中并最终影响人的行为。诗人清醒的声音无论多么孱弱,它就像细雨,由于诗歌内在的超越性也使得它更能沁入人类的心灵。当扫地机器人听从人类的指令开始打扫时,它的一声“开始打扫”之后,其嗡嗡声给主妇带来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它就像“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那种惬意。人工智能时代无疑会解放人类的身体,释放更多的闲暇,当然也不排除会带来更大的精神困境,但它需要的不是排斥——事实上也无人能阻止,而是以一种一元论的世界观和谦逊的态度,去规范它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边界。与机器人相处,就像山水诗中的诗人与自然,山水诗蕴含的古典世界观,有助于当代诗人发现与机器人或AI的相处之道。没有哪个“时刻”或“当下”是绝对孤立的,排除过去和未来的“活在当下论”,本质是一种虚无主义。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是人类的精神困境所在,迟早会得到诗歌的教育并从中受益。诗歌之光穿透从山水诗到人工智能的某个晦暗的空间,那样,我们就又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汇聚在此时此地的某种关联性之中。
草树,本名唐举粱。著有诗集《马王堆的重构》《长寿碑》《淤泥之子》和诗学随笔集《文明守夜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