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桃花园序》与《姑熟亭序》的两重对读
2024-06-17海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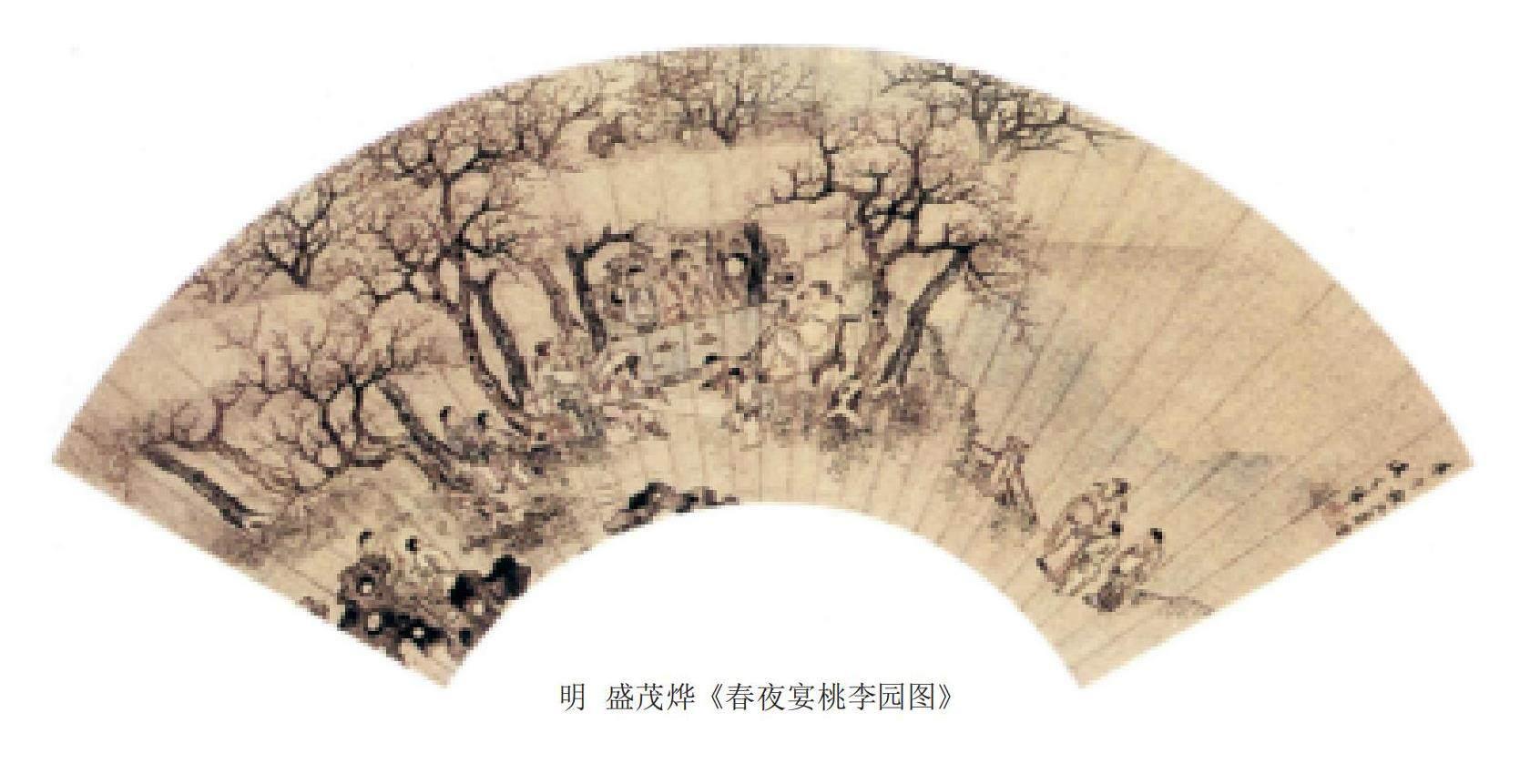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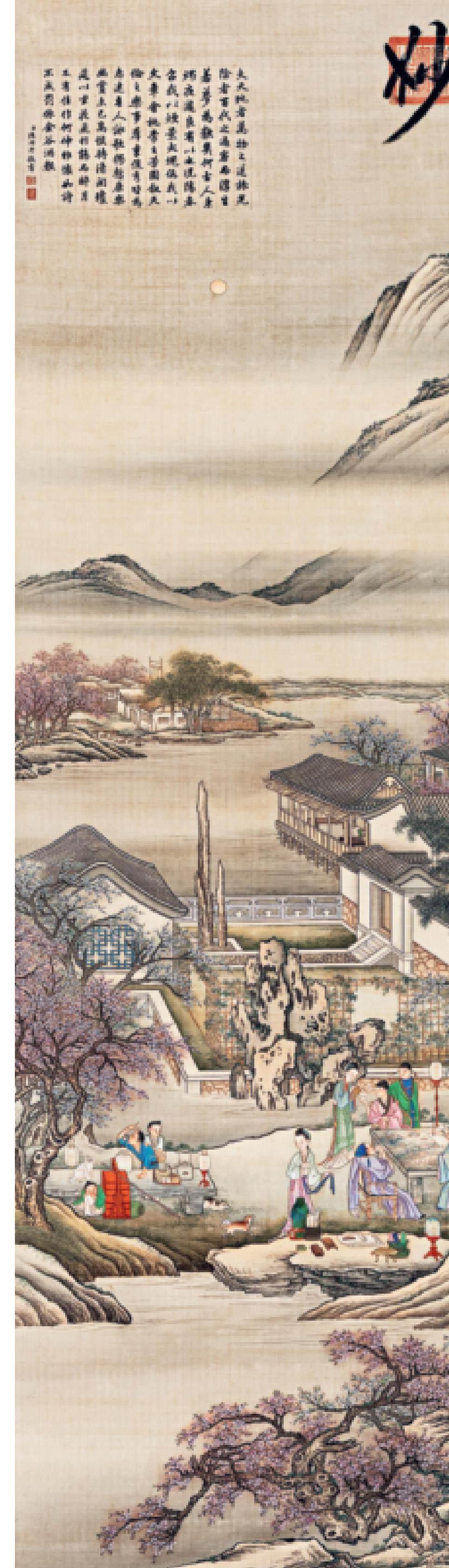

对读李白《桃花园序》与《姑熟亭序》,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两个变化:就文体发展而言,出现了从虚笔纵横的雅集诗序到言之凿凿的胜概事记的转变;就文章主旨而言,出现了从『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到『名教之内自有乐地』的本质性升华。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简称《桃花园序》)大约创作于唐开元后期,同期尚有《愁阳春赋》《惜余春赋》;《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简称《姑熟亭序》)大约创作于天宝后期,同期尚有《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赵公西候新亭颂》。结合这两个时期李白的人生遭际、人际交往与思想情感,联系创作于同时期的诗文,对读李白《桃花园序》与《姑熟亭序》,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两个变化。
从雅集诗序到胜概事记
就文体发展而言,这两篇文章出现了从虚笔纵横的雅集诗序到言之凿凿的胜概事记的转变。《桃花园序》类似王勃《夏日宴张二林亭序》,四六成文,典故迤逦,借虚笔烘托园林之美、雅集之盛,更多发挥着诗集之序的功能。
李白《桃花园序》全文如下: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像王勃《夏日宴张二林亭序》这样的文章,《全唐文》里收录的王勃及其他初盛唐文人的类似文章还有很多,我们仅以此篇为代表,借以对应解读《桃花园序》。言及宴饮环境,王勃曰“林亭旷望,季伦调伎之园;泉石周游,子晋登仙之浦。舟浮叶影,簟积花文。黄鹊度而飚惊,丹乌倾而日晚”,李白曰“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言及美酒,王勃曰“香杯浊醴”,李白曰“羽觞而醉月”;言及座中客,王勃曰“胜侣”“神交”,李白曰“群季俊秀”;言及作诗以纪胜,王勃曰“共题横吹之篇,用记兹辰之乐”,李白曰“不有佳咏,何伸雅怀”。这几组文字,若将李白文和王勃文互换,基本不影响各自的表达,甚至李白文章中的“罚依金谷酒数”和王勃文章中的“季伦调伎之园”都指向了同一位典故的主人石崇。之所以两人的文字能互换,典故能通用,一是因为二者表达的内容高度相似,二是因为二者是虚指而非写实。
但是,到了《姑熟亭序》,我们则看到李白以近乎实录的文笔叙写时间、地点、人物,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提炼雅集的主旨深意,更多体现亭台楼阁记的功能。
《姑熟亭序》全文如下:
通驿公馆南有水亭焉,四甍翚飞,巉绝浦屿。盖有前摄令河东薛公栋而宇之,今宰陇西李公明化开物成务,又横其梁而阁之。昼鸣闲琴,夕酌清月,盖为接轩、祖远客之佳境也。制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马武公长材博古,独映方外。因据胡床,岸帻啸咏而谓前长史李公及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称为姑熟亭焉。”嘉名胜概,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绂冕者,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云,逍遥偃傲,何适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所以司马南邻,当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挥辞锋以战胜。名教乐地,无非得俊之场也。千载一时,言诗记志。
序文首先描述姑熟亭的位置—“通驿公馆南有水亭焉,四甍翚飞,巉绝浦屿”。接着回顾姑熟亭改扩建工程的历程—“盖有前摄令河东薛公栋而宇之,今宰陇西李公明化开物成务,又横其梁而阁之”,并介绍其堪当迎来送往的文化功能—“昼鸣闲琴,夕酌清月,盖为接轩、祖远客之佳境也”。然后引出主人公司马武公为此亭命名的雅举—“司马武公长材博古,独映方外。因据胡床,岸帻啸咏而谓前长史李公及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称为姑熟亭焉”。文章写到这里,几乎是一篇高度写实性的亭记,后半部分则赋予了姑熟亭更为厚重深远的意蕴。
李白在同一时期代宣城太守赵悦起草了一封致宰相杨国忠的书信—《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可见李白与赵悦关系之特殊。此外,李白又为赵悦建亭作《赵公西候新亭颂》。这篇文章分两部分,正文是一篇极其详尽的亭记,结尾是一段篇幅不长的“颂”。
文章首先充满敬意地详细回顾了赵悦的仕宦经历与德政嘉范,交代了天宝十四载(755年)赵悦在宣城任太守之后的政绩—“至于是邦也,酌古以训俗,宣风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镇唯静,画一千里,时无莠言”。然后分析宣城重要的地理交通优势—“此郡东堑巨海,西襟长江,咽三吴,扼五岭,轩错出,无旬时而息焉”,以及恶劣的设施条件和环境—“疾雷破山,狂飙震壑,炎景烁野,秋霖灌途。马逼侧于谷口,人周章于山顶。亭候靡设,逢迎缺如”,再阐述历任长官的不作为—“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数,因循龌龊,罔恢永图”。进行上述铺垫后,浓墨重彩地叙写赵悦是如何观风相地、损益营造,完成了泽被一方的建亭工程,并描述了亭子的壮观—“若鳌之涌,如鹏斯骞。萦流镜转,涵映池底,纳远海之馀清,泻莲峰之积翠。信一方雄胜之郊,五马踟蹰之地也”。接着笔锋一转,胪列共襄盛举的当地官员如长史齐公光乂、司马武公幼成、录事参军吴镇、宣城令崔钦,其中司马武公幼成正是姑熟亭的命名者、《姑熟亭序》的主人公,并赞扬了他们“纵风教之乐地,出人伦之高格。卓绝映古,清明在躬”的人格品质。最后,自然过渡群僚请颂、李白捉笔的为文缘由。这篇《赵公西候新亭颂》堪称《姑熟亭序》的扩写版。
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纵目考察,可以从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发现《姑熟亭序》与《赵公西候新亭颂》的文章脉络,也可以发现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与《姑熟亭序》在文章经营方面的相似性。
从“为欢几何”到“名教乐地”
就文章主旨而言,这两篇文章出现了从“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到“名教之内,自有乐地”的本质性升华。
《桃花园序》的开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与王羲之《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表述相类。其“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感慨与汉乐府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以及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几乎是一脉相承,更与李白《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情绪相一致。
《姑熟亭序》与《赵公西候新亭颂》则不约而同地提及“名教乐地”。《姑熟亭序》中写道:“且夫曹官绂冕者,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云,逍遥偃傲,何适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名教乐地,无非得(德)俊之场也。”对于曹官绂冕者,外形有限但内涵丰富的姑熟亭是一个鉴别人物德行的特殊场域:如果是大贤处于亭中,就像漫游青山、高卧白云一般,逍遥偃傲,悠游自在,无往不适,何适不可,亭中天地无穷无尽;如果是小才处于亭中,则逼仄窘迫,自拘行迹,身心仿佛戴上了枷锁,精神失去了格局,即使面对清风朗月、河英岳秀,也丝毫无感,江山变成了弃物。而“名教”恰如这姑熟亭,无德的小才居之,自缚手脚,苦不堪言;有德的贤士大夫居之,则是无边乐地。
李白《姑熟亭序》隔代阐发《世说新语》中乐广“名教中自有乐地”的思想。无独有偶,其《赵公西候新亭颂》在叙议诸公共襄建亭盛举时,也有“纵风教之乐地,出人伦之高格”之语。很明显,“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和“名教之内,自有乐地”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欢乐,我们在充分肯定两种欢乐美美与共的同时,也不能不正视其区别。借用李泽厚先生《美学四讲》的说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乐,更多停留在悦耳悦目的感观表象审美层次,而“名教之内,自有乐地”之乐则更倾向于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心灵、情志、精神等内在审美层次。从“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到“名教之内,自有乐地”,李白实现并表达了一种本质性的思想升华。
显而易见,这种变化与《桃花园序》诞生于亲族天伦欢会,而《姑熟亭序》写就于贤士大夫雅集的创作语境有关,同时,这也与从开元后期到天宝后期李白的思想情感的发展变化有关。尽管其“已将书剑许明时”“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伟理想是一以贯之的,但开元后期的李白并未实际接触权力中心,未能深刻认识政治现实。此时,李白的自我更像是一个小我,自然本真地左突右奔,抢天呼地。而天宝后期的李白经历了三年供奉翰林,体验过天子身边月下独酌的痛苦,目睹了朝廷政治倾轧而悲愤写下“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他北上幽州一探虎穴,西走报忧无果而终,只能再次南下疗治自己遭受重创的内心。此时的李白,其自我是融入了深刻丰富的现实体验和忧愤深广的现实关怀的一个大我。
李白将从小我到大我的人格变化投射到文学创作中,才呈现出从“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到“名教之内,自有乐地”的巨大变化。这种本质性的深层次的思想升华,我们也可以从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的总结、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以及欧阳修《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寄寓中读到回应的影子。
海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