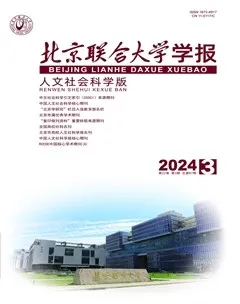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历程、取得成效与未来展望
2024-06-16张耀军陈芸
张耀军 陈芸



[摘 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经过10年来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在科技创新、空间布局、生态保护、对外开放、民生领域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创新转化能力不足、产业转移承接断层、“过密过疏”现象突出、生态联合治理及生态补偿机制有待完善等挑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一目标任务,应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空间功能布局,以新质生产力为协同发展的新引擎,让数据要素成为协同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关键词] 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F127;F124.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4)03-0073-12
一、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协同发展是京津冀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前提。协同发展是一个“博弈—协同—突变”的非线性螺旋式上升过程,这一过程使得城市间联系趋于紧密、分工趋于合理、发展差距趋于收敛、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最终实现区域规划、交通、产业、市场、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全方位协同发展的共同体[1-2]。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3],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指向。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紧密联系,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和实现途径,高质量发展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4]。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研发创新、生态环境、区域开放、民生福祉等领域,区域间合作不断加深,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深层次、全方位协同,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失衡、环境制约区域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5]。
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超过1亿人,经济体量超过10万亿元,在全国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中占据8%的比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①。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6]新时代新征程中,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不仅对京津冀自身,而且对其他大城市群乃至全国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升竞争力都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历程
(一)三地政府主导的合作初探阶段
1981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5个省区市联合成立了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这是第一个包含京津冀的区域合作组织。1986年,河北提出“环京津”战略,天津提出环渤海区域合作,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成立,是当时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2004年,环渤海7个省区市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辽宁7个省区市。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区域合作机制从构想推向了实践。2006年,北京和河北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2008年,天津和河北签署合作备忘录,京津冀合作迈进更具实质性的阶段。
这一阶段,京津冀区域发展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三地协同发展逐步从概念层面向实质性的合作阶段迈进,但尚未形成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三地寻求合作的积极性也存在一定差异[7]。
(二)中央顶层设计的协同发展阶段
2011年,“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对三地协作提出7项具体要求。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协同发展要在京津冀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要方面率先取得突破。随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纲领性指导文件及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一系列实质性进展。
这一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北京、天津和河北由简单的地区合作转为全方位的协同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逐渐建立,在产业转移承接、生态联防联控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深层次、高水平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三)持续推进的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迈向新阶段。《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等各领域政策文件的颁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空间布局上,2018年,《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颁布,提出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2020年,《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颁布,致力于打造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典范。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8]。
在新的发展阶段下,面向新定位、新目标、新使命,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高水平、更优效益和更高质量不断迈进。
三、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取得的成效
(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协同联动日益增强
科技创新是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动力[9]。从研发投入看,京津冀三省市研发投入持续上升,但增速不一、分工不同,创新资源进一步集聚。北京是京津冀地区的创新中心,研发投入远高于津冀两省市,且增速快、占GDP的比重高。从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以下简称R&D经费)支出看(见图1),2014—2022年北京R&D经费支出规模由1269亿元增长至284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1%,占GDP的比重由6%增长至7%,提高了1个百分点。天津研发投入规模次于北京,但研发投入增长缓慢,与北京研发投入的差距逐渐拉大。2014年,天津R&D经费支出为46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2022年缓慢增长至569亿元,仅相当于北京研发投入的1/5。河北创新基础落后于京津两市,但后发优势明显,创新投入快速增长。2014—2022年,河北R&D经费支出规模由314亿元快速增长至84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3%,占GDP的比例提高了1个百分点。
从研发产出看,京津冀三省市专利授权量呈上升趋势,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从专利授权量看(见图2),2014年,京津冀三省市专利授权量共12万件,2022年增至39万件。其中,北京占京津冀专利授权量的一半多,从2014年的8万件增长至2023年的19万件。2014年,天津和河北在专利授权总量上相差不大,但河北增速远高于天津。2023年两省市专利授权量分别为6万件、10万件。
从创新要素流动看(见图3),京津冀三省市技术市场交易额逐年增加,并且北京流向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比持续增长。2014—2023年,北京技术市场成交额由3136亿元增长至8537亿元,占京津冀技术市场成交额的3/4以上。天津次之,技术市场成交额由2014年的418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1677亿元。河北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长最快,由2014年的30亿元增至2022年的1010亿元。从区域内创新要素流动看,北京流向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由2014年的83亿元增加至2022年的749亿元,占北京技术市场成交总额的比重由3%增长至9%。区域内技术市场交易日趋活跃。
(二)非首都功能得到疏解,人口趋于相对平衡
高度集聚的城市群中心常常面临着经济密度过高过大并导致膨胀病的问题[10]。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在于缓解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通过疏解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机构、部分行政性与事业性服务机构,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推动京津冀地区人口协调发展。一般性制造业方面,北京市制定实施了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10年间,北京市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超3000家。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方面,10年间,北京市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近千个。教育医疗机构方面,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签署《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通过设立新校区、整体搬迁等多种方式向北京市郊区、天津、河北疏解转移;天坛医院实现整体搬迁,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扩建等重大疏解项目完成。行政性与事业性服务机构方面,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向通州区转移参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水平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105/t20210507_1279324.html。。
从京津冀地区人口布局看,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一定成效,京津冀人口趋于均衡发展。总体而言,京津冀三地人口平稳增长。2014—2022年,京津冀常住人口规模由10 923万小幅增加至10 967万,占全国人口规模的8%,在全国的比重略有下降。其中,202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为2184万,在京津冀人口规模中的占比为20%。2014—2022年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始终在2200万以下。2017年以后,常住人口持续减少。北京中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常住人口比重大幅下降,201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1172万,占北京全市人口的60%。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小幅降至1099万,占比降低至50% 参见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北京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beijing.gov.cn/gongkai/shuju/sjjd/202105/t20210519_2392886.html。。天津常住人口规模在波动中下降,由2014年的1429万降至2022年的1363万,在京津冀人口规模中的比重为12%(2022年)。2014年,河北常住人口规模为7323万,2020年增至7463万,在京津冀三地中的占比为68%。随后受疫情影响小幅下降,2022年河北常住人口规模为7420万(见图4)。
(三)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步入低碳发展之路
城市群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是统筹产业转型升级、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冲突的核心地区[11]。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为担当好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京津冀针对生态环境、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协议。京津冀地区生态联防联控机制逐步完善,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空气质量方面,京津冀三省市空气质量保持整体改善趋势。以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例(见图5),2014年,京津冀三省市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86μg/m3、83μg/m3、165μg/m3,远远优于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经过近10年的治理,2023年,三省市PM2.5平均浓度分别降至32μg/m3、41μg/m3、39μg/m3,较2014年分别下降63%、51%、77%。其中,北京已连续3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生态建设方面,京津冀地区突出新发展理念进行生态环保建设。2014年以来,京津冀三省市城市绿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有所提升。2014—2022年,北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49%提高至50%,天津由35%提升至38%,河北由42%提高至44%(见图6)。
从经济发展模式看,京津冀三省市推动绿色转型,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益不断提高,碳强度呈下降趋势。京津冀地区着力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例如,北京向远郊农村地区拓展“煤改电”工程、推动车辆电动化,天津推动实施大港电厂关停替代工程,河北省推进新能源重型卡车更新替代。从2014—2021年,京津冀三省市单位GDP碳排放量均明显下降。2014年,北京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4吨,2021年降至0.2吨,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优水平,降幅高达52%;天津由1.5吨降至1吨,降幅为33%;河北由3吨降至2吨,降幅为30%(见图7)。这说明,京津冀三省市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益不断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逐渐走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路径。
(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12]。2023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13]。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实施以来,京津冀三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以开放联动、制度创新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打造更加便利自由的营商环境。2021年,京津冀三地签署《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3年签署《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2年,京津冀三地签署营商环境合作框架协议,先后推出多项“同事同标”“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事项参见金朝力、冉黎黎:《实施五大行动 京津冀共推自贸区高水平开放》,北京商报网,https://www.bbtnews.com.cn/2023/1225/499342.shtml。
。2023年,开通京津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协同服务专区,实现了三地国际贸易用户体系互认、特色功能互用和物流数据共享,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天津打造关港集疏港智慧平台,率先探索和推广进口“船边直提”和出口“抵港直装”措施,大大便利企业进出口业务,为企业降费增效。
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国际重大活动为重要抓手,提高区域国际影响力。2022年,北京、张家口联合举办了冬奥会、冬残奥会,这一国际重大赛事进一步提高了该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国际知名度,拓展了对内对外经贸合作空间。此外,北京举办多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天津举办世界智能大会,河北举办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在各个领域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进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五)教育医疗深度合作,民生共享红利释放
高质量协同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同发展。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成果由三地人民共享,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深耕,增进三地民生福祉。
居民收入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10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上升。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实施之初,北京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 489元,2023年增长至81 752元,年均复合增长率7%。天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28 832元增长至2023年的51 271元。河北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由2014年16 647元增长至2023年32 903元,增长率为8%。河北居民收入与北京、天津两市的差距不断缩小。2014年,河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北京的37%、天津的58%,2023年分别增长到40%、64%(见图8)。
公共服务方面,京津冀三地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深入合作,北京、天津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向河北转移,推进三地人民共享协同发展成果。教育方面,多所北京中小学和高校在河北建立分校,并通过教育集团、学校联盟、结对帮扶等形式开展合作办学参见《中国教育报》:《推动基础教育资源共享,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京津冀共绘教育“同心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306/t20230613_1064058.html。。医疗方面,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深入推进,深化医疗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通过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取消异地就医备案、京津冀检验结果互认、推进京津冀医联体建设等举措便利群众就医 参见万秀斌、邵玉姿:《河北深入推进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月8日,第1版。。
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创新转化能力不足,津冀产业承接断层
尽管京津冀地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居全国前列,并且坐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但京津冀地区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有待加强,区域内创新成果转移、区域创新协同也有待提高,创新驱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全面形成。
由于京津冀地区产业链和创新链衔接存在堵点,尽管京津冀地区尤其北京创新研发产出居全国前列,但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较低。2023年,北京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总量达106 552项,成交额达8536.9亿元,但落地北京本市的技术合同仅35 361项,占比33%,成交额2333.1亿元,占本市的27%。流向外省市的技术合同中,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748.7亿元,占总量的9% 参见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岁末年初话创新|合同量破10万项,成交额破8000亿元,北京技术市场实现“双突破”》,https://kw.beijing.gov.cn/art/2024/1/22/art_10540_672822.html。。换言之,2023年,北京流向京津冀地区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仅占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36%,北京市64%的技术合同落地在非京津冀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和广东省。导致京津冀地区创新成果本地转化率低、在京津冀落地难的主要原因是京津冀地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衔接存在堵点,产业结构和创新结构匹配程度较低。根据叶堂林、李国梁(2021)的研究[14],京津冀地区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的节点度值偏离度高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其中,张家口、秦皇岛、廊坊、石家庄和保定的偏离度最高,创新链滞后于产业链发展。
受地区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发展差距的影响,河北、天津在承接京企向外疏散与北京技术转移中仅有地理距离优势,其他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从产业转移看,以2018年为例,该年北京迁出市外企业中仅27%迁至河北、天津,迁往浙江、广东、山东、湖北、江苏的占45%参见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北京市市场主体发展分析简报》,https://scjgj.beijing.gov.cn/zwxx/sjfb/sjjd/201902/t20190225_108770.html。。从技术转移看,2012—2022年北京流入外省市的专利中,38%流向长三角地区,14%流向珠三角地区,仅12%流向天津和河北[15]。尽管河北和天津是承接北京产业疏散、技术转移的两大主要区域,但随着京津冀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上海、深圳、成都、西安等城市的总部经济快速发展,津冀地区在承接北京项目上的竞争优势逐渐下滑。导致河北、天津承接北京技术转移、产业疏散能力较低的原因有三。一是京津冀内部技术发展差距过大,北京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都远远高于河北、天津。2022年,北京R&D经费支出是河北的3倍、天津的5倍,专利授权量是河北的2倍、天津的3倍根据北京市统计局京津冀解读专栏(https://tjj.beijing.gov.cn/zt/jjjjdzl/sjcx_4303/)数据计算得出。。二是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差异大、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性不足。北京的创新产出集中于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精尖领域,而天津和河北以能源化工业等传统产业为主。三是行政区划分割带来的边界效应。京津冀分属不同的省份,在产业转移与创新协调的过程中,需要跨省跨部门沟通、协调。但各地区的经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竞争关系,这会增加产业转移与创新协调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
(二)“过密过疏”现象突出,空间布局待优化
从人口规模看,京津冀地区人口高度集中于北京、天津两市。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天津为超大城市,城区人口分别为1987万、1093万参见国家统计局:《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9/16/c_1127863567.htm。。而河北省城区人口最大的城市为石家庄,属于I型大城市;其次为邯郸、唐山、保定和秦皇岛,属于Ⅱ型大城市;其余均为中小城市参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2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从人口密度看,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天津两市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公里1334人、1159人。而河北11个地级市人口密度均低于每平方公里100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为毗邻北京、天津的廊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51人。
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核心因素。京津冀内部经济活动、产业基础、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存在过度集中的态势,这是导致京津冀13市人口分布差异明显的主要原因。从经济活动分布看,尽管河北市场主体总量大于北京、天津,但从密度看,河北经济活动密度远远低于京津两市。截至2023年底,北京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到256万户,其中新设经营主体数量达到34万户参见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北京市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简报》,https://scjgj.beijing.gov.cn/zwxx/sjfb/sjjd/202401/t20240124_3544453.html。;天津实有市场主体约195万户,新登记市场主体约30万户 参见《天津日报》:《经济运行整体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3年天津市经济运行情况解读》,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https://gyxxh.tj.gov.cn/ZWXX5652/GXDT9285/202401/t20240122_6515690.html。;河北全省经营主体总量达到853万户,新登记经营主体145万户参见《河北日报》:《截至2023年底 河北省经营主体总量超过853万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lianbo/difang/202401/content_6928731.htm。。考虑到河北全省面积分别约是北京和天津的11倍和16倍,河北市场主体密度远低于北京、天津。从公共服务看,2022年京津冀三地人均重点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分别为13 802元/人、8818元/人和5823元/人 参见国家统计局:《京津冀协同步伐坚实 区域发展指数进一步提升》,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12/t20231228_1946006.html。,京津冀地区优质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
(三)生态经济“两难”选择,联合治理机制待完善
首先,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治理的两难选择,京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面临着巨大的生态保护成本,生态补偿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京津冀三地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的环境效益、生态治理的经济成本均存在差异,这导致三地在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利弊权衡并不一致。例如,《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共建环首都生态环境绿带,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生态保护举措,但诸如潮白河和北运河沿岸两公里范围内严格禁止工业建设的举措,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三河、大厂、香河(以下简称北三县)经济发展、产业承接的发展空间。当前京津冀三地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由政府执行,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补偿对象集中在河北全域,存在部分地区生态补偿力度较低的问题。生态补偿与发展经济的机会成本不相一致,阻碍了地区协同发展、均衡发展、高质量发展。
其次,京津冀三地山水相连,但又各属三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划,跨区域生态治理合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津冀水体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合作协议》《生态环境监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联合整治方案已经出台,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已经建立,但客观上,京津冀三地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政策落实力度存在差异,生态治理步调不完全统一,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效果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此外,尽管目前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在整治现有环境污染、应对突发问题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但尚处于末端治理阶段,基于统一标准的长期全过程监测机制尚待完善。
五、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权责利对等“新机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16]。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实施10年来,京津冀三地围绕土地、教育、卫生等各领域签署了一系列专项规划和合作协议,但由于中央与京津冀三地行政格局的复杂性,分税制、地方“锦标赛”等制度安排带来隐形行政壁垒,不对等的行政级别强化了“灯下黑”的虹吸效应,一些制约要素自由流动、资源有效配置和生态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跨区域治理新机制,推进京津冀三地全方位、多层次协作[17]。
京津冀高质量协调发展,需要构建跨部门协调合作机制,统筹各部委各地区的统一行动,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各方共同遵守规则。要从三地急需解决的问题、发展诉求和共同目标上找寻区域合作的利益契合点,拓展北京发展空间、提升天津发展质量、增加河北发展机会。要在已有的三地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营商环境一体化、信用协同监管等制度基础上,在产业联动、创新协同、营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等领域进一步创新和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合作机制,推动三地联合治理走深走实。
同时,还要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尤其是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建立跨区域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机制,使生态价值可量化。在政府主导和资金支持制度的基础上,对生态资源进行产权界定,培育京津冀地区生态产品交易市场,推动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建立多层次的补偿标准、多样化的补偿形式,确保资源输出和生态治理地区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补偿。要推动生态利益补偿立法,通过京津冀三地地方法规创新探索区际利益补偿立法,实现京津冀三地生态利益补偿有法可依。
(二)优化人口布局“新空间”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由以单一城市或区域为主向大空间尺度下多节点、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转变,城市竞争正在转变为城市群竞争。因此,要继续着力打造京津冀地区“一核两翼”的空间格局,发挥北京的核心引领作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北三县”、雄安新区、滨海新区的高质量发展,充分利用区域协同效应,打造新的强有力的京津冀增长极。
综观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是辩证统一的一体两面。北京需要疏解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天津需要打造制造业集群,提振经济发展信心;河北各市需要挖掘经济增长点,不断扩大经济规模。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由京津冀经济和人口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现象所导致的,培育和扶持新的增长极至关重要。借助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一体化建设,率先实现京东地区与河北的一体化;借助雄安新区建设,带动京南与河北劳动力及其他经济要素在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双向转移;借助滨海新区建设,实现天津东部与河北的协同发展并增强其在京津冀协同中的辐射力。通过新的增长极的打造,形成布局合理、层级完善、科学规划的城镇化体系,可有效发挥区域内不同城市的优势,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协调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此外,持续推进京津冀地区统一的劳动技能认证制度、区域内互认岗位培训证书等,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信息库,有效促进区域内高层次人才的共享和互动。要盘活存量土地、合理利用增量土地,优化区域内部职住平衡、住行协调、宜居宜业的居住空间结构。
(三)打造新质生产力“新引擎”
新质生产力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高效能生产力,是技术创新对传统生产力的颠覆性变革,是新时期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生产力。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8]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9]新质生产力成为激活京津冀地区要素禀赋、发挥京津冀地区比较优势、赋能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主要载体,培育引领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并形成分工明确、层次清晰、协同高效、创新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发挥京津冀地区现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坚持产业差异化发展原则,科学规划定位,实现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低水平竞争,提高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作与分工水平。同时,要坚持集中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和各自的产业亮点,释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
发挥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紧紧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整合京津冀地区创新研发资源,加强协同创新,推进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要深入推进京津冀地区基础研究合作,发挥京津冀地区丰富的科研资源优势,合力解决协同发展中意义重大、急需合作的共性问题。要构建高效的产学研协同体系,打通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供需之间的堵点,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和地区发展需求,制定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扶持政策,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移和转化。
(四)发挥数据要素“新动能”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资本、土地是三大投入要素,异质性劳动、企业家等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数据是一类“要素”。2024年,《“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数据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在优化区域生产函数、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区域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20]。
紧抓数字经济机遇,使数据要素成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新动力。着力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领域新基建的统筹规划与共建共享,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保障。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业,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以数据要素赋能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跨地区融合,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格局。
推动数据要素跨地区、跨部门自由流动,发挥数据要素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作用。京津冀三地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各自的比较优势,北京具备人才优势,天津和河北拥有重要港口,河北土地要素相对丰裕,三地共同筑造起京津冀雄厚的算力基础,为数据要素赋能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因此,推动京津冀地区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促进数据要素跨地区、跨部门互联互通,促进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要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的服务生态,建立健全跨地区数据交易平台和协同监管机制,为数据要素成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源头活水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覃成林、姜文仙:《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动因与机制体系》,《开发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18页。
[2] 方创琳:《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规律性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1期,第15—24页。
[3]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央视网,https://news.cctv.com/2019/12/15/ARTIiSq8Cgxu2HY1TRcGwwFh191215.shtml。
[4] 魏后凯、年猛、李玏:《“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第5—22页。
[5] 阎东彬、孙久文、赵宁宁:《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动态评价及提升路径》,《工业技术经济》2022年第6期,第129—134页。
[6][8] 姜赟、史鹏飞、王昊男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23年9月14日,第1版。
[7] 张可云、蔡之兵:《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第101—105页。
[9] 方创琳、张国友、薛德升:《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地理学报》2021年第12期,第2898—2908页。
[10] 沈洁、张可云:《中国大城市病典型症状诱发因素的实证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期,第1—12页。
[11] 黄跃、李琳:《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与时空演化》,《地理研究》2017年第7期,第1309—1322页。
[12] 徐现祥、李郇:《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第57—67页。
[13] 新华社:《习近平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新华网,http://m.news.cn/2023-05/12/c_1129610708.htm。
[14] 叶堂林、李国梁:《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页。
[15] 叶堂林、王雪莹、刘哲伟:《京津冀发展报告(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75—211页。
[16] 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第63—70页。
[17] 张贵、孙晨晨、刘秉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成效与推进策略》,《改革》2023年第5期,第90—104页。
[18]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72.htm。
[19] 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834.htm。
[20] 李兰冰、商圆月:《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22—128页。
Historical Progress,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a national strategy.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reg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nnovation synergy, spatial layout, ecological protection, opening up, and peoples well-being. Nevertheless, there are challenges that must be overcome, including a lack of capacity for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the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with both overcrowded and overpopulated areas, and the need for deepening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o a higher level and to position the region as a pioneer and model in pursu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inforce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enhance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hould serve as the new engine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data, as a production factor, should be a kinetic energ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Beijing-Tianjin-Hebei;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new quality produ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