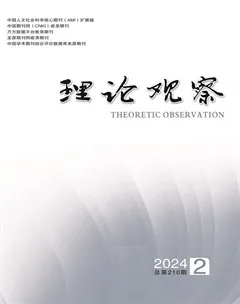从唐律中的婚姻制度看唐代婚姻特点
2024-06-13张婷
张婷
摘 要:唐代律法中的婚姻制度涉及婚姻缔结、婚后家庭关系、婚姻解除和再婚四个阶段的内容,体系完备,内容全面,维护了夫家和封建社会的秩序和利益,一定程度上也保障妻子的婚姻权利,具有进步性。唐律的婚姻制度体现出婚姻法援礼入法的特点与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保守性,其立法思想和内容改进对后世有借鉴意义。而现实中又存在与婚姻制度相违背的婚姻实态,可见唐律的相对弹性和唐朝婚姻的开放之风,但也随着唐朝国势转折后对儒家伦理的重视而逐渐减少。
关键词:唐代律法;婚姻制度;婚姻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2 — 0098 — 04
婚姻是社会各阶层的重要生活内容,关系到夫妻双方的人生、家庭与家族的利益、血脉传承和社会的秩序与规范,因此封建朝代的法律将婚姻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法典发展顶峰的产物,唐朝的《唐律疏议》对意义重大,承前启后。其中的《户婚篇》同和唐代其他令、格、式对婚姻制度中的婚姻缔结、夫妻关系、离婚、再婚都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唐律中的婚姻制度以维护社会中家族、家庭的和谐为目的,为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王朝统治服务。唐律更继承了历代律法“一准乎礼”的准则,援礼入法的特点在婚姻制度中也有体现。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不常见的全面开放朝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常被后人传颂,称作“大唐风气”。唐朝时民风开放,礼教约束力松懈,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还未被普遍推广,社会中出现不少与唐律中婚姻制度相违背的婚姻实态,唐人的婚姻观念也有巨大变化。
一、婚姻缔结的条件
古人对于婚姻的理解,可追溯至《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1]婚姻不仅是人生大事,并且关系到祖先祭祀和家族延续,唐朝统治者通过法律对婚姻缔结设置条件,严格规范婚姻缔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唐代实行婚姻家长包办制,子女婚事必听从于家长安排,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不被重视,这是中国古代一直遵循的旧例。《诗经》有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2]若子女违抗家长定下的婚事,家长有权上告官府追究子女的刑事责任。据唐律,这里说的家长不仅包括祖父母、父母,期亲和余亲也可作为家长主婚,不过后两者的主婚权排在祖父母、父母之后。不过也存在未得主婚者认可但仍得到法律承认的婚姻成立情况,“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己成者,婚如法”[3]223一条就规定了当子孙弟侄在外地娶亲,家长在其成亲后才为其订婚时,若已形成事实婚姻,可以承认婚姻合法性。这种特例的前提仍然是婚姻得到家长的同意。
男女嫁娶还须经过媒妁说媒。《唐律疏议》卷十三“为婚女家妄冒”条疏议云:“为婚之法,必有行媒。”[3]214媒妁行媒成为婚姻缔结的必要条件写入法律是从唐朝开始的,与之相伴的是关于媒妁违律的法律责任。例如,在《唐律疏议》卷十四“嫁娶违律”中规定“未成者,各减已成五等。媒人,各减首罪二等。”[3]229未成者指因违反唐律规定同姓为婚等婚姻缔结限制性条件而导致违律结婚的结果,媒妁要承担徒刑处罚。唐律中还有不少对媒妁的要求,媒妁规范化行媒离不开法律的强制要求,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婚姻缔结违律情况。媒人认真工作不仅可以使两方家族更了解对家,相对减少一些婚姻悲剧,也使媒妁说媒更得百姓认可。
不过,社会生活中仍有不少自主择婚情况存在。《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虬髯客》一文中,姬女红佛女私下投奔李靖,私定终身,辅佐李靖立下功业。此类故事在《太平广记》中仍有不少,他们的婚姻虽没有经过父母同意也没有媒妁说媒,不符合唐律,但却被写进了传奇小说中为世人传颂。
(二)婚龄
古代男女成婚的另一个前提是达到法律规定的婚嫁年龄。《通典》中有记载“其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4]唐初李世民规定男子年龄20岁及以上,女子年龄15岁及以上,达到此要求者必须结婚。唐玄宗将婚龄改为男子15岁,女子13岁。唐太宗时期社会初定人口较少,因此鼓励婚育以增加人口。唐玄宗时期降低婚龄的早婚政策使人口再度膨胀,给社会带来了负担。
婚龄规定了结婚的合法年龄,但唐人的实际结婚年龄与法定年龄是有差异的,晚婚者不在少数。除“居丧不婚”、丧夫丧妻或离婚后再婚等特殊情况外,实际结婚年龄还受以下几点影响。第一,因为唐代门第之风盛行,所以婚姻中门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虑条件,不少男性选择考取功名、从官后再结婚,以便能够与高门攀亲。第二,士庶有别,庶族若想与世家大族联姻,财力就成为一项重要因素。家道衰落的子女结婚不易,白居易曾作诗讽刺过这一现象,“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5]非世家又无财力的家庭很难嫁娶子女和挑选满意的亲家,也产生了不少出卖子女婚姻换取钱财的买婚卖婚现象。
(三)婚姻缔结的禁止条件
从周朝就有婚姻缔结的禁止性条件,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唐律中的婚姻缔结禁止条件有:第一,同姓不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3]219,疏议明确指出同宗共姓、同宗异姓不能结婚,纳妾也受此限制,复姓有一字相同则没有此禁限。第二,亲属不婚,《唐律疏议》“同姓为婚”条规定姻亲不婚和再婚亲不婚,“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3]220第三,官民不婚,监临官员不可娶自己部下或管辖的平民为妻为妾,即便是监临官的亲属所娶也要杖一百。第四,良贱不婚,不同色的贱民间也不可通婚。唐律对良贱通婚的惩罚也较为严厉,良人和贱民的阶级区分和此项禁止相伴而生。除此之外还有禁僧道为婚,禁娶逃犯为妻妾,异族不婚、禁男女欺诈隐瞒己方情况或假冒顶替,禁恐吓强娶,禁丈夫转嫁妻子以收取聘礼,居父母和夫丧不婚等。同姓不婚和亲属不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近亲婚姻和相关的生理、伦理问题,对阶级限制、损害对方和社会利益的恶邪情况的禁止又很好地维护了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体系,有利于统治阶级和贵族将其血缘关系稳固在上层社会,享受特殊权利,又促使社会各阶层秩序稳定。
现实中,良贱不婚、亲属不婚、官民不婚等都有为违律的婚姻实态存在。违反亲属不婚的,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九《琴台子》中,赵郡李仲希将女儿嫁给了内外三从的兄弟临淮县令崔祈。违反良贱不婚的,如《大唐新语》中记载:“(许敬宗之)子昂,颇有才藻,为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继室,假姓虞氏。”[6]如此光明正大的违禁婚姻不仅没有按律惩处,还被记载到了史书中。唐代社会下层还有“借吉”习俗,贫家女在父母双亡有没有强亲主持婚姻时,为生存可在父母丧期嫁人。在史书文献中还可找到不少其他违禁婚姻事例而且多数未被处罚,可见婚姻缔结的禁止性规定在社会各阶层中皆有一定弹性。
二、婚后夫妻的关系
由于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结构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唐代的夫妻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男尊女卑。虽然有不少学者论证唐代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权力上升,但婚姻中妇女始终不平等地受夫权支配。《唐律疏议》中多有夫为妻纲的话语,如“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3]225,“夫为妇天,尚无再谯”[3]216等,多次强调夫妇之道是妻以夫为天,妻卑夫尊。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也有许多体现夫妻地位不平等的地方。如《唐律疏议》卷二十二“殴伤妻妾”和“媵妾殴詈夫”两条关于夫妻斗殴的规定,夫妻犯下同一违律行为,判处的惩罚相差甚远。若丈夫殴打妻子使其受伤,减凡人二等,致其死亡则以致死手段不同判处不同方式的死罪;若女方殴打男方但并使男方未受伤,判处徒刑一年,致其重伤的加凡斗伤三等,致其死亡的判处死刑。同时殴伤对方,妻子的刑罚比丈夫的高出五等。同时殴打对方且不致伤的情况,妻子徒刑一年而丈夫则不追究责任。种种不平等的夫妻法律规定可见妻子不仅在家庭中要服从于丈夫,法律中也无法享受公平的待遇。
唐朝虽有男尊女卑夫妻关系,但受胡族文化影响,形成开放的社会风气,也存在不少性格强悍的女子,产生妻子善妒和丈夫惧内之风。记载于史书中的著名妒妇宜城公主为典型,《新唐书》记载:“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刵耳劓鼻,且断巽发,帝怒,斥为县主,巽左迁,久之,复故封。”[7]宜城公主性格刚悍,驸马的反应未被描写,妻强夫弱一目了然。从唐朝正史小说里的妒妇事例中可以看出,此风气从上层向下层扩散,正史中记载的越来越少,笔记小说记载的越来越多,可见唐代妇女地位的相对提升。同时丈夫的形象越来越惧内,在家不能主持大局、掌握财权,人们在讲述妒妇故事时,对故事中畏惧妻子的丈夫的嘲讽意味增强。
三、婚姻解除的规定
婚后夫妻关系并非不可变动,可能因一方死亡导致婚姻关系客观消亡,夫妻双方也可主动选择解除婚姻关系,一般称为离婚或离绝。唐律中规定妻死丈夫服丧一年后可再娶,夫死妻子服丧三年后可再嫁,关于离婚的规定则复杂得多。
(一)七出与三不去
法定婚姻解除的第一种方式是“七出”,这是只能由丈夫提出的离婚方式,又称休妻。《大戴礼记》对“七出”的定义是“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8]《唐律疏议》在《礼记》的基础上对七出内容做了些修改,“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3]224总体看唐律中的“七出”与《礼记》中的内容一样,只是顺序有所不同。出于对传宗接代和血统纯正的重视,妻子五十岁以上无子上升为第一,淫佚上升到第二位,反映出婚姻对家庭和家族的重要性,损害家族利益的妻子不被社会认可。唐代盛行妒妇之风,因此妒忌的排名有所下降。“七出”是丈夫提出休妻的七条理由,妻子犯“七出”中任意一条时,丈夫就可以不经官府直接写休妻文书令其归娘家,休妻文书必须在夫妻双方、父母亲属和邻居的见证下才生效。“七出”严格规范了妻子的行为,即便无子、恶疾可能不是妻子的主观过错,唐律和礼法还是选择牺牲妻子以维护家族和男子的颜面和利益。
“七出”使丈夫拥有单方面的休妻权力,且不事舅姑、口舌等条弹性大,往往成为丈夫任意休妻的理由。在家庭中若丈夫休妻的权力得不到约束,妻子的地位就会过于被动,导致家庭失衡、人伦乱序,因此唐律设定了“三不去”以限制,具体内容是:“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而出之者,杖一百。并追还合。”[3]224妻子曾为公婆服丧三年,证明成婚已久且妻子于夫家有恩情;妻子在贫困时陪伴丈夫,丈夫在飞黄腾达时休共患难的妻子是忘恩之举、不仁义之行,因此不被认可;妻子在夫家没有财产积累,若被休也无娘家可回,基本生存权利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丈夫也不可休妻,这是出于对妻子人身保护的考虑。但妻子有恶疾或与人通奸不适用“三不去”,说明对家族利益的保护更为重要。“三不去”符合儒家的孝道和仁义的精神,肯定妻子做出的贡献,保障婚后妻子的权益,不至于夫权过大导致妻子遭受冤屈,家庭家族失衡。
(二)义绝
法定婚姻解除的第二种方式是义绝,与“七出”的不同在于,若妻犯七出,丈夫不论休不休妻,都不违律,而义绝是官方规定的强制离婚条件,夫妻两方不论谁犯义绝,官府都裁定必须解除婚姻关系。《唐律疏议》卷十四“义绝离之”条疏议中指出,夫妻因恩义和情爱而结合,若情义已绝,再继续勉强维持夫妻关系,只会危害双方家族与社会,必须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当夫或妻实施了逆悖人伦、废乱纲纪的行为时,官府就可能裁决夫妻已义绝。唐律规定具体违法行为为:“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3]224这些罪行皆违逆人伦、败坏风教,经官府确认后夫妻必须离婚,不肯则判刑一年,强制效力远超“七出”。“义绝”中妻子和丈夫的标准不同,如妻子与丈夫缌麻以上亲属通奸即为义绝,丈夫与妻子母亲通奸才算义绝,如妻欲杀夫即为义绝,夫欲杀妻则没有规定。从这些条款差异可见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
(三)和离
《唐律疏议》卷十四“义绝离之”条还提出了第三种婚姻解除方式和离,与现在协议离婚类似。唐律中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3]224,疏议增加解释“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3]225此方式较温和,因夫妻感情破裂,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也有因生活贫困各寻出路或婆媳关系不睦而选择和离的情况。《云溪友议》记载:“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饘臛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9]处理官员颜真卿虽不认同妻子的做法,罚了妻子二十大板,但二人婚姻关系最终还是解除,可见妻子弃丈夫而去在法律上得到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允许,但在社会中不被接纳,妻子主动提出离婚仍不常见,在小说史书中多作为反面例子。敦煌出土的放妻书是唐代和离的离婚文书,其上记载:“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娉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僧,一别两宽,各生欢喜。”[10]丈夫在离婚时向妻子赠送美言,祝福其日后婚嫁,可见唐代平等婚姻观的进步和不以离婚为耻的风尚。在和离制度中妻子可以提出离婚,这是与另外两种方式最大的不同。和离在实际使用中多用作“七出”的体面处理方式,因“七出”内容多为家丑,夫家为不张扬丑事多选择和离代替“七出”,给两边家族保存颜面。
四、再婚
婚姻解除后的再婚在法律上没有阻碍,社会中也不罕见。从敦煌出土的离婚文书中对再婚的态度十分宽容,“自后夫则任娶贤妻,同牢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之净虑。”[11]唐人对丈夫再娶的态度更为支持,但受贞洁观变化的影响,对女子再嫁有着矛盾的态度。
男子再娶多被社会所接受,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贵族、官员、富裕农民等再娶。再娶的前提条件是妻亡或者离婚。对于妻亡的丈夫,唐太宗颁布诏令“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丈夫要为妻子服丧期满才可再娶,否则妻死后马上再婚会败坏社会风气。当出现重婚情况时,如果女方家族知情丈夫要被判徒刑一年,如果女方家族不知情,丈夫重婚且骗婚,要被判徒刑一年半。
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女子再嫁问题在唐之前的朝代都比较保守,《礼记》直接提出妻子“夫死不嫁”。唐朝民风较开放,唐太宗为鼓励生育曾颁布诏令劝适龄寡妇再嫁,还将再嫁寡妇的人数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政绩标准之一,唐律也规定丧夫的妻子服丧三年后就能再嫁,也没有阻拦条件,可看作是支持离婚或丧夫妇女再嫁。《北梦琐言》中记载,岭南节度使裴璩的女儿年少丧夫,裴璩做主将其再嫁。书中认为寡妇再嫁自此开始,上至皇室和士族,下至普通民家庶族,都不以妇女再嫁为耻,唐朝皇室公主再嫁的也不在少数。
但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人反思社会作出一系列改变。赋税制度的改变使妇女地位下降,之前不是特别重视的儒家思想被重拾用来维护纲常伦理,妇女贞洁观被推广。种种变化导致社会反对妇女再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唐朝后期颁布了不少限制公主再嫁的法令和惩罚公主不贞行为的判决。唐宣宗规定有子女的公主、县主不可再嫁,无子女的也要经过批准才可再嫁,若是隐瞒子女情况则要被惩罚。
五、结论
唐律严谨地规定了婚姻的各个阶段,从婚姻缔结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到婚后男尊女卑夫妻关系,从婚姻关系的解除到再嫁再娶。唐律中的婚姻制度基本完备,唐人婚姻生活的各方面都可找到法律依据。但在法律制度之外,仍存在不少相悖的婚姻实态,如自主婚姻、亲属通婚、妒妇和惧内之风、妇女改嫁再嫁盛行等。
唐人的婚姻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保守性,男尊女卑特点突出,此观念贯穿全部唐代婚姻制度,夫妻双方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始终存在,体现维护夫家家族利益和三纲五常的特征。二是援礼入法,将以前只是作为礼法的婚姻礼俗写入法律,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社会礼制正式成为法律规定,和离正式成为法律承认的离婚方式。三是开放性,唐律中的婚姻制度与现实中的婚姻实态存在不少矛盾的情况,尤其是唐王室婚姻开放性更显得唐律婚姻法的弹性。
〔参 考 文 献〕
[1]礼记[M].崔高维,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27.
[2]程俊英,撰.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8.
[3]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岳纯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杜佑.通典:卷五九·嘉礼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8:1676.
[5]白居易.白居易集[M].顾学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36.
[6]刘肃.大唐新语[M].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141.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50.
[8]戴德撰.大戴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0-221.
[9]范摅.云溪友议[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0]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177-178.
[11]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75-76.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