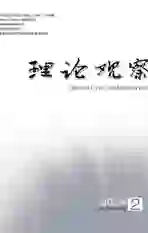辽代赐剑予权考
2024-06-13鲁志伟
鲁志伟
摘 要:关于中国古代帝王赐剑专杀、许以便宜从事的滥觞,学界暂无明确说法,钩沉索隐,笔者认为该制度始于宋辽时期。辽代赐剑予权发端于辽圣宗时期,被授剑者往往在某具体事务或地方委派上拥有生杀予夺的特权,赐剑予权的出现同辽朝中期中央政治势力的重组、地方部族势力的衰弱、皇权的加强、对外征战的需要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辽代赐剑予权也是辽代中后期政治发展脉络的体现之一。
关键词:辽代;赐剑;中央集权;便宜行事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2 — 0091 — 07
一、引言
辽朝为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其开创伊始在政治制度上便呈现出较为浓厚的部族特征,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发展程度相较中原王朝而言尚不成熟。但随着其封建化与汉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上农业生产所占比重的增长,辽朝游牧行国的色彩逐渐减退。在中央上,官制完善、君主权威增强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地方上,整合部族、加强控制的手段日益增多;而在对外关系上,辽朝与北宋争夺正统,以“彬彬不异中华”①自居,力图在朝贡、颁历、军事、文化等方面拔得头筹。革故鼎新必然有不可避免的阻力,在经历景宗朝的短暂稳定与发展后,辽圣宗不仅要延续辽朝蒸蒸日上的局面,更迫切的是要维持政权的稳定与彰显君主的威仪,赐剑予权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关于辽代赐剑予权的关注,尚属稀少,且缺乏系统性研究。林鹄在其著作《南望:辽前期政治史》中谈及辽圣宗统和初年政治局势时,以较少的篇幅举例说明了赐剑专杀所体现的中央集权精神。②武玉环在其著作《契丹史》中论及契丹部族的管理机构时,曾援引五国、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隈洼请求道宗赐剑以解决部族难制问题一事,认为这是辽代部族制度管理严格的体现之一。③以兵器史研究见长的学者周纬在其代表作《中国兵器史稿》中对于辽代兵器并无太多记载,仅附于元代兵器之后,且未提及有关辽代剑的问题。④近年来由龚剑撰写的《中国刀剑史》较为详细地收录了有关辽代剑的史料与考古资料,具有一定价值,可供学者参考,但多为简单陈列,并无深入探讨与解读。⑤在学术论文上,见于崔跃忠《辽墓出土兵器探索》,作者在对辽代剑的功能探讨中提及了其作为权力信物的作用。⑥彭文慧在《辽朝西南面招讨使研究》中以韩德威为例,认为辽代君主赐剑即予权,忽视了这一制度发展的阶段性。⑦以及周月峰《“尚方剑”考》,作者对古代史中帝王赐剑以便宜行事的案例进行了通史性的梳理,在涉及辽代时仅举两例。⑧
笔者认为,对辽代赐剑予权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有助于更好解构与把握辽代政治发展脉络;而关于辽代赐剑所呈现出的汉化趋势与北族传统演变的讨论,则可从渊源上厘清这一特殊政治行为。
二、辽以前赐剑发展的历史轨迹
赐剑在辽代以前具有三种功能:其一,赐剑可意味着极端惩戒,被赐剑者即被赐死,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身所服者七十余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于杜邮”。①秦代公子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②又如西晋时期,汉赵刘曜夺取关中渭水以北后,虏获晋建威将军鲁充,鲁充拒不投降,刘曜亦“赐之剑令自杀”。③据《三国史记》记载,高丽瑠璃明王亦因太子叛逆,而“赐剑使自裁”。④其二,赐剑又是恩幸的象征,隋代名将贺若弼在荡平南陈后,“命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宝剑、宝带、金瓮、金盘各一。”⑤其三:赐剑可作为予权与便宜行事的象征,但辽宋以前并不常见,兹举三例:据《晋书》记载,南阳王司马模曾赐予前凉政权奠基者张轨宝剑,并说:“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⑥唐宪宗时期叛臣李锜在谋划吞并淮西之地时,“室五剑,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⑦在后晋时期,出帝石重贵也曾授予臣下宝剑,以专任扩财之事:“晋因辽国入侵,国用逾竭,遣使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⑧
北宋时期,“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⑨,出现了许多赐剑予权的案例,检索《宋史》,其数量远超前代,兹举数例如下:
三、辽代赐剑予权的开端与渊源
最早见于《辽史》记载的赐剑案例为辽太宗时期,一为“特授回鹘使阔里于越,并赐旌旗、弓剑、衣马,余赐有差”,?輥?輳?訛二为给予讨伐后晋的功臣高模翰“玺书、剑器”?輥?輴?訛。然而此处的赐剑却并非予权,不是履行某项具体事务时所赐,其意义更多体现在恩宠功能上,换言之,即使具备部分权力信物作用,其表达也十分抽象和模糊。且后期的世宗、穆宗、景宗朝,再无赐剑的记载,因此这一时期的零星赐剑并不能称为赐剑予权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早期尝试亦是辽代赐剑体系的开端与重要组成部分。直到辽圣宗时期,赐剑才作为常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赐剑往往同军事征战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赋予受赐者专杀与便宜从事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辽代赐剑予权首创于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复诏赐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剑,不用命者得专杀”。①辽代从始至终都强调政权上的正统性,以继承唐代颁赐的旗鼓作为可汗权力象征便是体现之一。②此外,辽朝又同北宋在历日、历法、朝贺、礼仪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竞争。③对于汉文化修养极高且在改革中重视汉化教育的辽圣宗而言,④选定何种信物作为皇权的载体授予蕃汉大臣便成为一件值得斟酌的事情,是效仿辽太宗赐予王峻木拐⑤还是继续赋予旗鼓更多的意义?可以说两种选择皆非圣宗所愿,前者代表着草原本位与北族旧制,单独使用后者则始终难以脱离祖辈曾为中原王朝附庸的阴影,而剑却是辽圣宗效法中原所构建的礼制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辽史·礼志》记载,辽代的受册仪中关于剑的摆放、安置有一套较为复杂的程序,由尚舍奉御在东西阶设置安放宝剑的“解剑席”,以捧册官为代表的官员由东西阶进入殿内,需要在“解剑席”卸剑脱靴,而百官在退殿时仍需经过席位,佩戴剑履,关于这一套仪礼,《辽史》记载为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施行。⑥除此之外,《辽史·仪卫志》也记载了自辽景宗至辽兴宗三代完成了朝服由契丹国服向中原汉服的转变,这一演变的主体当为辽圣宗时期,关于这一时期朝服的形制,《辽史》多次提到“其革带剑佩绶”,而作为宝剑装饰品的佩绶,在朝服中亦有等级之分,即“七品以上去剑佩绶”,并非所有官员腰上宝剑都能如此华丽,⑦可见象征礼乐与文质的剑在辽圣宗时期获得了非凡的地位,直到天祚帝时期,文妃萧瑟瑟嘲讽佞臣萧奉先所作诗文也说:“丞相朝来剑佩鸣,千官侧目寂无声”,⑧这是一种受中原伦理影响的汉式认同:持剑上殿已经被视为超越礼制规格的宠幸了。同时,《耶律宗允墓志》记载:“珥貂冠而示贵,佩駞剑以增辉。”⑨《耿崇美墓志》亦言:“公则中丞之令子也,驾海灵峰,倚天长剑。”?輥?輮?訛2002年,辽宁省阜新市腰衙门平顶山辽墓发掘了一块墓志盖,上书“故于越宋国王墓志铭”,应当为耶律休哥之墓,墓中出土壁画上多绘有男侍抱剑图案,宝剑形制优美,剑穗迎风飘扬。?輥?輯?訛由此可知,剑作为文化意象,在辽代既涵有身份尊贵之意,也是对人才俊杰的高度赞美。于是作为对前述圣宗一朝选择的答复,既能表示章服华美与恩宠,也能涵有“假节钺以示征伐”之意的宝剑便成为新的权力信物。赐剑予权在辽代形成制度规模,亦是有大量例证可言的,兹列举如下:
根据《辽文萃》所录《高丽史》诏书记载,辽兴宗朝也曾在与高丽交聘过程中赐予其宝剑,④但此处赐剑应当具有一定的恩信意味,因此不录入上表。
四、辽代赐剑予权阶段发展特征
(一)赐剑予权的鼎盛:辽圣宗时期
1.显性功能:赐剑予权的军事目的
辽圣宗时期为辽代赐剑予权的发端时期与鼎盛时期,其赐剑活动从直观上看是围绕三个递进的目标展开。
其一为加强对部族的控制、巩固边境安全:圣宗即位之初,可谓强敌环伺。南有北宋虎视,因此委派耶律休哥总管南面边事;西有党项侵边、阻卜叛命,故以耶律速撒与韩德威主持对阻卜与党项的战争;北有乌隈乌古里、乌隈于阙、女真五国部等羁縻属国,便任命耶律章瓦、耶律隗洼为节度使,管理部族事宜。⑤其中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在主持对党项的作战过程中,屡立奇功,统和元年(983),“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奏党项十五部侵边,以兵击破之。”⑥《韩德威墓志》亦记载,在战胜党项后,“捷音继达于圣聪,宠泽遂行于赏典”。⑦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集军功与恩信于一身的韩德威被赐宝剑,得以便宜从事与专杀不用命者,统辖突吕不、迭剌二糺军。根据箭内亘的考察,此二部名为糺军,实则为部族军。⑧故以此来看,韩德威乃掌御剑以统二部族。次年,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洼亦请求赐剑,以加强对部族的统御力度,获得批准,被授予便宜从事的权力。关树东先生认为,五国乌隈于厥实为两部,即女真五国部与乌古部,被整合安置于今呼伦贝尔草原西部克鲁伦河流域一带。⑨按《耶律延宁墓志》,统和元年至三年的羽厥里节度使为耶律延宁,则延宁与隗洼当为一人,向南亦持此观点,据墓志记载,耶律隗洼此后一直掌管二部族,最终死于任上。?輥?輮?訛若以之与前述韩德威领二部糺军对应,统合初年的赐剑或专涉部族统辖也未可知。此后,圣宗任命部族官员皆从中央,部族祥稳的世选权也被打破,当划离部提出反对意见时,圣宗强硬表态:“诸部官惟在得人,岂得定以所部为限。”?輥?輯?訛可以说,这是圣宗统和初年实行赐剑予权制度的初衷。
其二为同北宋作战的需要:前述圣宗即位之时,北宋对其虎视眈眈,在与辽朝交界的河北防线一带陈兵布军,引起了辽方的恐慌。作为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伐辽政策的延续与对太平兴国七年(983)圣宗即位前夕辽军南下满城的回应,这一战争阴影终于在雍熙三年(986)转化为现实。是年正月至二月,宋太宗点集兵马,以曹彬、田重进、潘美为三路大军主帅,向辽朝发起征伐。?輥?輰?訛从宋方军事力量的布置来看,当以曹彬所率直指幽州的东路军为主力,这一战略构建亦与宋太宗意图收复燕蓟的情节有关。在此情况下,辽南京缘边多次告急,曹彬大军先后攻克固安、涿州、新城,直过拒马河;与此同时,潘美与田重进率领的西路军与中路军沿山后北上,云朔诸城多望风归降者;可以说,彼时情形十分不利于辽朝。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圣宗召集各部军力,派出耶律斜轸总山后兵事,耶律休哥负责南京布防,平州沿海则安排节度使迪里姑与林牙勤德防备宋军偷袭,同时将先前东征高丽未果的军队调回增援。①在这一过程中,被赐剑予权的二位将领都是奔赴南京战场者,足见圣宗对该地的重视。其中耶律抹只时任东京留守,于是年三月甲戌受命率领大军跟随援助耶律休哥的诸部兵进发,并受赐御剑,许以专杀;次日,辽圣宗便决定亲征,并祭祀山川陵庙。②不久,抹只的军队到达南京,先是修缮工事,并在圣宗亲临后与耶律休哥一道逆击宋军于涿州以东,获得局部胜利。③三月癸巳,圣宗派遣耶律谋鲁姑率领禁军中的精锐加入战场,并赐予他象征权力的旗鼓与剑,令其援助休哥。由此可以看出,辽方军队调度极为从容与灵活,辽方将领在统兵过程中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不仅宝剑作为象征专杀与便宜从事的信物被下放给将领,旗鼓与杓窊印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以趣征讨”时反复出现。④此后,辽军捷报频频,终于在是年五月击溃了宋军。反观宋军,宋太宗并未亲临前线,却担心武将权重,处处设防,横加阻挠,最终导致宋军各方接济不周,指挥不灵,终得苦果。⑤可以说,赐剑予权在这场大规模战争中,成为辽圣宗统驭军队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三为征讨高丽的需要:开泰六年(1017),介于辽朝与高丽在江东六州与越界事宋问题上的长久争端,圣宗决定再次讨伐高丽。⑥是年五月戊戌,圣宗任命萧合卓为都统,王继忠为副都统,萧屈烈为都监,并赐予萧合卓宝剑,使其有专杀之权。然而此次征讨却以失败告终,萧合卓一行在攻打高丽兴化军时不克,于是年九月乙卯还师。⑦
2.隐性功能:赐剑予权的政治目的
针对辽圣宗时期的赐剑予权活动,若从受赐者身份角度进行考察,亦能得出些许政治信息。辽圣宗即位之初,太后萧绰曾哭诉:“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⑧前述赐剑予权制度的出现源于圣宗早期维护统治的需要,不久“族属雄强”与“边防未靖”都得到了解决,但这仅为显性功能,“母寡子弱”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危机才是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在萧绰表达完其担忧后,得到了耶律斜轸、韩德让、耶律休哥等人的支持,漆侠先生指出,他们所代表的是皇族的拥护力量。⑨
在圣宗朝受赐宝剑的群体中,韩德威为韩德让之弟,而韩德让家族不仅为景宗、圣宗二朝显赫的大族,据路振《乘轺录》记载,韩德让本人与萧绰之间也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輥?輮?訛《辽史》记载,德威在景宗朝便颇受信任,担任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墓志作“汝州”)、北院宣徽使等职务。?輥?輯?訛《韩德威墓志》亦言,其于保宁十一年(979)“擢居亲近之用,首冠殿庭之班。”?輥?輰?訛可以说,韩德威与其兄韩德让皆为景宗托孤的旧臣、重臣,也是维护圣宗母子统治的核心力量。
耶律隗洼《辽史》无传,经墓志佐证,其与耶律延宁当为一人。《耶律延宁墓志》载,其为皇族宗亲萨割太师之后,亦是景宗朝的藩邸旧臣,在景宗重病卧床之时,耶律延宁甚至提出“愿随从死”,出身上的高贵与政治上的忠诚,使得圣宗即位之后延宁一跃成为节制北方诸部族的封疆之吏,?輥?輱?訛不仅如此,按《秦国太妃墓志》记载,延宁之妻为章圣皇太后(即圣宗钦哀皇后)之妹,?輥?輲?訛如此看来,延宁与圣宗亦有连襟之关系。
受赐宝剑的第三位大臣耶律抹只为隋国王释鲁之后,?輥?輳?訛从这层关系看,他与圣宗初期著名辅政大臣耶律休哥为堂兄弟,休哥亦为释鲁之后,?輥?輴?訛二人皆隶仲父房。耶律休哥在景宗乾亨元年(979)对宋作战中便崭露头角,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于高梁河大败宋军,此后,休哥便长期主持南面边事。作为休哥同房兄弟,抹只早年以皇族身份入侍,其后更是随同休哥在两次对宋作战中大展身手。
谋鲁姑在圣宗朝受赐宝剑的群体中为比较特殊的存在,虽赐剑但并无专杀与便宜之权。谋鲁姑其人,《辽史》无传,石刻史料亦无踪迹,其身份不明,有关记载皆出于《圣宗本纪》中东征高丽与南御北宋时谋鲁姑的零星活动。但可以获知的信息有二:其一是谋鲁姑官任林牙,①其二是谋鲁姑在败宋后与萧继远巡视边疆。②其人其事与《辽史》中《耶律磨鲁古传》恰相重合,③由此可知,谋鲁姑即耶律磨鲁古。磨鲁古之祖为于越曷鲁之弟,太祖时期的六院部夷离堇耶律觌烈,④故《辽史》中将其与同属耶律偶思后裔的曷鲁之孙耶律斜轸⑤并称为“族帅”。⑥关于圣宗虽赐剑磨鲁古令其率领禁军征讨,但并未使其行专杀或便宜之权,或与其父耶律虎古有关:圣宗即位之初,萧绰诏虎古入见,然而虎古性格耿直,先前便于料敌之事上忤于德让之父燕王匡嗣,此次言语上又顶撞韩德让,为德让当庭击毙。⑦韩德让虽权倾一时,但将原属宫分户的玉田韩氏与契丹本族势力中尚且强大并顺从的迭剌部、六院部相衡量,圣宗仍需斡旋与妥协,毕竟统和初辅政大臣之一的耶律斜轸便是这一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虎古之子磨鲁古重得重用,但重用之余也有所保留,虽赐剑却不可便宜专杀便显得合乎情理了。
萧合卓与上述受赐臣子不同,其出身极为低微,为突吕不部部民。合卓的发迹始于统和初年,起初就职于本部,仅为胥吏,但因为其行事严谨,受到圣宗的重视,得以参与政事,被补为南院侍郎。而后合卓平步青云,更是与王继忠分掌北南院枢密使,并在开泰六年(1017)征伐高丽时成为主帅,受赐宝剑。⑧以上仅为《辽史》的说法,笔者认为其深层涵义值得商榷:圣宗之所以任用萧合卓并大胆予权,应当也与政治势力的变化与加强皇权的较量有关。前述圣宗即位之初,以韩德让、耶律休哥、耶律斜轸为辅政大臣,并启用与之有关联的韩德威、耶律延宁、耶律抹只、耶律磨鲁古等人,组成维护圣宗统治的政治集团。但随着圣宗统治的巩固与内忧外患的平息,以及统和二十七年(1009)亲掌权柄,以上或是出自部族酋豪,或是出自外戚连襟,或是出自显赫家族的诸臣,反而使得圣宗在行使皇权时显得处处掣肘。这一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据《耶律室鲁传》记载,耶律室鲁本为六院部部民,但却因为深受圣宗喜爱而成为君王身边的近侍“祇候郎君”,而后更是外放军队,统兵作战,更耐人寻味的是,室鲁后来代替韩德让官拜北院枢密使,受封韩王。在室鲁受命之日,朝野相庆,其原因竟然是“自韩德让知北院,职多废旷”。⑨此后,室鲁之子欧里思亦受重用,官至西南面招讨使,而在此之前的辽代西南面边防却长期被玉田韩氏家族垄断。?輥?輮?訛圣宗启用部民,打压贵族势力,加强皇权的目的昭然若揭。而赐予萧合卓宝剑并给予专杀之权,亦是这一目标的体现之一。
综上,圣宗朝赐剑予权的政治目的是围绕两方面展开的:在圣宗统治前期,内忧外患,景宗的猝然离世使得辽朝境内的诸多部族呈现出一种潜在离心的阴影,而在边境地区,党项侵边、北宋威逼。如此情形,圣宗首要任务是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以稳定内政、部署边防:重用与契丹皇族亲善的玉田韩氏家族、仲父房的耶律休哥与耶律抹只、世袭迭剌部与六院部的贵族耶律斜轸与耶律磨鲁古、作为外戚的连襟耶律延宁等。但此处需要做一解释的是为何圣宗赐剑于德威、抹只、延宁、磨鲁古,而不对德让、休哥、斜轸复行此法?原因是圣宗在统合初年的政治架构中组建了由内到外的两道权力分配阶序,直接为圣宗母子发声且掌军政大权的一批人便是韩德让、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顾命大臣”,他们是皇权传递的第一环节,也是权力分配中获益最大者,并不需要赐剑予权这种形式凸显其尊贵与威信。而作为他们家族成员与势力范围延伸的德威、抹只、延宁、磨鲁古一行人,不管是官阶还是影响,都远远小于第一圈层,但同时真正能将圣宗意志进行扩散与实践的,却正是这些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却全力维护圣宗母子统治的大臣们,因此对其进行赐剑予权,乃是圣宗统治手腕的高妙之处。圣宗自统和二十七年亲政后,不再依赖后族与顾命大臣的支持,这一时期威信与皇权进一步加强,赐剑活动已经没有此前频繁,且赐剑对象也随意化,跳出了贵族群体,转向如萧合卓这样的普通部民,这也是圣宗压制贵族势力,意图体现皇权独尊。
(二)赐剑予权的失语:兴宗、道宗与天祚帝时期
随着圣宗朝政治改革与汉化改革的推进,辽朝彻底完成了封建化的转变,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进入了鼎盛时期,而这一时期亦是辽朝国力发展的鼎盛时期。立储制度的完善,使得此后皇位继承虽有波折,皇族后族偶有较量,①但总体上仍呈现出平稳的态势。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去世,耶律宗真即位,是为辽兴宗。自兴宗至道宗,其间虽有同西夏、阻卜、高丽的零星冲突,但并不动摇辽朝霸主地位,同北宋之间虽有增币之争,但终未开战。总的来说,兴宗、道宗朝七十余年可谓无事。②在这种情况下,赐剑予权作为彰显皇权的临时手段,若大量出现便显得不合时宜了,如针对部族问题,兴宗朝似乎对其拥有了更加强有力的控制,“(重熙十二年)六月丙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③对于以往影响皇权的块垒,兴宗朝已经能从容应对,从极其细微的角度制定规则,将其严格规定在不可逾越的空间之中;除此之外,曾经象征权杖的旗鼓与以示专征的节钺、杓窊印在兴宗、道宗二朝也逐渐淡出视线。但这并不代表赐剑予权从此消失在辽代政治舞台上。
此后见于记载的赐符印与宝剑,仅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一例:《辽史》载阻卜塔里干叛命,道宗授予耶律仁先鹰纽印④与宝剑,命其进行讨伐。《耶律仁先墓志》亦言:“皇上以北鄙达打、术不姑等族寇边,命王为西北路招讨使往讨之。”⑤此次阻卜、鞑靼等北族叛乱,应当是辽代规模较大的一场,有学者认为此次叛乱加重了辽朝政府的内耗。⑥笔者赞同此观点,其实早在咸雍四年(1068),对于西北路诸部族的管理,辽庭便已显现出些许吃力的迹象。首先是西北路发生了自然灾害,如“西北路雨谷,方三十里”,⑦这说明该地发生了严重的龙卷风灾害,同时,是年正月至三月,西京、应州、朔州等地出现饥荒,⑧该地为今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中部,气象系统上受蒙古冷高压影响极大,这说明西北路所在的漠北产生了强烈的倒春寒现象,不出意外,当时西北路诸部族便已经因牛马冻毙、缺衣少食而蠢蠢欲动。除此之外,辽道宗于是年七月设乌古敌烈统军司(前身为乌隈于厥节度使),管辖今呼伦贝尔草原至蒙古国东方省一带的部族,应当是预料到山雨欲来,进行的防秋准备工作,足见其对西北路诸部族的重视。自道宗即位以来,未尝遭遇外患,此次猝不及防,重新启用赐予宝剑与杓窊印的仪式,既突出对此次出征的重视,也显示出道宗在阻卜大规模叛乱问题上的不安。然而虽为赐剑予权,但却并未提及“专杀”或“便宜从事”,这或许是在道宗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下赐予权力信物时的一种弱表达。
最终西北路诸游牧部族没有成为压垮辽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而是东北黑龙江流域一直处于蒙昧状态的渔猎民族生女真使得天祚帝成为辽帝国的亡国之君。由于金朝崛起迅速,以黑水狂飙之势灭亡辽朝,导致有关天祚帝时期的史料颇为稀少,且有东拼西凑之嫌,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苗润博在《辽史探源》中指出,《辽史.天祚纪》的史料来源有三,少部分为耶律俨《皇朝实录》,其余则是抄录史愿《亡辽录》。⑨官方资料来源的缺少,以笔记强充篇幅的做法,使得《辽史》中有关天祚帝的许多记载自相抵牾,而至于天祚帝时期是否还有赐剑予权的做法,于传世文献与石刻史料中皆未得踪迹。
五、结语
综上所述,辽代的赐剑予权活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圣宗以前为酝酿阶段,如太宗朝虽有零星赐剑之举,但多是延续前代的恩信功能,并未与实际效用相结合。圣宗时期出于巩固统治、对外征战的需要,同时得益于汉化改革以及同北宋在制度名物上的互动,赐剑进入高潮,并常能赋予专杀与便宜从事之权。圣宗以后辽朝完成向封建化的转变,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赐剑予权不再是必要之举。从具象角度看,辽代赐剑予权涵有专杀、专征、便宜从事三大特权。而结合辽代政局,可以看出赐剑予权对于帝王而言,因所授群体与相关史事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作用。可以说,赐剑予权的产生、发展与衰落,正与辽代政治史发展的主线相符合。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