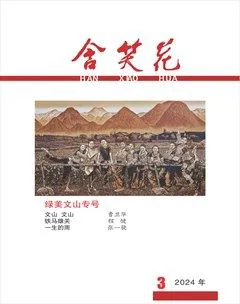一生的雨
2024-06-12张一骁
你记得雨,雨便会来到你的一生中。
天空被几张厚实的云蒙得紧紧地,只洞开了一个小孔,云朵挤在一起,正在商榷一会儿的雨要下多大才好。我们太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雨,让草木及生灵喝个够。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般关注天气了。我从那个四处布满缝隙、头顶小青瓦的土房子里出走十余年,充满过家家、烧洋芋、掏鸟窝、捉泥鳅、放秧田水等的童年,只是紧紧抓住了我人生的前十多年时光。其后经历了青年再到现在的中年,我现在成为一个城市的寄居者,貌似离开了依存土地、靠天吃饭的日子,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那个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农村开始在我脑海中逐渐远去,不管我如何眷念,我的土地该承载的一切似乎在我这里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我时间荒野中自然消亡的部分。其实,反过来说,这是一场我们身不由己的告别。
在我不操心吃饭问题和义务问题的前十多年间,我听得懂鸟鸣,听得清楚植物说的话,能在浑圆的山坡上精准识别菌类的生长地,并在一个有露水的清晨准确的和它们相遇。甚至能够很轻易地根据风走的方向,云的走向判定一场雨到来的时辰。相较于现在的我,那时的我是另外一个我,关于贫穷,我很无辜,我还只是个孩子。
那十多年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会离开这个叫咪西底的村子,离开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地方。村子给我的感觉是很寂静,仿佛我一张嘴说话,整个世界都在听我说话。山坡安安稳稳地一站就是几千年,老树平平安安地一活就是几百年,石桥沉默寡言一躺就是几十年,苞谷铆足劲一长就是几个月,雨水顺顺当当地一下就是几天。草垛像幸福的俘虏,在田地里画地为牢。谁都不担心谁会被什么力量平移到另外的场域,甚至谁会死,死后会去哪里,我们似乎对这些漠不关心。它们却齐刷刷走进我的眼界,走进我的生活,嵌在我所走过的年岁里。十多年,眨眼间,我就稀里糊涂地把它过完了,就这样白活了下来。
这是云贵高原,只要有雨水,什么都能活下去。关注雨水自然成为我一生中重要的事情。要有雨水,就必须要有云,等待云朵不是易事。一朵云不会跟着你的意愿来到你的头顶。在滇东南,头顶的天空像是一条高远的路。春末夏初,一块一块的云相继向东边跑,这种云一般落不到我们这里,雨水被其他地方算计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余粮。在北方人看来,南方出现旱情,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同样,冬天,倘若北方不落雪,我们也觉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干旱确实在发生。冬春两季,天空很难看到云,寡蓝寡蓝的,也不是深邃不见底,更像是辽阔的空乏的镜像,自然也就没有雨。万物渴得要命,皲裂的土地上,偶尔有几株芨芨草、扁茅草之类的耐旱植被抽出萎靡的绿色。其他抵御不了干旱的草木和生灵,处在昏迷中,甚至懒得舒展茎叶,懒得呼吸。在这片几个月不见雨水的土地上,无论是草木还是生灵,抑或是人,一律都在求雨,想尽办法活着。屋后一株柳生的菜籽,因靠近排水沟终于活了过来,果实累累。
没有雨水的日子,时间是干瘪的,在这片小地域任何的地方弯弯曲曲地流动。我常坐在老屋的石阶上,抬头看天。看得出神,眼睛酸涩,困意袭来。许久以后我会迷迷糊糊想起更久以前的某个午后,我也曾这样坐在石阶上,苦思冥想,自我诘问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个村子,村子以外的村子是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么大的地域,究竟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村子。想得深远而入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时间默许了一切的发生。耳边是风吹来的声音,竹叶的响声告诉我,风是先从竹林吹过来的。现在想来,风吹过竹林,会是多么惬意且诗意。不过当时并没有这般感觉,风吹来就吹来了,多么平常,像我们吃饭喝水和呼吸,一阵风吹来和一个人从木凳子上起身一样平常。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事情会一直持续发生在这个地方。
一朵云并没有先于更多的云来到我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我和万物一样的饥渴和灼热。我从石阶上移步中庭,靠在一棵老椿树下,极力避开厌烦的烈日,依然燥热难耐。我又换到屋子旁的榕树下,躲在树荫下。那是一棵很大很有年份的榕树,树冠如盖。阳光依然从树冠的缝隙间照射下来,打在我的肌肤上。阳光比我更熟悉人世间的每一处裂缝。你很难去躲避阳光,所以你只能穿更少的衣服,时不时冲冲凉。一生中你能躲避的东西很少很少,哪怕你暂时能躲得过现在,你的一生也很难绕得过去,有些事情会缠绕你的一生,某段时间、某个场域,你会忘记你的生长而记住这些事情。比如你遇到的曲折,错过的爱情,或者别人能买到而你却始终也买不到的药方。
雨水不来,我把不耐旱的洋菊花、兔耳兰、海棠等花木搬到偏房的阴凉处,我总得关照它们,它们从远处或者近处,或者从其他人家来到我的家里,这就是缘分。能和一些花花草草共命运,时间长来,你也会活成草木的样子,听到草木说话。花木暂时没有体会到陰凉处的恩蕴,依旧懒洋洋的,把卷起来的叶子萎蔫给你看。我懒得再搭理它们,我还有我的事情。我把花盆腾出来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用腾出来的地方迎接一场雨的到来。
打理完这些花花草草,我还要去村子边走走。说是村子边,其实就是走出院子,再往屋后东边走约莫三四十米,便是山坡和整片的林木。我家位于村子最东边,成了每天最先和林木握手的人家。那么茂密的林木,雨季时看得见湿气滋养苔类和蕨类。那么多的林木,其实多次我仅是和它们擦肩而过。这些最常见最常相遇的老伙伴,我置若罔闻,像是没有看见它们错落地站在那片土地一样。回想起来,很是没有礼貌,我应该和它们打招呼的,问声好也行。
林木依然口渴,它们很想饱饱的喝一次够够的水。我知道林木根部的地底深处依然有水,干旱的天气暂时要不了它们的命,要不然它们也不可能存活那么多年。倒是它们懒得从地底深处提水给自己的树干和叶片洗澡。没有天然的储水器,它们把命交给天气和时间,彼此在浩荡的群落中孤单地面对自己的生长。不论如何,一株草、一棵树、一朵菌类、一块石芙子,都不会忘记生长。生长这种使命,在一粒种子形成时候就被嵌入。
每年干旱季节,这样的担忧都要在这片土地涌现,就像我们,每年都要碰到一些坏运气和不理想的境遇。随着雨季的到来,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每一块树皮因历经坎坷而变得凹凸不平。同样,每一个人因经历太多,额头沟壑纵横。
我看到一个人的苍老,是为了进入人群而又远离人群。
立夏后,雨水终于姗姗来迟。那是一个夜晚,屋子里很暗,窗外也很暗,我看不清雨水。但从雨滴撞击青瓦的声音里,我知道雨水落下来了,毫不保留地降落。落在土墙上,落在院子里,落在杉树林里,也落在花盆里。我暂时不能出去,我要等到第二天清晨,一场雨为土地清洗出一个好黎明,之后才会开门迎接迎面扑来的潮湿。我再不像以往,冒冒失失地把自己抛向雨中,把自己淋成一只水猴子,让雨水知道这个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酸汤冷水也能养活的人。我不急于证明自己。其实,这世界、这雨水不会在乎这些,能够头顶云朵的地方,就能够得到雨水共同的恩泽。一个人并没有那么伟大,世界也不会对你特殊照顾。没有特殊的眷顾,到处反而更加欣欣向荣。可惜很多人黄土埋腰也不一定会明白这个理,非要在某个领域,某个地域把自己高高的摆在众人的上头。
人活着,你只需要时刻为死亡这件事做准备,其他的仅是附属品,没必要争个高下。
经历了这么多的雨季,我已经明白我们是离不开雨的,无论我离开这片土地,离开这些古老的作物,离开这些胡子拉杂的男人,还是离开这些不打扮不时髦的女人,我们都需要雨。纷纷扬扬的雨,细密若游丝的雨,还是疾风暴雨。能形容的或者不能形容的雨,都会落在我所经历的任何一个年岁里。当一个人的岁月像荒野一样敞开时,更需要一场场雨来为他证明,证明霜欺雪压的年岁也并非一荒千年,颗粒无收。行走人间,仿佛每个人都在用一生栽种一块土地,一块实实际际的土地或者是心上的土地。很少有没有栽种过的土地,让自己的一生放荒,最多是收成的多少,由不得自己。雨水牵扯着太多的命运,你得相信一场雨,以及一场雨背后的命运。
就像现在,窗外是千万条的雨丝,努力连通云朵和地面上的万事万物。究竟要构建一个怎样的逻辑网,我尚且不知。我在雨丝之外,忙于替麦子、稻秧、果木树、漫山遍野的草木、蕨类和菌类喝足水,让它们饱满且充实。因为身外有物,我仿佛在替万千的草木和生灵活着,我活得好,它们跟随我摇曳,我活得不好,它们为我殚精竭虑。我再不能以一个屋檐下的人、温室里的花草式的独自活。另一个我,永远行走在旱得冒烟的土地上祈求雨水,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流年。当我端起桌上那碗白花花的米饭,我就知道,合理的降雨,壮实的作物,才能让我饱腹,继而好好地活下去。我关心它们胜过关心我自己。
雨后,行走山野荒地,我们能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很难想象,一场雨,能够唤醒那么多的生灵。我甚至怀疑生灵体内有一个锈蚀的生物钟,雨水如发条一般,准时启动它们体内的生长机器。该长叶的长叶,该开花的开花。短短几天,漫山遍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幻色彩。雨水是最有用最百搭的肥料。草木发芽、生长、抽薹、开花、结果,甚至把种子再次回收到自己的根部,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株植物便因此获得自己最独有的便签。一种植物有一种的叫法,一种菌类有一种喊法,一种生灵有自己独有的名字。漫山遍野长满不同的草木和生灵,放眼望去,遍野都是名字,遍地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像一群走散多年的名词。我手拿一条小木棍,渐次把它们赶到一起,圈养在一篇文章里。这样的历程谈不上艰辛,文字里透着草木香气。
最让我觉得神奇的是,有一种长在土埂上的花,具体什么名字我叫不上。它的叶子和茎与水仙花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应该属于水仙科植物,我有很大的把握。我租住的房子周围就有,它们把肥硕的块茎深埋在土里,始终不愿意张扬。冬春两季,它的叶片枯萎,你根本不会知道那些土埂上会藏有绽放。雨水不来,它们隐藏很深,不会轻易露出一点马脚。很难想象,一朵花居然能够在时间里潜藏。只要雨水不来,它们在浩渺的时间里便深度睡眠。其实就是那么几个月后,具体来说是那么两三天。一阵透透的雨后,我一转身,它们齐刷刷从土埂上冒出来,全开了花,一大片一大片的,好像谁吹了集结号,非要全部的开,整齐的开,热闹非凡。谁也不能上前,谁也不能掉队,就要约好了开在那几个时辰。
土地终究埋不住花朵,雨后便在太阳底下摊牌。
美丽且开得齐整的花,我不可能对它们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下班后,我走近它们,花朵摇曳,粉粉的,煞是好看。遇见最美的花朵是一天之所幸。过个两三天,这些花朵断然不会再重新开一次,那些风,断然没有可能同时摇晃那么多的花朵。一场雨,让一丛花朵有了花本该有的尊严。多少年后,我才幡然惊醒,我何尝不是和这些花一样,淋了几场雨,就想让岁月开花。淋了几场雨,我就长大了。
一场雨看似有很大的神奇魔力,如果你剖开来看,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它开始只是某个池塘、某条河流、某片海域的小小水分子,在太阳的炙烤下,向上爬升,一点一点爬,向天上汇集,一朵云的肥胖程度,往往取决于它能吸纳多少水分,拥抱多少颗水珠。还需要这些水蒸气遗忘以前的生活,掸尽自身的杂质,不以池塘、河湖和大海自居,干干净净地作一颗水珠,作一颗透透亮亮的水珠。每一次的时间轮转,原来的它已经消失了,它将陷入自我孤独,和更孤独的水珠走到一起。一种向上攀爬的孤独,变得轻盈而生动。
还需要一场风,可以是东风、东南风,抑或是西南季风,讓云朵行走起来。其实,风的使命并不是要推动云的行走,风有风的盘算。一朵云的行走和一个人在世间的行走差不多,令人胆战心惊。云朵要在天上走天上的路,天空辽阔,漫无边际,没有一条固定的道,也许今天偏北,明天就会偏南。是什么力量拖着一朵云走命定的路,一直是一个谜。云朵走得太快不行,云朵里水珠的孤独,需要沿途逐渐稀释。走得太慢也不行,时间会把一朵云逐渐磨损、耗尽。一朵云有诸多的不确定性,能够落下雨水的云朵,它的过往令人津津乐道。
一个人的行走也好不到哪里去,世界上看似路子很多,猫有猫的路,耗子有耗子的路。人的道看似很多,但是你只能选择走一条。你不可能同时出现好几个自己,你往东走,他往西走,或者一个往北,一个往南。你的大脑存储不了那么多东西。东边走的你看见了水仙花开。南边的你正在栽种洋菊花、剑兰和海棠。西边的你和一场雨相遇,淋个里外凉透。北方的你正向霜和雪进发。哪有那么多荒诞的事。一个人的一生,你的时间就是这么多,谁比谁不会多一点。行走的疆域和扩张的领域同样如此。你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并把自己全身心地走上这条道。不管你走哪一条道,你都不可能只遇到太阳而遇不到月亮,只有白天而无黑夜,好运与曲折紧紧抱在一起,你分不开它们。换句话说,就是你一生将有干不完的活计,你还要兼顾与他人的生活交集。你甚至不能浪费一点一滴的生活。最后,你依然只是为了活下去,没有更多一点幸福的可能。一个人,并不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见过很多很多的世面,干了很多很多的活计,你就会过得很幸福、很自由、很自在,有时候恰恰相反。
你在人间贩卖掉的日子,多半是青春被买走只留下粗糙的年岁。
我看到过村里的男人带着媳妇,在一个雨夜,悄悄辞别熟睡的孩子,像一朵云一样飘进一个陌生的城市,绑那这辈子也绑不完的钢筋,挑永远也挑不完的砂浆,身份扑朔迷离。一朵云,把所有的雨水落在那个城市,世间就再也不出现这样一朵云了。同样,从此村子里又少了一个男人和女人,多了一个束手无策的留守儿童。三岁看小,没有父母的关怀的七岁留守儿童看不到老。你一生所渴望的那朵云,终究飘不到这个村子。你不能怪一场雨因此带来了什么,你应该庆幸一场雨见证了什么,让你明白了什么。
一场雨还会带来惊心动魄。特别在乡下,每个人都要经历且独自面对一场雨的寂寞和恐惧,无论在屋檐下还是在荒野中,你少不了和一场雨打上好多次交道。
有一次,母亲把一场子的麦子交给我,他们去另一块土地上忙活其他的活计,把我留在院子里看护麦子。一场子的麦子,一粒紧挨着一粒,静静地躺在水泥地板上,彼此互不侵犯。临近日中,麦粒的水分正在烈日下蒸发,在光晕里我甚至能够看清楚水汽氤氲的气流在光束里漂浮。午后,一场雨带来了惊心动魄。我看到厚实的云朵从村子前的山顶垮塌到山谷,暗黑色的云朵下,灰白色的雨幕向着我袭来。我使尽浑身解数,慌忙收拾麦子,在“雨口夺食”。仍然有两袋多的麦子浸泡在雨水中。那场雨,有麦子的气息。
事实上,一场雨带走了两袋多麦子的收成,我并没有因此被父母“修理”。深感惭愧。父母眼中,我始终比两袋多的麦子金贵,以致后来我都没有轻贱过自己。那场雨,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潮湿。那一刻,我恍然明白,比起下在荒野中的雨,下在地块上的雨,或者下在小路上和院子中的雨,下在心头上的雨,会淋湿你的一辈子。然后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脑中、梦境中,会出现一个小男孩,挥舞着铲子,整理着麻袋,手脚凌乱的在收拾麦子,直到满头大汗,脖子里喊也喊不出声音……
你也可以选择安静地看雨,小雨有小雨的看法,大雨有大雨的疾骤。一个人看雨,时间会慢下来。你等待许多水珠在瓦沟间汇集,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四处溅开的小水珠也在侧目观察你,看你这副新面孔。之于它们,你的这副面孔是陌生的。它在亿万颗雨珠中打算和你认识,非常难得。人世间,其实就是一种陌生主动的间接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去接触另一种陌生。最终两种陌生冲破中间的隔栏,走到了一起才变得熟悉。当水珠越汇越多,最后顺着瓦檐流下来,在滴落的瞬间,水珠熟悉了你。成为你想起雨就能想起来的清凉。当一个人百无聊赖的去认识一滴水珠,你不能说他是孤独的无厘头的,他已经寻找到新的慰藉,让自己安静下来。
一个人的心中,无论他深处闹市或者何种喧嚣,他的体内将永远有水珠的滴答声。他的内心是柔软的,有能让他如水汽般漂浮起来的安静。他的时间,将会走得很慢很慢。
在很多人看来,赏雨是一件很高级很浪漫的事情,认为每一场雨都是新的,会催发新的叶子,吹开新的花朵,洗出一个人崭新的灵魂。倘若是一个老泪纵横的人,他将在生活的深渊中置换回一个新的自己。其实这些雨都是被前人用旧的雨。这些细密的雨丝,曾经穿过城市的下水道,学校的操场,牲畜的圈舍,村庄,荒坡,墓地,麦田,甚至生死场,等等,已是百转千回。特别是清明时节的雨,它们从海上急匆匆向内地赶路,比背井离乡的人还要先一步赶回到他们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的故乡,替这些人回到他们祖先的坟头。一场雨的慈悲,不仅仅是让草木和生灵从旱得喉咙冒烟到喝得经脉粗大,得到孜孜不倦的滋养,而更多的是像一颗草药一般,无意识进入你的腹部,在你的体内熬制、煎煮和提纯,涵养治愈灵魂的药性,让你能在每一场雨中主动认领自己,指引自己回家。
在雨中,葉片舒展,鸡狗不叫,老屋紧闭着嘴,我看见了自己的小时候。小时候多傻,盼望自己在雨中长大。现在,又盼望自己能够回到小时候,还是一样的傻。哪个年纪该干哪个年纪的事情,你把它做好了,遗憾会少很多。
你把一场雨看旧了看腻了,一场雨也把你熬老了熬倒了。在乡下,最关心雨的,除了麦子,稻子,玉米,蚕豆,白菜,土豆等一众粮食和菜蔬。还有依附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农人。雨水不来,农人均得了懒病,他们很随意地把自己丢在床上,沙发上,偏檐下,墙根脚。太阳从山那边起身他们也不愿起身。他们知道,靠天吃饭,你就得听从老天的安排,你自发走到老天的前面,老天也不会给你好过。雨水不来,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因不能尽快把自己投放到土地上、融入农忙中而内心焦虑,焦虑到住在同一个院子的人,他们甚至不愿意在早晨或傍晚彼此打声招呼,好像谁也没有看见谁一样。在等待雨水到来的日子,我看到时间对人和事物的耐心等待,人可以接受雨水的枯减,却不愿接受自己的闲暇、自己的干涸。
农人永远这样以为,他们一生下来就应该永远永远地忙碌,闲下来将会成为自己的另一种羞耻。
和人一样,一年中太阳在夏季起得最早,在冬季起得最晚。冬季气温低,谁都想懒在床上多眯一会儿。夏季水草好,空气潮湿,能在夏季早早地起来,呼吸到最早的空气,你的喉咙会变得很舒服。对于农人来说,多好多清新的空气,都不如晨起的一口旱烟来得实在。鸡也会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游走,用咕咕咕的声音唤醒农人,给它们带来谷粒和玉米粒。它们就等这一口。一天中,没有吃到来自主人在清晨所给的粮食,那一天鸡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整天围着院里院外闲逛。它把所有的想法,都换成了无厘头的游走。一只鸡不会关心雨,雨来不来,它都能从主人那里获得粮食。
雨水来了后,农人的懒病瞬间被农活治愈,一场雨让农人忙得手忙脚乱。玉米地需要被农人翻起来,让更深层的土块翻身晒太阳。雷响田需要农人亲力亲为的去打理,做成供秧苗安身立命的床被。菜地要移苗,粪土要发酵……同样需要那双粗糙的手,淌汗的额头。常年以往,农人只能从大脑中翻出那张几代农人集智慧绘制地完完整整的耕作图,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了然于心。这个时候,他们永远比太阳起得早。根据耕作图里指引的轻重缓急,制备农具,置办化肥和良种,然后把一众牲畜喂得饱饱的,从家赶往不同的地块。我父母的流程也和其他农人的一样,大抵就是如此。同一个村子,大家的活法差不了多少。
我曾多次翻看他们的背篓,里面最常见的就是镰刀、水壶、冷饭、咸菜和围腰。如果我参与了这天的农活,背篓里还会有水果和饼干,那些都是奢侈品,在山头的地块上,能饱腹的,都会吃出大餐的味道。一场雨能带给农人的,就是这么多的活计,一个母亲或者一个父亲带给孩子的,也就是这么多的饭食和零食。
那一天,所有人将埋在无休止的农活中,抬起头,直直腰的功夫也没有。一个农人的栽种,看似还在翻地和播种,其实其后的管护,收获,归仓,贱卖,一季一系列的流程,早已经在他们的心中走过并结束了。有时候,我真担心他们过于忙碌,让自己活不过秋天。
但我们从不抱怨一场雨带给我们这么繁重的活计,忙不完的事情。我们在内心深处反而感激头顶上的那些云朵,来自池塘、小溪小河,大江大湖大海的那些水汽,因为天上有雨,我们才有了种养,有了收成。在乡下,往往是雨水刚刚消散,锄头和镰刀还没有来得及生锈,庄稼人走到最接近太阳的地方,便和上午才分开的麦田相见。农人活下去,不需要啥勇气,需要的是坚持,用过去的每一天,积累成过去的年年岁岁。用无休止的劳动,欣然逆来顺受。
我在村中生活的那十多年,大抵就是这样,没有太多的新意,也没有太多的新活法,看过了太多的事,走过了太多的场合,也淋过太多的雨。把什么事情都经历了个遍,把该淋的雨也淋了个遍,可以预见的是再待下去个几十年,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也很难遇到啥可言可谈的新鲜事。倘若我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一辈子的谈资将会是庄稼的病虫害,杂草的去除法,草药的种类和药性,风湿病、肩周炎、腰肌劳损的病变,等等。我万不可能再谈论其他的,如果再沿着生活继续走下去,将会是娶妻生子,赡养父母,偶尔参加一些红白事,认领一些风俗习俗和礼节。或者被无意料的变故击中心脏。离开这些,我将成为一个木讷的人,从自己的侃侃而谈又顺从外乡人、城里人的侃侃而谈。我将成为人群中最无话可说的那个人,像一条刚被雨淋湿的老狗,站在一群人的前面,耸拉着脑袋,耷拉着眼皮,无助且可怜。
我是被一场雨从那个咪西底的村子运达另一个陌生城市的。十五岁那年,我从咪西底村前往文山市区读书,离开那天,一场雨把院子洗得干净。母亲终于从农活里直起身子,目送我离开。车还没有到站,我抬着雨伞回望村子,这个老地方依然是老样子。该绿的绿,该黄的黄。我将要把这个村子交给草木和生灵,交给我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那群农人。交给那一场场说来就来,抑或该来却不来的雨。我不需要叮嘱它们什么和告诫它们什么,反而它们要交代我很多,刚要张嘴和我说,又变成一串古老的省略号。
一条狗要守好一户人家,一群人要守护好一个村子,突然变成了难而又难的事情。
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一样,看见云朵就想到一场雨的一生、拿起镰刀就想到庄稼的一生、扛起犁耙就想到耕牛的一生、抬起饭碗就想到父母的一生……不会这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一生。我将要去何方,未来会走到何种境地,和什么样的陌生接触,碰撞出什么样的熟悉,看不见尽头。我似乎突然被一场雨淋湿,被一段时间埋了起来。如果未来的光束照不见我,我打算一辈子埋在这段时间里,像做了一场梦。如果前路真的打不开,就去接受,给未来系个花样。我只能这样想。
那一天,山谷里的云道仍在源源不断地向我头顶的云朵供应雨水,一场雨暂时不会停下来,为我的一生让出过道。那年我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
人的一生挥霍不了几场雨,一场雨把你从童年搬到青年是容易的事情,一场雨再把你从青年搬运到中年更是眨眼间的事。在我印象中,我才从童年的谷雨中爬出来,同庄稼一起站在旷野淋了几场雨,突然间就来到了中年。有些悲伤。那天,我就这样安安稳稳地端坐在窗台处,望着这异乡的雨。雨丝依然细密,夹杂着店铺的音乐声,内心本应舒缓却变得紧张,我张望着屋檐下的水珠,一滴,两滴,三滴……我失去了内心的宁静与和平。我多么希望小时候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那颗小水珠,再次穿越时间和空间,主动来看看我。观察了很久很久,始终找不到童年里那一颗透凉透凉的小水珠。遗失在心底的小水珠,它永远不再回来。
我成了一个不再受小水珠待见的人,是啊!这么多年来,我关注花的绽放,林木的饥渴,牲畜的无忧无虑,农人的靠天吃饭,我却始终没有关注一场雨的成熟和生死。雨的变化其实也是人的变化,雨可以让人生长,也可以让你的一生泛滥。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要去追逐一场雨,直到把自己全部淋湿才打算回去向生活自首。
我已经把一天的时间拿来作案牍之事,思考花草树木之外的事,所看见的熟悉都是真实的陌生。我失去了我的村庄,我的草木,我熟悉的生灵。好在我在这个城市再一次看到了熟悉的雨。当不规整形状的云朵从我故乡的方向带来雨水,我便经常在熄了火的车里,安安静静听雨声。或者选择一个安静的城郊,安静地听雨声里的蛙声。早年我居住的村子,蛙声最为动听。每一只青蛙都抱着一只小鼓。青蛙的小鼓不会敲给花朵听,也不会敲给云朵听。夏季的雨,会准时为这些青蛙奏响前奏,剩下的时间交给青蛙,每一只青蛙会铆足劲,捶响自己的鼓面。当你听完青蛙的鼓乐,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得到一个好睡眠,你在这个交易中狠狠地赚了一笔。
雨正在时间里变老。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一个雨天回了一趟故乡。雨中的故乡依旧是老样子,十多年来没有太多的变化。要说真的不同,就是房子老了,荒地多了,人也少了。老狗不知跑向何处,没有和我用一个字辈的人,在村子不同的角落渐次走失。我熟悉的本地冷水稻已经被不知品种的杂交水稻所代替,和我做了多年忘年交的高粱,已经卷铺盖到另外的地域谋求生路。仿佛时间在这个村子上空开了一道口子,把一切衰老的东西都往天上送。叫不出名字的农人见到我,总是要拉住问长问短。
在雨中,他们的热情和多年一样没有丝毫的衰减。他们是被故乡的雨水洗干净过的人,手袖和裤管沾满泥土但灵魂干干净净。
我庆幸选择在一个雨天回到故乡,回到那个充满霉臭味的老房子。这座老房子,多少次尝试在一场暴雨中飞向天空上的裂口,又在多少个有星空的夜晚安然降落,抛开逃跑的念头。曾经住在这座老房子里的那个少年,却在梦中一次次飞回到这座老房子,像一只经年不走的山麻雀,在墙洞里、裂缝里筑巢为家,和这座老房子静悄悄地生活,彼此相安无事。其实可以预料的事,这样的坚持不会太久,再来个几十年,再来几十场雨,时间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小房子从村子里抹去,成为一个小事件,一个平平常常的小事件。那个时候,你熟悉的云朵下不再会有这样的一所小房子。即使在雨里,你多想再一次成为那个不管吃穿,整日玩过家家、在粪堆火里烧洋芋、上树掏鸟窝、下田捉泥鳅的孩子,你终究和村子一起老去,和小房子一样消逝。假使这样的场景仍然未付诸实际,像一个梦,等你梦醒来,你仍然会不敢相信这么一个梦,你会小心翼翼且轻飘飘地把剩下的日子一点一滴地过完。
一场雨,定会让你心惊胆战。你得在一场雨里认命。
行走人间,每个人的心头都有属于每个人的雨季,童年的你,中年的你,老年的你,心头的雨是不同的,当有一天,时间老人提着灯笼,颤巍巍走向你,告诉你你一生的雨季已经用完,后面你将面对的是干涸和搁浅,那么请你收回你的潮湿和不甘,安静回礼,像你出生时,亲朋好友用欢庆的仪式迎接你一样,你回以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你需要慎重且严肃的和一场雨告别,感谢雨水这么多年不远千里,滋养你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能够坦然接受人生旱涝的人。
这人间你已经来过了,和雨水一起来过的。再怎么蒼老的雨水,都愿意成为你一生的拐杖,扶着你穿过摇摇晃晃的人间。
【作者简介】张一骁,云南文山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美文》《滇池》《阳光》《散文诗》《鄂尔多斯》《牡丹》《含笑花》等刊物,有作品入选《云南文学年度选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