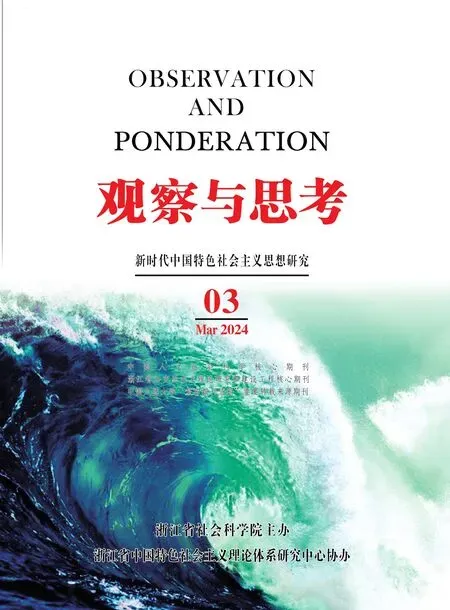理论驿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怎样制定出来的?
——再读《论犹太人问题》
2024-06-10冯景源
冯景源
提要:在我国学界,有的论者一谈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时就论及《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马克思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经过理论研究制定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理论驿站。这个理论驿站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有重要的关系。这里,主要研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科学理论是怎样产生的。理论驿站是要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内在关系上研究其发展。这需要对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手稿》、1843 年《论犹太人问题》、1844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内在关系作深入的剖析。不研究这三部经典著作,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后的发展就没有了根基。理论驿站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是我在一本新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论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 年版)中提出来的。在这部著作中,理论驿站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平面结构,是由一种理论运用、推广出来的。理论驿站不同,是一个历史的、逻辑的方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论。在这部著作中主要是对“三个组成部分”展开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缺乏深入研究。现在研究这个问题,刚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矛盾:版本的问题。以上说的这三部经典著作,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刊载于“全集”第一卷;另一个是1843 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刊载于“文集”。在“文集”中,既刊载了1843 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也刊载了1844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且排序有了颠倒,即1844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前,而1843 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在后。这两个版本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集”是1956 年出版的,“文集”是2009 年出版的。“文集”说新版的译文准确,我的研究只能采用这一说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为此,我有言在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第一次批判——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开始
1859 年,马克思在总结他的理论研究的时候这样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2、411、411-412 页。这里说的都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前者是“批判性分析”(1843 年),后者是“导言”(1844年),这是两部著作。这一点在下面的分析中才能表现出来。
(一)两个“苦恼的疑问”——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是其理论创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说的“苦恼的疑问”是两个,对这两个“苦恼的疑问”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一个“苦恼的疑问”是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说:
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2、411、411-412 页。
第二个“苦恼的疑问”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理解。
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2、411、411-412 页。
纵观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有两个从社会舞台退居书斋的过程。一次是从《莱茵报》被查封开始,一次是从第一国际解散开始。每次都有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两次期间,马克思都进行理论研究,其研究成果就是通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这两次退回书斋研究的成果。我现在的研究就是第一次的研究成果。它包括人们常说的两个转变: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个看法有偏颇之处,我下面会谈到)。这里的转变都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达到的,其转变就是由两个“苦恼的疑问”引起的。
(二)普罗米修斯精神是两个“苦恼的疑问”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大学是学法律的,毕业的时候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罗米修斯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心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实践精神。这两个方面可从他的中学毕业论文到《莱茵报》被查封这一阶段的态度转变中看得出来。
他的中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青年人职业选择的考虑。那时,他就确定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马克思指出: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7、190 页。
马克思在大学时是学法律专业的,可他为什么爱好哲学呢?他认为,哲学就是普罗米修斯精神,哲学就是为人类的幸福“盗天火”。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就是这样说的: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
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7、190 页。
如果说,这是马克思学生时的志向,那么,经过《莱茵报》的实践,他获得了两个“苦恼的疑问”。在报纸被查封的那天,他在该报上刊登了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的画像,青年马克思的这个举动十分不寻常,表示着他要为实践普罗米修斯献身精神而奋斗。
(三)研究两个“苦恼的疑问”的重要意义
1.对第一个“苦恼的疑问”的研究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开始,也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开始。马克思的第一个“苦恼的疑问”是物质利益问题,为什么要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呢?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就从这里研究开始。
物质利益是一个社会发展原因的问题。社会发展是由于物质的原因呢?还是由于精神的原因呢?所谓社会,就是黑格尔说的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市民社会的研究是在他的法哲学中。《法哲学原理》(以下简称“《法哲学》”)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任教授之后的第3 年出版的一本教材,正是这本教材,使他的哲学成了国家哲学。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具体运用。黑格尔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批判它的法哲学就是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就是批判它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2.物质利益的性质与研究对象的选择。物质利益研究的重点,不是唯心唯物的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当时最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研究的。《法哲学》的性质是属于历史观的问题,而历史观的问题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3.针对这个逻辑起点,我国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再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另一种认为是从两个“苦恼的疑问”开始的。我是赞成后者的。前者的观点是偏颇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观,既不是单一文本解读,也不是“三个组成部分”的平面结构推移,更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运用、推广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在实践中的、理论的“苦恼的疑问”(历史之谜)基础上产生的。对此,恩格斯有很好的说明。
1869 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409 页。
4.马克思研究物质利益问题是一个过程,是由两篇文章表示的。第一篇文章是1843 年夏天写的。1843 年3 月18 日《莱茵报》被查封,当天的报纸刊登了普罗米修斯画像之后,马克思来到了克罗茨纳赫。这是他的未婚妻燕妮的娘家。他们订婚后燕妮等了他7 年,就在那时二人结婚。马克思客居克罗茨纳赫,这时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所以,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又称《克罗茨纳赫》(手稿)。
5.黑格尔国家观的泛神论唯心主义,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中选择了《法哲学》,从这一著作中又选择了国家观的理论。
黑格尔国家观的主要观点:
黑格尔国家观是他的《法哲学》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他把他前面的家庭、市民社会联系起来论述。这种论述,就是他的整个哲学的运用。马克思批判的这一章,是这章的二六一至三三三节,可以说包含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称黑格尔哲学体系是一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黑格尔的国家观,就是这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具体体现。现在,就来看看国家观中的主要观点。
(1)国家观理论。在第二七二节中说:“(国家的合理性)人们所必须希求于国家的,不外乎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因此,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是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做地上的神物……”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324-325 页。国家是什么?是自在自为的地上的神,是绝对的观念,是精神。这个论断就是,国家是精神为自己创造的世界。
(2)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手稿)中对《法哲学》第二六二节的分析和批判。
第二六二节:“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于是这种精神便把自己这种有限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给上述两个领域,把所有的个人当做群体来分配,这样,对于单个人来说,这种分配就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为中介的。”
如果我们把这一命题译成普通的话,那就是这样:
国家怎样同家庭和市民社会发生关系,——这是由“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所规定的。因此,国家的理性对国家材料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间的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中无意识地偶然地产生出来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仿佛是黑暗的天然的基础,从这一基础上燃起国家的火炬。国家的材料应理解为国家的事务、家庭和市民社会,因为它们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它们是国家本身的参加者。
这种看法在下述两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1)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做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做国家的有限性。这一国家把自己分为这些领域,并以它们为前提,它这样做“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它划分自己,目的是……”它“于是便把自己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给这两个领域,……这样,……这种分配就是以……为中介的”。所谓“现实的理念”(即无限的现实的精神)被描述成似乎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抱着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它把自己划分为有限的领域;它这样做是为了“返还于自身,成为自为的”,同时,它这样做,是要使结果恰恰成为在现实中存在的那样。
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249-250、253-254 页。
对这一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进一步批判,是在第二六六节。
第二六六节:“但是,精神本身不仅作为这种(哪一种?)必然性,而且作为这种必然性的理想性和实在内容,都是客观的和现实的;由此可见,这种实体性的普遍性是自为的对象和目的,因此,上述的必然性同样存在于自由的形态中。”
因此,家庭和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推移在于:本身就是国家精神的这两个领域的精神现在也把自己当做这种国家精神来看待,并变成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实在内容的那种自为的现实的东西。可见,推移不是从家庭的特殊本质等等中引伸出来,也不是从国家的特殊本质中引伸出来,而是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这正是黑格尔在逻辑中所玩弄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推移。在自然哲学中也玩弄这种推移——从无机界到生物界的推移。永远是同样的一些范畴时而为这一些领域,时而为另一些领域提供灵魂。总之,就是在替各个具体规定寻求适应于它们的抽象规定。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249-250、253-254 页。
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到,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用的方法,是他哲学体系中的普遍使用的方法,是他的方法在《法哲学》中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方法论的批判非常重要。很多的读者不可能读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但是常常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遇到逻辑的泛神论的概念。马克思在这里的批判,可以说使一些读者比较容易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秘密。
(3)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理性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理论批判也十分重要。这一批判是针对黑格尔《法哲学》第二六七节的。
第二六七节:“理想性中的必然性就是理念内部自身的发展;作为主观的实体性,这种必然性是政治情绪;作为客观的实体性则不同,它是国家的机体,即真正的政治国家和国家制度。”
在这里主体是“理想性中的必然性”,“理念内部自身”,而谓语则是政治情绪和政治制度。译成普通人的话就是这样:政治情绪是国家的主观实体,政治制度是国家的客观实体。所以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到国家的这种逻辑发展纯粹是一种假象,因为这里没有表明:家庭的情绪、市民社会的情绪、家庭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本身怎样对待政治情绪和政治制度,和它们发生怎样的联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情绪”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254-255 页。
以上这段文字,主要是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为什么要批判黑格尔的理性理论呢?是为了进一步批判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可以说黑格尔的这一方法论是由他的理性理论辅助完成的。不了解黑格尔的理性理论就很难真正地理解逻辑的泛神论的意义。理性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里,借着这一方法论简略作一下说明。
第一,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论,总称为逻辑的泛神论的唯心主义。
第二,这一方法的应用,可称为理性唯心主义。例如,在《法哲学》“序言”中的名言: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13-14、14、14 页。这是在“序言”中强调理性的意义。“现在这本书是以国家学为内容的,既然如此,它就是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的尝试,除此以外,它什么也不是。”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13-14、14、14 页。再进一步论述国家这一章中的第二五八节中“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13-14、14、14 页。。
第三,理性的作用。作用有二:一是认识的作用,二是中介的作用。作为认识的作用。黑格尔论证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13-14、14、14 页。这里存在的东西,指的是现时代的必然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哲学说的存在就是现时代的必然性。
作为中介,是通过思维抽象,运用概念反映本质的各个环节来理解这一时代的必然性。这一切都是通过理性来解决的。所以理性既是主体又是中介:理性可以分解自身(异化)、认识自身、反还自身。像神创造世界一样那样神秘。
马克思非常重视逻辑的泛神论的唯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其中的理性的批判,认为其中有合理的内核。我现在的研究,就是为了剥出这个合理的内核作准备。
二、《论犹太人问题》研究的意义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1843 年秋天写于克罗茨纳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和1843年夏写的《克罗茨纳赫》(手稿)相联系的内容,即两个“苦恼的疑问”中的另一个疑问: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
马克思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和他正在写的文章有关,都是他要批判、研究的内容。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他的思想就不能向前发展。所以,写了以上的文章之后,他紧接着就开始了这篇文章的写作。一篇是写于夏天,一个篇写于秋天。可将之称作姊妹篇。可是,《全集》和《文集》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排版却不同。现在,研究这些经典著作,必须按照准确翻译的版本来进行。这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排版前后的样子。但是,按照思想发展,我还是把1843 年的《论犹太人问题》放到1844 年的《导言》前面来研究。
(一)《论犹太人问题》主要内容
马克思写作这一著作是由于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引起的。犹太人有什么问题呢?犹太人和基督教有关系。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前期,有一个犹太人如何从封建专制的普鲁士王国解放的问题。这是当时德国社会的政治问题。马克思遇到的“苦恼的疑问”中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理解的问题,这是黑格尔市民社会中引起的人类解放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德国社会的重要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又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解决呢?当时的马克思认为,应当首先解决德国犹太人的政治问题,才能解决人类解放的问题。这样,就有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
(二)马克思写作《论犹太人问题》的特点
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开头的鲍威尔的两篇文章的题目中。
(1)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 年不伦瑞克版。
(2)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3 年在苏黎世—温特图尔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第56—71 页。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21 页。
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做呢?原因有二。首先是科学性,把论题的观点原封不动地摆出来;其次是说明时间:1843 年,是当时的时代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当时要解决的政治问题。
(三)鲍威尔问题核心是什么?
是解放问题。不是一般的解放,而是政治解放,是德国人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鲍威尔这个大理论家提出来的。鲍威尔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首领。鲍威尔问题是根据德国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
鲍威尔是个什么样的理论家?他的专长是研究基督教。他的两篇文章就代表着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手稿)中研究的就是解放问题。这是两种解放理论的较量。这可以说是马克思遇到的两个“苦恼的疑问”中的一种新的理论疑问。这一疑问又是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观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一解决又促进了他的理论发展。
开宗明义地摆出解放性质的分岐。这正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手稿)研究中应包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
德国的犹太人渴望解放。他们渴望什么样的解放?公民的解放,政治解放。布鲁诺·鲍威尔回答他们说: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怎么可以使你们自由呢?你们犹太人,要是为自己即为犹太人要求一种特殊的解放,你们就是利己主义者。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而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而奋斗。而你们所受的特种压迫和耻辱,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例外,相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证实。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21 页。
这里,马克思对人进行了分析:人、德国人、德国犹太人。这三种人的解放具有不同的性质。德国人的解放,正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手稿)中研究的问题,即市民社会中人的解放。德国犹太人的解放,是从宗教中解放的问题,即获得人权的问题。人的解放,这是在以上两个解放之后才可能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称之为“通则”。
(四)马克思的“通则”及其重要意义
意义一,“通则”是什么?就是鲍威尔不知道的人类解放的三种形式及其关系: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及其内在关系。
意义二,“通则”是对着史学方法论的。殊不知,鲍威尔的宗教解放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是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黑格尔那里是包括在逻辑的泛神论的唯心主义之中的,即包括在精神中,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包括在思维中。到了鲍威尔这里,史学的理解变成了世俗的问题。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是有历史功劳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的解放(人权)及其能力,都要在人世间(世俗的市民社会)来寻求。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27、39、39、40 页。这里,主要指的是宗教解放的世俗意义:它是人的解放的中间形式,即世俗的、实际的解放。
马克思说的“通则”,是历史发展中内在联系的规律。这种通则不是神的意旨、精神的理性,而是客观的历史自己的。
意义三,“通则”说的进步(通过政治解放获得人权),这是相对于封建特权说的,也即神权(王权神授)说的。这是世俗的历史观。鲍威尔不研究世俗的历史,他研究的是宗教史,这是不够的。马克思不同,政治解放他研究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历史,这是世俗的历史,研究人权的发展史。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27、39、39、40 页。在马克思看来,把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搞清楚,就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依照鲍威尔的见解,人为了能够获得普遍人权,就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所谓人权,确切地说,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即它们的发现者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的形式吧!”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27、39、39、40 页。下面就是马克思对人权的引文及其研究:
1791 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0 条:“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即使是宗教信仰,而遭到排斥。”1791 年宪法第I 编确认“每个人履行自己信守的宗教礼拜的自由”是人权。1793 年人权……宣言第7 条把“履行礼拜的自由”列为人权。是的,关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的权利、集会权利和履行礼拜的权利,甚至这样写道:“宣布这些权利的必要性,是以专制政体的存在或以对它的近期记忆为前提的。”对照1795 年宪法第XIV 编第354 条。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27、39、39、40 页。
马克思还有其他引文,略去。在马克思分析人权宣言时,关于民主制度中的自由的问题对人们应是有启发的。人们常说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自由应该怎样理解?
马克思的分析很有启迪。马克思指出:“自由是什么呢?第6 条:‘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或者按照1791 年人权宣言:‘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27、39、39、40 页。这里原文有一个注,现抄录如下:
1843 年夏,马克思在研读威·瓦克斯穆特的著作《革命时期的法国史》时发现菲·约·本·毕舍和皮·塞·卢-拉维涅编纂的《法国革命议会史》(四十卷集)1834—1838 年巴黎版为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外,马克思还研读了他本人的巴黎藏书之一、由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加代编纂的《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1821 年巴黎版第1 卷。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援用了这些著作中的有关资料。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69、40、41、45 页。
这就是说,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69、40、41、45 页。
为了说明这种单子的自由,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
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
第16 条(1793 年宪法):“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的权利。”
这就是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自由首先宣布了人权是
“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69、40、41、45 页。
意义四,马克思的“通则”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人的自由的理解。这里的自由,主要涉及人、私有财产和自由。这三者都主要是研究市民社会中人的关系。这里的人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
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
因此,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
但是,利己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
因此,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他没有摆脱经营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经营的自由。
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69、40、41、45 页。
意义五,人类历史发展之谜——人的彻底解放。这些谜可以说最初都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来的。下面就是马克思说的这些谜的内容: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1791 年《宣言》)。后来,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又再一次这样明白宣告(1793年《人权……宣言》)。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的,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
“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1791 年《人权……宣言》第2 条)“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保障人享有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1793 年《人权……宣言》第1 条)
……所以,这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但是,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即使人们认为革命实践是对当时的关系采取的正确态度,下面这个谜毕竟还有待解答:为什么在谋求政治解放的人的意识中关系被本末倒置,目的好像成了手段,手段好像成了目的?他们意识上的这种错觉毕竟还是同样的谜,虽然现在已经是心理上的、理论上的谜。
这个谜是很容易解答的。
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它们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就是说,规定了他的政治关系,即他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分离和相排斥的关系。因为人民生活的这种组织没有把财产或劳动上升为社会要素,相反,却完成了它们同国家整体的分离,把它们建成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因此,市民社会的生活机能和生活条件还是政治的,虽然是封建意义上的政治;就是说,这些机能和条件使个体同国家整体分隔开来,把他的同业公会对国家整体的特殊关系变成他自己对人民生活的普遍关系,使他的特定的市民活动和地位变成他的普遍的活动和地位。国家统一体,作为这种组织的结果,也像国家统一体的意识、意志和活动即普遍国家权力一样,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
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它把似乎是被分散、分解、溶化在封建社会各个死巷里的政治精神激发出来,把政治精神从这种分散状态中汇集起来,把它从与市民生活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构成为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务的领域,在观念上不依赖于市民社会的上述特殊要素。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降低到只具有个体意义。它们已经不再构成个体对国家整体的普遍关系。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45 页。
这个时候的人权和自由又是什么情况呢?
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正像等级制度中和行帮制度中的人的关系通过特权表现出来一样——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但是,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即非政治的人,必然表现为自然人。Droits de l'homme [人权]表现为droits naturels[自然权利],因为有自我意识的活动集中于政治行为。利己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有直接确定性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最后,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5-46、46 页。
最后,马克思借着卢梭的话来结束自己关于人的历史之谜的理论。
可见卢梭关于政治人这一抽象概念论述得很对:
“敢于为一国人民确立制度的人,可以说必须自己感到有能力改变人的本性,把每个本身是完善的、单独的整体的个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体以一定的方式从这个整体获得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有能力用局部的道德存在代替肉体的独立存在。他必须去掉人自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人一种异己的、非由别人协助便不能使用的力量。”(《社会契约论》1782 年伦敦版第2 卷第67 页)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5-46、46 页。
以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的谜。这些谜是马克思研究了人权理论、政治革命之后提出来的。今天研究这些谜还有什么意义呢?仍然有,而且很大。
意义一,资产阶级理论家宣传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是资产阶级运用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这是《人权宣言》多次明确阐明的原则。把这种狭隘的自由权宣传为社会的普遍的人权。这是一个历史观上的伪命题。这个伪命题直到现在,还被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到处乱用、大搞颜色革命。
意义二,政治革命就是政治统治权力的斗争,目的是政治异化。政治异化就是统治权力的改变。在这一改变中突出的是国家这个权力统一体的出现。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代替了封建等级制的政权,这就是市民社会发生的革命。这时人权发生了怎么变化呢?
变化一,原来私有财产的自由权依附在封建制的同业工会、行会的等级制中,现在统一到国家这个统一体中,其中的私有财产的自由并没有改变,还是人权的存在。不过,它从原来的同业工会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存在,成为国家的保护对象。
变化二,如果说以上是物质方面的变化,那么下边是精神方面的变化。政治国家的产生,把市民社会的利益分成了两类: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私人利益仍然是人权方面的利益,而社会利益则是从封建等级的“巷子里”激发出来的。在这种关系中,私人的自由仍然服从国家的自由。可是,私人财产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保护私人财产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却把手段的人权宣布为目的,把政治统治权这种目的宣布为手段,这种颠倒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国家性质。
最后,研究马克思的政治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里可探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用来分析现在的资本异化。我国现在的政权是怎么来的?它的性质仍然属于政治异化,是通过政治斗争引起政治权力的变化。毛主席早就说过,“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意思就是要使无产阶级获得统治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要政治异化。在我国,政治异化也引起了市民社会的两种变化:一种是社会权利,一种是私人权利。社会权利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统一的意志来体现,私人权力是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前者以精神的形式形成统一的国家。这种统一的精神是哪里来的?是从资本统治的“巷子里”和封建统治的“巷子里”激发出来的。由于它们的无能,反而激起了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最终取得政权。后者的私人自由是原来就有的,没有经过“批判”转过来的,还带有原来的痕迹。在这两者之间,从发展前景上看,社会利益代表前进、向上的动力,私人利益是从旧有社会中遗传下来的。它有两个发展方向:一种是向上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一种是沉渣泛起,严重的就是官员的贪腐。这种贪腐,我称它为资本异化。这种异化的行为无一不是旧社会腐败现象的那一套。这是倒退的人、民族的败类,只有严惩,才能更好地振奋民众的精神。
另一个方面,是人民议论中的国营企业资本与民营企业资本的关系问题,即这两种资本应当怎样变化?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就变为私人资本的自由。这时,资本的自由就有了性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运动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为社会主义发展助力,这是进步的社会资本;另一种属性或者说它的本性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效力的。当下,社会中人们热议的民营企业家——某公司的创始人,本是一个科学家,却盗用民营企业家的名声窃取国家的资财,变公有财产为私人财产,表面上是共产党员,暗地里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骗局。他玩的是资本,是资本的异化、倒退,制造资本主义的“沃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异化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倒向资本主义的叛逆行为。
某公司创始人的行为只是资本异化的典型代表,一些政府官员的贪腐现象是政治异化,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叛逆。两者性质相同,都是通过资本异化表现出来的,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十分不够。按照社会发展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政治革命,是统治权力的异化,这种异化使社会发展的方向发生了变化,资本运动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但那些使社会倒退的资本运作是反动的,仅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来处理是不合法理的。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的很多谜,主要的是以下三个。
第一,一切政治革命都是统治权力的异化,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人权和政治统治权上的颠倒的谜。
第二,政治权力异化,突出的只是政治统治权的异化,市民社会中的其他阶层,如:私有财产与人权的自由权没有“批判”性地改变。这就为像旧社会中的遗老遗少一样玩起资本的骗局提供了机会。
第三,对人的自由的研究。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的论点第一次是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中发表的。这个观点是从考察历史中来的。当他把人权放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中考察时,这是从与神权的关系中比较来说的。过去的财产权的处理是由神权、王权决定的。通过人权的斗争获得了财产的自由权,财产处理的自由权只是局部的权利。完全的权利怎么获得呢?这是要等到共产主义才能获得的。对共产主义的考察是在马克思的下一篇经典著作中进行的。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我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一部分,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就是理论驿站。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理论驿站,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物质利益不是解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问题,而是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是市民社会这一物质力量和阶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关系问题。以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发展,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这种观点具有偏颇性,主要是前一个判断就有偏颇性。不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分野问题,而是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按照理论驿站的观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有轨迹可寻的。我现在的研究就是寻找这个轨迹。
《莱茵报》的两个“苦恼的疑问”都是历史观的问题,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历史观的问题,才和马克思的第二篇重要论著《论犹太人问题》发生联系。在第二篇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三种解放的理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在第三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是对《莱茵报》中两个“苦恼的疑问”和三种解放理论的深入研究。这种深入研究,为什么还是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有关系呢?这里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个,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到底怎么理解?第二个,德国的现存社会处于社会发展的什么阶段?第三个,马克思要解决的是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研究马克思对这些方面的探讨,对当今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怎么理解?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克罗茨纳赫》(手稿)阶段,即1843 年的时候是从物质利益方面来理解的,后来演化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第二个阶段是1844 年《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理解是在《论犹太人问题》基础上进行的,即在社会发展“三个解放”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这时,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区分为三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解放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制度。黑格尔说的市民社会就是以法国为典型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在分析政治解放时接受了这个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从奴隶制的等级制到获得人权的政治解放,这是一种进步。这是狭义的解放。
什么是广义的呢?这是马克思从他的物质利益和人权这两个视角进一步分析市民社会的时候得出的,从市民社会的人权理论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中,看到现存(以法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权是和私有财产相联系的,这时得到的自由只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把这种人权的自由扩大为普遍价值,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东西,是天然的、合理的、永恒的、理性的,等等。当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人类解放的时候,这时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法国,而是德国。当时的德国既没有法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却有着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有着私有财产权,却没有人权的自由。这样,就引起了马克思的进一步研究。这种研究既和人权私有财产有相同之处,又有极大的区别。其核心是在后进的国家如何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个问题解析开来就是:人类解放、政治斗争、统治权力、物质利益。这些因素归结为两类: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即认知社会发展的哲学的水平;物质力量是指市民社会中一定的特殊阶级能够代表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能力推动的社会发展,核心是政治的统治权。
马克思是这么说的:“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15、13、13、13、13 页。以上这是马克思分析法国的情况,在法国“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定成为引起普遍不满的等级,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定被看做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消极普遍意义决定了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积极普遍意义”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15、13、13、13、13 页。。马克思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导言》的这些话的?是在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之后,又研究了犹太人的政治解放问题,特别是研究了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市民社会中的等级、阶级关系的政治问题,即一个特殊的等级、阶级变为普遍自我解放的阶级。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进一步研究了市民社会中的等级、阶级关系的政治变化。下面来谈谈马克思对德国的分析。
第二个问题,《导言》要解决的是对德国市民社会的理解。这种理解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德国的哲学发展状况,这里的哲学,是指对人类发展的认知能力。具体的说,就是黑格尔哲学——法哲学的国家观理论。“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15、13、13、13、13 页。通过同英法国家的比较,特别是同人类解放这个最高的目标相比较:“彻底的革命(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种称谓——引者注)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15、13、13、13、13 页。另一方面,德国又有优越的方面,德国的哲学较为发展,特别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如果说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它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一方面的抽象痛苦同另一方面的抽象活动相适应。”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15、13、13、13、13 页。德国抽象思维能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优点,同时对德国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矛盾:“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15、13、13、13、13 页。德国的彻底的革命应该怎么发展呢?
第三个问题,彻底革命的道路——“两个武器”的理论的诞生。马克思依据以上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彻底革命的道路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哲学的,像黑格尔法哲学这样用抽象思维来把握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规律;一个是在市民社会中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担当普遍的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
对于第一个基本条件,德国虽然没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上通过抽象思维即在哲学上达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什么?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于唯心主义这一方面,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手稿)中进行了批判,只剩下历史观了。黑格尔的历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家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无法相比。黑格尔的历史观有着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与辩证法联系着,虽然是泛神论的;第二个是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联系着,虽然是理性的。但是,马克思正在发展着的科学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是人类自身的解放,既不是靠神,也不是靠理性,而是要靠两个基本的条件:一靠哲学,二靠抽象思维来把握市民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第二个基本条件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认识。“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样一来,无产者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就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一样了。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就是国王。”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7、17-18 页。“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7、17-18 页。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是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分不开的,特别是与人类发展的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理论分不开的。人类的解放不单纯是政治人权、私有财产自由权的解放,而是全面自由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的解放、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既超过了鲍威尔、也超过了黑格尔、超过了所有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历史理论。更有甚者,是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以表述自己理论的基本特征。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7、17-18 页。
马克思这个论断是就德国来说的,特别是最后一句:“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前一个“德国人”是指当时的德国人——素朴的人民园地的人,后一个“人”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共产主义的人。这个意思是坚定地表示共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第二个,坚信“两个武器”的结合。第三个尤为重要,即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解。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由实地考察实际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生产情况得到的,而是靠两个方面的结合得到的:一个方面是典型的历史材料,另一方面是抽象的思维能力。如同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的国家观,它是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和他的哲学抽象能力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的抽象思维能力与他的历史知识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有了以上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识,又有了人类解放三种形式的理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当然的一种科学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