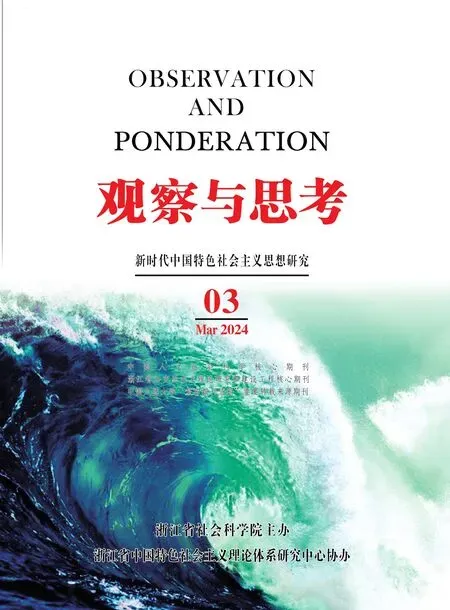“内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成因与应对策略*
2024-06-10李键江张子怡
李键江 张子怡
提要:探究“内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成因与应对策略,对于引导青年正确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在“内卷化”背景下,青年社会获得感的缺失是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内因,主要体现为“习得性无助”降低青年的自信感、“主动污名化”宣示青年的抗议,以及阶层焦虑导致青年斗志消沉。而亚文化中部分消极文化的流行与扩散是外因,主要体现为“丧文化”下青年情绪消解方式的扭曲、消费文化下青年认同危机的加剧、网络文化下核心价值观对青年引导作用的削弱。为了应对青年“躺平”思潮的不良影响,亟待加强心理健康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健全青年社会经济保障体系,甄别研究青年合理社会利益诉求,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网络技术的跃迁式发展,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网络环境相互渗透,尤其在当下,“内卷化”与“躺平”之类的网络热词备受媒体与社会大众关注,关注者以正广泛参与社会劳动的青年群体居多。纵观上述网络热词的发展轨迹可知,“躺平”因其传播广度、与青年群体关系密切性及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深刻性等特征,或许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思潮,且“躺平”思潮的流行有其独特的现实基础与形成原因。此外,“躺平”也与当今的“内卷化”社会背景关系匪浅。具体而言,“内卷化”可用来指称一种无实际发展的社会形态,即社会呈现出一种“恶性斗争频繁”“高度内耗严重”的现实状态,在“内卷化”的现实背景下,“躺平”成为了青年在互联网上热议的主要话题之一,甚至不少青年在互联网平台公开发表“躺平”宣言,青年“躺平”正成为继“佛系”之后的又一潮流。但青年作为国家和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如若选择“躺平”,终归不利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因而必须对“内卷化”与“躺平”的现状、成因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加以深刻审思,以找寻矫治的正确方法。
与此同时,有关“内卷化”与“躺平”的研究在不断增加,有的研究将“内卷化”与“躺平”当作有着鲜明网络文化特征的青年亚文化形态,表明它们正以趣味性的调侃方式昭示对主流社会和文化的抗争与挑战,①参见付茜茜:《从“内卷”到“躺平”:现代性焦虑与青年亚文化审思》,《青年探索》,2022 年第2 期。有的研究将“内卷化”与“躺平”都理解成时代变迁过程中青年群体的不同社会心态。其中,较多学者的观点认为,青年群体选择“躺平”是由于“内卷化”作为低水平、无意义的社会竞争形态消耗了自身的奋斗意愿与精神,导致青年群体的发展动力与精神内驱力不足,“躺平”实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抗。②参见林龙飞、高延雷:《“躺平青年”:一个结构性困境的解释》,《中国青年研究》,2021 年第10 期;令小雄、李春丽:《“躺平主义”的文化构境、叙事症候及应对策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也有学者认为“躺平”与“内卷化”之间具有重要的因果关联,破除社会“内卷化”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躺平”对于青年群体的不利影响。然而,目前很少有研究将“内卷化”作为社会形态、“躺平”作为社会思潮进行拓展与分析,因此,笔者试图对“内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的形成原因及其应对策略展开深入研究,以期为其他学者针对青年“躺平”思潮的研究及寻求治愈之策开拓思路,提供有益借鉴。
一、“内卷化”与“躺平”的内涵与联系
(一)“内卷化”:无实际发展社会形态的客观反映
“内卷化”,即Involution,也译为“过密化”。根据其特定含义,“内卷化”状态是对无实际发展社会形态的一种客观反映,也可用来描述社会发展的停滞现象或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基于“内卷化”是社会形态的视角看,社会发展水平与个体能力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社会由于对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追求表现了对发展与竞争的迫切性,个体在有限能力水平的约束下也渴望融入当下的竞争形态以促进自身发展,由于社会竞争是社会群体的全面参与,有些个体在奋力向前与追赶不及的双重影响下,会普遍选择不断提升竞争水平进而抬高自己的价值和地位,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趋势,促使公众的工作与生活形成一种尤为激烈的社会竞争状态,而这一社会形态即称之为“内卷化”。由于社会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均衡特性,社会大众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过多的竞争,且这种竞争大多是一种无意义的自我消耗,并未使得个体的社会生活产生实际性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可以说,当下的社会发展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内卷化”的社会形态。
关于“内卷化”概念的起源,其最早由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他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将“内卷理论”与“演化理论”进行了区分,并指出内卷是与进化完全区别开来的事物演进方式。①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85 页。此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将“内卷化”用来描绘“某种文化模式在达到某一特定形态后既无法保持稳定状态又无法突破自我,只能在内部变得更加精细化与复杂化的文化现象”②Alexander Goldenweiser,“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6,pp.99-104.。随着之后的发展,“内卷化”真正成型于格尔茨针对瓜哇岛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他以“农业的内卷化”用来概括“农业因条件受限无法向外拓展,劳动力却不断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为使人均收入不至于下降从而实现自我战胜,只能使得耕作不断趋于精细和复杂化”③GEERTZ C,“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p.80-81.的过程,此定义对后续关于“内卷化”的研究和解释具有奠基作用。黄宗智则基于中国社会情境对“内卷化”展开研究,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内卷化”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④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65-124 页。其又在后续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中,把“增长”和“发展”区分开,说明了“内卷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⑤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 21-93 页。刘世定和邱泽奇将土地和资本类比作画框、画布和可以使用的绘画要素,指出受画框和颜色种类限制,绘画只能通过增加色彩调配使画作更加复杂化和精细化,生动形象地讲明了格尔茨所讲的“农业的内卷化”的深刻内涵。⑥参见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5 期。美国学者杜赞奇则通过对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现象的研究,提出了“政权内卷化”的概念,指明国家机构通过对旧有的国家和社会体系及其职能的重复、延展与精致化,借此实现行政职能的扩大。⑦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09-211 页。
总之,“内卷化”虽外在表现为数量的增长,实质上却并未实现发展水平的提升。从发展系统角度理解“内卷化”,可以看出,“内卷化”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发展系统表面呈现的是一种“虚假的进步”状态,实际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发展系统内各要素所谓复杂化、精细化的发展,只是系统在某一发展水平上的不断重复与延展,是无意义的重复,受系统本身发展规模和条件的限制,系统最终无法真正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因而,结合社会发展情形来看,“内卷化”是对无实际发展社会形态的客观反映,精确描述了一种社会中存在普遍无效竞争的社会发展形态。
(二)“躺平”:青年“低欲望”社会思潮的现实呈现
关于“躺平”,学界尚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与概括。现实生活中“躺平一族”“躺平主义”“躺平学”的出现与流行,使得现今“躺平”在网络上极具热度,一度成为谈论的焦点。一般将“躺平”定义为:一种青年群体以无所作为的方式反叛裹挟,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规训的顺从心理。教授储殷认为,“躺平”可以与生活中的颓废、消沉和玩忧郁相提并论。白岩松指出,“躺平”是青年个体一种缺乏动力、不焦躁的生活状态。范荣认为,“躺平”是指一种无欲无求、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状态,与“丧”“宅”“佛系”等异曲同工,并且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自强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品质。①参见范荣:《莫用“躺平”误读奋斗着的年轻一代》,《北京日报》2021 年6 月2 日。客观地看,“躺平”并非完全消极且一无是处,“躺平”是青年“低欲望”社会思潮的现实呈现,描绘出青年一代降低自身欲望、反抗“内卷化”的姿态,其所处的状态暂且可称为一种“无欲无求”“就地而安”且远离竞争与压迫的处世状态。大部分青年群体面临无效率、无实质进步的“内卷化”竞争,察觉到自身的劳动投入最终并不会获得理想的回报,不能使自己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得到相应的满足,于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生存的“躺平”方式。他们面对外界刺激,会坚持自己所思所想,不会任意更改,会顺从本心,不再执着追求众人眼里的优质生活,暂时放弃追求上进与艰苦奋斗,尽量降低自身欲望,依靠适当的物质条件,甘愿享受低标准的生活,在自我降低负担和压力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舒缓与安宁。
在内涵概括的基础上,对“躺平”的深层意蕴进行剖析。“躺平”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进行理解,其是对当前广泛存在的、特有的社会现象的反映。社会群体中青年个体因为自身生活情境的驱动与外部群体情绪的渲染,不约而同地选择“躺平”这一在社会中日渐流行的生活姿态,并利用群体力量在“躺平—族”中实现群体的自我强化与壮大,最后“躺平”通过网络的传播与发酵,逐渐在青年群体中形成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广为流行,并对社会群体内成员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且以一定的思想理论为核心的思想趋势、价值理念或者理论体系;②参见浙江省团校课题组:《青年和社会思潮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4 年第1 期;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对青年学生影响的新趋势及应对策略》,《中国青年研究》,2015 年第11 期。社会思潮也可理解成反映某些特定阶层或群体的利益诉求、为广大人群所知晓和掌握、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对主导社会价值观起消解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观点。③参见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的内涵、特征及其研究意义》,《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 年第19 期。“躺平主义”虽缺乏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理论基础,但它在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社会大众间广泛传播,也鲜明地表达了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对青年群体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使青年拒绝无效奋斗、选择低消费,并且其所蕴含的消极的价值理念,也对主流价值观起到了消解作用。因此,基于以上角度,“躺平”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思潮。作为与“内卷化”社会背景关联颇深的一种社会思潮,“躺平”反映了青年群体“反感无效奋斗”“拒绝无意义内耗”的心理状态,同时它也是青年群体的一种情绪宣泄与保持群体共鸣的重要方式,允许青年个体通过自身行为进行思想表达与行为抗争。此外,“躺平”作为一种对青年群体具有深远影响且趋同作用明显的思想趋势,与已知的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联系密切。
值得强调的是,“躺平”社会思潮并非突然爆发形成的,而是有其渐进发展的演变过程与逻辑。就“躺平”的社会发展轨迹与文化发展趋势而言,“躺平”是“丧文化”、消费文化及其他主流亚文化的一种最新的表现形式,其基本内涵与上述文化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因为“躺平主义”带有时代赋予的新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若将“躺平”与早年间日本学者描述日本社会时所用到的“低欲望社会”或者“无欲望社会”相对照,可以发现“躺平”与“低欲望”有着几乎一致的行为表现,且此行为表现贯穿于个体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不穿名牌、不吃大餐、不买房以及不生子。然而,“低欲望社会”是日本独特的社会现象,受日本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影响而产生,“躺平”则是中国社会发展情境下的特殊现象,在差异显著的社会背景下,两者各有其独特的内在发生机制,因此,虽然表现形式几乎一致,但在成因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
(三)“内卷化”与“躺平”的联系
“内卷化”是时代变迁和社会综合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当下时代特征的社会形态,“躺平”社会思潮则是“内卷化”社会形态下的时代产物,“内卷化”的社会形态是滋养“躺平”思潮形成的土壤,两者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与竞争相关的高度“内卷化”特征,会使社会群体不满于参与无意义的内耗斗争,容易引发社会大众内心的浮躁与焦虑情绪,广大青年群体是不愿被迫融入和适应“内卷化”的社会形态的,在身体与内心两个层面都拒绝卷入无效斗争当中,也会相继选择“躺平”的心态或者姿势,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躺平”的社会思潮。“躺平”社会思潮与“佛系”“丧文化”等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渗透息息相关,最后由于受到“内卷化”社会形态这一诱因的激发,从而实现了自我的扩散与成熟发展。“内卷化”的社会大环境下,个体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种竞争当中,并遭受竞争失败的频繁打击,不仅身心容易受到严重损害,还可能导致其彻底丧失向上拼搏的斗志,主动选择“躺平”或许是对个体身心的一种自我保护,可以帮助个体在内心建立牢固的“围墙”,以抵制外界不利社会环境的侵害。
同时,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躺平”也是一种个体抗击“内卷化”的方式,通过减轻自身压力对抗社会不断施加的“压迫”。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期,开始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阶段,因而进入一个同质化竞争激烈的过渡期,此时,中低水平的供给过剩,在社会总体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使得生产与就业等社会活动因要维持竞争力而造成个体压力过大。①参见张立伟:《应该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让年轻人不再无奈“躺平”》,《21 世纪经济报道》2021 年5 月27 日。通过实施青年劳动教育培育具有持续奋斗精神的青年一代,是党在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迎接新形势下社会劳动环境改变带来挑战的需要,②参见常宏宇:《党的青年劳动教育:演进逻辑、基本经验及未来展望》,《重庆社会科学》,2021 年第8 期。现实劳动环境赋予青年群体较大的压迫感,青年作为劳动主体无力改变大环境的影响,但也不会一味地被迫接受,因此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自我回避,其选择“躺平”看似不争气、没志气,实则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据此可知,应秉持客观态度正确,理性地看待“躺平”,需明白选择“躺平”有时不是出于青年群体的内心意愿,而是受到社会大环境的驱使,尤其是容易受到当前激烈竞争的“内卷化”环境的影响。在实际生活中,少数人的力量难以抵抗大势,“内卷化”的社会形态短期内难以被改变,它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在不断侵害着当代青年群体。在万物皆可卷的“内卷化”社会形态下,竞争不可避免,个体不免会被卷入各种竞争中,其中不乏无情且残酷的恶性竞争,青年不畏惧竞争,但会厌倦个人的诸多努力只能得到微薄的回报,也会不甘于参与竞争的结果是无效或是失败的,以致于产生深深的无力感、无奈感,由此会觉得心累、迷惘、沮丧,从而变得屈服和顺从现状,且容易逐渐丧失上进心与拼搏斗志,最终青年个体的消极情绪利用网络平台在群体间不断扩散,并在青年群体间滋生“躺平”思潮。
二、“内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成因
(一)内因:青年社会获得感的缺失
1.“习得性无助”与青年的自信感降低
“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一现象或机制,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在研究动物行为的实验中发现,该心理学家随后证实人的行为表现也具有并适用此种现象。赛利格曼将人在经历诸多失败与挫折之后,察觉自身对事物失去掌控力并对改变事情结果无能为力,造成的面临问题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丧失信心、消极无望的特殊心理状态与行为定义为“习得性无助”。①参见Seligman,M.E.P,&Maier,S.F,“Failure to escape traumatic shock,”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Vol.74,No.1,1967,pp.1-9.
聚焦个体实际生活来看,竞争的失败、自我提升无望、实现自我价值不得,由此造成的习得性无助会带给个体较大的负面影响,让个体感到沉重的无力感与灰心感,甚至挫败一个人的自信心,使其消极地面对现阶段的人生。习得性无助不同于非习得性无助,后者虽然外在表现为“无助”,实则是以“无助”为外壳从而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反击,前者则是真切的、实在的“无助”。②参见杜骏飞:《丧文化:从习得性无助到“自我反讽”》,《编辑之友》,2017 年第9 期。就事物的原因而言,有着习得性无助心理的个体,通常倾向于将自己经历的失败归咎于自身内部因素,如:素质能力低下,而不会归因于外部情境或人员。就结果而言,习得性无助个体面临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获得理想结果的情形,会变得失落、失去信心与斗志,以致进行自我怀疑和否定,最终通常会选择放弃奋斗和逃避现实。“内卷化”时代的到来,带给多数人的不是竞争与成功的喜悦,而是种种失败感和随之而来的颓废感,如若青年失去了对多数事情的控制力,是“事”战胜了“人”,“人”败倒在“事”的脚下,青年在降低自信感的同时,也会拒绝去努力、去奋斗,从而选择“躺平”。
2.“主动污名化”与青年的无声反抗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界定的概念可知,“污名”(Stigma)代指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社会不认可的、令人丢失脸面的特征,其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污名化”(Stigmatization),则用以重点强调某群体被不断贴上负面标签,群体或群体成员具有的某个或某些负面特征被扩大化,以致身份接连受损的动态过程。③参见Goffman E.,“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63,p.68.尽管被污名化的程度或高或低,但都会对所指群体自身声誉、社会地位等造成一定损害,群体成员会因为自身带有的不同于常人的不光彩的特性而遭受社会排挤或隔离,且除了受到社会大众的歧视与排斥以外,成员也会进行自我贬低与唾弃。
而就青年“躺平”与“污名化”之间的关联而言,青年“主动污名化”是指青年群体选择主动贴上“躺平一族”的标签,以此宣示青年的抗议,重点并非自嘲与“污名化”。实则“躺平”被污名化的程度并不深,带有的否定与鄙夷的色彩不如以“葛优躺”等为代表的“丧文化”浓烈,社会群体对“躺平”的态度不一,否定与鄙夷有之,默许、赞成与鼓励也有之。青年选择贴上“躺平”的标签,更可能是想将自身纳入“躺平一族”的群体中,因为基于某些意义“躺平主义”是在宣示青年对“内卷化”社会形态的抗议。而一般来说无论是资源还是话语权,群体的力量更为强大,所以,此种举措也可被看成是一种战术,掺杂自嘲、戏谑与宣泄的成分,体现的是青年群体一种看似屈服而又不甘屈服的反抗方式。且正如萧子扬等定义“主动污名化”时指明,“主动污名化”区别于“污名化”的特点是其属于自我的主动接受、主动选择,它的初衷和目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叛逆表达。①参见萧子扬、常进锋、孙健:《从“废柴”到“葛优躺”: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网络青年“丧文化”研究》,《青少年学刊》,2017 年第3 期。
3.阶层焦虑与青年的斗志消沉
焦虑是夹杂着烦躁、不安、忧愁、空虚等情感体验的一种心理状态,焦虑多出现在个体心理落差大、对事物掌控力低、选择机会多和重大不确定性等条件下,主体内在地感受到力不从心又无法放弃的一种状态。②参见张艳丽、司汉武:《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及成因分析》,《青年探索》,2010 年第6 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体对困境、风险等情形高度敏感,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的压力最大,因此,他们的焦虑程度也最为严重。其中,当代青年群体的阶层焦虑表现得极为突出,究其缘由,向上流动的生存需求和困境造成的不确定性,是青年焦虑产生的个体心理机制,快速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社会流动渠道狭窄、少子时代青年的压力和焦虑的迅速传播则是青年的阶层焦虑症候不断显现的社会根源。③参见朱慧劼、王梦怡:《阶层焦虑症候群:当代青年的精神危机与出路》,《中国青年研究》,2018 年第11 期。
尤其是社会转型期内及“内卷化”社会形态下,青年群体所拥有的阶层焦虑感还可能导致种种消极后果,容易引发青年对社会与社会制度的不满,“求而不得”的挫败感和“高不可攀”的焦虑感会消解青年的奋斗意愿,使青年丧失向上流动的蓬勃热情,其会主动降低自身欲望,甘愿停留在自身目前所处阶层,变得斗志消沉,甚至选择主动“躺平”,与当初努力奋斗的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青年群体本是有着满腔热血的群体,理应充满赤忱之心与拼搏斗志,并且会因为不满于一直停留在低层或底层,从而希望拼尽全力向上游的中层和上层挺进,对财富和地位有着更大的向往与期待是青年群体所独有的特性,因此,巨大心理落差下青年的阶层焦虑显得更为严重与突出。此外,社会阶层固化容易加剧阶层焦虑对当代青年的影响,社会阶层固化表现为上等社会青年阶层的“世袭化”、中间社会青年阶层的“下流化”、社会底层青年阶层的“边缘化”,绝大多数没有背景或者关系的青年想要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愈加增大,最终只能无奈地停留在底层或者中低层社会,④参见熊志强:《当前青年阶层固化现象及其原因探讨》,《中国青年研究》,2013 年第6 期。由此激起社会中部分普通青年的阶层焦虑感,使其丧失斗志,最终选择“躺平”。
(二)外因:亚文化中部分消极文化的出现与扩散
1.“丧文化”下青年情绪消解方式的扭曲
“丧文化”曾因“废柴”“葛优躺”等话语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感染力,也是青年群体所熟知的一种流行文化,无形中为社会个体的人生选择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丧”带来的比较突出的好处,如:舒适、压力小,慢慢诱导青年选择此种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躺平一族”的产生。同时,“丧文化”在诱导青年以错误方式去宣泄或释放负面情绪,促使其选择用消极行动化解自己的内心矛盾以及自己与社会的矛盾冲突。
“丧”,顾名思义,是一个相当消极的词汇,多用来指不知理想、无所作为。“丧文化”散发出的丧气、不思进取等负能量,对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一种颠覆性毁坏,不利于青年建立健康、正确的价值观。青年或许刚涉足社会但也遭遇了不少打击,或许已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浸淫许久,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亟需一种功能强大的精神药剂以治愈其内心创伤,并帮助其振作精神重新迎接生活的挑战。而有的青年可能自我信念本就不坚定,个人的辨别能力薄弱,尚未形成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非常容易受到消极文化的错误诱导。若不论及“丧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其是相当契合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的。因此,“丧文化”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优势”,用它的“彩衣”蒙住了青年的双眼,迷惑青年,使其选择了消极的、错误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更有甚者,部分青年不仅态度上表现相当颓废、萎靡,还在行动上完成了“丧”的自我升级,选择了“躺平”的生活姿态,对赚钱、晋升、消费、娱乐等活动都不再热衷,只是一味地坚持己见,盲目地追求自由和自我解脱,看似挣脱了社会与伦理加于其身的沉重枷锁,实则也游离在集体、社会之外,游离在现实世界主流价值观之外。
2.消费文化下青年认同危机的加剧
消费文化是指特定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生产活动中综合表现的、与消费有关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①参见黄智君:《消费文化与青年认同危机》,《青年探索》,2006 年第5 期。消费是社会个体的一种经济行为与生活方式,在当今社会,消费商品的风格和种类在快速变化,时尚消费品日新月异,消费主流支柱却未发生较大改变,并在此方面表现趋向同一的消费主义倾向,即房、车等标记个人社会地位与价值的物品仍持续地受人吹捧。所谓认同危机,重点是指人的一种内在的自我认同,在个体对自己过往经历进行深度反思的过程中形成,并最终内化于心,②参见王成兵:《消费文化与当代认同危机》,《江海学刊》,2004 年第2 期。而出现危机代表着人的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③参见[美]罗洛·梅:《人寻找自己》,冯川、陈刚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5 页。即说明人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地失去了对自我的定位,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现代消费现象和消费文化正酝酿着当代多数青年的认同危机,消费不起的高档商品或房、车等高昂商品使得青年的自我价值感逐渐降低。在“内卷化”背景下,部分青年只能从自我消费中获得少量的满足感和自我认同感,恰逢某些较为偏激的消费心理或消费理念甚嚣尘上,使青年的认同危机逐渐加剧,有时甚至达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当今社会常以“高薪”标榜“能人”,多数个体潜意识里认同“消费得起”代表着“能力出色”的观念,所以,社会个体也时常通过各种消费来展现自己的生活格调与品质、社会地位及价值,虽然高档消费不可与高社会地位划上等号,但社会大众对此种消费行为趋之若鹜。过分追求时尚用品和高档消费反映公众比较畸形或偏激的消费心理,不仅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同时也体现了个体价值观的扭曲,在一定意义上引发并加剧了青年的认同危机,导致青年进行自我否定与怀疑,最终促使其选择“躺平”。
3.网络文化下核心价值观对青年引导作用的削弱
网络文化主要指网络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受自身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所影响,不断在网络空间发表显示自身个性的观点,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体系和价值判断逻辑。④参见平章起、魏晓冉:《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社会冲突、传播及治理》,《中国青年研究》,2018 年第11 期。2023 年11 月8 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发布重要成果性文件——《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两本蓝皮书。蓝皮书表明,截至2023 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达到10.79 亿、76.4%。①参见《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蓝皮书: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6.4%》,《中国证券报》2023 年11 月9 日。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网络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塑造与传播空间,接踵而至的网络流行文化在网络空间形成一种亚文化的狂欢,“宅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等不同形态的网络亚文化皆可归纳其中。
而“宅文化”“丧文化”等盛行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却在某些意义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积极引导作用,致使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即广大青年群体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出现偏差,较大程度上催生了“躺平一族”的出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精华和结晶所在,长期占据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社会风尚和公众自身的良好向上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且可以帮助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显而易见的是,受某些不积极或不健康的亚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躺平”社会思潮,其所传达的“追求安逸和享乐”“厌倦努力和竞争”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弘扬青年正能量”“树立坚定且远大的理想抱负”的价值理念相背离,可见,某些流行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虽不占据主流地位甚至是处于边缘化地位,仍能依靠自身的传播力与感染力在网络世界创造一种“文化狂欢”,替代主流价值观影响力的同时对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造成消极的负面影响,其破坏力之大也不言自明,值得警惕并应着力加以矫正。
三、“内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网民、学生……都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心理压抑、心理自卑、心态失衡、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孤独症等。……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加强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培养。”②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8 页。这就为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公共服务及其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丧”“颓废”“佛系”等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描述性词汇,说明当下的青年群体有着较差或者非常差的心理状态,也表明他们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服务。因此,国家和政府亟待加强心理健康公共服务及其体系建设,包括但不限于社区、共青团、社会团体等组织的心理服务设施建设,因为青年群体更需要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产品,在缓解其经济压力的同时帮助解决自身出现的不良心理状态问题。心理健康公共服务是指可以被广大社会公众所享有,负责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咨询、教育、治疗、辅导等活动的总称,③参见吴卫东:《论和谐社会建设中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继续教育研究》,2011 年第10 期。其中所指的心理健康,若说是一种特质,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会因为个体生活的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发生改变而变化的心理状态。④参见师保国、雷雳:《近十年内地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回顾》,《中国青年研究》,2007 年第10 期。当今时代各种消极亚文化的流行,无不反映青年群体焦虑、绝望、颓废等较差的心理状态,青年群体面临着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等巨大压力,因渴望突破阶层牢笼而自发向上奋斗,却遭遇了不少的挫折和打击,他们内心烦躁、苦闷、无奈等情绪无法消解,以致青年群体选择以在网络上自嘲、自讽的方式来宣泄和化解负面情绪,或者选择加入“躺平一族”的队伍来消极地应对生活。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需发挥自身优势对青年更广泛地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例如:可以适当建立线上或者线下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专业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扩大服务的受众面,提升针对性,可以完善或健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立包含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辅导和心理教育在内的,针对多种服务对象的多层次的服务机制。①参见张华:《青年压力来源与社会支持系统优化策略》,《当代青年研究》,2012 年第3 期。最终能够帮助青年群体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强化青年自身的健康心理建设机制,促进青年身心健康向上发展,有益于帮助其发挥自身潜能,提高青年适应和融入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建立健全青年社会经济保障体系
社会发展转型期内社会结构及体制变迁与青年发展的个人轨迹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压力成为现阶段青年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随着时间推进,青年自身压力在不断累积,却不能得到社会机制与政策体系的有力保障,更多时候只能依靠自己微弱的力量去化解压力。②参见王小璐、风笑天:《青年何以“暮气沉沉”——基于转型期青年压力的分析与反思》,《中国青年研究》,2014 年第1 期。青年群体正处于社会财富积累与社会地位创建的关键时期,同时肩负家庭与社会的期盼,他们面临的压力有时会比较大,且因为是自我奋斗时期,家庭能给予的帮助有限。青年群体虽不属于经济水平低下的弱势群体,但在“内卷化”社会形态影响下的青年社会经济保障问题依旧值得关注。由青年群体社会经济保障难题所引发的心理、生理等问题,需要得以妥善解决。
为改善青年群体的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遏止青年“躺平”思潮的传播,政府需要建立健全青年社会经济保障体系,逐步改善以青年民生为重点的住房、医疗、就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向新生代中低收入青年的覆盖,优化青年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制度,强化城市长租公寓的管理与监管,积极推动“租购同权”政策落到实处,保障青年群体“住有所居”进而实现“安居乐业”;扩大青年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增强青年的健康保障感和身心安全感;加大就业培训并提高青年的就业创业能力;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减轻青年养老负担和压力。③参见聂伟、蔡培鹏:《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1 年第3 期。
(三)甄别、研究青年合理社会利益诉求
“躺平”社会思潮的盛行以及“宅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等的流行,都从侧面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位于中低阶层的青年个体的话语权有时实在薄弱,青年群体发声需要利用一定的技巧以汇聚话语力量,才能使其利益诉求被社会所识别和关注。由此,利用网络平台表达利益诉求成为青年开展诉求行动的主要方式,此种方式也使得青年诉求的表达和实施变得更为快捷、有效。“内卷化”背景下青年的利益诉求,可以具体概括为需要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的向上流动渠道、希望机会和资源能够被平等享有、渴望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惠及广大群众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青年群体在内心有着多种诉求的同时,也希望诉求能早日得到满足,其心理和思想状态会因为社会压力的激增而变得更加脆弱,若他们切身、合理的利益诉求不能实现,将不利于青年成长,容易使其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
政府需要加强网络空间的监管力度,依托现有先进的网络技术,尽力甄别青年群体多元、合理的利益诉求,政府也需要团结社会整体力量和善于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帮助厘清和解决青年群体正当的利益诉求,同时建立适合青年利益诉求表达的更为适当、便捷、有效的渠道和途径。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方式开启了变革之路,从前社会运动的街头动员、全民参与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时代的带动下,青年群体利益诉求行为开始转向网络平台,并实现了向网络转型。①参见曾晓彬:《中国青年利益诉求的网络嬗变与统战路径分析——基于网络化创新治理的视角》,《北京青年研究》,2019 年第3 期。网络平台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广阔的情感表达、经验交流以及学习讨论的空间,活跃的网络平台成为当代青年最大的聚集地,从而方便青年在群体间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也满足了青年集聚力量为群体利益发声的需求。
(四)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②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 页。新时代,我们必须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广大青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有效抵御和克服“躺平”等错误社会思潮的不良影响。
在“内卷化”社会形态下,亟待加强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社会风尚和青年价值追求的引领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能反映国家的发展愿景和国民全体的共同价值追求,能极大地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发挥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也有利于青年群体思想道德素养的提高和健康向上发展,能够帮助其坚定理想信念与实现价值追求,从而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坚强、勇敢地向前发展。因此,不仅应根据形势需要对价值观的实质内涵进行完善,也需注重价值观宣传的形式,若宣传形式较为单一,将致使价值观倡导的内容因为形式枯燥等原因易被公众所忽视。此外,亟需实现主流价值观对青年自身存在价值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引导、认可和满足,加强主流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进而引导青年树立正确、适当的价值取向。
青年社会思潮的动向,反映的是当代青年的群体心态、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③参见雷开春、杨雄:《我国青年社会思潮新动向及政策建议》,《当代青年研究》,2015 年第6 期。青年社会思潮或者青年亚文化并不会因为与主流价值观存在冲突而自动消失,它们中既蕴含消极成分,也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因素,消极成分需要彻底否定和摒弃。其中,“躺平”社会思潮、“丧文化”等对主流价值观有着颠覆与抵制的一面,对青年群体的行为思想、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有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应彻底批判。在展开批判的同时亟待不断完善社会主流价值观,加强其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等方面的引领作用。④参见符明秋、孙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丧文化”治理》,《重庆社会科学》,2020 年第2 期。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所偏离,需要社会建立健全正确的价值引导机制,同时,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理应与时俱进以切实满足青年群体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并能够善于利用青年社会思潮或青年亚文化的存在进行有效引导,对相关制度进行相应补充和完善。